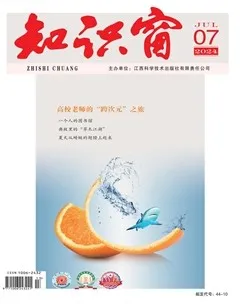用耳朵阅读
“从小我就是个用耳朵阅读的人,是一个听故事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演讲时说道。
按照常理来说,如果提及阅读,孩子主要通过眼睛来看纸质的报刊和图书,或是启蒙学习,或是找寻趣味。但莫言小时候是用耳朵来阅读的,显得与众不同。
莫言的故乡在山东省高密市东北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还是一个相对闭塞的农村。村里没有通电,每到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孩子们没有其他娱乐活动,听故事便成了他们最感兴趣的、最期待的事情了。
村里的老人多半不识字,但脑子里装了很多光怪陆离的故事,并且老人都是特别会讲故事的人。莫言说,他的爷爷、奶奶、父亲都是讲故事的高手。
在神秘的夜色下,村里的老树边,老人煞有介事,拿腔捏调,讲得绘声绘色,讲到情节跌宕处,还会手舞足蹈。莫言和小伙伴围拢在一起,竖起耳朵,听得真切而入迷,时而兴奋,时而恐惧,时而吓得尖叫。
镇上的小集市是莫言用耳朵阅读的另一个好去处。在儿时的莫言眼里,集市上的说书人俨然是高密乡间的故事大王。他们会把乡间搜罗到的和书上读到的故事,进行随机地添油加醋和各种杂糅,再次生动演绎,深深地吸引、感染着莫言。据莫言回忆,他最痴迷的时候,甚至梦想成为一个集市上的说书人。
值得庆幸的是,莫言这一梦想实现了,只是方式由“说”变为“写”罢了。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莫言演讲的题目即为《讲故事的人》。
儿时用耳朵阅读的这些故事,主角全是妖魔鬼怪、牛鬼蛇神,但蕴含的都是人间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有美善,也有丑恶。这些丰富而鲜活的文化元素已经深深根植于莫言的心底,以巨大的养分供给,孕育出这样一个成功的、会讲故事的作家。
莫言很多小说作品的灵感和素材都来自小时候这些用耳朵阅读来的乡间民野里的故事,尤其是一些奇思妙想,更是让他脑洞大开,受益终身。他还专门写过一本书,名叫《莫言的奇奇怪怪故事集》,分三个部分,即“奇奇怪怪的动物”“奇奇怪怪的人”“奇奇怪怪的事”。 他在序言里写道:“小时听人说鬼狐,夜晚走路心发虚,长大执笔写精怪,扬善抑恶学蒲书。”这不仅是对童年耳朵阅读经历的怀念,更是对乡村父老的致敬致谢。
用耳朵阅读并非莫言专属,在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作家,还是莫言的山东老乡,被莫言称为“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在村口,这个作家每天用桌子支起一个简陋的茶摊,外加几张破旧的凳子,供南来北往的行人歇脚、喝茶、聊天。就在这种轻松而自由的闲聊中,他用耳朵倾听,搜集了许许多多的奇闻逸事。他把听来的这些故事一个一个梳理,慢慢写了出来,经年累月,成就了一部经典的包罗万象的《聊斋志异》。这个摆茶水摊的人就是蒲松龄。
用耳朵阅读,也许更能调动感官,脑海里的形象思维更加活跃,内容的画面感更强,但这只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阅读方式。其实,无论是用眼睛、嘴巴,还是用耳朵来阅读,要读得好、读得深,终究还是要用心。我想无论是蒲松龄,还是莫言,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