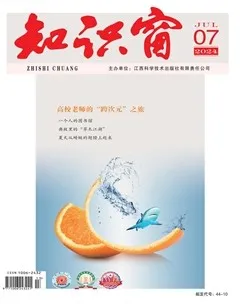金色的麦秸垛

在河套平原高远的天空下,我的目光穿过收割过的麦田,落在几户人家的门前,高高耸起的麦秸垛像一个个金色的大蘑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身在异地他乡,又见到熟悉的、亲切的麦秸垛,我的心中涌起感动和温暖。以田地为生的北方农人,谁家门前没有一两个麦秸垛呢?
堆垛是麦粒入仓后的一件大事。二叔善于踩垛,村子里一个个麦秸垛大都是从二叔脚板底下诞生的。堆垛需要三五个人合力完成,其他人用铁叉传送秸秆,二叔则不停地把麦秸分散摊到自己脚下,并踩实压匀。麦秸秆十分光滑,没有一定技术和经验很难做成麦秸垛。麦秸越堆越高,堆成一个伞状蘑菇头,最后还需用麦糠和成的稀泥糊好抹匀,以免因漏雨而造成发霉。
那时,麦秸在农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资源,它可以烧火、铺炕,也可以喂牛、喂羊,还可以堆一个温暖的鸡窝。麦秸垛伫立在那里,任凭日晒雨淋,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却始终挺拔。人们只有在需要时才会想起它,它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却又游离于生活之外。经历了丰收的欢腾,也能忍耐被冷落的寂寞,它静默无语,像在等待着什么,也似正孕育着什么。在农事稼穑的季候轮转中,它是参与者和守望者,也是最懂农人心思的知己。
麦秸垛间是孩子的乐园,孩子可以绕着它奔跑嬉戏,也可以捉迷藏,累了的时候便聚一堆麦秸秆,或坐或卧,它真是天然的软床。刚收获的麦秸秆散发着柴草的清香气息,在温热的晚风中缭绕、扩散,使人昏昏欲睡。这诱人的气息附在孩子的身上、发间,一直萦绕进梦里。
麦秸垛间也是大人时常逗留的地方。大人喜欢捧着饭碗聚在麦秸垛旁,边吃边聊些闲话,有私密的谈心,也有家长里短的八卦。当然,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农事收成,说说耕作的体会,聊聊来年的愿景。在短暂的休憩后,他们养足精神,又开始新一轮的劳作。
新打的麦子很快被农人磨成面粉,巧妇会做一顿手擀面犒劳家人。新面粉麦香浓郁,在擀面杖底下抖动丝滑如绸缎,吃起来也是筋道柔韧,咬劲十足。这时,麦秸秆决不旁观,而是拥围在炉灶里,等着自己的热情被点燃。麦秸秆焰炽火急,适合做快饭,是既顾农事又顾家的巧妇的最爱。只要两三把麦秸秆,一碗新鲜面条便可出锅了。
奶奶的茶饭手艺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最拿手的便是摊煎饼。麦收一过,新面粉入了瓮,奶奶总要用麦秸秆为一家人摊回煎饼解解馋。土锅大灶,手拉风箱,柴草气、烟火气像奶奶的爱心四处弥漫。随着风箱“卟嗒卟嗒”的歌吟,麦秸秆也在炉膛里跳起欢快的舞蹈。麦秸秆的火焰热情但不猛烈,不会将锅内的食物烧焦,是摊煎饼最适合的柴火。一勺面糊沿着锅边撒下去,迅速在锅内凝成圆圆的面饼,奶奶再铲起翻两次身,一张煎饼便做成了。咬一口,煎饼筋薄软弹,令人唇齿留香。在麦秸秆的助力下,奶奶身边很快就叠起厚厚的一摞煎饼,再爆炒一碟土豆丝,凉拌两根黄瓜,用煎饼卷起来吃,真个是人间美味。
麦秸垛在人们的一日三餐中逐渐缩小身形,不过来年,又会有一个新的麦秸垛伫立在人们眼前,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土地从不辜负热爱它的人们,粮食满仓、秸垛成山便是大地对农人辛勤劳作的最好回报。
如今,我的家乡已经很少能看到麦秸垛了。那亲切又熟悉的麦秸垛只能远远地伫立在我的记忆深处,我透过岁月的烟尘回望,麦秸垛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