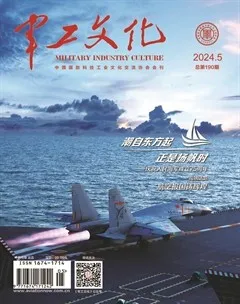红色跨界专家陆达与“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
陆达是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中国冶金事业的奠基人和主要创建者之一,他在担任冶金部钢铁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期间带头研制出铀同位素分离膜,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分离膜——“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
制造分离膜技术难度极大,是一项涉及粉末冶金、物理冶金、机械加工、金属腐蚀等众多学科的综合性高精尖技术,是铀浓缩生产流程的“咽喉”。当时掌握这一核心技术的英、美、苏等几个核大国均把它列为重大国家国防机密,严格封锁,严禁扩散。这里不妨插上一句,别说当时,直至今天,工业规模生产原子弹用高浓铀的核大国对分离膜制造技术仍守口如瓶,让试图挤进核门槛的国家魂牵梦绕。
没有王牌材料分离膜,就没有高浓缩铀 235原料,没有高浓缩铀 235原料,原子弹便是水月镜花。我国是放弃搞原子弹的计划还是另谋出路?分管国防科技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元帅说:“我们寄希望于中国自己的专家。”
不辱使命
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分离铀235所需的分离膜,是继续建设好并投产运行正在筹建中的气体扩散工厂的重要保证,是制造原子弹必须跨越的“娄山关”。
1960年4月18日,中央分别向冶金部和中国科学院下达了研制在当时缺一不可的两种分离膜的紧急任务。由冶金部负责研究乙种分离膜,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甲种分离膜。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东亲自将研制这项国防尖端材料的重大任务布置给陆达挂帅的钢研院,陆达成为一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他不失时机地把握住这一高科技的发展方向,决心把钢研院建设成为攻克尖端的“拳头”,要求大家正确处理破除迷信与尊重科学、个人刻苦钻研与集体团结协作两者的辩证关系。1962年11月中央专委决定首先要落实核工业急需的10项冶金材料,其中分离膜赫居首位。
分离膜的研制是国家绝密项目,为了掩人耳目,分离膜不叫分离膜,叫“真空阀门”。巨大的信任、巨大的责任、巨大的压力使临危受命的陆达充满了神圣感和使命感。他当即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项尖端材料的研制任务。学识渊博、实践经验丰富的陆达认定用粉末冶金工艺来研制较为可行。他将此项任务作为全院头等大事布置给粉末冶金研究室,组成代号为“418”的专题组。此室当时仅50余人,大多系刚步出校门的大中专毕业生,平均年龄不到25岁,除极少数学粉末冶金专业外,主要是从其他专业挑选出来的,共同组成一个攻关团队。当时正值全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供应不足,缺乏营养,不少人患了浮肿病。能不能战胜国家物质技术基础还很薄弱等诸多困难,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把分离膜研制出来,确实是一次重大而严峻的考验。
面对内忧外患,陆达不怕挑战与艰难,在基本没有资料和设备的条件下,针对分离膜结构独特、工艺复杂、要求严格,从原料到成型技术难题关隘重重的实际,亲自运筹,调兵遣将,动员和调集全院力量会战攻关。与中国原子能研究所615室和中南矿冶学院密切合作协同。他深入科研第一线,定方案,排进度,始终参与技术方案的制订,亲自参加每一个技术难关、技术关键的分析研究。他不怕剧毒,不嫌苦、脏、累,经常不分昼夜地战斗在分离膜研制第一线。隆冬季节,因陋就简、透风漏雨的实验室有他的身影,在破房子里搓手跺脚坚持试验的滋味他也体验过。在他的带领和指挥下,参研人员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激情澎湃,士气高昂,打破作息常规,晚上的试验室依然灯火通明,直至深夜。有人连续几年主动放弃探亲假,有人至亲去世了也未尽孝道,有人一再推迟婚期。大家瘪着肚子,冒着寒风,宵衣旰食,一心扑在试验上,将个人的一切全抛置脑后。
随着研制工作的步步开展,他带领大家在险峻的攻关道路上爬山涉水,就像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一样,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上的卡脖子环节。经过无数次推导、计算、实验和总结,终于在1964年提前研制成功国家急需的乙种分离膜。
1968年,冶金工业部、二机部根据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决定,联合提出《关于分离膜生产任务安排意见的报告》,文件中指出,钢研院继续研究开发的丁种分离膜全面提高了分离效率,简化了制造工序,正式决定丁种分离膜为原子能工业铀分离膜定型产品,取代上海冶金所的甲种分离膜,并不再生产甲种分离膜。丁种分离膜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铀同位素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由仿制苏联产品为主进入独创高性能分离膜的新阶段,跨入国际先进行列。
钢研院在取得了乙、丁两种分离膜研制技术和经验基础上,1975年后根据核工业发展需要,又相继成功开发研究性能更高的戊、己种分离膜新品种。己种膜在老扩散厂改造中发挥有效作用,使产品产量和效益显著增加。至此,形成了分离效率一代比一代高的分离膜系列。
分离膜的研制成功和顺利投产,保证了气体扩散分离老厂的生产,而且为地处大西南的三线新建厂做好了新型分离膜材料的充分准备,为发展我国核燃料工业作出重大贡献。
争与让
陆达一生中,很少与人争点什么。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争多做工作,为国家民族争气。他习惯于让。
1937年,陆达非常热情地接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逼令离军“出国考察”的杨虎城将军,陪伴其在欧洲一路巡行,担负其演讲稿的翻译。陆达陪同杨将军去西班牙慰问反法西斯战士,参与反对佛朗哥的活动。一次在散发传单时,遭到德国纳粹搜查的陆达机智地把装传单的书包放在一个德国妇女脚下而躲过一劫。陆达后与杨将军同船回国,足见其炽热的爱国抗日之情。陆达谦虚大度、厚人薄己,总把方便让给别人。在和杨虎城同船回来时,大家一起照相,陆达不抢镜头,平和让人,默默地站在后面一排,以致那张照片上他被前边和左右的人遮挡得近乎消失,只露出上半个脑袋,右肩的一个局部,五官全然不见。不知内情的话,谁知道那是谁呢?
20世纪50年代,陆达由设计人员转为钢铁研究院工程师,工资应该挂靠为工程师级别,比设计人员高。但他从来没有提出异议,以致在一次报表中有关人员将他一级工程师的职称误填为二级工程师,结果有好几年他拿的都是二级工程师的工资。他把金钱和名誉、地位看得很淡。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可是,在陆达的眼里,没有“冤家”的概念。经过千辛万苦的艰苦探索,钢研院于1964年在攻克分离膜的制粉、成型、物理参数和力学性能合格等技术难关后,陆达组织院内大会战,大家熬红了双眼,分离膜的耐腐蚀关终于迎刃而解。在钢研院的分离膜抗腐蚀性能过关后,这时,以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为主承担的甲种分离膜方案也正在过腐蚀关。遵照陆达的意见,钢研院从国家利益出发,发扬大协作的精神,毫无保留地将试验成功的耐腐蚀处理方法送交上海冶金所。1965年3月,上海冶金所甲种分离膜的科研试验任务也宣告完成。
其实,陆达的贡献,绝不仅仅局限于分离膜。他以院长兼党委书记的身份领导钢研院的工作,从1957年到1977年整整20年。在他的领导下,为导弹发射、卫星上天,提供了运载火箭所需的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以及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固体发动机用的超高强度钢和新型喷管喉衬材料;为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反应堆供应了提取铀所需的耐蚀合金和高纯氧化物坩埚,各种反应堆所需的耐蚀合金,动力堆壳体用钢、蒸发器用合v5Ku27na9hrRJ6Ak178JppauPw4zApaA4RPCn2kNV1M=金。1975年邓小平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时,陆达被任命为国务院钢铁领导小组成员,多次奉命带领工作组前往包钢、武钢及太钢,解决当时各钢厂出现的重大生产技术问题。1977年至1FJWu2Wqk20ykW/QmvEETfa0FrNZTQvquzIZnpfHuReI=983年,陆达担任冶金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在此期间,他为及时研制中国发射通信卫星、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和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等工程所需的冶金材料做了大量科研以及协调和组织工作。
陆达的大女儿陆忆兰回忆说:“爸爸一生中做过不少辉煌的事情,可他从来不说这件事是他干的,只说他参与了。”
昔人已乘黄鹤去唯有精神照千秋
陆达原名陆宗华,1914年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级职员。陆宗华先后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化学系、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后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钢铁冶金系,师从著名的杜勒教授学习四年,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迪普隆工程师考试。“七七”事变爆发后,祖国蒙难,他果断放弃学业,1937年冬途经香港、西安,1938年 1月抵达延安。为庆幸自己到达延安,更名陆达。
陆达出身官宦人家,家境优裕,他毅然放弃在德国当专家的安逸富足生活,也没有选择留在京沪渝等大城市为执政的国民政府当差。他爬山越岭到贫穷落后、当时还前途未卜的延安,又穿过日军几千里封锁线,视死如归地从延安奔赴太行山。
而今,陆达早已驾鹤仙去,他创造的辉煌在喧嚣红尘中渐渐暗淡下去。如今,他带头研制的分离膜已成为历史的回忆。有一位曾经身经百战的元帅在参观扩散机厂房时,震惊于巨大的厂房和庞大的扩散机群感叹:“我检阅过千军万马,但从来没有检阅过这么多的机器。”2023年,我到兰州铀浓缩厂去参观,摄人心魄的扩散机厂房已不见踪影,只留下荒草萋萋。远在巴蜀的分离膜专业生产厂也早就人去楼空,一片空旷与寂静。因为,我们有了更先进更加现代化的铀浓缩厂房、工艺和设备。我国核工业关键技术——铀浓缩技术完全实现了自主化,并跻身国际先进水平行列。国产铀浓缩离心机技术所需的耗电量约相当于气体扩散法的1/25,综合成本约减少一半。
分离膜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陆达创建的业绩是永恒的,他的精神将如同日月星辰一样万古流传,永垂不朽。
(作者系中国核工业史志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