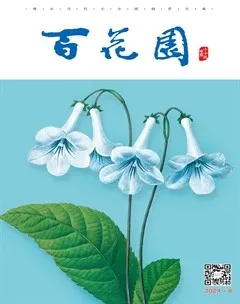是谁解剖了田鼠
于子寒,写作爱好者,原声吉他音乐普及推广人。著有散文诗集《银色森林》,随笔集《心中永怀圣火》。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等作品见于《海燕》《短篇小说》《小小说选刊》《青岛文学》《东方少年》《宝安日报》等。曾担任新媒体平台“指弹吉他”主编,“吉他情报局”主笔。
李小南是一个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在于德北的小说里,他呈现出的特点是情感细腻、精神世界丰饶。李小南有一颗柔软而胆小的心,对细小之物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还时常对这些事物生出好奇和关怀。
我们可以轻易地从小说中辨认出这一切。
在《青涩》一题中,李小南想起那个明显被同伴们排除在“择偶序列”之外的、得了肺结核的邻居女孩时,作此感想:
“一听见她咳嗽,胸口就闷得想哭。”
在《金太太》一题中,当金太太讲述了那个洋溢着超现实色彩的故事后, “母亲不信,李小南信”。
这些语句短促、有力,高效地勾勒出了李小南的内心景观。与此同时,无论放置在小说原文中,还是单独引用出来,这些语句还显露出一种诗意。我想,这和于德北作为小说家之外的另一重文学身份——诗人——有着必然的联系。
当然,是小说家的有心营造也好,是诗人的顺势而为也罢,这些自在浮游于文本沟回中的“诗意”除了独立的美感以外,还体现出一种叙事层面的强功能性:它们从整体上赋予了三题小说一种统一的朦胧感。这份朦胧感既暗合着李小南所处的生命阶段——如梅雨季般潮湿、懵懂的“青春期”,也隐喻了李小南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九八〇年前后)和地域(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是青年于德北生活的时空特有的社会现实跟人文气氛。
这是一种怎样的现实和气氛呢?读者们无须特意查看历史材料,也能从小说中找到线索,比如《青涩》一题中昭然若揭的“性压抑”、《金太太》一题中影影绰绰的朴素婚姻观、《长跑》中被青少年群体深深信仰的“江湖义气”等。它们当然不是这三篇小说的着力点,却共同编织了一张纹理模糊、边框清晰的时代之网,为每一个已经或可能出现在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跟事件事先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我的分析在作者本人的创作谈中得到了印证,他说:
“我想放置一个更宽阔的背景给我的读者,让他们去探索、认定他的家庭背景与社会背景。”
具有那个时代生活经验的人都不难明白,李小南的性格是“非主流”的,是极容易和“矫情”“怕事儿”“娘儿们”等等明显是牵强附会的评判纠缠在一起的,只要稍不注意,他就会跌进“男子气概”的绝对反面。“男子气概”的反面不是“女子性情”,而是一片莫须有的沼泽,陷进去容易,爬出来难,它会成为一个男性的“案底”,会在一个阶段内甚至整个生命中给他的一切活动蒙上阴霾。
在小说中,这层阴霾早就让李小南跟他的朋友之间产生了似有若无的疏离感:
“……春末夏初,人们身上的棉衣、棉裤还没有脱下来,但云逢龙已不再遵循父母‘春捂秋冻’的训诫,只要一出家门,就找个地方把棉裤脱下去……李小南不敢。”
当这份疏离感还收敛着的时候,是不易察觉的,或是缺乏被揭露的动机的,可一旦它因某事爆发,则无所谓过渡期或缓冲区,而是直接演变成硬邦邦的法槌,把李小南捶在集体认同的安全地带之外。比如,《长跑》中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叛逃”。
在《长跑》的结尾,李小南受到了“应有”的审判,作者如此说:
“在李小南的少年生活里,这是一段苦难的经历。因为自从这件事之后,他被云逢龙他们孤立了。他变成了一只随时可以被霸凌的田鼠,惶恐不安地度过了他初中生活的最后一段暗黑时光。”
可想而知,对于一个生活空间和心理资源本就逼仄匮乏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既然救几只旁人眼里无关痛痒的、可以被生吞活剥的野生动物的代价如此大,李小南又为何如此做呢?上文中引用的段落之后,于德北这样交代:
“……因为大地赋予了他向上生长的力量,这力量足以应对所有的狼狈不堪和重重困难。”
在创作谈中,作者已经说明了,这种“向上生长”的力量并非完全源自人性中天然的善,而更像是作者本人在小说之外因为“自我救赎”这个动机而在小说中必须要使用的叙事手段:
“毋庸置疑,在李小南的身上,有我少年时期的影子。我分解了一些我的经历在他身上,他也推脱不了地以代言人的身份,阐释了我的叙事视角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因为李小南的身上不乏“我的影子”,所以,作者在虚构的故事中延伸了自己的人格和行动,以填补或雕饰自身在现实生活里留下的遗憾、产生的困惑。
说到这儿,或许不得不聊聊作者于德北这一个体。
足够熟悉于德北的朋友们,大概能够达成一种共识:于德北的性格特点极其明显,甚至展示着某种自我边缘化的倾向。他身上具有大多同龄人(1965年生人)没有或许也“不该有”的未成熟的部分,比如,他明显地耻于也拙于养成某些被认为是必要的社交习惯,怯于也不屑于行使某些理所当然的个人权利。他有字面意义上的孩童性情(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刻意保留了某种被他视为“单纯”的表达习惯……
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对于德北其人,我们无权做任何评判,我只是想说,于德北和他的作品形成了一种不可多得的镜像关系:相较于文本,作者本人的种种是理解李小南,甚至是理解作者一切其他文本的更便捷有效的途径。可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许多作家在写作中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尽量对作品中映射了自身心理特征的部分进行这样那样的遮蔽。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而于德北则以其人、其作,表达着另一种观点:遮蔽是没必要的。或者,至少于他本人来说,遮蔽与不遮蔽,都是无所谓的。
恰如李小南一样,有点儿“执拗”,有点儿“反常”。至于为什么“执拗”和“反常”,作者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解释权交给了读者,而根据我对于德北的了解,或许连他自己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从上面那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一些大众习以为常的世俗规训,于德北并非刻意反叛,更无心解构,他只是有一点儿“懵懂”,这懵懂或许源自某些特定的、不为人知的经历。当一个人将这份懵懂视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把形成这个问题的过程命名为“创伤”;当一个人将这份懵懂视为强壮身躯上一块不起眼的“胎记”时,则不会专门为它起一个名字,更不会为它赋予什么严肃的意义。
或许你曾试着反问李小南的那几位伙伴:如果“江湖义气”真的那么高尚、光荣,如果几只可以随意被杀死、解剖的田鼠幼崽真的那么渺小、低微,你们为何又要为了它们而推开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兄弟”呢?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