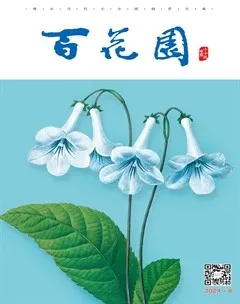金太太
金太太是李小南家的邻居,湖南礼陵人。她和丈夫金先生是大学同学,毕业结婚,随丈夫来到松城。金先生是个翻译,日语很好,能模仿日本天皇背诵“投降书”。金先生大高个儿,人长得帅,业务也过硬,很受人尊敬。就一点不好——贪酒,是一个每喝必醉的人。金太太不和他吵架,和他冷战——不和他同床,吃饭都两个灶。
怎么才能好?
除非金先生戒酒。
金先生也尝试过戒酒,最长的一次戒了七天,第八天就以“成功戒酒一周”为借口,自己庆祝了一下。这一庆祝,就又喝得昏天黑地了。
有一次,李小南在师大北门见到他,他正坐在阳光地里胡言乱语,看见李小南就龇牙笑,用手指着他们家属楼的方向,一连声地喊着金太太的名字。
李小南对金先生的印象并不深,但他永远记得金太太。
金太太去他们家和母亲聊天,聊到她和金先生的故事,就操着湖南口音说:“那是个才学很好的人。”
她讲他们一起去农场社会实践,男同学趁着夜黑,给女同学讲鬼故事,别人都讲得血淋淋,吓得女生往一块挤,只有他,声情并茂地讲了一个“菊花精”的故事,文白夹杂,让人听得舒服。比如,那故事的开头,他讲得很简洁:“马才子,顺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
有女生就说:“你文绉绉的,根本不像讲鬼故事。”
他才换了口吻,说另一段:“陶公子大醉,倒在地上就睡,谁知,化成了一株菊花,有一人多高。马才子吓了一大跳,赶紧去叫他的姐姐黄英。谁知那黄英并不以为奇,只道:‘怎么又喝成这样?’就连根拔了,平放在地上,把衣服给他盖好,一个人回房了。”
金先生的故事迷住了许多女生,金太太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故事很好听,李小南一直想听完整,可是没有机会。
长大了,读《聊斋志异》,李小南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名字叫《黄英》。
金太太的个子不矮,四十岁了,依然身姿曼妙,见人不说话,只微笑点头。她的眼睛是细长的,躲在眼镜的后面,偶尔会有光芒,但很快就会悄然地散了。她和金先生没有孩子,都说是金先生的问题——他长年喝酒,把精虫都杀死了。
金太太养花,只养灯笼花。她四处淘弄品种,日子久了,竟有三十余种。灯笼花花期长,一开几个月,这茬落了,那茬又起,跑接力赛似的,把金家的窗台装点得十分鲜艳。金太太的灯笼花,有白的,有粉的,有红的,有紫的,最奇怪的是还有黑的,一簇簇,一丛丛,争奇斗艳,会说话一般。
金太太对李小南的母亲——她受金太太的影响,也养灯笼花——说:“你信我的话,夜晚开着窗,拉开窗帘,让月光进来,你能听见灯笼花唱歌,声音细细的,到了高音的时候就断了。”说到这里,她叹口气,接着说:“唉!怎么就断了呢?想必是气不够。看来我还得给它们浇一点儿黄豆水。”
把黄豆泡发了,浇花肥力大。
可黄豆水也有气味,会招苍蝇。
灯笼花唱歌的说法,母亲是不信的。她以为南方人和北方人不同,思维方式也是有差别的。灯笼花是草木,怎么会唱歌呢?难不成世上还真有“菊花精”那种东西?如果真有,天下可就乱套了。
母亲不信,李小南信,他专等着有月亮的夜晚,苦熬着不睡,坐在椅子里,听灯笼花唱歌。他听见了风声,还有鸟的叫声,就是没有听见歌声。不过,他看见了几只萤火虫,围着灯笼花翩翩飞舞,一闪一闪的萤火神秘万分。他家住四楼,他没去想这么高的楼层,萤火虫是怎么爬上来的,而是推断出金太太的话是有道理的:如果灯笼花不唱歌,萤火虫为什么来伴舞呢?这么想,他就下意识地去掏耳朵,笃信灯笼花会唱歌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他记得清楚。
那是一个下午,他替母亲去金太太那里还盆,金太太对他说:“灯笼花,杜鹃花科,树萝卜属附生灌木,叶片革质,椭圆形……”这段话很长,李小南只记住了这么几句。他从来没听人这么讲话,一下子被语句排序给迷住了。同时迷住他的,还有金太太的表情——柔和,平静,舒缓,释然。那天,她没戴眼镜,眼皮有点儿肿,两眼之间的鼻梁上有两块压痕,显得鼻子更加直挺。
金太太病了,她的灯笼花也有些萎靡。
金太太嘱咐它们:“就算我死了,你们也要好好活。”
不久,金太太真的死了,骨灰被金先生送回了她的老家。她的那些花,金先生不想留,一部分送给了李小南的母亲,还有一部分被他丢到垃圾站去了。转移到李小南家的花,自然得到母亲的细心照料,而被遗弃的那些,却也没有因为环境不好而死去,它们歪歪扭扭地生长着,很快就形成了一片花海。
有一天,李小南做了一个梦,他梦见灯笼花唱歌了,声音很齐,也很大。他最担心的高音部也上去了,把月光震得扑簌簌抖动。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