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霸权”,暂未终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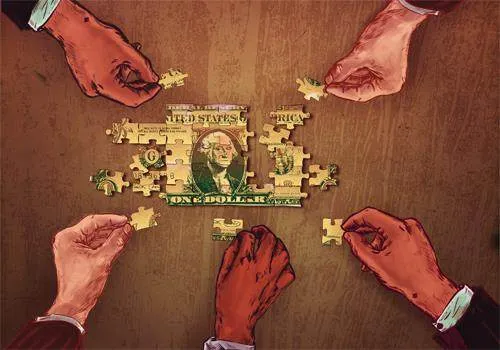
6月9日前后,一则“石油美元协议”即将终结的消息开始流传。该消息称,1974年沙特与美国长达50年的石油美元协议已于2024年6月9日到期,沙特不再续签。一些观点开始将其解读为“美元霸权”即将终结的前奏。
但随后,不少机构媒体开始质疑以上消息。有调查怀疑,这很有可能是比特币炒家发布的假消息。
对这一消息根本不用投去过多的注意力。显而易见的逻辑是,对于产油大国来说,以何种货币结算石油贸易,是关系“国本”的问题。即便真的要“终结”,也必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必须要在国内外进行长达数年的准备和铺陈才行,突然用一个“大新闻”来终结,根本不合常理。
一直以来,沙特的主权货币里亚尔(SAR)实行的是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即沙特的主权货币也类似于一种“准美元”。这种货币局制度,充分说明了沙特希望货币体系绑定美元的决心,其突然“终结美元结算”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过,就国际政经领域的“阴谋论”而言,它们的信息质量固然不值一提,但其产生的确还是有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趋势性变化作为支撑。比如,近20多年来,在全球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占比的确在不断降低。IMF在6月11日更新的一份报告就指出,这一比例已从本世纪初超过70%,下降到了目前大约58%的水平。
变化的确在发生,但不一定像它表面所呈现的那样。
布雷顿森林体系80年
与这个并未被证实,所谓石油协议的“50年期”相比,另一个“整10年”事件更值得关注,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80年。回顾这一体系的建立和终结,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7月,全球战胜法西斯在即,主要国家的代表们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货币金融会议,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旨在塑造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其中,最核心的两个内容一是组织上的,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集团的核心机构);二是全球货币体系的构建问题,将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元币值必须和黄金绑定。
在二战之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战后全球经济复兴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这一体系之下,很多国家将本国货币和美元进行汇率绑定,最多在狭窄的区间浮动。这样一来,就极大地降低了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汇率风险,推动了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繁荣。战后的两大出口强国联邦德国和日本之所以快速崛起,很大程度正是受益于此。
以日本为例,1949年开始,日元兑美元采用固定汇率,即360日元兑1美元。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元的实际购买力开始上升,但为了刺激出口部门,日本人一直将这个严重低估本币的汇率保持到了1970年代初。此时,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之时,可见战后日本人希望绑定美元的决心。
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一些观点习惯从“阴谋论”的角度理解问题。其实,这里没有什么“阴谋”,实际情况就是,美联储认为自己无法继续履行过去一直履行的“义务”,所以选择“违约”。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协议,一旦外国央行用美元向美联储兑换黄金,那么美联储必须如约支付。这一美联储对外国央行的“刚兑承诺”,也是维持美元信用的底层逻辑。
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全球的美元越来越多。一旦遇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就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央行提出兑换要求。于是,美联储认为自己的黄金储备已无法继续满足未来的兑换要求,所以在1971年开始拒绝向外国中央银行兑换黄金。于是,美元绑定黄金,而其他各国绑定美元这一“连锁绑定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了。
但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惯例却保持了下来。一种十分常见的分析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之后,美元已经岌岌可危,但美国用武力威胁(或提供军事保护)迫使海湾国家用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所以最终保住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对这种观点,不便于做出评论。
用事实和逻辑来看问题,才能洞察本质。在1970年,美国的GDP是1.1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约为31%,这个比例已经比二战结束之后大大降低。二战之后,美国GDP曾一度占据全球的四成。
再看同时期其他主要工业大国的数据。德国、日本的GDP都在全球的6%左右。英国和法国的GDP更低,占比都没有超过5%。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几个主要工业国和日本的经济总量加在一起,都低于美国一国。那么,此时如果选择一种发达国家外币结算石油贸易,美元至少也是最不差的那一种。
另外,现实问题可能更加关键。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中东的石油富国们利用石油这一经济武器,展示了自己的力量。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将欧美国家带入了“滞胀”。然而,中东国家也发现一个问题,以石油价格为武器的博弈是一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
如果国家财政过度依赖石油出口,一旦未来油价出现大幅波动,特别是进入长期的下跌通道,那么将给自己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带来严重的冲击。此外,石油储备总有耗尽的一天。于是,中东国家开始陆续成立主权财富基金,将石油出口换取的外汇留存下来,在全世界进行投资,实现国民财富的保值和增值,以应对石油资源枯竭的风险。
于是,在这个“石油外汇”积累,然后对外投资的操作链条中,以哪种货币结算,就变得至关重要。这时,美元再次展示出其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一种独特优势,让它成为了石油富国的不二选择。而且,这种优势后来也被很多其他货币效仿,愈发深刻地影响今天全球主权货币的力量格局。
主权货币的力量来源
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它必须同时具备三大功能。第一是支付媒介,石油以美元结算和支付,就是这一功能的直接体现。第二是价值储藏手段,各国的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其次以欧元的形式存在,就是一种储藏手段。第三个功能是记账单位,也可以叫作价值尺度,即优质的资产以这种货币标价。
在国际金融市场,如果一种货币同时具备以上三个功能,那么它成为国际货币的概率就很大。实际上,同时具备以上三个功能的主权货币实在是太稀缺了。美元的独特优势,正在于其国内金融市场的巨大体量,以及其高度发达和开放性,有效地激活了这三大功能。其他主权货币暂时还做不到。
相对于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美国经济拥有最高的资产证券化程度,也拥有全球最大、收益率最高,并且最稳定的资本市场。这意味着,如果以美元结算,石油富国的“国民养老钱”主权基金不用货币兑换即可投资美国,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避免汇率风险。如果采用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结算,便没有这种优势。
比如,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的复兴,联邦德国马克成为了美元之外最强大的货币。但联邦德国的问题是,它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并不发达,而且市场的规模、深度和体量都太小,根本无法满足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其他同一时代币值相对稳定的货币,如英镑、日元都面临这个问题。
于是,在种种有利条件之下,美元成为了石油贸易结算的首选项。这是一种基于成本和收益的经济选择。至于其他因素,固然存在,但很难说是支配性的因素。
然而,美元的强势也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演变而变化。IMF的报告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出现下降的同时,两种替代品开始崛起:一是黄金,新兴经济体央行所持有的黄金总量已接近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二是其他非传统国际储备货币的崛起。
除了美元之外,其他传统的国际储备货币还包括欧元、日元和英镑。尤其是曾被视为美元最大竞争对手的欧元,从本世纪初到现在的20多年内,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一直都在20%上下浮动,根本没有成为美元真正的对手。相比而言,其他非传统储备货币的比例却在上升,比如人民币、韩元和新加坡元等。
人民币和新加坡元的崛起并不难理解,一个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一个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受益者。韩元为何也成为一个新兴的热门货币?IMF的报告并未对此进行详尽分析,但一些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数据,透露了线索。
三星是韩国的第一财团,其销售额几乎可以占据韩国GDP的1/4。然而,三星却有点类似于“外资控股公司”,在三星的普通股中,外资持股占比曾一度超过55%。这背后透露的信息是,韩国的金融市场已经高度开放,三星这种关乎“国本”的超级大财团,竟然允许外资持股的比例如此之高。
实际上,在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外汇和金融管制便进入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宽松通道,即使是“左派”领导人上台,依然没有改变这个大趋势。放松监管为外资进入和退出提供了更加顺滑的通道,非但没有资本外逃,反而使得外资更愿意在韩国投资。某种程度上讲,韩国人正是在学习美国人当年的经验,打造更开放的金融市场,以优质金融资产吸引外资,打造本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性基础。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韩国的故事并不一定适合中国。近年来,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屈指可数的强大货币之一。比如,IMF的报告就指出,在市场份额上升的非传统储备货币中,人民币比例的增幅,相当于美元比例降幅的1/4。
从很多中国出海企业和旅行者的现实经验来看,在一些新兴市场,人民币已成为了重要的国际货币,开始在企业和机构间交易,以及在消费者日常生活中,承担起一定的支付功能。近几年,中国央行和其他经济体货币当局进行了大量的货币互换,背后原因正是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功能变得日益强大,有了境外的市场需求。
国际货币体系一直都在变化之中。美元在国际支付和储备中的强势地位,被一些观点认为是“美元霸权”。然而,这一状态暂时还不会出现根本性逆转。对其他有着雄心的经济体来说,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发展,让自己的货币变得更强大,逐渐成为其他经济体国际储备的优选币种,才是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