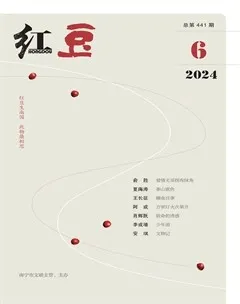少年游
玉轮悬空,银汉无声,整个槐树湾沉浸在幽静的睡梦中。高高低低的农舍参差错落,我在屋脊上奔走如飞,脚步轻胜狸猫。从一个房顶跳跃到另一个房顶,其间一丈余宽的间隔根本阻挡不住我,更远的距离我就借助旁边的树冠或柴垛。我跃上枝头,不等枝叶摆动,已腾空而起。起起落落之间,我已在槐树湾所有的房顶上游走了一遍。我看到有的院子里垛着白天割来的青草,草汁特有的清香沁人心脾;有的院子里晾衣绳上挂满滴水的衣服,如同被满月的银辉浸湿。最后,我来到小东北家年久失修的房顶上,伴随着碎瓦坠地的声音,跃上村口那两棵高大的古槐。没想到这两顶遒枝杂错的树冠竟是如此之大,里面栖息的鸟儿竟是如此之多。黑色的乌鸦,灰色的布谷,花白的喜鹊,墨绿的斑鸠……它们被我惊醒,纷纷振翅而起,五彩羽毛悠悠飘落。我站在一根粗壮的树干上,仰望它们扶摇直上,空气被震动得嗡嗡作响……
我带着一丝隐痛睁开睡眼,痛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实,来自左脚的拇趾。摸起床头的手电筒,借着暗淡的橘光,我看到趾甲折裂,有一丝殷红。一定是梦中踢到墙上了。我回想起刚才的梦,似乎是飞上了村口的槐树,一群鸟被惊起,我想跟随它们一起腾空直上,却一脚绊在丛生的树枝上。
待疼痛减轻,我趿拉着凉鞋走出房门。院子里遍洒满月的银辉,令我手中的光亮仿若秋萤之光。于是,我关掉手电筒,随手把手电筒放在门口旁的鸡窝上,走到院墙根的榆树下撒尿。树上垂下一条条细丝,悬挂着一个个蜷作一团的“吊死鬼”,我小心地躲避着它们。头顶的月亮像一个巨大的白玉盘,映衬得天空愈发湛蓝。墙角的砖缝里有蟋蟀在弹奏《月光曲》,曲调清脆;牛栏里的黄牛在睡梦中反刍,声调沉缓;鸡窝里,不时传出一阵叽叽咕咕的梦呓声,喑哑低短;遥远的地方,似有狗吠之声,细听又不真切。我站在树下,又一次回想起刚才的梦,那种轻盈如飞的感觉令我心里泛起一阵微澜,便收拢双腿,跳了几下,身体依旧沉重如石,落地又加剧了脚趾刚刚平复下来的痛感。
电视里飞檐走壁的大侠们都是夜间出行,我踮着脚往院门走,刚走出两步,忽觉墙头上似有黑影一闪而过,就赶紧转身回屋了。
吃完早饭,走出家门,燕飞已在老枣树下等我。他是从犁城来姥姥家过暑假的,他姥姥家跟我家仅一墙之隔,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此时他正仰望着树叶间青绿色的枣子,见我过来就问我这枣子啥时候能熟。我说早着呢,得等到中秋。“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竿。”我显摆了一句从作文书上看过的谚语。他说:“那我吃不着了。”我说:“一个破枣儿有什么好吃的?”“你不是说很甜吗?”他问我。我说:“你还稀罕这,你在城里啥好吃的没有?”他摇摇头说:“那不一样。”
我挎着篮子,提着镰刀,和燕飞顺着我家西墙根往村后走。正是盛夏时节,虽然早上的阳光还没有发威,树上的蝉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鸣唱。路边青草细长的绿叶上还滚动着夜间的露珠,牵牛花擎着一个个小喇叭,白色的、粉色的、紫色的,仿佛准备随时吹奏一曲天籁。蚂蚁们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有的单独行动,有的成群结队。我挥舞着手中的镰刀,眼前浮现着电视里那些持剑打斗的画面,但我只会左右比画,几下便没有了兴致。
我们走进那片开阔的荒草地,高高的蒿草没过膝头。我把篮子和镰刀扔到草丛里,和燕飞爬上一道半人多高的土堤。土堤的顶部只有一拃来宽,土质干松,全都是旁边田里泛起盐碱之时人们用铁锨铲起的薄薄的一层浮土,长年累月堆积而成。我们一前一后在土堤上奔走,练习飞檐走壁的本领,碎土在我们脚下簌簌滑落,腾起阵阵黄尘。这是燕飞想出的主意,他说这儿的土这么松软,我们在这上面练习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快速度,想方设法减轻自身的重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我们已经练了半月有余,却没见任何效果。
我们都迷恋而且梦寐以求地想练成在武侠剧里看到的武功,包括拳脚和剑术,甚至轻功。别说小小的槐树湾,方圆十几里的村庄里从没听说哪个人会一招半式,我们想找人指点也无人可找,只能自己去琢磨。好在燕飞说他会一套拳法,是学校里体育老师教他们的。他打了一遍给我看,一招一式,缓慢而不连贯,也没有电视里那种打出来呼呼挂风的效果,但我还是非常羡慕他。我们槐树湾只有一个老师,除了语文和数学这两门课,我都不知道还有体育课这一说。除了拳法,燕飞还有一个让我震惊的本领,他会鲤鱼打挺,他说这是他一个在武校的小伙伴教他的。武校,这又是一个新鲜的名词。那一刻,我真恨自己为什么没像燕飞一样也出生在城里。我问燕飞武校是什么,他说是专门学武的地方。我问他在哪儿,他只说了两个字——很远。我又问他怎么不去学,他说他爸妈说知识比武功更重要。我们都觉得这种说法可笑至极。燕飞说他的这两项本领都可以传授给我,条件是我要和他一起练习飞檐走壁。
“飞檐走壁我当然更愿意练。相对于拳脚,这是更上乘的武功,可是没有人教咱们啊。”我说。
“咱们自己练。所有的武功不都是人琢磨出来的?”燕飞很有把握地说。我同意他的说法,可心里却没有底。
我们在土堤上跑了几个来回,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却依旧没有丝毫进步。堤上布满了我们的脚印,还有一个个犬牙交错的豁口。
“还是不行啊。”我说。“咱这才练了几天啊。”燕飞毫不气馁地说,“等啥时候咱把这土堤踏平了就差不多了。”
他这话让我不禁想起电视里的侠客为了练功踢呀踢,踢断树干的画面。
“你还是先教我鲤鱼打挺吧。”我平复了一下呼吸,说。“那套拳你会了吗?”“会了。我打给你看看啊。”
我一招一式地练起来。由于不熟练,一边练一边回忆燕飞教给我的动作。
“不对。”燕飞打断我的动作说,“你脚下的动作配合得不对。”他说完又给我演示了一遍,然后让我照着做,直到我跟他做得一样了才罢休。
“这下可以教我鲤鱼打挺了吧?”我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
可燕飞还是拒绝了我。他扯下一根狗尾巴草,一边摆动一边说:“鲤鱼打挺不难学,现在我们要先练成飞檐走壁。”
我很失望。“那你再练一下让我看看?”我简直要为自己这种卑下的口吻感到害羞了,同时又生怕他拒绝。我的算盘是先把他的动作记住,然后去偷练。在飞檐走壁练成之前,这是他压箱底的功夫了,当然不能轻易教人,电视里的高手不都是这样的吗?
或许燕飞也不敢得罪我吧,他点点头,把狗尾巴草扔到地上,走到草地上躺下——蚱蜢惊散。之后两臂抬起,双手放在头两侧,然后抬起双腿,直抬到屁股离地,最后腿猛地往下一摆——惊起更多的蚱蜢。但是这一次,他的身子刚起来就往后倒退了两步,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又是一片雨点般的蚱蜢惊惶飞逃。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竟隐隐有些高兴。“可能是刚才练得太累了。”我惊异于自己的卑鄙心思,赶忙安慰他说。话一出口脸上又爬过一丝热辣,于是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燕飞脸色绛红,没有注意到我的慌乱。他又一次躺倒在地,又一次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大叫一声,从地上站了起来。我动作夸张地给他鼓掌。燕飞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呼吸却好长时间平复不下来。
太阳当空,晒得我后背火辣辣地疼。
“真热。”燕飞擦掉额头上的汗水说。
“你先回去吧。”我对他说,“我还得去拔菜,等会儿我去找你。”
燕飞手搭凉棚望了望太阳,点点头,踩着厚厚的野草回家了。
阳光下,青草的叶子反射着银色的光,阵阵浓郁的花香暖烘烘地从簇拥着竞相开放的野花上袭来,吸引着一群蜜蜂嘤嘤嗡嗡,还有几只白色的飞蛾翩跹飞舞。在过往的夏天里,这片草地曾是我的乐园,我在这里捉过蚂蚱、蜘蛛、青蛙,还有一只刚刚睁开眼的野兔崽儿。但是今天,我不打算在这里停留,只想赶快找个隐蔽又凉爽的地方去练习鲤鱼打挺。我捡起地上的篮子和镰刀,翻过土堤,穿过一片玉米地,来到一棵大树下。树荫下清凉,我精神一振。我把人们扔在地头的半干的杂草收起来,铺到树下,开始偷偷地练习,但是一连做了十几次都没有成功。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气,腿和腰都在隐隐作痛,心里面懊恼至极。一只鬼鬼祟祟的蜥蜴翘着半个身子嗖的一声从我面前蹿过去,我抓起一旁的镰刀追了上去。
夜深了,我却无法入睡,满脑子想着鲤鱼打挺。我躺在床上,回忆着白天里燕飞的动作,又做了几个,依然没有成功。小床吱嘎作响,似要散架,我不敢再做,四仰八叉地望着漆黑的房顶出神。
突然,我听见燕飞在窗口叫我,转头一看,只见他倒挂在我小屋的窗户上。
“快出来。”他压低声音对我说。
我一跃而起,从床头跳到窗台。“我还要练鲤鱼打挺呢。”我悄声说。
“咱先出去飞一圈,完了我教你。”他特意用了“飞”这个字,脸上洋溢着得意的微笑。
我钻出窗口,双手搭在瓦上,轻轻一跃,跃上房顶。头顶圆月高悬,地上亮如白昼,连瓦片上的裂痕都看得一清二楚。“咱俩比赛。”燕飞站在我家坑坑洼洼的屋脊上,抬手画了一个圆,说,“围着槐树湾跑一圈,不能落地。甭管谁输谁赢我都会教你鲤鱼打挺的,说话算数。”
我答应了。
我们在墨蓝的夜色里穿行,越过宽宽窄窄的胡同,高高低低的砖墙、土墙、篱笆墙,脚下声息皆无。月色溶溶,一排排瓦片就像鱼的鳞片,有又细又高的野草从缝隙间钻出,在水一样的光里一动不动。人们都沉在睡梦里,整个村庄阒寂无声,瓦缝间夏虫的振翅声清晰入耳。房顶的烟囱、接收电视信号的天线杆在我们身边闪过。村庄外,树影沉沉,大片的庄稼地望上去一片漆黑,而坡下湾里的水却平滑如镜。借着电线,我来到同桌小黎家的房脊,他的院子里停着新买的拖拉机,车轮旁睡着他的大黑狗。起夜的小黎提着短裤,看见房顶上的我们如鬼魅闪过,惊讶得咽下打到一半的哈欠却合不上口。我得意至极,脚下用力跃上两米开外的另一个房顶……顷刻之间,我们到了村子的另一头,一户人家的墙头悄立着一只偷鸡的狐狸,狐狸皮毛火红,尾巴硕大,转动的眼珠如鬼火闪烁。“抓住它。”我和燕飞异口同声叫道。与此同时,警惕的狐狸也发现了我们,身子一扭,跳下墙头,向着村外箭一般窜去,我和燕飞紧随其后。荒草萋萋,狐狸在草间潜行,身影忽隐忽现。草丛中掩藏着干结的牛粪,还有地鼠掏洞拱起的土堆。我们踏草而飞,始终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一片坟茔边,狐狸消失不见。我们站立在两棵高立的红荆树的枝条上。这种农人用来编筐的枝条质地柔韧,在我们脚下一起一伏,细密的针状叶子散发出浓郁的涩香。耸起的坟头间茂密的杂草兀立不动,压坟纸却飒飒作响。我和燕飞对望一眼,都看出了对方心里的畏怯,转身向着村子的方向跑去。
回到家门口分手的时候,燕飞对我说:“其实鲤鱼打挺很简单。”他告诉了我其中的要领,让我先练习仰卧起坐,以增强腰腹肌肉的力量。“我当时就是这样练的。”他对我说。
回到家我就躺在床上练习,直到腰膝酸软,才倒头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上,我觉得全身骨骼酸痛,耳朵嗡嗡直响,咬牙勉强起了床。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说我发烧了,找出之前的退烧药让我服下。
院外,燕飞在叫我。
“我发烧了。”我对他说,“今天不能去练了。”
燕飞难掩满脸的失望之色。
“我去,也只能看着你练。”我心中不忍,又补充了一句,“要是我感觉好点了就和你一起练。”
“好。”燕飞喜笑颜开地说,“今天练完了我就教你鲤鱼打挺。”
“你已经教过我了。”
“啥?”燕飞疑惑地看着我,走过来伸手摸摸我的额头说,“你真发烧了。”
那天上午我一直看着燕飞在土堤上来回奔走。他奓着双臂,身子歪歪斜斜,脚步跌跌撞撞,完全没有昨天夜里的轻盈。我看着他的身影,只觉得天旋地转,只好躺在草地上。天空万里无云,蓝得仿佛拿笔尖一蘸就能写出字来。燕飞几次叫我上去,我都对他摆摆手。
“还不行吗?”他从土堤上跑下来。
“头晕。”我说。
“现在我教你鲤鱼打挺吧。你先看我做一遍。”
我缓慢地坐起来。
燕飞躺在地上,一边做动作一边讲解,毫无保留,就跟他昨天晚上对我说过的一样。“要加强腰腹的力量,练仰卧起坐最管用了,我当初就是这样练的。”他最后对我说。我一时分不清正在发生的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恍惚之间竟然没有听清他到底说了什么。
夏日漫漫,燠热似乎永无尽头。我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学会了鲤鱼打挺,虽然不能做到每次都利索地站起来,但十次里面还是能够成功多半的。而飞檐走壁依旧丝毫不见长进,我渐渐地感觉到心灰意懒。每天正午时分,骄阳如火,我躺在铺在院门下的凉席上,听着焦躁的蝉鸣声,看着门前不远处在池塘中央戏水的小伙伴,对他们的召唤充耳不闻。燕飞躺在我的旁边。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对练功的热情丝毫不减,总是抱怨时间过得太快,而早上凉爽的时间又太短,因为回到城里他就找不到这种练功的土堤了。一进八月,田里的玉米秀出细细的棒槌儿,棉花结出豆粒大的棉桃,燕飞就被他的母亲接走了,说还有很多作业需要做。与燕飞相比,这是我唯一一个可以骄傲的地方,我们槐树湾的孩子永远不用担心假期的作业。临走之前,燕飞嘱托我还要多加练习鲤鱼打挺,并约定明年再一起练飞檐走壁。说到飞檐走壁,土堤在我们脚下坍塌得七零八落,再加上几场大雨的冲刷,似乎比原来矮了整整一头,可我们的功夫却还是在原地踏步。我们只有在夜晚的月色里闪转腾挪,在各自的梦里相遇。白天,我们回味着身轻如燕的感觉,共同研究着夜里的动作,却始终不得要领。
燕飞的离开让我若有所失,也在突然间感觉到夏日其实所剩无几,天空的颜色与穿过树叶的风不知从哪一天起似乎悄然起了某种变化。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天天和燕飞腻在一起,企图成为人人艳羡的武林高手,而冷落了昔日的伙伴。等到我再想回到他们中间时,却感到一种若有若无的疏远与排斥。
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土堤上跑了几个来回,感觉索然无味。旁边玉米地里的庄稼已经有一人多高,我提着篮子钻了进去,里面密不透风,花粉撒落在身上,融进汗水里,密密麻麻地刺痒。后来,我提着满满一篮野菜往回走,在打麦场上被小武拦住。不知道为什么,我和小武天生不对付,一见面用不了三言两语就会掐起来。在教室里,他坐在我的后面,经常在我起身时用脚把我的凳子钩到他的桌下,让我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屁股坐在地上,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而他更是拍着手笑得肆无忌惮。因为这事我们两个更是不知打了多少架。
小武二话不说,冲着我就要撞过来。我早有防备,看他的样子是又要打架了,这也正合我心意,正好试试燕飞教我的拳法。
但是还没等我放下菜篮、摆出架势,小武一下就抱住了我的腰,我急欲甩开他好施展拳法,可用尽了力气也摆脱不开,反倒被他一下摔在了地上。菜篮滚到一边,野菜撒了满地。打麦场的地面虽说不上坚硬却仍令我后脑嗡嗡响。此时我早已忘记了刚刚学会的鲤鱼打挺,即使想起来也根本来不及施展,因为对手随即就坐在了我的身上。
一群在麦秸垛边玩耍的孩子见我们打起来,都嗷嗷叫着跑过来看热闹,小武的哥哥小文也在里面。但我的兄弟不在场,即使在场他也不会出手,这是槐树湾孩子打架的规矩。看到小武坐在我的身上,小文就放心了,大声叫着:“揍他,压住他,可别让他起来。”其他孩子也跟着起哄。
小武真的在我头上揍了两拳,让我眼冒金星。我急了,不管不顾伸手去抓他的脸,指甲在他脸上划过,留下血痕。
“抓人脸,娘们儿打仗才抓人脸!”小文在旁边嚷道。其他孩子都跟着附和。
大概是因为面部吃痛,小武力气一松,被我翻身压在了身下。我也照葫芦画瓢还了他两拳,他情急之下挠了我的脸。这下小文没有叫嚷,但有别的孩子打抱不平:“咋都学娘们儿啊?站起来打。”
我又揍了他两拳,起身让他站起来。
小武气咻咻地爬起来,刚想往我身上冲,就被几个大孩子拦住了。“好了,好了,打平了,谁也没吃亏,就这样算了。”他们把小武推到小文身旁。
小文没理他弟,只是看着我笑,一脸讥讽之色。
“你给我等着。”小武指着我跳着脚叫道。
“等着就等着,我还怕你?”我也毫不示弱。
往家走的路上,我越想心中越懊恼,不是因为上来就落了下风,也不是因为自己率先使用了无赖的招数,而是因为无论我怎么琢磨,似乎都无法用燕飞教我的拳法挡开小武扑过来的身体,那我练它还有什么用呢?
八月过半,暑热渐退,虽然树上的蝉声依然聒噪,但我已收拾起书包进入学校了。在课堂上,我时常想起燕飞。农村的孩子因为还有秋假,所以暑假比城里的短,燕飞一定正在家里做他的作业,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我。我又和小武打了几架,却依旧没有使用上从燕飞那里学来的一招半式。好几次,我想起燕飞说过的武校,明年我一定要问清楚到底在什么地方,那里的武功一定可以把小武打倒在地。
年少的我从没出过远门,连去犁城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远方,对我来说既是一种美好的诱惑,也是一种未知的恐惧。趁家中无人,我从炕席下摸出一卷零钱塞进裤兜,偷偷摸摸地出了门。玉米、高粱夹峙的田间小路上空无一人,我顺着小路走上碎石铺就的乡间公路,路过几个村庄,行不到五里就到了乡里。街道两边排列着供销社、邮局、粮所、饭馆、杂货铺,门前全都冷冷清清。循着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我来到一家铁匠铺,店前同样门可罗雀。以前我跟着祖父赶集来买铁锹、镰刀到过店里,我记得店主是个粗壮的中年男人,但这回却换成了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门口摆的、墙上挂的也不是粗糙的农具,而是一把把精心打制的刀剑。我暗自纳罕,心里想或许可以买把剑带上,就不由自主地走到老人跟前。问完了价钱,我才知道自己连最便宜的都买不起。老人看看我,问了几句话之后,点点头道:“好啊,那我就送你一把剑。”
我惊奇地望着老人。他慈祥地笑了,说:“我小时候也有一个远方的梦,可是没有胆量出走。等你哪天回来给我讲讲,就算是这把剑的价钱了。”
我把剑扛在肩上,向着前方大步流星走去。天苍苍,野茫茫。微风轻拂,路两边的庄稼奏出轻快的乐曲,我心中更是轻快得都要飞起来了,二十公里的路程一闪而过。
远远地,“犁城车站”四个大字冲着我招手,我走进车站,里面空荡荡的。燕飞曾告诉我,有个窗口上写着“售票”两个字,就在那儿买票。我走近窗口,女售票员奇怪地看了我一眼,问我去哪儿。
“武校。”我压抑着心中的自豪与激动说。
“哪里?”售票员又提高声音问。
“武校。”我又说了一遍。
“什么武校?我问你到哪一站!”售票员白了我一眼,高声叫道,“喂,这是谁家的小孩?买票要大人来哈!”
“我家的,我家的。”一个中年男人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来,不由分说就抓住我的手。
“不是,我不认识你!”我大叫一声,伸手去摸挂在腰间的剑擎在手中,却发现竟是一根开了叉的高粱秆。
“跟我走吧,你这孩子!”中年人狞笑着。
“不!”我惊叫着从梦中醒来,额头冷汗涔涔,心口突突直跳。
秋风渐凉,学业也一天天紧了起来,我没有时间再去那道长长的土堤上练习飞檐走壁。偶尔,月夜之下,我依旧奔跑在槐树湾的房顶上,翻墙越户,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在第二天早上起床时疲惫不堪。等到大雪纷飞之时,我就缩在冰冷的被窝里,抱着母亲给我装满热水的烫瓶,再也不想出门了。
第二年暑假,燕飞依约前来,在最初的生分过后,他对我说:“咱去钓鱼吧,我带了钓鱼竿来。”
他给我看了他的钓鱼竿。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钓鱼竿。
我偷拿了两角钱去小卖部买了鱼钩和鱼线,用鹅毛做了鱼漂。每天我和燕飞扛着钓鱼竿提着小桶——我还挎着篮子——去村后的河边钓鱼。树荫下,清风徐徐,水面波光粼粼,我们一边盯着水中的鱼漂一边说说笑笑。
远处的荒草地里,那条长长的土堤已被人修补好了,并添了春天新铲下的生满盐碱的泥土,看上去比去年更高了。在阳光炽烈的幻影中,两个少年在土堤上行走如飞,脚下飘起股股黄尘……
“哎……”我刚想重提飞檐走壁的话题。
“嘿,来了。”燕飞欢呼一声。一条鲫鱼闪着点点白光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身后的空地上,蹦蹦跳跳……
【作者简介】李成墙,作品散见于《清明》《春风文艺》《文艺报》等刊物。
责任编辑 梁乐欣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