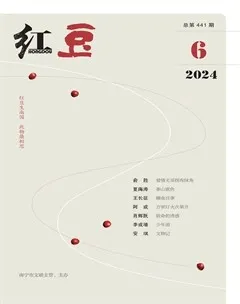活色生香的生活
天涯海角
三亚大东海的海景房,透过窗户能看到远处波涛汹涌的大海。大海辽阔,深不可测。我和五一住的套间,床很宽,五一满床翻跟头,可惜没有乾坤圈,不然他能当闹海的哪吒。
赶海,凌晨就要起床坐车去海边。渔民们捕鱼归来,既会批发,也会零售一些给来赶海的人。熙熙攘攘的人群簇拥着满船活色生香的海鲜,它们带着海腥气扑面而来,起再早赶海再辛苦也会觉得是值得的。烹制海鲜,更为重要的是食材,厨艺显得没那么重要。买回去各种海鱼、扇贝,或清蒸或水煮,只用葱姜去腥,加些海鲜酱油提味,便是人间至味。
海虾格外鲜活,须子在锅里抖动着。五一守着养在盆里活蹦乱跳的海鲜,怎么也不能将它们和中午盘子里的美味联系起来。他不让我动它们,那去赶海干什么?难道是为了回来养一盆子宠物?
大海起伏不定,五一用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在海滩上用木板修建城堡,又是挖掘又是夯筑,一刻也不得闲。城堡看起来异常坚固,颇具规模。傍晚时分,涨潮了,他苦心经营的城堡顷刻间被海浪拍毁在沙滩上。我以为五一会沮丧,但他似乎并不在意,他奔跑着躲避一波又一波追逐他的海浪,早没心没肺地将他的城堡丢弃在脑后。我很羡慕五一这样,不管曾经多么热爱,他能自然而然地接受变故,没有怨言,也不悲伤,轻轻松松就放下了。而我,总是会被满脑子执念折腾得痛苦不堪。
经过刻着“天涯海角”的巨石时,我们停留了很久。那一刻,属于过去的一年。我们兴高采烈地买了许多苦丁茶回去送人。只是苦味似乎从来都不讨好,除了我们,因为知道是自己辛苦背回来的,别人谁会认真喝它?我带了成套的竹茶杯回家。闹市里的小小房子里,每每泡茶,青绿色的茶叶隐约夹杂着竹器的清香氤氲起伏,令你身心安详。只是那套竹茶杯没多久就在遥远的北方失掉了颜色,干燥开裂,只能陆续丢弃了。
三亚道路两旁,高大的椰树后面是一栋栋穹隆式屋顶的房子,墙壁上的马赛克奇异而多彩。我和五一在冷饮摊要了一支冰激凌,用两根小勺,就着那酷暑慢慢吃掉它。五一指给我看,满街穿着长长短短裙子的女人炫目。我试着用五一的眼光打量自己,T恤短裤,我不是个优雅的女人。大海很近,最凶猛的风暴大概是在内心席卷。每个夜晚,我将自己困在文字中。我听不见海的涛声。我的内心嘈杂如潮。
大东海酒店离海咫尺之遥,五一有时候会穿好泳衣,裹上大毛巾去海边,他在海水里扑腾,看起来像是青蛙而不是鱼。五一看到的与我看到的似乎截然不同,我对自己看到的东西讳莫如深。我去丢弃绝望,而五一带回来一堆贝壳,他说它们是大海的耳朵,里面藏着波涛的声音。
在三亚,我们每天傍晚都去天涯海角。我将发髻绾起,穿上有腰身的及踝长裙,我的背部被日光暴晒出丘疹,现在我仔仔细细给它们涂上冷藏过的芦荟胶。疗伤之后,我便不是过去的自己。我努力保持生活正常运转在轨道上。
五一在,也不在。这是我的天涯海角,一个人的天涯海角。孩子就是孩子,他总是快乐的,就算是听到不该听的话,遇到不高兴的事情,它们统统是沙滩上的脚步,浅得不能再浅。潮涨过后就消失了。
焦虑只是我的。生活常常是一个人的战争,硝烟弥漫。夜晚五一先睡了,我踟蹰在露台上,隔壁住的年轻人嬉闹喧哗,我听到一长串异乡话语接踵而至,却又听不清说了些什么,词语列队而来。人们在谈论自己时,总是理直气壮地高谈阔论。月亮是一块黑曜石。我在露台上,就着月亮饮尽一杯又一杯红酒。
我们从大海边归来,继续隐身在庸常的生活里,一言不发。
围棋
他是我儿时的同桌。我与他再度重逢时,五一已经上小学了。是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青涩的季节,爱情也是青涩、美好的。他每次见了我都不好好吃饭,说是没胃口,不饿。后来我爱上了别人,满眼都是对方,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满心患得患失,辗转反侧。忽然就理解了他曾经每次与我约会时的食欲不振。
兜兜转转多年,我们早已经有了各自的爱人。我却还记得他当初说的话:“谁都没有我好,谁要是和我相处不好,一定是别人不好。”这是他幼稚的执拗。哪里有什么好与不好之别?喜欢就是好,待到不喜欢了,再好也是不好。他依旧深情款款,但深情没有放对地方,终是错付。我们是对方眼里的风景,远观郁郁葱葱气象万千,近了却总显得有些与之格格不入。
他带着女儿、我带着五一去参加围棋升段赛。他女儿比五一小一岁。两个孩子下棋,我们就无所事事地在外面候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人生。操场上一群蚂蚁忙着往洞里搬运食物,一刻也不停歇,似乎它们从来就不知道消极怠工。其实此时看起来,我俩倒也算是同一类人,我俩要是成了家大概率也会如这些勤劳的蚂蚁,一心一意地顾念家,顾念孩子。
女孩子棋下得势如破竹,凯歌高奏。五一却连输了两盘。他笑着警告五一:“你再输就可以回家了。”五一又输了一盘。他笑着说:“完了完了,你全赢了也没用了,升不了段了。”五一的脸一点点阴下去,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下来。五一委屈得抽泣,后面的两盘棋,他说什么也不肯再下了,全赢了也升不了段了。我只好带着五一先坐车回家。五一委屈地哭了一路,进家门上床就睡了,没有吃晚饭。之后的一个星期,他没有提“围棋”两个字。我小心翼翼地绕过桌上端端正正摆着的围棋棋盘,假装视而不见。原本五一每天的消遣就是左手跟右手下棋,上桌打谱。
一周之后,五一继续下棋。之后,每次升段赛前报名,我都小心地和我的男同桌他们错开场次。我和五一提前讲好,无论输赢,都要下完最后一盘,否则就不报名。
那次围棋比赛之后,我与我的男同桌相忘于江湖,不复相见。
时光就是一列奔驰的火车。五一考上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学医。我的男同桌兴奋异常,在微信里缠着五一说话。五一告诉我,高考成绩公布了,我的男同桌告诉他,当年和五一一起下棋的他的女儿考上了清华大学。我在微信里呼我的男同桌,说:“儿子忙,咱俩聊一会儿。”他说:“女儿全省第十八名,考上了清华,打算和五一一样,学医。”他问我,“你说,如果当年我们在一起了,会生一个去哈佛或者牛津读书的孩子吗?”我大笑说:“也许我俩在一起,我们的孩子会是学渣,还是算了吧。现在这样挺好,培养出两个名校的孩子,多赚了一个。”
还记得当年我们分手的那个夜晚,下着毛毛细雨。我们聊了又聊,像是要把能说的话一次都说尽,我们在雨里绕着操场转了一圈又一圈。月亮清冷得像块冰。他问我他哪里不好。我承认他很好,可我固执地说,他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他问我想象中的他是什么样子,他可以改。我忘记我是怎么表述的了,大概说来说去就是那种指鹿为马的强求吧。我冷得牙齿打架,他的神色在月光下看起来越来越绝望而沮丧。终于谈清楚了,我们拥抱,告别。多年后他告诉我说,我的身体和那个夜晚一样冷而硬。他没有纠缠不放,他说走就走了,像水渍,渐渐地干了。
多年后的这个夜晚,他欣喜若狂,他压抑不住地想要有人和他分享喜悦。几天后,我正在忙。有好朋友忽然打来电话,说男同桌在英国留学的儿子发表了一篇论文,收到了一万英镑的稿费,牛津大学的导师给他儿子电话,邀请他儿子去牛津硕博连读……
好朋友问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生活原本就是一部《天方夜谭》。一天一个故事讲下去,听的人和讲的人有谁知道哪个故事是真哪个故事是假?
华西、清华、牛津,接下来该是剑桥?
离家出走
整个初中阶段,五一是叛逆的。男孩子们天天凑在一起不回家,隔三岔五打架。我对五一的要求越来越低,只要他不出门,老实待在家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学习反倒是没那么重要了。那段时间,是五一的青春期。
五一学校有食堂,可是他中午时不时溜出校门在外面吃饭,因为外面的饭馆有无线网络,可以上网。有一天回家,在楼下远远看见他骑在窗户上,我吓了一跳,狂奔回家。我家可是八楼啊!进门后发现他早就下来了,连窗户也关得好好的。我问他刚才在干什么,他半天不肯说。后来才明白,因我申请停用了家里的宽带,于是他用万能钥匙软件破解了隔壁的宽带密码。我看见时,他正骑在窗户上用手机联网打游戏,那是信号最好的地方。
青春期的孩子打不得、骂不得,我只好反反复复和他谈心,谈到词穷。家是什么?在他眼里,家是多余也是限制。他总是做各种坏事,爬墙上树,踢球砸玻璃,甚至把操场刨出坑来,说是挖蕨麻。
五一中考前,曾经离家出走。说起来老套,他在家给我留了一张字条,说他走了,不回来了,请我放心云云。我当然放心不下。满街找,在周围漫山遍野地找,发动老师和同学一起找,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找到五一的时候,才知道他和一个同学根本就没出学校门,而是蜷缩在学生宿舍里。这次捉迷藏他们赢得彻底。问他待在人家宿舍里干什么,他说在自学。一点儿创意都没有,和在教室里上课有什么区别?我受了惊吓,找到他时反而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惊喜,没有想起来要揍他。他回家那天,不像是离家出走归来,反而有点像凯旋的英雄般,我不由自主地煮了一桌子菜。
五一回家后的第二天,就是中考。分数公布后,我意外地发现他可以进这座城市最好的高中。那个暑假,他被特许可以自己安排。打游戏或是去旅游,由他。
五一上了高中之后,一切渐渐恢复正常,他的青春期终于收尾了。我松了口气,可以不用整日竖着毛和五一斗智斗勇。和孩子的战争大概率都是父母输,因为绳子扯到一定程度,怕他受伤,一定是父母先松手。
别人家的孩子
五一儿时有个同学,叫冯山齐。那孩子长得粉妆玉琢,学习好,又是班干部。虽是男孩子,可是他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放学了也不趴在井盖子上和别的同学打牌。在路上遇到我,能和我聊着天一路走回家去,说话也是规规矩矩的,很懂事。
五一最痛恨我的口头禅——“你看看人家冯山齐……”五一听了黑红着脸说:“你给他当妈妈去吧。”五一听不得我盛赞冯山齐,但不影响他和冯山齐是好朋友。学校文艺演出,冯山齐带着五一上台说相声,他是逗哏,五一是捧哏。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五一从小到大唯一一次上台表演节目。老师让家长去学校帮孩子化妆。那次,我见到了冯山齐的妈妈,我对她的日常充满好奇。养育冯山齐似乎用不着极大的耐心,他会与你站在同一立场,不会拒绝你走向他的通道,而我与五一的沟通简直就是死路一条。演出按时开始,漫长的等待之后,我给他们录制了视频。于是,五一呆瓜憨豆和冯山齐冰雪聪慧的样子就这样存贮在了我的电脑里,一直未长大。
五一非常抵触我对冯山齐的偏爱。正在开花的季节,骤然在枝头看到一枚早熟的果子,的确令人又惊又喜。冯山齐的优点是他的才能和爱好与家长和老师的期望高度吻合,他收放有度,微笑的弧度都恰到好处。而五一,永远不守规矩,各种投机取巧,能明天做的事,一定拖到最后一刻,整日和我斗智斗勇并乐此不疲……细细环顾左右,日日苦恼的妈妈居多,五一这样大概才是常态吧。冯山齐是一朵奇葩,他太像孩子们中间的成年人。
我一边苦恼,五一一边长大。我陪五一去中考。孩子们久久不出来。天是一整块的蓝,气温热辣焦灼,学校在黄河边,好在那天的风自西向东刮,顺风顺水。考完试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外涌出。有一个孩子和他的父亲走在一起,一看就是父子俩,模样差不多,可是他的脸仿佛比他父亲的脸还要老气几分,黑且沧桑,反倒是他父亲的脸上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稚气。接着看到混在人群里的五一。还没考完试,我不敢直着问五一考得怎么样,就指指走在他前面的那个孩子,问:“那是谁?”因为是他主动和我打了招呼,一定是五一的同学无疑。五一抻长脖子看看说:“是冯山齐啊,你不是认识他吗?”我吃了一惊:“他怎么就长成这个样子了?”五一说:“怎么了?”我停顿了一下,说:“他长得,嗯,脸长,像马。身子比腿长,像兵马俑。”五一说:“妈,你不厚道。”
五一和冯山齐一起考上了这座城市最好的高中。去往罗马的路从来不止一条,但是他们在罗马会合了。五一呼朋唤友联网打游戏,他开着语音,一个人就可以让家里热闹非凡。五一说他不是在打游戏,他是在社交。我不再勉强他,他在我眼中的出格,或许有他自己奇怪的道理。偶尔他也会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静坐,说是在冥想未来。我不再频繁提醒他不要浪费时间。谁也不是谁的救世主。
我和五一坐下喝一杯,用对待成年人的方式,请他为我们的生活添砖加瓦。亲历的、逾越的,不消说什么错误,由他去吧。我安静地看他走过烈焰或是蹚过激流,就算有魔鬼在他身后亦步亦趋,我也只能等待,等待他自己驱逐。
冯山齐在高中负责校刊的编撰。因为我在报社工作,他便频繁地联系我,让我看发刊词,帮他把关。他收集到年级每个任课老师写下的祝福语,他还邀请我参加首发式并讲话。他提的要求我尽全力支持和配合。首发式那天,一群燕子掠过教学楼,划出优雅的弧线,我在低处,望见它们露出乳白的胸脯。冯山齐邀请到校长发表了动人的致辞。那天,整个年级的孩子聚拢在阶梯教室里。冯山齐有很旺的人气,当他上台发言时,孩子们跺着脚,发出一阵阵欢呼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此时的冯山齐,周到得如一个立体的圆,你看不到丝毫的破绽。校刊首发式上,我见到了冯山齐妈妈,他妈妈焦虑地说:“孩子这么忙,哪有时间和精力学习呢?”我安慰她说:“这只是一段时间的工作,结束后就会回到学习的正轨上。”他妈妈叹着气说:“但愿吧。”
高考时,我依旧陪考。在酒店旁边的超市遇到冯山齐和他妈妈。我们笑着互相问候。我说:“冯山齐啊,你可养胖了,该减肥了。”他说:“是啊,是啊。”他的肚子如中年人般挺了出来,有种不合年龄的老气横秋,他的脸还保持着兵马俑般的沧桑。随着时间的推移,男人大概都会成为这个模样,可是他有点儿太早了。
我确信无疑的是,冯山齐的妈妈望向五一的眼神,一如当年我看冯山齐时那般。此时的五一,看起来挺拔俊朗,温和懂事。
夏季的傍晚,风热烘烘地吹着,世事难料。
华林山
我该怎么说华林山呢?那里有没有暖气的矮楼、屠宰场,大大小小的食品加工厂,还有烈士陵园和殡仪馆。那是我失去了亲人的地方。我为父亲挑选了船形的骨灰匣子,乐队隆重,小号尖叫,鼓声厚重得仿佛是在说“走吧,走吧”。父亲离去,我的生活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当。我仿佛是在华林山长出自己的第一道皱纹,那是愁苦在脸上留下的印记。
父亲毕业于医学院,他擅长画画,他的解剖图画得恰到好处,顶骨、额骨、蝶骨、眶上嵴、眼眶、颞骨、鼻骨、泪骨、眶下孔、颧骨、梨骨、鼻脊柱、上颌骨、下颌骨、颈椎……父亲知道太多人体器官、骨骼的秘密。
父亲寡言而严厉,我小的时候很怕他。我们家有一条完整的生态链,我怕父亲,母亲宠着我,父亲又事事迁就母亲。我那时精力过剩,没有午睡的习惯,可是父亲要求我必须午睡。他不跟我多说一个字,他只要我听从。他让我同他一起躺下,拉着我的手,让我乖乖闭上眼睛,不许说话也不许翻身。现在想来,我依旧无比痛恨那些被迫睡眠的时间。
为躲避午睡,坐在饭桌上我就开始渲染我有多少作业,一吃过饭我立即假装懂事地抢着去洗碗。我洗得无比仔细和缓慢,一直到父亲睡下我才洗完,接下来我就无比认真地坐在书桌前开始学习。我成功地摆脱了那令人绝望的午睡。父亲也好久想不起来让我睡午觉了……我一向都知道,父亲喜欢听话的孩子,他想把我关在笼子里,如同关一只被驯服的鸟。可我总是拼命挣扎,就算是弄断了羽毛,拉伤了腿脚,也要从木栅栏的空隙里挤出来。我从来就不是能关得住的鸟儿,除非将我用长钉钉在笼子里,这又是父亲无论如何也狠不下心来做的。我和父亲的斗争硝烟弥漫,从来分不出胜负。
五一骨子里比我更叛逆。我渐渐理解父亲了,而父亲开始频频输给五一,他似乎再没有赢过。书包放在大门旁的柜子上,父亲看着五一穿鞋,他帮五一拎着书包,站在门外等五一。他对我说,出去就把书包给五一,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我从窗户看着他们一直走出院子,书包还在父亲的手里拎着。
父亲和五一下棋,得毁掉一个车,再杀掉一匹马,每赢一盘就得想方设法再输给五一两盘。有时候忘记输棋给五一,五一便断然不肯继续下了。父亲和五一下棋,得费尽心机地让五一赢,赢得无比婉转,我看着都辛苦。父亲把这辈子生长出来的耐心都用在了五一身上,小小的一盘棋,布阵是未雨绸缪,他引导着五一早早看透楚河汉界,看透纵横开阔的战事风云变幻。有没有天赋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完成目标你就得向着同一个方向行动。须臾间,刻不容缓,五一渴望看到将帅的荣光。
“倒要瞧瞧你能想出什么法子来。”父亲总是这样说。五一舔着嘴唇左突右冲地尝试。父亲赞叹:“对,你这个法子不错。”于是照此继续走下去,走不通了也可以复盘再来一次。父亲笑着问:“你害怕了吗?”五一斗志昂扬地试了一次又一次。有时候,翌日一早再复盘一次昨天的,父亲任由五一来回折腾。
我常常费解,我父亲和五一的姥爷是同一个人吗?
人的身体有许多密码无从破解,父亲因感冒用药过敏,匆匆离世,没有逗留。我将一本新出版的书在他的坟前烧掉。我想他一定想知道我在书里写了些什么。父亲总是很认真地读我的文字,一个在我眼里沉默寡言、无比刚硬的人,读我的书会潸然泪下。
我渐渐地积攒起了许多朴素的生活哲学,父亲离开后没有人帮我验证对不对。我夭折了许多梦想,我一面执着一面学习放手。我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父亲永远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是他告诉我,我最重要。我永远是他最宠爱的孩子,虽然他从来不说。
有了他的宠爱,我就什么都不怕。我曾经为一个新闻选题在华林山上卧底了数日。我们昼伏夜出,每到夜晚就在华林山一个个巷道地搜索。我们寻找得辛苦,偌大的一座山,我们如沙里淘金,恨不得自带超声波,如蝙蝠在暗夜里精准定位。清冷的夜,凌晨没有风,苍穹显出月朗星稀来。这一天是二十四节气的冬至,这个年度的最后一场流星雨——小熊座流星雨如期而至。冬至撞上流星雨,这原本应该是我人生中最为温馨、浪漫的一幕,而温馨、浪漫之前,是痛彻心扉的伤害。
华林山在我眼里,是一条狭窄的通道。父亲离开后,我整理东西时,柜子里翻出父亲很多从未上过身的新衣服,他每次都说放放,先穿旧的。现在它们永远是新的了。家里沉寂了许久的橡皮树忽然生长出新的枝丫。
这座城市在华林山烈士陵园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我写下纪念兰州解放七十三周年的朗诵诗。烈士陵园里一群人被另一群人纪念和唤醒,朗诵的少年嗓音清透如清晨,没有烟尘也没有感伤。
我从高箱床里翻出那张卷放着的鞣制处理和拼缝过的狗皮,它大而厚实。它是父亲买回家的,但却从来没能派上用场,母亲总是嫌它铺在床上不平整,只好收起来。每年我会定时取出来晾晒后再裹了樟脑收起来。我将它挂在墙上,再回家时,迎面与那张硕大的狗皮相遇,它耀眼夺目得如同徽章一般,显然它找到了更适合它的位置。而我像与它第一次相遇。
华林山殡仪馆,巨大的烟囱肃立,可怕的鼻孔张开。黑夜和白天交替到来,悲伤想和欢乐换班。有人骑着摩托车,发疯般冲下山坡,逃离一般。
【作者简介】王琰,女,《兰州晚报》副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曾参加第三十二届青春诗会。作品散见于《天涯》《散文》《诗刊》《星星》《山花》《红豆》等刊物,并收入各种选本。出版有《格桑梅朵》《天地遗痕》《羊皮灯笼》《崖壁上的伽蓝》《白云深处的暮鼓晨钟》《兰州:大城无小事》《庄严的承诺》等多部。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