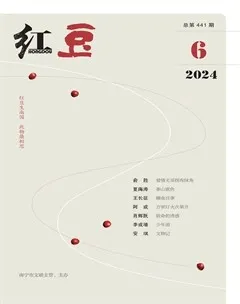阿克苏的风吹拂着
常常从梦中醒来,或写作后翻来覆去依然睡不着,孤独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一缕灯光就像一只船悠悠地驶入想象,伸手可及的天山就像张开的风帆,拽着船驶向阿克苏。
阿克苏对于我来说,印记是相当深刻也是难以忘怀的。特别是当我在字里行间走近它时,竟然感到人生的境界与阿克苏也有关联。想象中的船盛满这样的话题。尽管我从未攀登过天山,但可以想象出来,船航行于天山脚下,春风就成了今年的好兆头。
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环境,甚至刚刚走下飞机,脚踏上这片土地,心便坦然起来,仿佛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期待着来自远方的浏览和阅读。静静的夜色下,早已沉入梦乡的我,在多浪河的水声里,白天的旅途疲劳就这样渐渐地缓解了,梦中想象的船会继续前行。
远方的阿克苏令我沉醉和向往,我对它迷恋已久。缱绻于思念之中,陶醉于渴望之中,天山脚下的大美便在于此,同时道明这座西部城市的与众不同。我有意放慢脚步,静静地观望这座城市。街道上人来人往的生活节奏,是我最羡慕的,那么悠闲、轻松,就像多浪河的水流缓缓而去。思念的形状与其说是飞过天山的一只鸟儿,不如说是这里的似乎在阳光下燃烧的大峡谷,抑或是日夜歌声不断的响水河,当然这只是我心里想的。说起来思念比飞机的航行速度快多了,眨眼就到了天山脚下。可以想象天山脚下的梦,尽管是寒冷的,但这里的景色飘浮在梦里,八千里外的这个深夜,我依然感受到了阿克苏的热情和温暖。
在我的书房里,我的人生陡然缩小成了几行文字展现在眼前。激情昂扬之时写作的情绪犹如滔天波浪,起伏跌宕,犹如悬浮于天穹与大地之间。为了捕捉人生最灿烂的那一瞬间,或最痛苦、最寂寞的那一时刻,我依然漂浮于生命的大海之中,且时常告诫自己:“生命不止,写作不止!”
活着的生命几乎浸透了墨水,心灵的制高点依然是风雨中高高扬起的风帆。在我曾经走过的路上,各种各样的困难罗列起来可以排成长长的一大串,其中有许多均已被我彻底克服。唯有写作这个梦始终停留在我的身边,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一九九三年的冬天,当我从病床上强行支撑起身体时,即使面对眼前的一切现实和困惑,也依然扬起写作的风帆。如今我已是年近六旬的人了,仍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向西—向西—阿克苏就是我此次航行的归宿地,就是天山无声的召唤。
为什么感觉阿克苏伸手可及?为什么它常常闪现在我的梦中?无论八千里之外,还是梦幻之境,这种创作上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当我二〇一九年元月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尽管天气很冷,但我依然感受到了阿克苏的温暖。在我下榻的地方,多浪河紧紧地拥抱着我,浪花飞扬,就像众星拱月一样。这里的植被长势很旺,令我欣喜不已。
多浪河是由天山的雪水融化而成,河面很宽,河水清澈,并时时散发着天山的雪水味道。在河的对岸,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感觉是暖洋洋的,似乎已经驱散了周围的寒意。遥望西边隐隐约约的天山,我发现自己曾经的一个梦里我就依偎着多浪河。看到这儿,我侧身来到一棵树下,躲藏在一朵花蕊里。这些花瓣虽小,但它们却意味着人生的美好。或者就像一只小船,载着我驶向“归园田居·塔村”及天山托木尔大峡谷……
我已经无法将它们从视线里移开了。在这些景点之间,我就像一阵阵风儿吹来吹去,犹如飘浮在美好的传说里。塔格拉克大草原上,风在呼啸,雾水打湿了脚印。山头上的草原鹰,在冲向空中的一刹那,长长的大翅已把天空遮挡。寒冷填满了峡谷草原,雾气沉沉,只有山顶上可以看到一些金黄,那里的阳光确实暖着我的心。此时此刻,我仿佛已经触及了天山的深处……
自二〇一九年元月以来,我数次到阿克苏,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有时也会突发奇想:“阿克苏的存在是否就是一个奇迹?它究竟是人间仙境还是真实存在?”我不得而知。我曾以一个探险家的目光审视阿克苏,感受阿克苏,领悟阿克苏,我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走近阿克苏,不敢轻易惊扰。
年轻的时候,我就十分向往新疆,先后去过乌鲁木齐、昌吉、奎屯、石河子、塔城及额敏县。那时我还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是趁着暑假坐火车过去的。当时的出行条件还不方便,仅在绿皮列车上就用去了三天两夜的时间,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可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很辛苦,一路上都是满怀着好奇心挺过去的。
二〇一七参加年新疆兵团文联笔会的时候,我再次跨上这片疆土。笔会期间,我先后来到天池、喀纳斯湖,以及新疆卡拉麦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等地采风。真的没有想到,年近六旬之时,我又有幸踏上阿克苏这片神奇的土地,就像我年轻时那股闯劲儿一样,今天的风采劲头依然不减。
阿克苏时常会给我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正是我逐步认识阿克苏的好机会。随着认识的深入,我渐渐地发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之处:只要一来到阿克苏,我仿佛就不能自持。换一句话说,就是自己已经做不了自己的主了,脚步无论停在哪里,那里的风土人情就会牵引着我的情感,使之起伏跌宕。或者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我就是一阵阵风,来到天山脚下徐徐地吹着、吹着……
看来今生我已别无选择了,阿克苏既然是我不离不弃的第三故乡,那我明天就会远航。其实梦里的船早已驶向了阿克苏,船虽小,但船舱里盛满我的思念。也许可以这么认为,思念就像风一样推着我。即使船漂浮着去了远方,我依然能够操纵它、驾驭它、控制它,并及时调整船航行的方位,向西—向西—向着阿克苏出发。既然思念的船儿已经驶向阿克苏,那它就不可能再回头了。因为这样的思念,已经适应阿克苏的环境、气候以及天山脚下的牧场生活。
托木尔峰上的狂风暴雪吹来的时候,也许这一艘船的风帆会涨满天山的力量,并驶向峰顶。当然这是梦中的一次远行,船迎着风雪矗立山巅。或许只有这样的美好想象,才可以完成这一次英雄般的壮举,胆量、胆魄,哪一样都不能少。纵然在今天看来,天山脚下的船,确实是在看不见的冰雪海洋上航行。上百次、上千次的航行,每一次相见依然都有新的感觉和感悟。天空中传来一声声鸟儿的欢叫,梦中的相见尽管很短促,但令人难以忘怀。
先后八次入疆,时间的跨度已是三十三年。每次到新疆,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只船,时而畅读和田河,时而流连红沙河,时而泊在塔里木河,时而漂荡在阿克苏河,时而触摸托什干河……
晚风吹拂,玛尔浆湖湖面上波光粼粼。特别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奔腾的浪花显得异乎寻常,灿烂至极。今夜沉醉于湖水的遐想里,宛如一尾鱼,感觉今生再也离不开这一片热土了。换句话说,一旦离开这片土地,我的创作也许就会干涸、枯竭。坦率地说,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见到阿克苏了。这段时间里,思念的船停泊在淇河岸边,事实上就连风都按捺不住了。风儿把我从思念中唤醒,在我周身上下狂吹不停。其实,这样的日子看起来风平浪静,周围的一切也是那么安宁,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风起云涌。我常常扪心自问:“一个热爱阿克苏的人是应该继续停泊在淇河岸边,还是应该扬帆起航向西航行?”这不仅仅是一些想法,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心理反应。迫切的渴望在我身上荡来荡去,始终没有消失过片刻。在我垂垂老矣的今天,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依然没有第二种选择,这便是我一生坚定而崇高的信仰。
我何时才能再见到阿克苏呢?阔别已久的天山是否安然无恙?这并非一个多么令人头疼的问题,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当我的脚步渐渐地靠近天山时,向前的信念,也就是征服第一高峰托木尔山峰的欲望愈来愈强烈。离别的时间里,满脑子都是它可爱而且俊俏的模样。眼前高高低低的峰峦,犹如大海凝固的波浪沉默地奔腾而去。或者这样说吧,生命中的风帆因阿克苏而改变航行的方位,一路向西、向西,直到来到天山脚下才停泊靠岸。
去年秋天从阿克苏回来以后,我就一直琢磨这方面的素材,反复权衡该从何处下笔。在这之前,我创作了不少有关阿克苏的文章,但静下心来细细思量,总感觉还没有写透,或者说某个方面还没有写到位。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天山就已经闪现在我的文章里头了。云犹如一张信笺,上面书写着文章里头的一些思念。从中不难看出我在这里采风时一些踉踉跄跄的脚步。看来我与阿克苏的不解之缘,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当我把这些邂逅的感觉写下来时,我从这些文字中间,已经听到了多浪河哗哗的流水声……
如果从梦中醒来,我知道自己脸颊上会是什么表情。目光里写满“阿克苏”的字样,身不由己的我,已经彻底卷入向西的眺望中。当和煦的春风在生命里吹送时,窸窣作响的是天山的雪水融入响水河的声音,那么轻柔,那么欢快。大雁捎来远方有色泽的信息,捎来天山脚下塔村的邀请。这一切似乎与我无关,实际上又与我紧密相连。看来我必须从这篇文章里走出来了,跃跃欲试的生命似乎又重新回到过去,春天的风已将梦中的茫然涤荡而尽。思念的船又划到我的面前,和煦的春风徐徐地推送着我,船已经调整好了航行的方位,扬起天山力量的风帆,准备出发。
当船穿过天山绵延不绝的冰冷峡谷时,前方已经闪现出阿克苏的灯光。北山羊跑下山来,望着我这次出行的航线,指着远方说道:“前面就是阿克苏了!”草急忙凑上前来,也补充了一句:“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归园田居·塔村”了。这是一个天然的大牧场,响水河会带你去它日夜奔腾汹涌的地方。那是它已经征服过的,期待你的到来……”
我已经紧紧地握住草的纤手,并再次感受天山赋予的这些生命。我似乎已经触摸到天山那险峻的气息了,这样的气息在我身上注满阿克苏的活力和希望:千年龟兹城,神奇阿克苏,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天山脚下的神奇仙境,多浪河畔的灿烂童话,就像我内心深处的祝福和寄语。
阿克苏的风吹拂着,吹拂着……
【作者简介】田万里,河南鹤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诗刊》《中国作家》《长江文艺》《北京文学》《十月》《美文》《散文选刊》等报刊。出版散文集《兵马俑狂想》《青春的阿克苏》《沙雅沙雅》及长篇散文《阿克苏随想》,发表长篇生态散文《淇河》等。曾获吴伯萧散文奖、中国当代散文奖、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