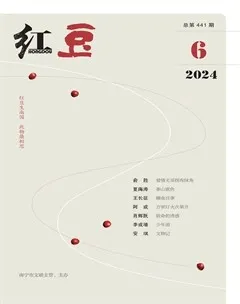致命的诱惑
黄蜂尾后针
一只大黄蜂沾得一身花粉,忽地从红蓼花上起飞,又“嗡”的一声钻到旁边的一棵黄连木里去了。
菜地边沿,我一共栽了六棵与人齐高的黄连木。当初选中这些黄连木是看它们四季常青,叶子和枝条吐司面包一般,揭开一层又一层。揭开十层以后,里面还有一堆枯萎的干枝落叶,估计这一堆下面还有十八层。如果有哪只鸟在这里面建一个巢,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鸟巢。关键是,先要能钻到树里面去。很遗憾,树已栽下一年,还没有哪只鸟儿有眼光,或者说有本事能在黄连木里筑巢。
黄蜂钻到黄连木里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这黄连木也不开花,它钻到里面干吗?我穿了有帽子的防晒衣,捡根长棍子轻轻挑开一根树枝。
一个南瓜大的黄蜂窝出现在眼前。这个窝很像礼花炮燃放后的空箱,所有的黄蜂都背对着我趴在窝上。我试图靠近去看一看,但我稍微一动,它们的后背就像长了眼睛,对我的行动明察秋毫。它们的翅膀开始扇动,细腰弹簧一样拱起。或许我可以像捏碎我脚边的土坷垃一样捏碎它们的细腰,然而大自然给它们的细腰配备了小巧而锋利的弓箭,且上面涂满毒药。“黄蜂蜇中一煎药,雷蜂蜇中一副木(棺木)”,要是被它们蜇中,不死也要脱层皮。我老老实实就地坐下,仰视它们。同为采花郎,黄蜂看上去就没有半点小蜜蜂的忙碌样子。有两只黄蜂警卫般站在巢边的一根树枝上,耷拉着脑袋打瞌睡。还有一半的黄蜂趴在巢洞边睡大觉。对于一只蜂来说,还有什么事儿比采花更有意义、更有乐趣、更甜蜜呢?
世界上恐怕没有比黄蜂追着你跑更惊心动魄的事了。我跨过一堆树枝,连着踢飞三颗挡路石,然后站在菜园的门口。我去解园门的绳结时,绳结被我慌慌张张一抽,竟然成了死结。本来那个绳结是我亲自设计的,无论从哪个方向去抽,都是一个活结,一抽就散。我一边对着自己打的这个结苦思冥想,一边双手乱舞。我的头上、背上有千军万马的进攻,一团又一团的黑影直朝我脸上扑来。
没有哪个女人不在乎自己的脸皮,一想到脸面问题,我立即双手捂脸蹲下。
一道电光石火般的奇痛,随着我敏感的神经,从我的右手食指传到我的脑部。随即我全身开始发麻、打战,眼前一阵发黑。我抱着头,感觉手指像吹着的气球在慢慢长大。一阵风吹过,一下就吹醒了我。
我一脚踢开园门,两步跨过菜园,三步就跃上地坪。“我中箭了!我中箭了!!”我一边高呼,一边从坐在门边正热烈讨论中美贸易战的一群人中跨过。在他们惊愕的注视中,我脱了外套朝椅子上一丢,冲进灶屋,将水龙头拧到最大,对着手指头猛喷水。我觉得手指就像一截燃烧的树棍,冷水一冲直冒热气。大家立即从“贸易战”中抽身,当过特种兵的陈强第一个抱着我的衣服冲进灶屋,连同粘在衣服上的一只黄蜂。有人冲上去将我的衣服踩在脚底。衣服被拎起来后,那只黄蜂变成一幅色彩明艳的油画印在我的衣服上。
抹酱油、抹盐、抹茶油、抹芋头茎的汁。都是乡村长大的几个人,大家的土办法多得很。在我那只肿成红萝卜大的手指上,随即用了好几个土单方。花露水!在大家的喊叫声中,婆婆终于搞清我是被黄蜂蜇了一针,于是举着打开盖的花露水递给我。于是我又抹了几滴花露水到手指上。我觉得婆婆的办法应该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亲眼见证过老人家洒了这个神水,才从 “猪八戒”又变回原形的。
像个期待在课堂上有出色表现的小学生一样,我一直举着右手搁在桌上,平生第一次用左手抓着筷子吃了一餐饭。饭后,手指逐渐恢复原貌,只是有点红而已,但开始发痒。戴了双手套,我又跑到黄蜂窝那里。我原地坐下,给它们拍了一张集体照。刚按两下快门,我的眼前又是一阵黑,它们冲出蜂巢来围住我。有了前面的教训,我双手抱头原地不动。黄蜂只是绕着我的头转了几圈,很快又飞回它们的巢。我这次并没有对它们吹风,也没有去揭它们的老底,为何它们还不放过我?后来一想,这不能怪它们。我手指上洒的花露水,有浓烈的花香,就像有一万朵花同时在向它们招手。你说它们生来就对花敏感,哪能受得了如此刺激?我连着往后退了几步,退到红蓼花旁,我发现红蓼花上也有好几只黄蜂。正在采花的它们,好像已经忘记我曾是它们巢穴的侵略者,对我的一再靠近很大度,全无半点儿张牙舞爪之势。与围攻我时的形象相比,它们现在都是彬彬有礼。也许在它们眼里,巢穴是它们的家,容不得任何外敌入侵。而花,是属于大自然的,属于懂花的那个人。大家都是自然之子,和平共处,才能保证都有花采。单就它们对花的态度,如果站在花的角度来说,花肯定更欢迎这样的访客。它们个头大,不但可以做到脚踩两朵花,还可以左拥右抱。它们对每一朵花都一视同仁,就是在一朵残花面前都表示其惯有的热情,没有半点儿嫌弃,直到那些残花完全凋零落地或变成种子。
人类都喜欢小蜜蜂,因为可以尝到它们酿的蜜。而黄蜂,就我的朋友圈来看,还没有谁有那个荣幸,或者有胆量尝到它们的甜头。倒是它们的肉身,有很多人尝过其味道。大家都建议我点火烧掉黄蜂的窝,以免后患。犹豫中传来新哥被黄蜂蜇中的消息。
每天午后,总有三四个邻居跑到新哥家玩纸牌。这天大家正玩得开心,一只黄蜂飞进客厅,不由分说对准新哥的脖子狠狠蜇一口。黄蜂找他下手的原因,应是他身上独特的气味。他身上有草的青气、鱼的腥气,还有烟气、酒气。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一般老农极少有的花香气,可以说是酒色财气集于一身。不找他下手,找谁呢?
到底他皮肉厚实,被蜇后皮肤不红不肿,只有点儿痒,抠两下就没事了。兰姐被吓着了,连声责怪新哥名堂多,在房前屋后种了五十多种花,他只要一有空就扎到花堆里不出来。现在好了,招蜂引蝶,引一只黄蜂来蜇自己。两口子在花里找来找去,找了一堆蜘蛛窠出来,连黄蜂窝的影子都没捞到。这一日兰姐打开玻璃窗,一抬头发现在玻璃窗的角落有一个茶杯大的黄蜂窝。兰姐一声令下,新哥举着长扫把就准备上战场。想了想,穿上长筒雨裤,再戴上一顶烂草帽,长扫把一捅,来了个强拆。“轰”的一声黄蜂炸了窝。长扫把再次朝蜂巢捅了一把,飞出去的黄蜂急急忙忙又跑回来,有几只趴在巢上死不松手,还有好几只紧抓着扫把,好像在哀求:“大哥,放过我们吧!我们再也不蜇您了。”现在哀求已来不及了,“啪”的一声蜂巢掉地上,原来的旧址上只留下一抹泥黄色的印记。黄蜂们立即扑上去,在那个残留的印记上踩来踩去。
我准备留两棵黄连木作纪念,余下的几棵都送人。但信息发出去一年多了还没人有意向。至于那个黄蜂窝我一直没有去动。新哥捅黄蜂窝的那个场景将永远烙在我脑海中,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强拆的帮凶。黄蜂窝是黄蜂家族奋斗史的一个标志物,就像我老家那顶挂在墙上已经五十几年的烂蓑衣。母亲一直没有扔掉,只因那是农耕岁月的一份怀念、一个见证。
遭遇野猪
山里的空气向来香甜,今天早上却有股臊气。路上一无牛,二无羊,不晓得臊气是从哪里来的。
老刘是前任村支书,带我到山里找野菌。人越向山上走,臊气逼得越近。山中美鸟无数,偏偏黑鹎和白头鹎两个顶着苍苍白发,老是跑到我们前方大喊:“小心!小心啦!!”难道前面还有老虎不成?这时天已大亮,山间小路还有些许昏暗。转过一个山角,我左前方二十米左右,灌木丛中突然窜出一个巨大的黑影——野猪。
老刘落在转角后,不见踪影。说实话我不是不怕野猪,而是见到野猪的喜悦已完全压制了恐惧。况且我现在处在它的下风头,它难以闻到我的人气。它现在正专心致志地在灌木丛中翻腾,看样子有三百来斤。颈上的鬃毛黑而粗,根根竖起。身上的毛色稍浅,上面挂着的一串串泥巴坨,让人想起一身金银珠宝的暴发户。
相比其门板一样宽厚的身躯,它的耳朵就长得有点儿小气,小气得像发财人家豪宅装的监控器。这“监控器”不只小还意外透明,上面没一根毛,透着一股哑光,干净得令人意外。看起来它长嘴巴翘起来真像一架铁犁。它在壕沟里弄到了半包槟榔,将那半包槟榔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然后挑了一个囫囵吞了。接着它眨巴着小眼睛,哼哼几声,尾巴弯举到半空,给槟榔打了个问号。问号慢慢拉直又变成一个惊叹号,接着它的前脚咕咚一声跪下半截,槟榔的后劲来了。它一边嗷嗷叫,一边往壕沟两边放肆地“犁”。那架“铁犁”挂着一把茅草、一串野果、一个矿泉水瓶、半包槟榔及半斤黄土。
完了,它要发“宝气”了。野猪在两种情况下会发“宝气”,一是当公猪为爱情而战,战败之时,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它的情敌;二是母猪生了小崽,一切看到它小崽的东西都是它的死对头。
很快,我就发现错误地高估了自己在野猪心目中的地位,我既没有资格做它的情敌,也不是它的死对头,更不是它无聊时玩耍的对象。
它的眼里只有鼻子上架着的那一大堆东西,它在为自己今天早上的收获而眉飞色舞。它一会儿丢下食物躺到壕沟里打几个滚,一会儿又奔上来将矿泉水瓶拱到路边,仔细查看了水瓶上的标签后,吧嗒一脚踩得粉碎。它大概也觉得用瓶子装水是多此一举,山中的泉水都免费让它喝的,还可痛痛快快泡个泉水澡。接着它一口茅草加一口野果混在一起大嚼起来,显然它对食物的味道很满意。
趁它嚼得如此有兴致,我便斗胆往前挪动几脚,我想再靠近一些去细看它的尊容。然而刚一挪脚它便发现了我。它连头都没抬,丢了东西拔腿就往山坡上狂奔。
我所幻想的所有惊险、刺激的画面通通落空。它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我往山上追去,山坡上有几泡野猪粪冒着腾腾热气。再往前追,灌木丛里散发出一阵浓烈的臊味,估计是它刚刚撒的尿。
老刘跟上来后,我把猪粪的照片给他看,他激动得语无伦次。他活了五十多岁,只听说山中有野猪,这次终于看到照片了。他对着那堆猪粪反复感叹,仿佛那不是猪粪而是一堆元宝。
与蛇为邻
没有路灯,没有林荫道,黑压压的稻田中一长溜弯弯曲曲泛着白光的便是马路。
我、细叔和新哥相约一起去散步,才到马路上,细叔的手电筒就扫到一条火链斑。我让细叔用手电筒照着火链斑,不要让它溜了,自己赶紧跑回去拿相机。
返回一看,火链斑还趴在原地没动。细叔一手举着手电筒,一手举着一块红砖,而新哥手头扬着一节光树棍。这时候满天的星光洒下来,路边的草丛也挂上了一层水霜,加上细叔的手电筒光,在火链斑的四周便笼上了无数斑驳的光点,这些光点映在它的背上,像是给它穿上了一件华贵的花衣裳,这让我想起某个著名的奢侈品牌的包包。这同时也暗示着,一切象征时尚、财富与地位的名贵包包也有着毒蛇一样的意图,只不过,一个是想夺人钱包,一个是想夺人性命。
以颜值来说,火链斑绝对算得上一条“美女蛇”。被美女蛇攻击过的,虽说不至于要命,但那火辣辣的滋味绝对也会让你下半辈子都记得。
它的头开始摆动了,咝咝咝地朝我们连连吐舌头。细叔的红砖举过头顶,新哥的光树棍抄在手心。“慢点儿!”我大喊一声。我发现蛇的嘴巴张开时,嘴里满是血丝。新哥也说这蛇张开嘴的势头不对劲,看上去是在吓唬我们,向我们示威,但明显看得出,它张开嘴时很费劲,更像是在打哈欠。我们猜可能是晚上气温低了,它动起来费劲,也可能是受了伤。细叔的手电筒光来回扫了蛇身三遍,并没看到有明显的伤痕。我们便都退到一边,让它自己横过马路。我念了一句:“唵嘛呢嗄条蛇,唵拿噶放心过。”我希望它能听懂我念的“经文”。
这条“经文”是福姐教我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福姐和德哥两口子在道林镇上做肉鸡生意,租住在道林镇麒麟山半山腰上的一户农家。麒麟山上历来有一个大蛇洞,这些蛇有麒麟护体,一直也平平安安,没想到哪日还是被某个青年哥哥挖了蛇洞。福姐两口子还有屋老板收工一回去,整栋屋五间房子里全是蛇:屋檐、房梁、阶基、鸡窝、灶膛,甚至床铺上都是,估计它们是跑来避难的。附近群众闻讯赶来捉蛇,屋老板一把锄头挡在门口,说:“哪个要捉蛇,先问我的锄头同意不同意!”好,蛇倒是没人来捉了,只是睡到半夜,不时有几条冰凉凉、肉滚滚的东西爬到你身上,想要你给它温暖。这份爱心还是需要有相当心理素质的人才敢奉献的。于是屋老板到处找能赶走蛇的人。寻来寻去,邻居中有四川来的老太,烧了几张纸钱,装了一碗水,端着碗,念几遍“经文”,那些蛇就排着队回山上去了。
我念了三遍“经文”,那条蛇仍是不动,看来是我的功力不够。最终还是新哥用棍把它撬到路边。奇怪!新哥说撬起那条蛇的时候,像撬一根树棍,硬邦邦的。“它装死咧。”细叔说。
第二日上午十点,我特意跑到昨晚发现火链斑的地方去看,结果发现它还是原样躺在草丛里。我用树棍拨了拨它的身子,它一动不动。再一细看,它的头部有一个鼓出的红色肉疙瘩,看来是受伤了。而它的肚子鼓得老高,估计里面是一只尚未消化完的老鼠。它的如意算盘可能是吃完这只老鼠后就钻到洞里去,美美地睡上一个冬天。
自从散步碰到蛇后,我和蛇差不多就成了亲戚,走到哪里都碰得到亲戚。这不,这天早上我推开灶屋门,屋中竟然盘着一条白节蛇。我做梦都没想到屋里会跑来一条剧毒蛇,看样子它是从我开着的窗户钻进来的。这样突如其来的碰面,双方都很尴尬。我的一只脚已跨进灶屋门,我是进也难退也难。进,它肯定会攻击我;退,它会追着我跑。
我手里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武器,只好站着不动,期待它良心发现,知道我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它是没有权利待在这里的。一转眼,我又发觉自己似乎错了。可能我建这栋房子前,这个地盘是它的也说不定。白节蛇和我对视了一会儿,可能也接收到我眼神里的警告信号,它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或者更准确地说像一个被冤枉了的老实人,不小心闯入某案发现场,但又口拙不晓得如何分辩。它慢慢把头低下去,带着满眼的羞愧恨不得钻到墙洞里去。可惜墙没有洞,它最终还是从窗户那里爬了出去。
它临走前回头瞅了我一眼,眼神温柔得像窗外的曙光。那一刻我真是羞愧无比,钻墙洞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它。自始至终我都恶狠狠地瞪着它、防范它,都在想着要如何结束它的生命。而它进来完全是出于本能。它以为那窗户是我们特意为它开的,要请它这个高手来捉老鼠。说实话我家老鼠的规模,在整个大屯营的猫界都赫赫有名。我感觉自己欠白节蛇一个人情。
晚上睡到半夜,新哥家的狗不停狂叫,声音一直绕着围墙打圈圈,最后定格在那棵刚栽下的大樟树上。坏了,家里来小偷了。公公背了锄头,我拿把长菜刀,爷儿俩猫腰摸至院中。借着月光一看,大樟树上果然有动静。“哪个?出来!”公公将锄头朝空中一抡。“唰——”一条白节蛇倒挂着身子从树叶里冲出来,吓得我连退三步。
新哥家的狗本来对蛇还有点敬畏,看到我们出来便增添了无穷的勇气,双脚一蹦就要跳上树去将那身蛇皮扯下来。白节蛇不敢恋战,顺着樟树往菜园逃去。公公还要去追,我说:“算了,菜园里黑咕隆咚的不要被蛇咬了。”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婆婆经常说鸡窝里的鸡蛋少了。其实我知道,是白节蛇和我们共享了鸡蛋。不过它也还够义气,临走时蜕了一身雪白的衣裳挂在鸡窝顶上当纪念,顺手将盘踞在鸡屋里的一窝老鼠也一锅端了。
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我到塘边锻炼。水面划过一长溜水波,一条水蛇笔直冲到我脚边。它摇着脑袋看了我几眼,然后脸上带着一副抱歉的表情,冲我笑了笑,好像在说:“得罪了,老邻居。”我待在原地动不得。我并非被它吓蒙了,而是它那笑容我是如此熟悉,又是如此陌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但这神情绝对不是一条蛇应有的。我还在发呆,它又再次朝我点了下头,随即消失在水边的石头堆里。
【作者简介】肖辉跃,女,湖南宁乡人。自然文学作家,鸟类摄影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自然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人文地理》《天涯》《散文》《湖南文学》《四川文学》等报刊。部分作品被《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选载。著有自然文学作品集《飞跃高原》《醒来的河流》等多部。曾获第九届湖南省科普作品优秀奖、第四届谢璞儿童文学奖提名奖。荣登二〇二二年度生态文学榜单、二〇二三年生态文学年选、二〇二三年度百道好书榜年榜。散文集《醒来的河流》获首届观音山杯生态文学奖、第七届中华宝石文学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 蓝雅萍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