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音乐剧编舞研究刍议
崔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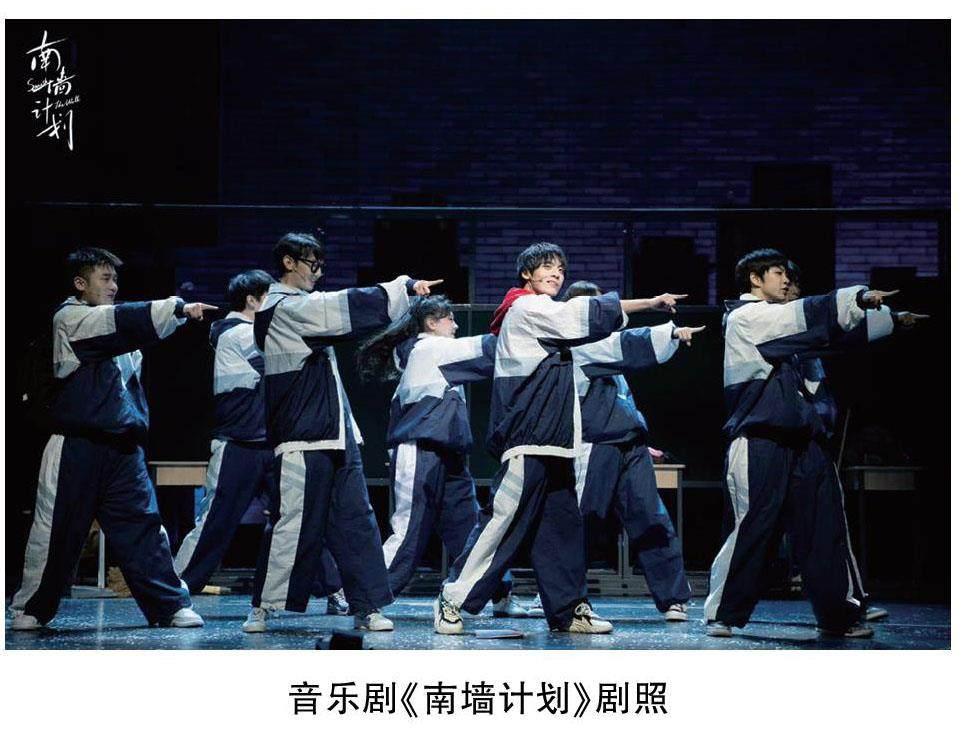


摘要:近年来,中国音乐剧发展态势迅猛,但相关理论研究则相对滞后,尤其在音乐剧编舞研究层面则更是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本文从实践层面出发尝试对中国当代音乐剧编舞的相关基本问题展开讨论,问题阈包括:音乐剧编舞的职能、音乐剧编舞与一般编舞的区别以及中国当代音乐剧舞蹈的现状与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提出“有机编舞”与“微观编舞”等音乐剧编舞视角与方法的概念。此外,通过结合中国本土音乐剧的特性来思考未来如何展开符合中国音乐剧编舞的创作方法与相关研究。
关键词:中国当代音乐剧;音乐剧编舞研究;“有机编舞”;“微观编舞”
一般而言,理论研究与实践摸索是一种相互促进与互相反哺的关系,但对于中国音乐剧编舞研究而言,国内目前在这一研究领域处于一种相对缺失的状态,国外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也屈指可数。上海戏剧学院的孙惠柱教授曾在其《跨文化表演研究的视角刍议》一文中指出:“音乐剧是当前国内演艺业中发展最快的艺术形式,编舞极其重要,然而很少看到有人对音乐剧的舞蹈进行深入研究。这个介于两种艺术样式之间的题目有点尴尬,舞蹈人认为是戏剧界的事,不懂戏剧不好研究;戏剧人认为是舞蹈界的事,不懂舞蹈也难以置喙。”可以说,正是介于舞蹈与戏剧乃至音乐之间的“尴尬”处境导致至今对于音乐剧舞蹈与音乐剧编舞的研究与论著寥寥可数。目前,中国当代音乐剧编舞研究有大量的空白值得填补,这其中既需要有学理性的研究,也需要有从实践出发的理论总结。笔者不才,愿根据自身的音乐剧参演与编舞经历出发,对中国当代音乐剧编舞当中的相关实践问题展开粗浅而不成熟的讨论。
一、“中国当代音乐剧编舞”之范围界定
有关音乐剧引入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音乐剧的历史与现状已有众多专家学者写了大量的文章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分析,笔者无意也无学力在此详细复述,本文聚焦于中国当代音乐剧编舞研究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但任何一篇学术文章,如不首先将所分析之对象与研究之范围进行界定,必将无法展开后续的讨论。本文标题内含“中国当代音乐剧编舞研究”,因此首先需就此范围展开界定。以“中国当代音乐剧编舞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并非笔者有意渲染一个大标题,实乃就音乐剧编舞层面而言,其所包含的范围相对较为复杂微妙。
首先,本文之所以没有用“原创”一词是因为就中国音乐剧编舞层面而言,其所编舞之音乐剧并非皆是原创,而是有大量引进音乐剧作品存在。就引进音乐剧作品而言主要分为以下几种,即:原版引进音乐剧、汉化全版权引进音乐剧、汉化半版权引进音乐剧、半汉化半版权引进音乐剧。就第一种原版引进音乐剧而言,这些作品往往为国外音乐剧的原版引进,其进入到中国市场,国内的联合出品公司往往只负责运营与宣发,而不参与创作乃至制作,当然这些所谓的“原版”往往良莠不齐,其卡司阵容与制作团队不乏滥竽充数者。第二种汉化全版权引进音乐剧,这一类音乐剧作品往往由较为大型的跨国集团或国内的文化演艺集团牵头出品,可以直接与原版主创方对接合作,如亚洲联创(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所出资引进的中文版《妈妈咪呀》和中文版《猫》,再如由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所出品和制作的中文版《狮子王》和中文版《美女与野兽》。这些作品往往制作团队精良,并由外方主创直接参与排演与制作,一方面还原程度高,另一方面排演水准较高。当然就以上所谈到的这两种引进类型而言,并不存在编舞问题,因为这些作品是高度还原的音乐剧作品,大部分作品至今还活跃在美国百老汇或英国西区的舞台上,中方并不参与舞蹈编创,更多的只是舞蹈的编排与复刻,而并无过多创作或再创作成分。而后两种即汉化半版权引进音乐剧和半汉化半版权引进音乐剧这两种类型则往往需要(并非全部需要)中国本土编舞的介入,这两种类型的引进音乐剧大多数只是购买了原版音乐剧剧本(包括歌词)的翻译和使用版权,而其他方面诸如舞美灯光设计、导演、编舞等方面都需要本土再创作,其中半汉化半版权的引进音乐剧甚至只是翻译了台词,至于歌词还是用英文来进行演唱。
其次,之所以没有用“本土”一词,乃是因为并非所有中国音乐剧的编舞都是“本土”,无论半版权引进音乐剧还是原创音乐剧,现今依然活跃着大量外国音乐剧编舞家,参与了大量中国音乐剧作品的创作。
再次,之所以没有用“华语”一词,一方面是由于有上文所论及的半汉化半版权引进音乐剧类型存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华语”本身的概念及范围的模糊性所导致。“华语”一词往往等同于汉语,汉语虽将方言也纳入到汉语的概念之中,但中国乃是多民族国家,如此称呼不免将已经出现或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音乐剧排除在外。
最后,本文需就“当代”一词来作出界定。界定“当代”一词是个复杂的问题,对于“当代”的讨论以及围绕其而引发的“当代性”问题无疑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所运用之当代一词主要指的是2000年以后的中国音乐剧。为此需做如下说明。其一,与音乐剧历史分析与研究作区分,即本文所聚焦之视点并非中国音乐剧编舞或中国音乐剧舞蹈的历史分析;其二,本文所运用之“当代”乃是时间界定的概念,而非“当代艺术”的概念;其三,本文更关注于中国音乐剧编舞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因此选用“当代”一词以强调讨论的现实性与实用性。
二、音乐剧编舞何为?
作为舶来品的音乐剧在西方乃至东亚的韩国与日本等国家都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产业与产业链,因此可以说商业性是音乐剧不可或缺的本质属性之一,对此,国内已有大量文章及书籍就此展开分析,笔者不再赘述。作为一种商业性的舞台演艺形式,音乐剧往往在实践中摸索,也在实践中更新。因此,对于各个音乐剧行业内各个工种的职能往往因“剧”而异,甚至因“地”而异,很难就此展开公式化的总结与归纳。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的Kathleen Kelly所做的研究Can a Methodology Be Developed for Musical TheaterChoreography?尝试性地从实践操作层面对音乐剧编舞家的工作模式和音乐剧编舞的工作方式来展开分析,但作者在文中也指出了目前美国音乐剧编舞的研究现状:“不存在一种训练和培养音乐剧编舞的课题研究。”
从词源上而言,编舞(Choreography)一词来自希腊语的两个概念,Chore和Grafein,前者代表唱诗班或者群体,后者则意味着书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利时著名编舞家安娜·特瑞莎·姬尔美认为编舞的词源其实提出了一个关于组织的问题——如何组织人群之中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而另一位编舞大师而威廉·佛塞斯则甚至认为编舞本身并不存在,至少代表这个术语含义的标准化模型是不存在的,威廉·佛塞斯认为不应该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编舞,而应该关注编舞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即抵制与革新旧有的定义。笔者认同以上两位世界级编舞大师对编舞这一“概念”本身所作出的思考,因此,一方面编舞需要组织与安排,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编排,另一方面编舞也需要创造与革新,创造是编舞这一职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以上由“编舞”(Choreography)一词所展开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作为一种职业或职能的音乐剧编舞来说必须存在创作方能称之为“编舞”。因此,音乐剧中有几组概念或职位则需要排除在编舞之外。以笔者所参与和参演的中文版音乐剧《狮子王》为例,围绕着《狮子王》的舞蹈部分会有众多职位,如编舞、联合编舞、全球舞蹈监督、舞蹈总监、中方舞蹈总监等等,而从创作层面而言只有原版的牙买加编舞家盖斯·菲根才称得上是编舞的工作,而其他职位更多地是对原编舞的编排与维护。
在对音乐剧的编舞进行了简要的界定以后,引出了一个不得不进行深入探析的问题——编舞与音乐剧编舞的区别。2000年知名音乐学家居其宏曾在《舞蹈》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音乐剧中的舞蹈创作问题》的文章,居其宏在文章末尾处直言不讳地写道:“中国的专业舞蹈家很多,有成就的舞蹈编创大家也不少,尤其是一批以搞歌舞晚会起家出名的舞蹈编导目前相当活跃,这当然是好事。但我要奉劝这些先生女士们几句——你们若不介入音乐剧创作便罢,若想从事音乐剧的舞蹈创作,建议诸位先将在老本行的大师心态抛在一边,还是老老实实从小学生当起,认认真真地学习一番欧美音乐剧的创作经验,仔细研究几部经典剧目的经典舞蹈场面,然后再来从事自己的创作,那时可能就会大有收获了。”作者的言词未免过于犀利,但时至今日就中国当代音乐剧编舞的现状而言依然适用,由此却也道出了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即音乐剧编舞是否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编舞?
任何一种舞台演艺形式必有其内在创排与制作模式,音乐剧作为一种高度产业化与都市性的舞台艺术,其内在的制作流程与程序则更为严密,这一方面源于音乐剧本身的跨界属性,而另一方面则是由其自身的商业性所导致的。笔者认为从事音乐剧编舞必先了解与认知音乐剧的基本制作流程与创作规律,而由此则需要具备以下三种能力。
第一,对音乐剧音乐的了解。所谓对音乐剧音乐的理解并非是一条严格的界线,作为音乐剧编舞并非必须具备高超的演唱能力、丰富的乐理知识、快速的识谱能力等这些“硬性”要求。而是要理解不同音乐剧音乐(作曲)的风格、种类等这些音乐常识以及不同音乐段落对于音乐剧叙事与抒情的作用。具体说来则是知晓不同音乐风格的节奏特性与调性,这其中既有流行音乐也有小众的摇滚乐,甚至还有传统曲艺的风格,在音乐种类多元化的今天,各种音乐风格、唱法都被音乐剧所吸收和借鉴。因此,作为音乐剧的编舞,如果不具备相应的音乐素养与广阔的音乐涉猎则难以理解不同音乐剧作曲的创作意图。
第二,对文本的理解。对于音乐剧的文本来说,则主要指的是传统文本意义上的歌词与剧本。与舞剧或舞蹈创作不同,音乐剧的剧本是一部音乐剧作品的核心,这种核心作用并非如同舞剧剧本的那种纲领性作用,而是更为关键到戏剧构作问题,毕竟音乐剧到本质属性是戏剧。对于一部原创或新创音乐剧作品而言,往往建组后还需要花费一周乃至更多的时间来坐排打磨剧本,使之从一个文学剧本变为舞台台本,更不要说在正是建组之前还要用两到三轮的时间(每一轮为两周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工作坊测试,工作坊的目的在于测试剧本与音乐作曲的可行性。而一个合格的音乐剧编舞是需要参与这些剧本讨论与实验的,同时也要给予专业性的舞台意见与建议。这就要求音乐剧编舞需具备对文本的理解与想象能力,具备剖析文本潜台词、行动动机、主题立意等理解能力。
第三,对戏剧的认知。从艺术样式的归属上而言,音乐剧实乃戏剧之一种,因此如不对戏剧这一行当有所认知则难以承担音乐剧编舞之工作,可戏剧之宽泛与深邃亦并非一朝一夕得以窥见。此外,从研究层面上来讲,在戏剧界中研究音乐剧之人也实属少数,“其原因在于世界上掌握戏剧话语权的著名西方教授多半只喜欢找新奇怪异、曲高和寡的先锋派新东西来研究发表论文,基本上瞧不起音乐剧这种太通俗、太大众、成功得太久的艺术样式。”因此,一方面即便音乐剧本身也缺少前人学理性的理论总结,另一方面学科壁垒越筑越高,这就导致舞蹈人越过戏剧之高墙再寻觅音乐剧之路途委实艰难。但如若不对戏剧本身有所认知则难以与导演沟通合作,也难以与演员排练工作。音乐剧编舞并非只是歌加舞的简单一加一模式,更重要的是要符合戏剧性的要求。
三、“有机编舞”:音乐剧编舞的“可舞性”问题
居其宏曾指出:“舞蹈编创一直是中国原创音乐剧的一个明显弱项,中国艺术家在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尚少,具体表现在:舞蹈编导们基本上不会用舞蹈写戏,也不擅长用舞蹈抒情。”这其实反映的是中国原创音乐剧编舞缺少有机性,这种“有机”指的是如何处理音乐剧编舞的“可舞性”的问题。
如同舞剧一样,音乐剧当中的舞蹈编创与设计也需要讲求“可舞性”的问题,简而言之便是音乐剧当中的舞蹈在剧中承担何种作用,当中的舞蹈段落编排是否符合戏剧的整体叙事,同时音乐剧当中的舞蹈段落与场面是否具备出现的合理性。由此便涉及到音乐剧舞蹈的类型问题,对于音乐剧舞蹈的类型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称谓和分类准则,无独有偶,这些为数不多的对音乐剧舞蹈进行研究的学者往往都将音乐剧舞蹈分为三类。例如,慕羽在其《音乐剧与舞蹈》一书中从西方音乐剧之舞蹈定位的角度对音乐剧中的舞蹈进行了分类,分别为:音乐剧中的肢体语言和戏剧行动、音乐剧中的歌舞以及音乐剧中的完整舞段。再如居其宏则按照舞蹈在音乐剧当中的使命这一原则将音乐剧当中的舞蹈分为戏剧性舞蹈、抒情性舞蹈和色彩性舞蹈。此外,还有学者根据舞蹈场面将其分为叙事性、抒情性和烘托性。通过对以上三种分类的对比其实可以发现,其“能指”虽然不尽相同,却都是相近的“所指”。以上三种分类方式归根结底所围绕的是音乐剧的戏剧性,即便是抒情性音乐剧舞蹈或者纯歌舞性的场面舞蹈亦或如“梦幻芭蕾”一般的幻想、架空舞蹈场面也要符合整体或分场的戏剧情境。笔者将这种与音乐剧叙事和戏剧性相贴合的编舞称为“有机编舞”,这种“有机”指的是与戏剧叙事与情境的有机关系,归根结底也是皮娜·鲍什的那句名言——关心的是为什么而舞。
“通常而言,好莱坞音乐剧编舞在两种创作模式中摇摆,即情节与舞码(Number)或叙事与场面设计。”这种“摇摆”其实便是如何处理音乐剧舞蹈的“可舞性”或者说舞蹈如何合理地融入到音乐剧的剧情中的问题。巴斯比·伯克利和金·凯利是美国黄金时代的两位著名编舞家,巴斯比·伯克利所在处理“可舞性”问题时所运用的方式是用舞台间隔的方式将非现实的舞蹈场面或歌舞场面合理为剧情的一部分,即运用“戏中戏”或者“后台”的方式来间隔歌舞场面与戏剧叙事。而金·凯利则是将舞蹈融入到戏剧的主要叙事结构当中,将舞蹈作为塑造角色的工具。巴斯比·伯克利和金·凯利处理音乐剧中舞蹈“可舞蹈”性问题的方法与模式是美国黄金时代音乐电影和音乐剧的主要处理方式,并随之影响着后来美国音乐剧舞蹈的编排模式。巴斯比·伯克和金·凯利对于音乐剧“可舞性”的这两种处理方式,时至今日依然是美国音乐剧编舞所沿用的方式。由此看来,音乐剧中的编舞如何与戏剧形成有机关系一直以来便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原则问题,当然欧洲的德系和法系音乐剧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同模式的探索,但即便如此如何保持编舞与戏剧叙事和呈现的有机关系依然是音乐剧编舞的重要准则。
笔者所谓的“有机编舞”指的是音乐剧当中的编舞需符合音乐剧整体与分场剧情、情节推进和整体的戏剧走向,所编之舞需与情节、人物、情境有机协调,并非“有歌必有舞”,也不能“为舞而舞”。此外,还要考虑与音乐的有机关系,包括音乐的调性与风格,传统舞蹈编导往往只考虑音乐的旋律与节奏而忽视了音乐的风格以及背后的文化意义。传统编舞在编排音乐剧中的舞蹈时往往是根据音乐的旋律与节奏来编排舞蹈动作,设计调度与画面,音乐剧舞蹈的动作编排与场面设计固然重要,但其重要程度是亚于戏剧性的。因此,传统编舞在进行音乐剧编舞时往往陷入了一种“无机”编舞的状态,即所编之舞即与戏剧情节情境无关,又与音乐或歌词无关,往往是“你唱你的,我跳我的”,造成了舞蹈与戏剧和音乐的割裂。“有机”指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音乐剧编舞需与戏剧和音乐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是自然的结合而非各自为政。
四、“微观编舞”
笔者所谓的“微观编舞”包含几个方面:其一,似舞非舞的舞蹈设计。事实上就目前大多数中国音乐剧而言,音乐剧当中的编舞家,与其说是编舞,毋宁说是肢体设计更为合适。这其中原因很多,一方面,当前中国音乐剧无论是引进音乐剧还是原创音乐剧都以中小剧场为主,中小剧场音乐剧的规模决定了并不具备大量群演的条件,这一规模设定必然导致歌舞大场面的“缩水”;另一方面,绝大部分中国音乐剧演员舞蹈基础与肢体能力都相对较弱,大量音乐剧演员缺乏或根本不具备舞蹈基础,面对这样的演员“质料”,即便再一流的编舞家也不得不另辟蹊径,编排更符合演员身体机能与舞蹈能力的编舞设计。这就导致当前中国音乐剧的编舞所承担的大部分是肢体设计的工作,他们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设计角色的肢体行为,设计演员的肢体动作,根据音乐剧演员的戏剧表现力优势来优化或强化他们的戏剧表演。当然笔者认为,此一现象并不有利于中国音乐剧的长久发展,这一现象也是当代中国音乐剧的弊端与问题之一,在下文中将会详细展开。
其二,肢体指导。中国音乐剧演员的专业背景往往分为三类,即舞者、歌者与戏剧演员。其中舞者背景的演员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一则是因为当前中国音乐剧更偏重歌与戏,而轻视舞蹈,因此从音乐剧的内容上决定更重视和强调演员唱与演的能力;二则是因为上文所提到的原因,即当前中国音乐剧以中小剧场规模的演出为主,而只有大剧场音乐剧才对纯舞者或者说舞蹈能力高的演员有需求。歌者或戏剧演员往往缺乏身体意识与肢体的敏感性,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戏剧艺术繁盛如英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彼得·布鲁克在其《敞开的门》一书中曾感叹:“事实上,要在脸部表情和手指头上做到敏感简直轻而易举,但要在身体其他部位例如腰背、臀部、腿部做到同样的敏感,那就不是生来就会的了,必须通过训练才能达到。敏感指的是演员在任何时候都掌握着他全部的身体,当他开始一个动作时,他知道他身上的每个部位。”对于当前绝大部分中国音乐剧演员来说往往缺少这种肢体的敏感性与控制能力,因此中国音乐剧之编舞在进行工作时往往承担着肢体指导的工作,指导意味着要承担着“既要练兵又要用兵”,所谓“兵”便是那些缺乏肢体敏感性和基本协调能力的音乐剧演员。
其三,日常生活动作或戏剧行为的节奏化设计。对于音乐剧来说,“戏剧是音乐的根本,音乐是音乐剧的灵魂。”将音乐付诸于戏剧的视觉化往往是音乐剧的常见表现手法,换言之这种手法指的是将日常动作、对白等戏剧行为编织进音乐当中,而在这编织的过程中往往运用节奏化的方式。对于音乐剧编舞来说,对节奏与肢体的敏感是音乐剧编舞的必备能力,如何将这些日常生活动作与肢体行为进行节奏化处理是音乐剧编舞的重要工作之一。
其四,调度设计。音乐剧编舞往往对空间与调度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这种深刻体现在对舞台空间概念深刻感思,对调度设计的周密感知,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音乐剧编舞往往可以弥补音乐剧导演的不足。一部音乐剧演出涉及大量的转场与换景,演员的上场与下场,如参演人数较少的音乐剧作品导演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对于超过一定人数的音乐剧作品或音乐剧调度较为复杂的音乐剧场面来说,音乐剧导演往往无从下手,这也就是为何时至今日,每逢重要的国家级或世界级文艺演出与开闭幕式,进行实际编导与排练的绝大部分都是舞蹈编导。从调度设计与组织人员的能力方面来说,编舞的优势毋庸置疑,这一点在国内外音乐剧的创作中同样如此。
综上所述,音乐剧编舞往往具备自身职业背景的优势,这些优势是一部成功的音乐剧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但也正是音乐剧舞蹈的特殊性,使得其往往需要承担着一般传统编舞工作中所不曾面临的工作任务。笔者之所以将其命名为“微观”编舞,一方面,这一“微观”指的是对身体设计之微观层面的感知;另一方面,则指的是对音乐剧细微之处的设计,而对于音乐剧来说,往往正是众多细微之处导致作品的连贯性与顺畅感。
五、中国音乐剧舞蹈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音乐剧发展至今,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尝试,原版引进,到汉化引进,再到原创尝试。而这些不同的阶段当中又有不同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时而偏向美式音乐剧,时而偏向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音乐剧,近年来更是有大量韩系和日系的音乐剧出现。在原创音乐剧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蜕变,从早先轻歌剧式的大型音乐剧到近年来中小剧场音乐剧的井喷式发展。有关中国音乐剧现状与问题的文章近年来有很多,但鲜有文章谈论中国音乐剧舞蹈的现状与问题,但作为戏剧、音乐、舞蹈三者合而为一的综合型艺术表现形式,只谈论音乐剧当中的戏剧与音乐而不对舞蹈以及编舞进行分析的音乐剧研究必然是缺失的。因此,笔者愿结合个人从业经验与经历就此展开几点不成熟的个人见解。
第一,音乐剧演员舞蹈基础与肢体能力缺失较为明显。中国音乐剧演员的舞蹈基础与肢体能力极其欠缺,大部分音乐剧演员有音乐剧演员之名而无音乐剧演员之实,大部分演员往往只是“会演戏的歌手”而全然不具备肢体能力,甚至于基本的肢体协调性问题都没有解决。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高校和艺术类院校的音乐剧专业本身便轻视舞蹈与肢体训练等方面的课程;另一方面,当前中国音乐剧演员新老断代严重,演出经验与经历丰富的演员往往具备唱、跳、演全能型功底,而新生代演员则短板明显。
第二,当前中国音乐剧“少舞”或“无舞”。当前绝大部分中国音乐剧基本“少舞”甚至于“无舞”,一些作品大都是从坐着唱到站着唱再到坐着唱再到站着唱,所谓舞蹈只是抬抬手、迈迈步,跳一下,转半圈。音乐剧演员的肢体能力弱便不安排舞蹈,故而也就出现了越来越多没有舞蹈的音乐剧,由此陷入一种长期的恶性循环状态。此外,当下中国原创音乐剧以及大量韩国汉化引进音乐剧当中的主要角色往往是一种“少舞”或“无舞”的设定,这就导致大量的音乐剧演员以不会舞蹈为“荣”,毋需跳舞甚至成为了主要角色的“标配”。
第三,音乐剧所编之舞与作品割裂。现今中国音乐剧编舞家往往分为三种:一种为常规意义的舞蹈编导,这些舞蹈编导专业背景不同,但绝大多数是艺术院校的舞蹈专业背景;第二种为以现代流行舞编舞,这些编舞往往是舞社当中自学成才者,长期为综艺与晚会编舞;第三类为具备音乐剧演出经历的编舞,这些编舞往往参与过音乐剧演出,是音乐剧演员当中舞蹈能力较高者,或者本身便是专业的舞者而后参演音乐剧。在这三种当中前两种编舞往往没有音乐剧的演出或制作经历,其并不了解音乐剧的制作流程与创作工艺,因而往往是将以往的编舞意识带入到音乐剧编舞当中,这就造成了所编之舞与音乐剧整体的严重割裂。
第四,选角机制与原则不利于编舞设计。中国音乐剧演员的甄选与招募往往从角色定位着手,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当下音乐剧出品与制作公司为保证票房收益往往选用具有一定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来担当A卡,但这些演员其实绝大部分并非是音乐剧演员,有大量的歌手参杂在其中,这就导致陷入到前面第二点所提到的恶性循环当中。当前中国音乐剧的演出市场是重“人”而不重“戏”,即观众或粉丝往往是因某一位或某几位卡司来购票观剧,而非因“戏”来观看演出。
六、总结
上海戏剧学院的熊源伟教授曾撰文指出:“中国音乐剧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从引进国外经典音乐剧,到‘描红搬演,再到创作自己的原创音乐剧,是一个‘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过程。”熊教授的所谓“六经注我”指的是引进国外音乐剧,是学习和借鉴的过程,而“我注六经”则是中国原创音乐剧的创造。其实任何一种舶来品的艺术形式都经历的是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的过程,中国的歌剧如此、芭蕾舞如此,甚至于舞剧本身其实也经历这样一种过程。作为舶来品的音乐剧经历从“师洋”到原创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当然中国原创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还处在艰难的摸索当中。但时下中国音乐剧的编舞依然还处于一种“师洋”当中,而并未展开原创的摸索。一方面,对于大部分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编舞来说,虽然名为原创音乐剧,但所编之舞从动作层面上来讲往往分为几种:其一是美国剧场爵士舞动作素材的重新编排;其二为流行舞动作套路的搬运,以街舞和韩国男团、女团舞为主;其三为初级芭蕾舞与现代舞动作元素截取。另一方面,即便是民族题材或本土题材的原创音乐剧,因必须使用民族舞蹈动作与元素素材,但这些编舞往往只是将已有的民族舞蹈素材堆砌或照搬到原创音乐剧作品当中,而没有进行符合音乐剧情境与叙事的创编,这就导致所编之舞往往是歌加舞,而不能称之为音乐剧舞蹈。
随着中国音乐剧的发展,中国当代音乐剧编舞研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这其中既需要学理性的论证与分析,也需要实践的理论总结,用传统编舞理论或方法来对待音乐剧编舞无疑是无法完全适用的,音乐剧编舞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特殊性,需要从跨学科的视角来进行深入分析。本文以“刍议”为题乃是因为中国音乐剧编舞研究实在还有太多问题值得深入展开,本文只是粗浅地点出中国音乐剧编舞当中的基本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值得更为深入的阐释与分析。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在读博士生)
参考文献:
[1]孙惠柱.跨文化表演研究的视角刍议[J].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21:03.
[2]Kathleen Kelly.Can a Methodology Be Developed for Musical Theatre Choreography?[R]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2004-2019, 3222.
[3]居其宏.音乐剧中的舞蹈创作问题[J].舞蹈,2000:04.
[4]孙惠柱.跨文化表演研究的视角刍议[J].当代舞蹈艺术研究,2021:03.
[5]居其宏.音乐剧中的舞蹈创作问题[J].舞蹈,2000:04.
[6]Lauren Pattullo.Narrative and spectacle in the Hollywood musical: contrasting the
choreography of Busby Berkeley and Gene Kelly[D].Research in Dance Education,2007:73-85.
[7][美]彼得·布鲁克.于东田译.敞开的门[M].上海:中信出版社,2016:18.
[8]熊源伟.何妨“六经注我”,安得“我注六经”——中国音乐剧创作之我见[J].戏剧艺术,2020(06):8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