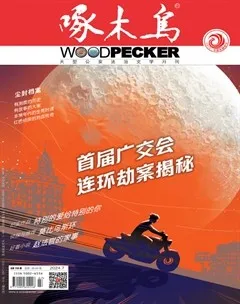最重要的

八岁那年,母亲带我进城。
在城里,路过一家商店,我看见店里放了一件精妙绝伦的小玩意——一辆火焰涂装的四驱赛车。
它是如此完美,低矮的车身紧贴着地面,舞动的火苗几乎要点燃一旁的纸箱,只要你按动一下车身上的按钮,它马上像一支离弦的箭,“嗖”一声射出去,一路风驰电掣。更神奇的是,在它的四个角,还装了四个纽扣一样的小转轮,这样无论它撞到什么,都会像阳光照射到玻璃一样,折射出去,不会卡死,继续一路奔腾而去。
我傻傻地看着它,腿有千斤重,再也迈不开了。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能有什么好玩的呢,无非是田里的泥巴、水泥地上的弹珠、后山的躲猫猫游戏,而这些玩意跟这辆四驱赛车比起来,判若云泥。
我撒泼打滚,倒在店子门口怎么也不愿起来。但显然,购买一辆四驱赛车的花销太贵了,也不在母亲这次进城购置家用物什的范畴之内。最终,在屁股印上几个巴掌印之后,母亲脸含愧意地把我强行带离了这家小店。
我号啕大哭。这一天,我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一个玩具。
十八岁那年,我参加了高考。
在中国,高考被称为最公平的一场考试,也被视为穷学生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十余年的寒窗苦读,每天天没亮出门,走在蜿蜒盘旋的山路上;晚上,月满山林,打着手电往寨子的方向赶。无论冬夏,不避雨雪,一切只为了考场上这几个时辰的较量。
我所在的中学不是示范中学,也不是重点高中,而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高,所以我的愿望也不像电影里经常演的那样,要上清华、读北大,只要是一所本科,甚至不需要重本,我就满足了。
但最终,事与愿违,皇天还是负了有心人,我最后以两分之差,只上了一所专科院校。
我失魂落魄,十余年努力一日化为泡影,那种感觉,有如斧钺加身。
母亲没有责备,虽有遗憾,仍对我说,没事,上大专也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往后的路还宽着呢。
我默默不语。这一天,我输掉了自己最重要的一场较量。
三十九岁那年,我迎来了一次转机。
我在一家企业工作,任劳任怨十多年,但职务一直是普通员工,难有半步升迁。三十九岁那年,部门的一个副主任到龄退休,于是,一个领导岗位空缺了出来。
在部门的所有普通员工中,我是资历最老的,能力也被认可,而且当下最喜欢提拔四十岁以下的年轻干部,也就是说,这是一趟末班车,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可能再难觅高升的良机。
平日不拘小节的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逢人点头哈腰,要是遇见了领导,笑容自然比牡丹还要灿烂几分。
我以为一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但一个月后,一纸任命的公文贴在了公示栏,新任副主任是空降的。
我回到家里,呆若木鸡。母亲见我丢了三魂七魄的样子,忙问事情的缘由。我诉说了心中的失落,母亲却满不在意,说,又不是吃不上饭,无官一身轻,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
我心有悻悻。这一天,我丢掉了自己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七十八岁那年,我病重躺在床上。
病魔像一头饥饿的恶狼,扑过来肆意撕咬,那锋利的獠牙穿过肌肤直抵血肉,羸弱的身躯即使插满维生的导管,也如一根风中的残烛,在无尽的暗夜里风雨飘摇。
我微微仰起头,回望自己走过的一生,如履薄冰,那么多失落,那么多重要的东西,却都一一离自己而去。
我满眼遗憾,登上即将远去的列车。
但就在离开的时候,我蓦然听到一声轻柔的呼唤。我转过身,循着声音望去,在目光的尽头,站着我的母亲。
我要走了,母亲来接我了。
我挣扎着站起身来,一路向母亲的方向跌跌撞撞奔去。
时空变换,斗转星移。
这短短的几步,我仿佛用尽了毕生的力气。一路上,我看见了自己三十九岁的不甘、十八岁的遗憾、八岁的泪水,它们曾经那么重要,但就在自己扑入母亲怀抱的那一刻,我才记起那个不管一切重不重要,都视自己为最重要的人。
小时候的风,悠悠从身边吹过。
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在弯弯的田埂上,就像小时候放学了,她来接我回家。
责任编辑/谢昕丹
插图/子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