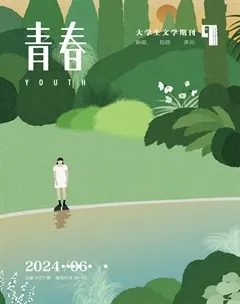写作是能够打开另一扇大门的行动
《我与先生》:艰难与伟大并存,悬崖与鲜花同在
周明全(《大家》杂志主编,文艺评论家):文学需要作者在逻辑和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来完成一个现实与虚构交融的文学世界。写作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工作,是一个几乎需要耗尽一生光阴而无从改弦易辙的事业。艰难与伟大并存,悬崖与鲜花同在,但不可否认,对个人而言,阅读和写作是一项能够打开另一个世界大门的秘密行动,对社会而言,也是在为人类精神的通天塔建设搬运石头和瓦片,值得我们去付出。
《我与先生》以一对夫妇从相识、相知、相爱到分离又重聚的完整过程,象征了1919年到1949年国家从危亡边际到重新统一的光景,其实是一篇很不错的微小说,如有不足,则是“我名为华安,先生名为祁原,祈愿中华安定”稍显流俗和段子化。文学有时不一定要说得很清楚、明白,或许自己感受到的才更好。
包倬(《滇池》杂志主编,作家):我觉得一篇小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开始写作,你首先要找到独特的符合小说气质的腔调,《我与先生》这篇在这一方面做得很好,非常浓郁的民国腔调,这样写是可以的,我觉得年轻的学生去写小说一定要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
《我与先生》这篇小说分成几段,其实就是写一对男女从1919年到1949年间相识、相爱,然后又分离重聚的故事。但我觉得首先有一点问题,小说中1919年的时候,“先生”是19岁,“我”是18岁,到后面1927年的时候,“先生”30岁,“我”20岁,这个时间是不对的,年龄没有理清楚,文章一直都有这个问题。
这篇小说除了好在腔调上,我觉得作者的想法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把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重要节点结合在一起。这其实也是很多小说的写作方式,呈现这种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生命状态。但这个小说要修改,我觉得年轻学生的写作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比较胆怯,不敢放开写,一个人一生几十年的时间,你用两千多字就写三十多年,这肯定是难以写好的。
所以我觉得作者要抓住在重要时间节点上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比如写到男主人公“先生”后来出国,而女主人公“我”留在国内,就可以抓住这一点,生发开来写。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写法,你不能把它当成流水线一样线性地写下去,而是需要再加很多东西进去,比如加入男女主人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甚至相爱的一些细节。这个同学可以再认真一些来写作,他完全有写作的才华和天分。
这篇小说的男主人公叫祁原,我原以为他是以民国时期某一人物为原型的,后来我才发现作者表达的是祈愿中华安定,是想把这个小说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但我想说,我们的写作,特别是年轻人一开始的写作,不要有那么重的包袱,写个体,写你能够把握的东西,我觉得就挺好。
张立军(《艺术广角》杂志主编,文艺评论家):《我与先生》,像包倬主编说的,文中几次出现年龄,这个时间在这里应该是一种标志性的符号,读者肯定会很仔细地去关注这几个年龄,但从第二部分,也就是从1920年开始,两个人的年龄出现了误差,需要再推敲一下。作者的本意是想展现一种变化。这种语言放进这个题材里,可以说这个故事和它的语言是严丝合缝的,但这只是一种题材追加的状态。从体裁上来说,它算不算小说,这个我也不太确定。
杨不寒(青年作家,诗人):《我与先生》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文体意识。这几篇文本有的不太好判断到底是小说、散文还是随笔,不过《我与先生》的作者在写这篇作品的时候,很明显是当成小说在写。这篇小说在很短的篇幅里写出了较长的时间跨度,也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小容量要装大内容,从技术层面来讲是很不容易的,一般的策略是写某个侧面,就像树的切面一样,从中能看出树的年龄、长势。另外,这篇小说的语言也比较有意思,刚刚包倬老师讲到腔调问题,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在于,这种腔调能够很明显地看到别人的影子,说白了就是鲁迅的影子。
《追光少年》:自我性的青春表达才更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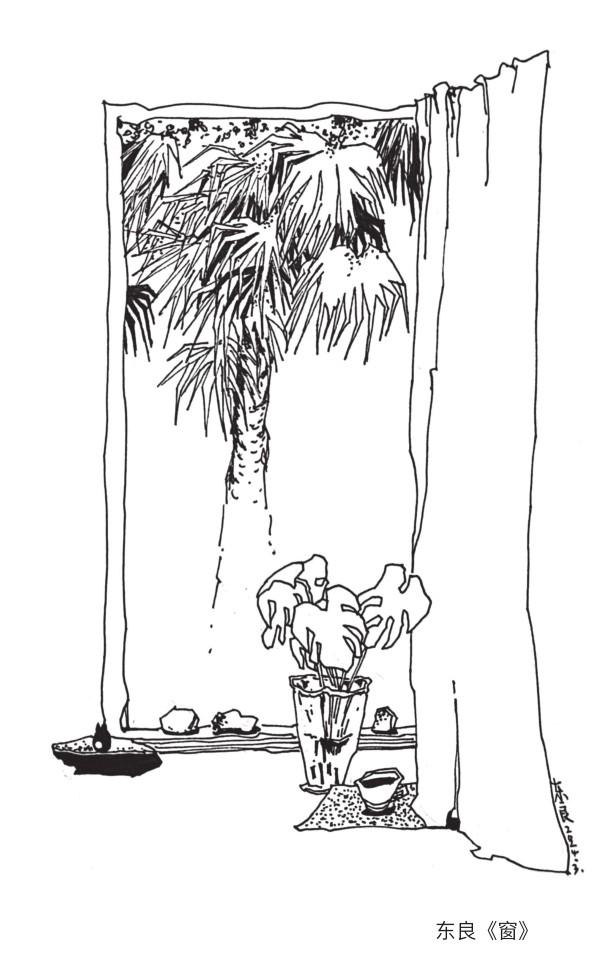
周明全(《大家》杂志主编,文艺评论家):《追光少年》用几个小章节追忆高中同学的纯真友情,细节处理有闪光点,“三生有幸”“向阳而生”这两章都写得细腻而有光,但开篇一章和结尾一章,感叹议论显得过强过硬。如将“三生有幸”“向阳而生”两章拓展,再写真实些,或再写相同的几章,可能会更好,更有意思,也更抓得住人的内心。另外本篇文章题记不错,但是从小说性质的角度上来说,它更偏向于散文而非小说,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
包倬(《滇池》杂志主编,作家):《追光少年》一开篇就引了《夏至未至》,有浓烈的青春文学气息,看得出作者应该是典型的青春文学的钟爱者。这个词不含贬义,我觉得我们的青春都是从那种青涩的状态开始的,正是在这种时候最容易接收到文学带给我们的气息,这是我们对文学的触觉最灵敏、最发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好地抓住这种文学的感觉。
“感谢相遇”“三生有幸”“向阳而生”“不说再见”四段,在我看来,这四段文字语言的质感都很好,也很灵动,但这个小说的主题既然是“追光少年”,我想你可能需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需要放开写,即便短篇小说也得写个五千字。
当然我提醒大家最好不要写爱情,因为青春爱情故事实在太难写了,太容易流俗。你可以写其他的,可以写一下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
张立军(《艺术广角》杂志主编,文艺评论家):《追光少年》截取的几个片段,让我们产生很多对青春的联想。我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更想知道现在大家的青春到底是什么样子,怎样用生动和具体的文字表达出来,我会把叙述的文字和我自己的过去做一个比较,如果没有变化的话,我觉得文字对我来说没有新意,仅从阅读者的角度来说,内容是无效的。在写作的时候,你应该抓住生活的瞬间,这几篇作品有很多感慨青春或者是在人生某一阶段的感叹,还有一些有意地对文章主题做一些提拔。单说反映青春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更具有当下性,同时更有自我性的青春表达才有效。
杨不寒(青年作家,诗人):《追光少年》这一篇写得很青春。这篇小说引用了不少郭敬明小说《夏至未至》的句子和片段,显现出作者的某种文艺趣味,文本内所写的青春感伤、懵懂情绪和阳光下的梦想、友谊,我们在青春期或许都曾经体会过这些滋味,或者说这些滋味正是青春的表现。从这个逻辑来讲,我认为年轻的写作者尽量不要在作品中感慨生活,而要感受生活。
在《追光少年》中,很多句子不能显现出某种真理或者灵魂的深度,只是加重了文艺的腔调,一些措辞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好像欠缺考虑。另外,虽然文学小说不是思想的练兵场,也不是展现思想的阅兵仪式,但我还是希望作者在写作的时候能够把情绪进一步转化为意趣,也就是说让自己的情绪在写作中得到反思,这样文本或许会更上一个层次。我们读什么、喜欢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本身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但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应该尽量提高文学的品位,多读经典作品,目光放得更高远一点,也就是古人讲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反骨人生》:“意识流”的写法能够给作者很大的自由感
周明全(《大家》杂志主编,文艺评论家):《反骨人生》独白式地反映一天生活状况的渺小,细节描写有效、到位,比如“走到门口我一眼瞥见楼道尽头窗户射进来的蛋黄派效应”这一段,有个体感受,有细节,感觉也压得住,基本能呈现出场景和作者内心的感受。喃喃自语的口吻,让人想起卡尔维诺、乔伊斯和“意识流”小说的某些片段,但这样泛化的写法往往需要收束和精确,否则容易产生一种碎片化和飘忽的感觉,让人联想到私人笔记的絮絮叨叨。
包倬(《滇池》杂志主编,作家):我特别喜欢《反骨人生》的语言,它整个叙述非常稳定,你能感觉到它的气息很沉稳。作者能够聚焦到他所写的东西上去,我们读到这样的语言时,其实很容易被带到他所书写的这个氛围当中去。
我仔细看了一下,小说里很多句子都写得非常好,你用这样的才华、这样的语言,去写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故事的选择稍微单薄了一点,可能因为同学们在写作中对小说的思考还是少了一点。
张立军(《艺术广角》杂志主编,文艺评论家):我觉得《反骨人生》采用的恰恰是青春写作里比较适合的一种叙述方式,除了题材,我们也要选择适合青年人的叙述内容。当然这不是一个导向问题,跟每个作者喜好的思维有关。《反骨人生》这种“意识流”创作,是与一般的现实主义写作有所区别的东西,从语言上、思维上我是比较喜欢的,这一篇与其他相比,在创作思维和方式方面是有突出点的。
杨不寒(青年作家,诗人):我觉得《反骨人生》是一篇更成熟一点的小说,也是一篇更具有现代主义气质的小说。作者在思绪的漫游中记录下了一整天的生活,小说里面写到的“蛋黄派效应”“好丽友报应”,都是很有趣的说法。虽然“意识流”的写法能够给作者很大的自由感,但在具体写作中一些基本逻辑应该照顾到。举一个例子,这篇小说第一段中有这样一句,“张嘴想说什么,人就不见了,又去敲隔壁门了”,似乎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首先这篇小说是第一人称,就意味着视角是被限制的,既然人眨眼不见了,怎么又去敲了隔壁的门呢?这样不起眼的细节需要作者小心注意。另外,读这篇小说稍感饥饿的地方是觉得作者写得太浅了一点,我认为这篇小说可以用力的地方在于对“意识流”深处,对内心最幽暗处的探察和关照。
《记事》:情真意切的小说是能够打动人的
周明全(《大家》杂志主编,文艺评论家):《记事》记录了自己从小时候第一次送葬到喜欢的亲人过世的生活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明白了大人口中的“走了走了”其实是回不来的远走,是一种对死亡的理解。文章质朴实在,文笔基本还压得住,但也因此稍有记流水账之感,显得不够生动丰富。
包倬(《滇池》杂志主编,作家):《记事》的出发点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生老病死,我们的亲人都会离世。作为年轻人,有亲人离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写一篇文章,比如这篇小说透过一位老人的死,去回忆他生前的一些经历,感觉写得还是有一点点仓促。其实我们认真去想,每个人的一生,特别是我们的至亲,或许都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这个人在时代当中,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他的亲人,是怎样一种状态,是可以由个体的非常独特的东西,写出亲情当中很多共性的。所以对这篇小说,我的意见还是你放开写,写五六千字,提几个老人生前重要的关键节点,把这个人写立体。
这篇小说的语言挺好的,写到动情之处,“磕了头,放完鞭炮,一道踉跄地下了山。从此,每年多了一个要上的山”,这句话非常打动我。亲人埋在山上,然后每年就多了一座要上的山,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张立军(《艺术广角》杂志主编,文艺评论家):我很喜欢《记事》,看了之后确确实实激起我的感动。但是这篇小说我又有一点疑惑,从三岁开始,他的记忆非常清楚,而且写得很深入、很生动。那么我就在想,人的记忆可追溯的源头在哪儿?三岁的事情可以记得这么清楚吗?不过这一篇的情感还是非常突出的,做到了以情动人,细节处理上也相对比较好,其实可以再把很多细节放进去,让生活更丰满一些会更好。
杨不寒(青年作家,诗人):相比之下,《记事》这一篇的文学意识和文体意识都比较薄弱,但却胜在情感真挚。虽然一心搞唯美主义的王尔德曾经说“一切恶劣的作品都是诚挚的”,但即便是从审美角度直观来看,情真意切的小说还是能够打动人的。换句话讲,作者的情感力量也是评价作品的一个指标。《记事》在亲人死亡的对比中表现抒情主体对亲情的体会、对死亡的感悟。我相信张立军老师可能也是在这个角度上觉得这篇小说很有意思,不过这篇小说也存在一些小瑕疵和小硬伤。所以,我认为该小说的作者,其实包括这几篇小说的作者,都需要提高语言的自觉,至少要消灭文本中的病句。当然文学写作本身就包含着对语法的冒犯,但在我看来对基本语法的破坏必须造成更多的意义,否则就只能算作败笔。整体来看,虽然我挑了一些问题来说,但这几篇小说都各有特点,各有长处,都有进一步改善成好小说的空间和余地。
注:实录中涉及的内容为修改前的作品,为保持现场研讨原貌,相关叙述予以保留。
本文由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金鹏辉整理。
内容梗概
《我与先生》写了从1919年到1949年,一对夫妇从相识、相知、相爱到分离又重聚的故事;《追光少年》以“感谢相遇”“三生有幸”“向阳而生”“不说再见”四个关键词,截取了四段与朋友们的青春回忆;《反骨人生》以个人独白的形式,写了一天中的生活;《记事》写了身边亲人去世后,作者的一些所思所想。
责任编辑 张范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