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 驰
一
王子悦的婚礼是要回国举行的,时间定在了下周。
段安年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头向后枕着,用指肚来回摩挲着烫金的请帖。早上的时候,同事小李说看到楼下前台有他的快递,就顺手给他拿了上来。段安年那会儿正忙着调试代码,最近电商都在搞购物节,作为分公司前端的一员,他离不开眼下的任务,只能头也没抬地给小李说了声谢谢。
结束手头的工作,胡乱吃了点外卖,段安年借来一把黄柄美工刀。长条状的快递盒并不大,但是却用了三卷互相垂直的透明胶布包裹,摸上去滑滑的,像是打了死结的绷带。徒手拆开是不可能了,段安年摁住快递盒,一小块刀尖钻进了盒子里面,轻轻舔舐着盒面,刀尖开始往前走,嘶嘶的声响紧随其后。
是一卷红纸。段安年把镶着金线的红纸取出,摊开。他这才想起来,几天前王子悦就在微信上说,要寄东西给他。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段安年的目光越过了那段证婚词,最后落在了末尾竖着书写的“伊素光”和“王子悦”上面。笔画有点歪扭,连带着记忆开始复现。在段安年的印象里,伊素光高中那会儿还是挺会写字的,不过他又忽然意识到,不只是伊素光,王子悦也有三年没有回国了。
去是肯定要去的,上一次收到王子悦的请帖,还是高考完那会儿。那一年,段安年和王子悦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一个学计算机,一个学医。两家的关系本来就很好,再加上“双喜”临门,索性就把升学宴都放在一起办了。
段安年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场景,在酒席上,两位父亲对着酒瓶吹,一瓶接一瓶,喝到满脸通红,几乎互认亲家。众人欢笑,一个接一个的红包也被塞到了段安年和王子悦的手里,他俩一边说着不要不要,一边还是把衣服的口袋撑到了最大。那一天真是热闹。
摩挲的手指渐渐停下。今天下班之前,得去给主管请个假,段安年思忖着。
二
华灯初上,摁下车钥匙,圆润的车灯闪了一下,随后车门自动打开,段安年钻进这辆半年前买的小车里,整个人缩小了一圈。下午故障的代码依然在脑子里四处游荡,他下意识地挥了挥手,质量较轻的函数,就先从他发烫的脑子里蒸发了出去,但是王子悦寄来的请帖,还是沉在了最下面。
直行,右拐,都市的霓虹在段安年的眼前不断游移,双向八车道上车流如织。在等红灯的间隙,段安年看到最近的公交车站旁挤满了和他同样疲惫的年轻人,众人裹紧了衣服,仿佛一排排刚抽完血的青色河虾。
出神的片刻,红灯跳到了绿灯,前车缓缓启动,灵魂回归,段安年轻踩油门跟上,后视镜里,那群青色的河虾依然在寒风中颤抖。
右拐,再直行,左拐,戴着白手套的保安向段安年和他的小车行注目礼,小区门口的道闸杆缓慢抬升,段安年将车驶入地下停车场。熄火,拿走车钥匙,上电梯。
在家门口的指纹锁解锁的间隙,段安年终于有了片刻放松的感觉。
解锁成功,门锁屏幕上的微笑脸和电子音机械地重复着主人欢迎回家,推开门,段安年看到老妈做了一桌好菜,老爸也久违地开了一瓶好酒。
“怎么了,今天这是什么日子?”段安年拿起筷子,径直坐在了餐桌旁边。
“儿子,快尝尝,看妈做得好不好吃!”段安年妈妈用围裙擦了擦手,坐在了他的对面,一脸期待地看着段安年。
段安年将一块红烧肉放进了嘴里。
“嗯……软烂鲜香,肥而不腻,简直是小时候妈妈做的味道。”
段安年妈妈被自己儿子这一副微闭双眼、摇头晃脑的美食家模样逗乐了。
“那也尝尝其他的,儿子。”
坐在旁边的爸爸也眯着眼,尝了一口酒,又夹了一颗小碟子里的花生米。
段安年搞不清楚今天这是什么情况,又不是逢年过节,不过也不至于胡思乱想,耽误吃饭。
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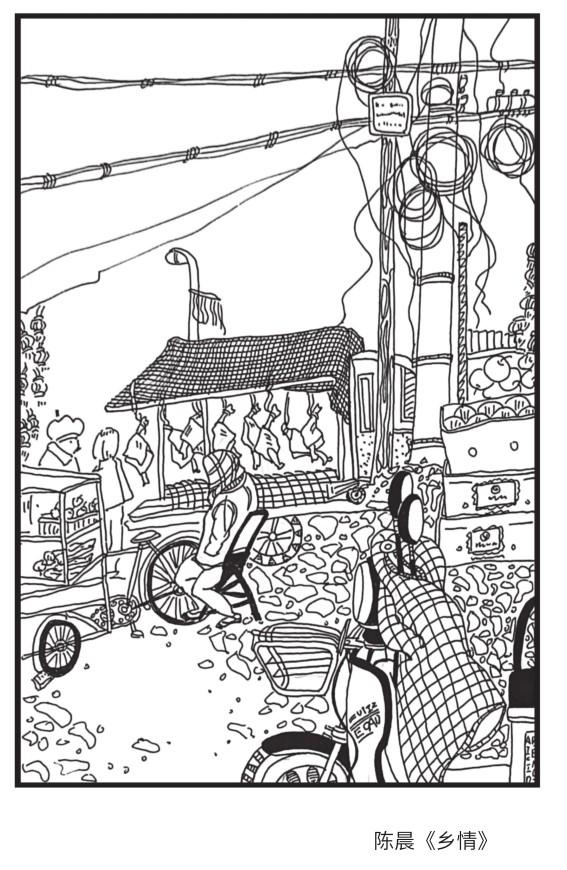
段安年妈妈一脸幸福地看着段安年狼吞虎咽、喉结上下疯狂运输的模样,本来还想叫段安年陪他爸喝一杯的,不过一想到现在的年轻人也没几个喝酒,之前过年回老家,段安年某个远房表舅要他陪着喝一轮,段安年百般说辞,见最后推脱不了,竟然直接起身坐到了小孩桌。
再说了,还有事要给他讲。
“儿子,吃完了妈和你商量一件事啊?”
段安年停止了咀嚼,含糊不清地问了一句:“啥事?”
“你先吃。”
段安年爸爸又喝了一小口酒,说让段安年先吃完饭再说。
吃完了的段安年心满意足地歪斜在客厅的沙发上,段安年妈妈感觉事情成了一半,拉着段安年爸爸笑吟吟地也坐了下去。段安年爸爸拿起茶几上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根烟,青色的烟雾向上,歪歪扭扭,老头的表情隐藏在了烟雾中。
“儿子……”段安年妈妈在斟酌着语句。
“妈,啥事你就说吧,不是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嘛。”段安年用一只手来回抚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皮,另外一只手则在惬意地刷着手机。
“前几天隔壁的张阿姨说,她家姑娘也是今年刚毕业找工作。那女孩子我见过,人挺好的,善良,能干。要不周日……咱两家一起在家里吃顿饭?”
段安年听到这话,一下从沙发上坐直了,条件反射一样,说:“妈,我才毕业半年呢,工作都才几个月,还小,不急。”
段安年妈妈见自己儿子又装小,连忙反驳:“不小了,你都二十五了,过完年就二十六了。”
“那六月份我过完生日,我又二十七了?”
“不然呢?”
段安年爸爸也赞同地嗯了一声,气息将烟雾向前推了一下。
本来是想用半年长两岁的事情提醒父母虚岁不靠谱,自己还小的,但是看见父母都这么认同这套关于年龄的陈旧算法,段安年泄气了。在岁数这个问题上,当他开始争的时候,就已经向父母说明,他是真的不小了。
“妈,我还小,再说了,我工作也忙,这事不急,您二位又不是很老了,要急着抱孙子。”
段安年妈妈见段安年上一秒还说吃人嘴软,下一秒就油盐不进,便开始打起了感情牌,什么趁妈年轻帮你和你媳妇带孩子,没有家庭的人生很孤独,什么年龄就该做什么样的事……一顿输出下来,段安年不为所动,段安年妈妈倒把自己的眼角说出了泪花。
段安年也有点烦了,刚毕业,家里就开始张罗着给他相亲,一周两个,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时间就定在了他不上班的周日。可相到今天,浪费休息时间不说,也没有出现什么重大突破。
没有想到自己亲妈,要把相亲的地点从咖啡厅搬到家里,还是对门张阿姨的女儿。那女生他见过,标准的过日子的好伙伴。唯一的问题就是,段安年不喜欢她,在段安年的心海里,那姑娘翻不起任何波澜。
“妈,反正我是不会见的,那女生我不喜欢,不合适,要是你和我爸真的急着抱孙子,不是还年轻嘛,国家又鼓励三胎,你们自己生,我肯定支持,还得生两个!”
听到这话,段安年爸爸咳嗽了一声,将烟头燃起的烟雾都咳散了,段安年妈妈则是气不打一处来,生儿子是生儿子,那能和生孙子一样吗?
“那你说说,段安年,你喜欢什么样的,相了那么多个,一个都没成,到底是人家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不会还喜欢小悦吧,人家都要结婚了,都要结婚了!”
段安年妈妈将最后一句话的尾音拉得很重很长。
段安年用求助的眼神看了一眼他爸,刚刚咳散的烟雾又重新聚拢,段安年爸爸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抽烟。
“我去洗个澡,今天累了。”
段安年丢下这句话,留下了一脸沉默的父母,转身向浴室走去。
头顶的花洒抛出冒气的热水,将脑袋淋了个透。段安年闭着眼,任凭水流流过他的额头和脸,那封红色请帖的女主人也在一片氤氲之间,从他的心底浮起,借着没来由的酸楚,由小变大,穿过他的胸膛,径直来到了他的身边。
三
王子悦是段安年的发小,两个人是一个小区长大的,幼儿园毕业就被分到了同一所小学,双方父母进了微信群才惊讶地发现,这俩孩子竟然是一个班的。于是一合计,干脆一家轮流接一天,接的大人负责把小朋友一块儿领走,再送到各自家楼下。
每天回家的路上,两个人吵吵闹闹。不是段安年欺负王子悦,王子悦哭哭啼啼地给段安年妈妈告状,就是王子悦莫名其妙地生段安年的气,说今天不喜欢段安年了,紧接着就是把脚一跺,嘴一撇,连手都不给他牵。段安年这个时候只能仰起头,一脸无辜地问王子悦妈妈:“阿姨,我干啥惹她生气了?”
太阳升起又落下了两千回,从家到学校的这段路上,段安年和王子悦一起走了六年,可没想到小升初的那次考试,段安年因为贪玩,去了一个稍差的学校,而王子悦则是超常发挥,考入了市里的一所重点中学。王子悦一家为了陪读,索性搬了出去。
刚分开的时候,两个小朋友都还会用电话手表约定好时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每天晚上,段安年看着窗外的灯火,都会抬起手腕给电话手表那头的王子悦说,他段安年今天又干了什么大好事,结交了几个新朋友,还不忘承诺等楼下的竹蛋长起来了,就第一个挖给她吃。而另一头的王子悦,总是用双手紧紧握住那只和段安年颜色配对的电话手表,一边听着段安年如同大将军般的叙述,一边想象着声音那头,不断模糊又不断鲜活的、有关段安年的模样。
也许是上了初中以后,王子悦的学习压力更大了,段安年的玩心也没有减,两个人还是渐渐没了联系。本以为缘分就这样结束了,直到段安年他爸过年吃饭的时候,顺嘴说了一句:“段安年,你的小女友呢?怎么不领回家一起吃饭了?不会是喜欢上别的男生了吧?”
段安年爸爸爽朗的笑声,没有让小段安年将嘴里的饭继续咽下去。他像是玩木头人被捉的一方一样,一动不动,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什么话来。最后他胡乱扒了几口饭,撂下筷子说,不吃了,他要去小区竹林里挖竹蛋。
段安年说的竹林,是小区在开发的时候就种下的,可能是天天经过的缘故,所以一直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变化。一家人每次路过这片竹林,段安年爸爸总是摇头晃脑地对段安年说:“竹子厚积薄发,几年不长,夜里一场大雨,第二天醒来就能蹿几米,我们要学习竹子的精神。而且竹子还会下蛋,叫竹蛋,炒来下饭吃,香。”
做人的精神小段安年没有听进去,但是竹子会下蛋勾起了他极大的兴趣:竹蛋?竹子的蛋?小竹子是从蛋里长出来的吗?段安年想象着一场暴雨过后,在竹林的枯枝落叶中,一颗颗洁白的竹蛋出现细细的裂缝,裂缝逐渐扩大,有蛋壳开始剥落,掉到地上,一颗颗小竹子探出了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甚至还发出了小兽一般的叫唤。
可惜今晚的小段安年还是没有找到竹蛋,因为突然下大雨的缘故,他出去了一会儿就心事重重地回家了。
第二天中午,段安年妈妈轻轻敲了敲段安年的卧室门,手里是给他的压岁钱。在段安年接过红包,开心地说着谢谢妈妈的时候,段安年妈妈无意间看见他的书桌上,摆上了几本他从来都不写的作业。
那天以后,段安年妈妈发现段安年真的长大了,以前的小霸王不玩了,捉鱼摸虾不干了,也不带着小朋友们去废弃工厂“探险”了。段安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回家写作业。
段安年妈妈看在眼里,既为段安年的转变而高兴,也会因为深夜看到儿子的卧室门缝下依然透着光而心疼。
寒来暑往,一晃中考就结束了,段安年成功考入了王子悦三年前考进的那所重点中学。王子悦不用说,还没中考就被学校“内定”了,依然是本校高中的重点班。
段安年妈妈悄悄联系了王子悦,说是要给段安年一个惊喜。
其实段安年也打着一个小算盘。他知道自己中考成绩还行,努力没白费,学校是和王子悦一样了,但是分班他没底,所以他准备摸黑候在学校的大门旁,第一时间冲进去看分班结果。
八点整,学校的保安撤掉了警戒线,在段安年冲进去的背影后面,是乌泱乌泱的人群,其中也有被挤在最后面的段安年妈妈和王子悦。
段安年仰起头,看着告示板上那二十多张用A4纸打印的分班名单,一行行地查找着自己和王子悦的名字。
与此同时,王子悦和段安年妈妈也悄悄摸到了段安年的身后。
三年不见,王子悦惊讶地发现段安年长高了。刚分开那会儿,自己的个子和他齐平,偶尔还能打赢他,但现在只能到他的下巴了。他整个人也瘦了,以前肉嘟嘟的,现在有棱有角,肩膀也有段叔叔那样宽了。
两人的目光在他的身上不断游移着,几乎是同一时间,王子悦和段安年妈妈都注意到了段安年的后脑勺。
段安年从小就是自来卷,在那一绺绺盘曲着的头发丝中,有一根白发从后脑勺上直挺挺地钻出来,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像是一根晶莹剔透的鱼刺。
段安年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和王子悦的名字,在一个班。他长舒了一口气,心中的鼓点开始奏响,变得激昂猛烈。他想要马上找到王子悦。
段安年转过身,发现自己老妈和王子悦就站在他的身后一动不动,他太高兴了,以为她俩红了眼眶,也是因为知道他段安年和王子悦,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
于是高兴的段安年展开双臂,紧紧抱住了哽咽着的两个人。
四
加了三天班,组里的工作差不多完成了,剩下几天就是维护。同事们早就撤了,小李也一样,说是要去做个美甲奖励自己,整个办公室就剩下段安年一个人。
他现在还不是很想回家,摘下眼镜,揉了揉发胀的双眼,午夜时分,窗外的高楼大厦变成了烧焦的棉花糖,不时有鸣笛的声音传来。段安年看着玻璃墙里倒映的脸,只有大致的轮廓,迷茫,憔悴。
家里对于他相亲的事,开始步步紧逼了。前天对门的张阿姨真的领着自己女儿去了他家,他一进门,就看到四个老人齐刷刷地盯着自己,脸上堆满了呼之欲出的笑,好在那姑娘倒也没有看他,只是在一旁漫不经心地刷着手机。
段安年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强撑着吃完那顿饭的,又是如何加了那姑娘的微信,硬着头皮聊下去的。
微信里全是单方面的绿色气泡,早上的问候,那姑娘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复。和段安年想的一样,他看不上人家,人家又何尝不是举着手机上的聊天记录,大声地向自己闺蜜吐槽:“这人真烦!明明不喜欢他,他还一直发消息!”
不发怎么行呢?毕竟家里的两个甲方可是很重视这个项目,前期投资了那么多,一毕业自己就“全力倚父”,靠着家里买了房和车,还有时不时的额外赞助。随便拿出来一样,段安年都知道,自己作为乙方,没有微笑也要挤出微笑服务。
段安年麻木地刷着手机,朋友圈突然多出了一个小红点,像是水手看到了海岸,段安年急匆匆地冲进去一看,是王子悦的更新。
不是文字,没有图片,只是推荐了一首歌。

段安年从裤兜里掏出耳机盒,取出耳机塞到了耳朵里。歌不是很长,叫Afterlife,听完了一遍,段安年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最好再下点雨。差不多收拾好了心情,他默默地给王子悦的更新点了一个赞,准备下楼去。
同样的华灯初上,同样的摁下车钥匙,同样圆润的车灯闪了一下,随后车门自动打开,同样的段安年钻进了同样的车里。
车靠着肌肉记忆往前开着,不回家又能去哪儿呢,可家里越是操心他的终身大事,他脑子里关于王子悦的回忆就越清晰。
五
段安年记得最后一次和王子悦散步,是在大三开学报到的那个晚上。王子悦在那个寒假留了校,兴致勃勃地说等他来了要去接他,有个好消息要和他分享,等两个人坐了十几站的地铁,赶到校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那天教学楼下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整座学校都被一团青色包围,光线是青色的,头顶的月亮是青色的,就连雾也是青色的,他和王子悦就这样并排行走在这团无边无际的青色之中。
王子悦蹦蹦跳跳地拉着段安年的行李箱,行李箱的轮胎摩擦着地面,发出连绵的辘辘声。
“安年,你这学期课多吗?”
“还好吧,你呢?”
“我都快修完啦,大二真是忙死了。”
“也是,那这个学期你有啥打算呢,子悦?”
听到段安年这么问,王子悦侧过身看了他一眼,幽幽地说:“我看了排名,再坚持坚持,应该是能保研的!”
段安年把手伸进衣兜里,里面有王子悦接到他时送给他的小礼物,一辆小汽车模型。看到王子悦微微泛红的脸颊,他就莫名心痒。
他不是没有想过表白,甚至很早就想了,在高考完的那个长暑假,他和王子悦在家里的支持下,一起结伴出游,把周边的省份都逛了一遍。山湖塔河,吃喝玩住,王子悦一路上照顾着段安年,几乎成了他的私人导游兼生活助手。在回家的列车上,段安年的话都到嘴边了,可是看着眼前这个把邻座的小朋友逗得嘎嘎笑的女孩,他也只是把礼品袋上的提绳,在手指间绕了一圈又一圈。
反正认识这么久了,也不急,段安年觉得,早晚都是他的。
“子悦,那你要是保本校,我就考本校的研,要是保外校,那我就考外校。”
段安年深吸一口气,接着说:“不过你要是保研了,可不能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啊。”
王子悦被他这话逗乐了,嗔了他一句:“还不一定能保上呢。”
段安年叹了一口气,他相信王子悦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好像不太行,在他这个专业,大家都在一门心思地挣外快,毕竟进大厂不要求会做试卷。
“确实是好消息啊,子悦。”
听到段安年这么说,王子悦倒是吞吞吐吐了:“不只是这个啦,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
“到那个草坪再给你说!”
王子悦所说的那个草坪,在图书馆楼下。草坪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但是在草坪下面,学校还挖了一个很大的人工湖,很适合坐着聊天。
第一次去大学报到,收拾好宿舍,王子悦就兴冲冲地拉着他来到这个湖边,两个人沐浴着夕阳,走了一圈又一圈。
两个人一路上说着闲话,王子悦说,她们专业有一个人他绝对猜不到,是以前班上的同学,现在很优秀,很受大家欢迎。段安年问她,是谁?王子悦眨了眨眼,说是伊素光。段安年哦了一声。对于这个男生,段安年只记得他字写得很好,作文也不赖,考试的时候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那会儿班上有些女生仰慕他,故意喊错他的姓,叫他:一束光。
段安年和王子悦就这样慢慢逛到了图书馆的草坪上。夜游的人不是很多,三三两两,像泼墨的点一样散在各处。段安年给两个人找了块较为干燥的草坪,这块位置极好,既可以小坐不湿裤子,又可以俯瞰整个人工湖。
月光下的湖面,一根又一根的银线正贴着湖水随风飘荡。
王子悦选了个视野范围内的地方放下行李箱,坐了下去,双手抱膝。段安年也陪着她一块坐了下去,见王子悦一动不动,段安年悄悄往她那里挪了挪。
王子悦沉默地看着湖面,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安年,老师跟我说,明年开始学院有公费留学的名额,总共是两个,从保研的名额里面选……”
段安年听到王子悦这话,随手拔起了脚边的青草,冷手,他假装漫不经心地揉捻着。
“你想去吗?”
“想。”
有学生传言说夏天的早晨,这个人工湖边会聚起无数的水泡,等到太阳跃上枝头,有的水泡会顷刻破裂,但也有水泡却能乘着阳光,缓慢升空。王子悦在听了这个传闻以后,拉着睡眼惺忪的段安年蹲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没有看到那梦幻的场景。
“安年,我能出去的话,可能就不会回来了。”
像是被人抓着脑袋反复往水里摁,段安年一下子窒息,一下子又能大口呼吸。
在段安年的记忆里,他最后还是表白了,只不过王子悦在那天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只是安静地听他讲着。
等到王子悦说时间不早了,两个人起身,开始聊起以前的事,第一次相遇,第一次离别,第一次争吵,第一次和好……两个人从小学说到了初中、高中、大学,还有那块配对的电话手表,王子悦说虽然五六年前就开不了机,但她依然有好好保管。
一路上王子悦都有说有笑,段安年也有说有笑,行李箱的小轮胎摩擦着地面,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灰色的痕迹。
等到了宿舍楼下,王子悦主动提出抱抱段安年。
“怎么这么僵,感觉你穿得也不少呀,要再多穿点,我先回宿舍啦。”
王子悦的叮嘱像她一样,慢慢地消失在了视线之中。段安年呆滞了好一会儿,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行李箱,这才反应过来,原来王子悦已经走远了。
六
段安年觉得自己肯定是疯了。
从省城开车回老家,要将近三个小时,凌晨两点,高速路上,速度表在十一点方向摇摆,雨刮器一直来回刮动着。
王子悦给他打电话那会儿,段安年正在小区的地下停车场里倒车入库,还差一点点就完美倒进去了,兜里的手机却紧贴着他的大腿,有节奏地振动着。段安年很烦,那姑娘白天不回,中午不回,下午不回,偏偏挑这个时候回,饭点早过了,难道她和她父母又在我家了?
最后还是不完美的倒车入库,段安年愤懑地掏出手机一看,是王子悦的电话。
雨水哗啦啦地打在段安年的前车玻璃上,王子悦几年前送他的小车模型,正在余光里左摇右晃。大车到手的那天,段安年就把王子悦送的小车加了弹簧和基座,改装成了一个摆件,摆在了自己的大车上。
大车拉小车,他不敢再开快了。还记得第一次上高速,段安年握着方向盘的双手汗津津的,他爸坐在副驾驶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叫他往前开。段安年压着速度,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想超他的车,慢腾腾地开到了加油站。
这是他第二次上高速,视线里没有一辆车,一排排路灯发出蚊子一样的光,脑子里嗡嗡的。段安年留意到了这些光亮,但这些光亮很快也被暴雨遮掩。越往前开,段安年越觉得自己不是在开车,而是在黑色的汪洋里开一条破船。
当他接通王子悦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起初带着犹豫,段安年也犹豫,但他还是试探着问她怎么了。王子悦支支吾吾,反而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一般,整天被逼着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相亲,开心不起来。王子悦笑他,说他眼光太高,相亲不是谈恋爱,喜欢不重要,再这样下去,他迟早要打光棍。结果段安年听了这话之后,神经分岔一般说了一句:“你分享的那首歌很好听。”
沉默,紧接着就是低声呜咽,段安年紧张了,赶忙问她:“是不是伊素光欺负你了?”对面响起抽纸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王子悦在电话那头说:“没有。”
王子悦刚出国那会儿,把段安年拉进了一个微信群,里面只有三个人,另外一个是伊素光。一开始的时候,三个人还会在群里兴致勃勃地聊天,分享着异国的见闻,王子悦甚至还时不时地艾特段安年和伊素光,提醒他们段安年的学院真不是人,怎么会不给自己的学生争取出去留学的机会。
之后没几个月,段安年看着异国他乡的王子悦和伊素光在群里记录着他们的艰难日常。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段安年很受挫,他只能干着急,帮不上什么忙。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的疫情,让段安年觉得前路茫茫,他开始逃避有关王子悦的消息,甚至开始逃避王子悦。
直到这通电话,段安年这才明白,这些年王子悦是如何与伊素光在国外相依为命,两个人的感情是如何升温,三个人的小群又是如何开始沉默的。
车还在雨夜里疾驰,段安年重复咀嚼着刚刚的那通电话,王子悦在电话里跟他说,她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坚持把婚礼放到国内,伊素光已经拿到了绿卡,她的也在日程上了。家里老人退休了之后,她的爸妈和伊素光的爸妈都爱上了旅游,四个老人一起结伴出去游山玩水,很快走遍了半个中国。
本来他俩是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把双方父母都请过来的,中国的山山水水看腻了,那就看看洋人的。伊素光一开始也是这个想法,可王子悦说她在某天夜里醒来之后,看着四周黑漆漆的墙壁,还有枕头旁边睡着的伊素光,突然就下定了决心,要回国办婚礼。
王子悦说伊素光还是那副老样子,只要是王子悦的决定,无论多么离谱,他都支持。两个人去请假回国的时候,主任签好了字,还用带笑的怪异汉语对她和伊素光一字一顿地说:“型——分——快——勒!”
王子悦说她听不懂,但是一旁的伊素光却摇摇头,纠正道:“Thats not how its pronounced,follow me,新——婚——快——乐!”
主任听了之后,在一旁有样学样:“型——分——快——乐?”
王子悦最后说,结婚之前,她想见他一面。
七
What is passion?
Is my desire sin?
What is freedom,
If theres a price,
That we have to pay? have to pay...
(情为何物?若欲望能激发起罪恶,何为自由?若以代价为筹,那我们岂非要付出全部?)
王子悦分享的歌,在段安年的耳朵里回荡,时间虽然在驾驶室里停止了,但是依然哗啦啦地流过高楼的玻璃,流过绿化树,流过小区路面停放的车顶,流过下水道,流进地底。
离王子悦的家越近,段安年的心情就越复杂:激动,害怕,还有莫名其妙的勇气。他看了眼手机,除了半个小时前的电话,两个人最近一次聊天,还是在两周前。那个时候王子悦问他搬家没有,想给他寄东西,他回复说,早搬了,寄到公司吧。过了几分钟,王子悦回他说,好。
那个时候他没有问王子悦要寄什么,值得让王子悦大老远寄过来的东西,他觉得应该挺重要的,可后面轮到自己加班,他还是把这事给忙忘了。现在想想,快递盒被王子悦用胶布裹成了那个样子,她是希望自己亲自打开它,还是希望自己永远不要打开它?
凌晨四点,车窗玻璃干了。
手机从手心里传来一次不大但是清晰的振动,王子悦的思绪被拉回了现实,她紧张快速地点亮了手机屏幕,是段安年的消息,只有一句话:“我到你家小区门口了。”
王子悦抓了一件长外套套在身上,也不管身上穿的还是睡衣,就冲了出去。
五年的时间,王子悦发现段安年变了,变成了面前这个双眼泛红,胡子拉碴的成年人。
段安年也发现王子悦变了,以前总觉得她活泼可爱,时刻散发着青春的光芒,可现在看她的眉宇间,也有了成熟的感觉。
两个人就这样呆站在段安年的车前,不时有汇聚成珠的雨水从旁边的树上掉下来,砸在地上。
王子悦首先打破了沉默。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
段安年的嘴唇有些许干裂,回答她说:“嗯。”
空气凝固了一会儿,段安年主动开口:“去逛逛?”
王子悦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段安年侧过身去,给王子悦拉开了车门。
在进到驾驶室之前,段安年回头看了一眼王子悦家所在的小区,他发现有一户人家的灯一开始是亮着的,随后又熄灭了。
责任编辑 猫十三
作者简介
辅秦,本名杜开国,2004年生,贵州大学中文系在读本科生,有作品见于《水城文学》《乌蒙新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