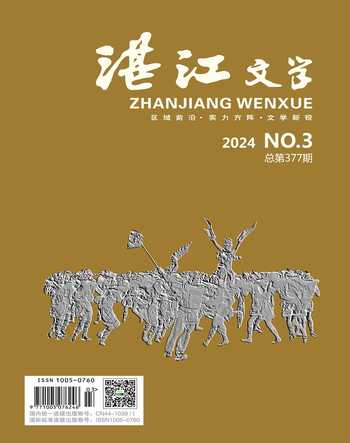三体空间的时间孤独和语言迷宫
张楠
风从《玫瑰湖畔》吹来,它是轻的,轻过生死,也轻过轮回。而时间重于湖水,它在湖水的深处沉没着世纪之音。沿着湖畔行走,你要学会遗忘,遗忘一些人,一些事,甚至遗忘自己和那来自母体的语言。又要去打开认知,在一个蝶变歌剧中,接纳着虚无和现实的隐忍,生死之间的永恒之物,或者从一个百年孤独将读者引向了时间孤独。
我是读完《百年孤独》再读张苏楠的小说,似乎为了增强一些阅读能力,似乎又从《百年孤独》中试着解构一些关于小说的密码,像拿到一把钥匙试着去打开另一把锁。如果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读小说是咀嚼着一些干草,我承认我有吃力的苦涩,但是通向语言的迷宫似乎又可以相通的。可以说,在三月我是抱着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走向了张苏楠的三体空间,他又轻而易举的覆盖了我的奇异之心,在想象世界和语言的迷宫之中,我总是有一种错觉,我所钟爱的两个大作家都在,一个马尔克斯,一个博尔赫斯,仿佛他们都给了张苏楠一些创作秘籍,而我一再地追崇他们,只不过是在别处能认得他们的魔力而已。在玫瑰湖畔我迷失在语言的风暴和故事的癫狂中,以及细节之中的漩涡吞噬,我的确是要交出许久以来的空白,我会在失语之后,重新学着说话,在思维困乏之后,又重新学着悟道。
当然你开始会莫名于玫瑰湖畔的狂澜,它似乎都没有激起涟漪,也无法找到它的象征,以及那宫殿与爱情有关的想象。好像只是湖水的无声了。或许作者的高明你要在这本书中走了很久,才会找到一朵叫玫瑰的花了,或者它根本不是花,只是一个地址,出处,一条湖的悠远。为此我想到了博尔赫斯的玫瑰,“一代又一代的玫瑰/在时间深处相继消失/我希望失逝去的事物中/有一朵不被遗忘/没有标志或符号的一朵。”只是玫瑰湖畔绝然不同于玫瑰的本意,它也并非是一个模糊的花园。如果陷落于《玫瑰湖畔》不是花朵的芬芳,而是时空的冒险,我要说那也是孤独的冒险,但不仅仅属于我,而属于每一个小说的人物,也属于每一个读者。孤独之上它没有时间的限定,一百年,几百年,一千年,光阴唏嘘,张苏楠构造了一个无限的三体空间,你不知道你在哪,你是谁,一直以来的疑问和怀疑都如同湖水的倾斜。天空似乎在下雨,雨中有飞行的刀剑,雨中有划过的银河,雨中有消失的流星,雨中也会在滋生着爱情。你会觉得冒险于爱情的颂生和麦心要一直抱着爱情的火焰与时间抗争才应该是一种完美,只是当死亡成了尘埃,一切的存在或活着应该属于时间上,空间之上的向死而生,或者科幻了他们一直活着的理由,从张苏楠的三体空间传递到读者的心灵空间。
三条平行线,划向了时间,时空和心灵。站在上面它所呈现的似乎都是我从未有经历的,即便我曾用一个月的时间在《百年孤独》的马孔多小镇徒步行走,一块吉卜赛人的飞毯也会把我送向遥远,但是一定离太空遥远,离银河遥远,离一个梦也遥远。张苏楠站在了月球上看吉卜赛人的飞毯,那么我就更为渺小了。蝼蚁一般的迷恋,也只不过是向着《玫瑰湖畔》
说出了精神向度,它同样也可以给以缪斯的浪漫主义观念,又给以古典的白话回源,事实上所有的语言碰撞,让我在不同的空间被捕获,被湖水捕获,也被玫瑰湖畔的阴影和星光所捕获。当故事带着棱角,滴血的死亡像血吸虫进入了人物的身体,孤独和冒险也会得到一种切肤之痛。意义之中我又倾覆于张苏楠的写作功夫,或写作艺术,他有了魔法般语言的掌控能力。在宗教和科幻,古典和神话之中,他运筹帷幄。最为通俗的说法就是,他懂得太多了。以至于我要不停地看,不停地琢磨,像一个外星人进入他的星球,几次被那些闪光的事物昭示,几次又陷入了懵懂之中。像被一块黑布蒙蔽了眼睛,我必须用心去触摸才可以找到他的时光之门。他所铺设的庞大孤独,并非以百年为限制,并非以生活为证据。生死又是它的序言之中的主体,超脱于现实的永恒记忆,以巨大的空间推移着玫瑰湖畔。
小说的卷一从战后疑云开始,瞭望塔上仿佛有一双世纪之眼,洛克活在了时间的隐痛之中。“就算发现真相又能怎么样呢?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瞭望塔工人的话。”“这是三条看似平行的直线,可是如果我的本子足够大的话,它们总会在某一个点上交会,如果你有想象力,就不难看出学一点。”如果沉稳于叙述,多维叙述是一个小说家的本领,他在无形中展开的铺垫只是片言,读完了,你才会觉得他的举重若轻,像一只鸟的灵魂,它在飞。几句话打开的门楣,像整个小说的总结,也是开始。当然张苏楠的语言能力远不止这些。当故事在叙述之中跳跃,在个性视界中精神传承,你从中收获的正是它的本源探秘。“机械联盟决心诉诸武力,维持霸权,他们手中的王牌就是‘通感机甲,这种战争机器让光荣欧亚最精锐的两支集团军都毫无还手之力。战争的天平落向机械联盟一侧。可是,双方爆发的两次全面冲突,都被一道蓝光极影化解。人们看到的是一条华夏神话里的神龙,将一台台坚不可摧的机甲化为熔沸的铁水。”是的,这样奇幻的场景,我只有在张苏楠的小说中才会遇见。
“只不过当人们以为救世主真的存在,绝望的祈祷终于得到反馈之时,龙再也没有出现。”一条龙成了无声的精神图谱。在我看来张苏楠的语言诗性也随之而来,他在写作的常态之中加持着诗歌的审美纬度,我又觉得他是一个好诗人。当然他的语言空间也放大了无限的精神空间和未来结构。读者要在那些空间意识中寻找着一个存在的时空,而并非虚无。“我找到了!我们所能见闻的世界之外,一定还存在一处不为人知的空间,本应只存在于传奇中的生物就来自那儿,乔伊意外地打通了前往那里的通路,也迷失在那儿!而要想知道是谁制造了欧陆浩劫,也只有从那个地方才能找到答案。”这里有许多陌生化的语言,当我读完又会发觉“空间”“生物”“欧陆浩劫”这些都是隐喻在文体中的线条,但对于一个写诗的读者来说,我读的时候又仅仅当成了一些意象,如此的荒谬,我也想嘲讽自己一番。随之而来的人物登场,又让我看到张苏楠对于细节的描写,掌握的如丝线的柔韧,细腻之中都可以牵动着整个小说的情绪。对于细节的描写我是在读高研班听黄发友老师的写作课时,黄老师特别强调的内容,也是我特别记住的内容。“无论如何,温柔的细雨照旧无声坠入硬实的土地,这一夜终将过去,什么都没能挽回。”小说以细雨的温柔划过人心,它有着雾水般的轻正好与土地的坚硬对立着一种决绝。我读到了也是诗性的语言,在它的现实精神中的有了特定指向。顺着它指引就会有了时间意识,空间意识。
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跨度在时空的河流,湖畔往事到底是往返于多少年,多少个世纪呢?三界之中,谁又在主宰着这个世界?“异界不灭不生,无故无新,恒如残烬,不复燎燃。”作为一个读者,我首先是在学习张苏楠的语言,因为一下子似乎都找不到南北了,语言的特质又让我钦佩他,他能在古典文学中游刃有余。“北地广袤,毗连冰洋,蝎尾湾伸延入内陆,同黑墙古林接壤一处。望龙海渡历经风雨洗礼,伫立湾头,已然连通大地血脉,共海天浑然一景。此处本为圣王御用旧港,昔时龙焰炽烈,海外应龙之息岛高炉矗矗,炉火熊旺,握有秘术的地精一族世代于焉生衍,为圣所炼造萤金。”语言之内它是狂热的,语言之外它又是冷静的。对于这样的语言我不得不说着迷,像我走进了博尔赫斯的时空,通常他给我的,都会是史诗或篝火般的宽宥和美学延伸。芸芸众生,行走于此,我也学着一个古人一样说话,好像光阴慢了下来,只是那些刀光剑影又会在心底落下疤痕,所以语言的功效又会达到一种语言时效,被那些寒光穿过,作为一个读者也会遍体鳞伤的。“元清流已是怒不可遏,手里的长剑被他手上的力道攥得铮铮有声。原本心底被封存无隙的烈痛重又炸裂开来,直透骨髓。”还有更多的如此声像具存的句子,像一个武术大片,我也想当一个侠客,为一些事不平,为一些人两肋插刀。“爱意横扫了他在虚空中悬置的不安,好像他来到这世上,历经苦痛折磨,终于沉静成熟,并非为了去死,而是为了更长久的存活,为了有朝一日,报答沉在心底的母爱。”所有的活着都以生在抒情,精神境遇之中它又是亲情正本,正在打动着读者。小说之中除了故事,又无不在历史经验,个人经验中提升着作者的人性关怀。
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再次回归于太空之旅。星海浩荡,回归于人的尺度,张苏楠又在提出了关于人性的诘问。关于人类的现实对比,并发出最为客观的正向凝视。“人类极其渺小,甚至我们的太阳系也局促拥挤得可怜,跟宇宙的恢宏相比,连一粒粉尘都比不上。可到了具体问题中,我们就遗忘了这一点,或者选择忽视它,因为我们坚信宇宙共享相同的物理和生态法则,在这一系列法则的制约下,人、地球、太阳系的大小都恰好符合孕育智慧生命的条件”。或许作者站在一个时空之外看世界,而作为读者就必须要跟着他的所有发现,美学发现,哲学发现,以及情感发现……。最终抵达人与自然,人与星球的终极关怀。“我们依然有希望在人这个尺度上,找到地外文明,虽然,那庞然者的阴影,已经降临。”雷杰明的笔记也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在每一个章节作者依然用它庞大的语言构筑着一个魔力,超脱,科幻的空间维度和诗学编年体系。“消失的鸟,消失的小孩,消失的自己,只有梦才能解析这些确凿无疑的存在凭空消失的根由。”我想所有的消失正是一切的存在,一如博尔赫斯的诗句:“构成你的物质是时间/无尽无休的时间/你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合上《玫瑰湖畔》,我恍惚于现实的朴实性。一如生活脱下了语言的华服,也就脱下了光芒和魔力,接收到的事物只是一些粗糙的碎片,它们每天都在漫无目的碰撞着。好像这是读张苏楠小说之后有了诗学焦虑。但《玫瑰湖畔》似乎也是一个自我对照和自省的镜子,走进去,再走出来,谁都可以获取时空之上的无限回声。而《玫瑰湖畔》是属于张苏楠的命运共同体,我想这也许会成为张苏楠文学创作的一个无限序列的开端。我以《三体空间的时间孤独和语言迷宫》为他的现在和将来的写作前景命名或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