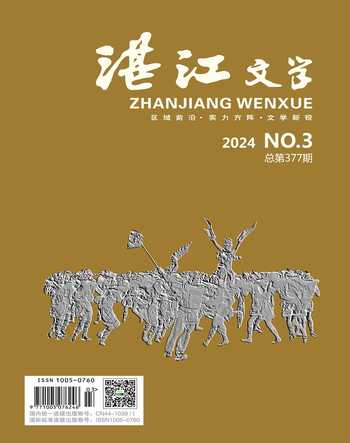救援记
董洪良
我已渐渐趋于昏迷。但我却能知晓救援中发生的一切。
秋日的午后,阳光煦暖,照耀着这茫茫群山和深涧峡谷。微风起处,绿树摇摆,鸟雀鸣叫;高山村镇,农户庄稼地里成熟待收的庄稼,露出欢欣的笑脸。蓝色的天幕下,远山苍翠,山河壮美,宛如一幅幅时代奔流中村美如画的美好画卷。一个男孩远离了位于这画卷之中的自己的家,走进了茂密丛林和山野。他是准备去山林里与鸟雀、昆虫和翻飞的蝴蝶、蜜蜂等交朋友的,或者说是去看看那些鲜花、野草,并亲近一下大自然。这是一种小孩子的天性和情趣。他要试着独自一人去发现未知的美好和愉悦。男孩的身上,似乎弥散着这片大山和土地的一些气质,比如坚韧、顽强、刻苦、洒脱,和祖上就遗传下来的那种隐身于体内的好奇和探索精神。因为,在全国乡村振兴的时代洪流中,他和村里的小朋友们,也不屑于再像前辈人一样走出大山,而是要靠着国家的良好政策、自己的勤奋与智慧,来创造和改建自己的村庄及家园。他这么想着,也这么欢欣鼓舞地四处观赏、游玩,好像这些平日里看惯了的大山和村庄,每日都在更新,并且越来越完美无比。
这个聪颖而乐观的男孩,看起来只有七八岁,脸上有着高山与阳光混合而成的健康色泽。他是享受到国家由扶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最小的受益者之一,在村上小学读书。他的父亲,是镇上和村里有名的摩托车骑手,因为,他不仅骑术好,重要的是,他曾经把大山的山楂、苹果、香梨、茶叶、核桃等物资,拉出了大山,以价廉物美的价格送到了县城,并由此中转发运,发往更多、更大的城市。当然,他也是县乡5G网络覆盖后,村上较早接触网络并玩起短视频与直播的“播主”之一,他把自己家乡的变化和山村美景推荐给了全国网友。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体里流淌着像国旗一样的鲜红血液,从不轻言苦难、挫折和失败,他的体内有着被新时代点燃的火苗甚至有着一种会燃烧火焰。这个男孩,也遗传了父亲这些优点,并运用到了日常生活。此刻,他在群山的某处山林之中,夸张地作出类似于征服大山、征服滚石、征服泥流和扶住树木摇晃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学校的老师和父亲在家时,也和他一起演练过!地动山摇之中,他发现自己的身体根本不受控制,而是抱着一棵树一起摇摆,或者下落,或者又是在说不清的下落里,努力地稳住身形,蹲伏,然后抱头。他发现自己四周,此时早已没有了鲜花和青草,天空也不再晴朗,蓝色的天幕上白云忽然不见,取代代之的是乌云。很快,他就被倾泻而下的山土和泥沙半掩,又被某几颗倾倒的大树遮挡住了。无巧不巧的,那些大树交叉地相拥,像搭建起一个临时性的大棚,呈现出“丫”字形或不规则的“井”字形,蓬松而杂乱的树枝树丫和绿叶,连同大树构建了一个不大的虚空的掩体,挡住随后再次下倾的土丘和泥沙——你可以说这根本不符合逻辑,但当时的实情的确如此!那个男孩,没有太多想象中慌乱,但被细碎泥沙和树枝扫中、而不是砸中的他,几近昏迷!
很明显,这里发生了震级很高的地震!
尽管男孩就快要昏迷了,但他警醒自己,绝对不能放弃。他慢慢积攒起全身的力量,努力地、缓慢和坚强地爬起来,并试着慢慢站立。他不知道现在所处的具体位置,也不知道村子和家里发生了什么。但可以想象,在成片大山垮塌的一瞬,这个乡村、镇子、县城和离此很远的地方,都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既然上天选择了战斗,那就必须要无畏地站起来,与之对抗!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想到了村里的玩伴和学校里的老师、同学,那是一种不可割舍的情感和奋勇的力量。于是,他体内的血液像父亲一样燃烧了起来,越燃越烈。而在不断的积攒力量和燃烧的过程中,他觉得空气似乎稀薄了一些,大脑里像缺氧一般,他感觉到有些昏厥,意识也不由自主地感到开始模糊,灵魂似乎在那一刻跳跃了起来,挣脱他的身子,一把扶住了他。像身子和灵魂,既融为一体,又可以在特殊时候独立的存在,可以做到脱离,相互搀扶和相互救助。
那个男孩不知在什么时候,终于站了起来!这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大河的边缘,河流很湍急。汹涌的河浪和怒吼的波涛,让他觉得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因为在很多年前,这条河流就挑衅过他的祖辈,但是结果呢,却被几根铁索和木板治得服服帖帖,再也没有任何的嚣张跋扈和张牙舞爪。接着,他发现湍急的大河之中,零星地散落着一块块巨大的石头,距离岸边也不是特别的远,看起来也就仅仅七八米、十来米的样子吧,如果纵身一跳,完全可以一步跨过河岸。应该说,这是自然界中假想的天敌,在威胁这座州城和州城里的人们,说小一点,这是在威胁他的村庄和家园。他准备一跃而过,毕竟,这在他看来,什么大河什么滔天巨浪,不过是一步之遥而已!此刻,他再次想到了父亲和村里的玩伴以及老师同学,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关切和思念,决定自己一步跨过去,或者像一只飞翔的雄鹰,立即飞过去。
但就在这时,他发现这条巨大河流的上空,一群人站在左右岸边,朝着虚空抛出了一根粗大的绳索,一个头戴头盔、脚穿警靴、身穿黑色特警衣裤的年轻叔叔正倒悬在绳索上,不断地向前攀爬着。那姿势,好像挣脱了地心引力,向着对岸勇敢地冲了过去。接着,是第二根、第三根。男孩并没有兴趣去细数。当时,他就在想,这根绳索和这群倒悬在绳索上跳舞的人,他们搭建起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窄、最细、最有弹性,但又是充满着最果敢坚定、希冀之光和欢欣鼓舞的“生命之桥”。其后,其他人也陆陆续续通过绳索所搭建的生命桥,通过了那条河流。男孩好像用了一种隐秘的力量,也很快跟上了他们。他悄无声息,以至于那些人并未发现他。既然家园遭难了,他便有义务和责任,与这些远赴而来的警察、森林消防员一起参与救援。尽管他小,但却连续作出了匍匐、攀缘、前倾、扑倒、打挺、背动、小跑等一系列动作和姿态,防滑刺靴、头盔、面具、防割手套、手电筒、背包、帐篷、睡袋等工具,也在脑海中试了一试,觉得极为顺手,丝毫感觉不到有任何的不适和障碍。他谨慎而小心地冒险前行,随时注意着余震和山间滚石、塌方和泥石流的发生。此刻,他控制不住对自己亲人,以及那些不是亲人但胜似亲人的人担忧,和救助她们的强烈渴望。
沿着奔腾的河流岸边,他继续往前。一路上,他看到身着橙红色衣服的森林消防员背着一个个受伤的人,这里边,有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有行动不便的老大爷,有头发凌乱却仍喊着孩子的阿姨和年轻妈妈,还有面色忧戚的小朋友,甚至于襁褓中的婴儿。他察觉到了地震破坏力带来的灾害的严重,很多不太明确具体方向的无声的爱的力量,在快速地聚集、凝聚,朝着这些受灾点和潜藏的风险之地奔赴而去,比如,他之前藏身的树木掩体,无数被毁坏的村庄和房舍,以及无数个废墟。突然之间,他觉察到了又是一阵摇晃,地动山摇之间,山崩地裂,那些山巅巨石,带着铺天盖地的滚滚泥沙,扑向山间公路,扑向峡谷和深涧……较之于先前,他觉得这次余震的毁坏力和伤害性,可能更大了,因为,这是距离前不久发生地震上的又一次灾难的叠加。他像一只敏捷而又吓蒙了的兔子,蹲坐在通往大山深处的林间小道上,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天地间发出的轰隆巨响,和巨响间略带细微差别的不同声音。地震带来的破坏,已经让原来的山体、山势和道路发生了改变,一时之间,没有了熟悉山峰的指引,没有了那些他认为熟悉的山峰上的大树作为参照物,他明显有些分不清楚方向了。他来不及分辨和细看,便跌跌撞撞地冲进一片林子——可能就是自己用树木做掩体的林子。余震波下,倾斜而交叉的树木那“丫”字形或“井”字形,似乎没有那么牢固了,毕竟,即便万物有灵,可树木始终还是树木,哪怕它是有灵的树木,也经受不住持续不断的天地震颤。他那娇嫩的皮肤,被树枝和滚下的泥沙划破了。遗传了父亲那大山与阳光一样的笑脸上,脸色虽然坚毅,但比之此前,却多了几分苍白。他把双手拱在头顶,像个“八”字一样保护着脑袋;因为逼仄空间的原因,空气变得更为稀薄了,它们不能像风儿和水流一样,自由地吹进来、漫进来。小男孩他看了看自己,他的呼吸还算平稳,却又细弱了一些;小心脏持续地跳着,一跳与一跳之间的频率也还算正常。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想办法,自己把自己拽出来,然后安全地带回去!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他开始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这片林子里,试图找个向阳的出口,可以钻出去。他觉得如果灵魂能够钻出去,那欲灵魂相连的身体,也很带出去。但是,那些平日里与他嬉戏的鸟雀,此刻不来和他聊天了;阳光也像去午休或打盹了一样,害羞地躲了起来,穿不透泥沙、巨石及由多根树木搭建起的临时空间。他怀疑,逼仄空间如果撑不住,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会在某一刻变成一个别人看不见的房间,把他永久地关在里面。
他的昏迷状况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过了不知又多久,感到自己的意志在与周边诡异的轰隆声的抗衡越来越弱的时候,他终于扛不住倦意,疲惫不堪地睡着了。在睡着时,他作了一个短暂的梦,梦到了村里新修的住房前后,父亲在焦急万分地找他,不断地换着他的小名。甚至,他听见了父亲嘴里喊着的“孩子”的声音。惶恐的黑和喊声,让他看得出父亲忧心如焚和为他而心碎。但是,在梦中,他却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来路,也找不到归路。奇怪的是,或许是口渴,或许是因为中午吃完饭消化后需要排泄,他又被惊醒了。
他又一次努力地站起身来。湿润的泥土,在没有阳光照射的时候,反倒生出一阵人体的寒意,令他暂时忘记了心中对黑暗的恐惧。也不知是基本哪种不确定的本能,抑或是某种信念,支撑着他来到一处绝壁的悬崖。上边,是山体滑落后光秃秃的峭壁,没有一棵树木、一颗青草,坡度近乎垂直;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河谷,看不见滔滔河水是否已被滚石征服,或者被其无情地阻断及掩埋。但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空之中,却开来了几台挖掘机。是的,他觉得应该给开挖掘机的叔叔阿姨道一句歉,因为他的确没有看清楚具体数量——但这绝对是欢欣的希望之光!只见挖掘机抓住一块块滚落的巨石,然后狠命地抱起,像宣泄着内心仇恨一般把它抛向了峡谷深涧;而那些随同巨石滚落的土丘、泥沙,却被抱起、铲平,而后用来堆坑、填方,继而铺平道路。男孩想着,这些曾经滋养过大山村民和山中生灵的泥土,怎么就一下和滚石混在了一起呢?它是不是因为地震,而无力地屈服并与滚石一并滑落,或者说,在滚石滚落时也曾在悬空中拉了它一把,只是力气太小而未拉住!男孩好奇地把眼光投向了绝壁悬崖的中间,轰隆隆的声音,此刻成了这片大山最美最险的协奏曲——他确定不是独奏,而是和大渡河边、那震中深处、那无数的废墟中的救援声,以及空中飞翔的直升机的声音,形成了一个个天籁般的音符,代替那些哀鸣、惨叫和哭泣!
从已经被开通生命救援通道的绝壁上退下来,男孩又费力地走进了悬崖前后的树丛。他尝试着从中穿过,这样就可以回到村子并见到父亲。刚才在梦中,父亲的焦急和无奈,太让他揪心了。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打通了生命通道的路上,穿着各式衣服的人,陆续多了起来。这让小男孩特别欣喜。有可能是在树木形成的临时掩体里待了太久,他的注意力悄然发生了改变。他没有像平时一样,礼貌地向这些行色匆匆的人问好或打招呼。远方,余震后的垮塌还在不断发生;近处,废墟中传来的呼救声,一声比一声弱。男孩看着听着,内心里开始有些惧怕起黝黑的树林来,他怕这些黝黑的色泽如果再配上暮光,那种幽深中的黑暗就会慢慢笼罩并袭来,令人更加地不寒而栗。
他想,必须要在暮光来临之前走出去才行!他加快了脚步,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呼吸有些急促,心跳也时快时慢,而模糊的眼光之中不知道何时竟升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这突发的情景吓坏了男孩本人,他不相信自己示弱了、哭泣了,更没有觉得自己会面临绝望和放弃。他想快些逃离这片树林和这几棵遮挡住自己的树,因为,空气已经变得越来越稀薄了。他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那些救援者的声音和脚步影响了自己的呼吸。突然间,他看到自己的前方有奇怪的东西正在移动。在他看来,可能是某种体型与他大小、但嗅觉肯定比他灵敏的一只狗,或是一双及几双孔武有力的大手,甚至是一把手电筒在树林、房舍和废墟间投下的虚光也说不定。在他的模糊意识中,他不敢确认和确定,尽管他先前在河流上空见过特警,但他对搜救犬还一无所知。毕竟,他想象中狗的样子都差不多吧。再说了,怎么会一下子就有了橄榄绿、橙红色、黑色、白色,乃至于灰色、青蓝色和村子里彝族同胞的服饰?他判断着这些颜色,更判断着这些距离,想着是不是彩虹的颜色,或者是去往天堂时,上天给人间留下的令人怀想的颜色。
一半出于惊奇,而另一半则处于恐惧。他自然不知道这正是解放军、森林消防员、警察、医护人员、志愿者和当地的村民,在他昏迷和震区灾民受灾的时候,全都一同参与了救援。
男孩子终于靠近了一些,他要努力地看清那些手,那些颜色。整个过程,推进得很小心、很慢,也很令人揪心。外面的人,可能怕滚石再次移动、滚落,砸中树木从而使其断裂,或是怕泥沙经不住这样的气氛和胆战心惊,从而偷偷开溜和钻进空隙,堵死了受灾者一息尚存的生还空间。他们从上边,从左边、右边,从前边、后边,甚至于从下边,小心翼翼地刨挖——因为男孩知道,这狭小而逼仄的空间是临时性的,是不牢靠和稳固的!
他觉得,如果把这个临时的空间比作一个鸟巢和爱的核心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是鸟爸爸鸟妈妈。他们各自都在暗中加油、鼓劲,像一个个与时间和危险赛跑的人,与自己比、与同行之人比、与天地比,与悬崖峭壁比,与废墟和即将到来的黑暗比。从四面八方,不对,是四面十方涌来的细小而温情的力量越来越多,越来越近:他感受到了这种爱的气息!
他觉得自己实在有些疲倦和调皮!他感到自己不能喊、不能打招呼,但是意识却可以漂移,虽然在昏迷中,但他还是努力地通过掩体的缝隙,偷瞄了几眼。此刻,一群人正在用他们的手和膝盖匍匐在地上。他们的腰上,系着急救包;他们的双手,在废墟一样的掩体上刨挖;他们的膝盖,扎在石块石子和瓦砾上;他们的额头,汗水直淌。旁边,还有扩胸器、急救垫和担架等应急救援设备。他们在面对每一捧刨挖开的泥土与瓦砾时,都会不自禁地颤抖一下;随着探测仪的显示和搜救犬的打转、犬叫,他们又感到庆幸,眼中再次充满了希冀。他们拼命而忘我地做着这一切,向着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一步一步地往前,一点一点地递进。随后,男孩把视野放得更开了一些,他终于发现那种充满悲凉与悲悯性的壮观:一个人,两个人,一小队人,他们在划定的搜寻区内搜救;又一小组人,一小队人,一大队人,在前赴后继,拼死奋战。时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停下来测探搜寻,另一部分人则会快步跟上,绕开他们,然后继续前行和展开救援行动。他们成千上万地紧急出动,队伍在群山和峡谷中分散开来,在树木和废墟中蔓延开来,仿佛无穷无尽。
偶尔,男孩也会看到这一群群人悄然脱帽,面对忧戚和悲伤,甚至是无助的伤心痛哭。他完全可以想象,他的那些乡村里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大妈阿姨,兄弟姐妹们和玩伴,不幸中,会有人像他一样躲在掩体和废墟的某处,躺着、蹲着、伏着,一动不动,再也不会与人打招呼,寒暄和聊家常。这些人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怪姿势,比如手脚、胳膊、脑袋,乃至手掌、脚掌、小腿、大腿、肚皮和心肝脾肾……男孩没有再敢看下去,他也没有残忍地喊出一些他熟知的名字或称呼——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祈祷,像此刻仍旧在外边刨挖着泥土瓦砾的那一群人一样,静默地起身、脱帽,并低头致哀!
随着外边的救援越来越近,陡然升起的光亮,在原本逼仄而现在却越来越宽敞的空间地上,投下了影子。清新的空气,带着山野的气息,和着微风,开始充盈在这片空间。滚石被挪开后,那些泥沙接着被人刨起,移向别处,树木的枝丫几乎在同时被剔掉。最后,便是起到了绝对遮挡功能的树木。这也是男孩在昏迷之后,始终还有适量空气和微弱光线的原因,使他不至于身处绝对的黑暗而感到绝望!而在男孩的旁边,另一片废墟中的其他人员却没有如此幸运,殷红的血粘在他们的衣服上、头发和脸上,看起来异常恐怖。幸运的,有的尚存一息;不太幸运的,或者是为了保护其他人的,有些已呼吸全无,再也没有脉搏与心跳。看到这里,困惑的男孩更加迷惑,他看了半蹲着蜷缩在空间中的自己一眼:怎么自己就在模糊中爬出了这空间,游荡于大渡河上和悬崖巨壁之间,甚至还随着救援的队伍,一同来到树木这处掩体中拯救自己。从孩子眼中,他看出了自己的惊讶和不可思议。难道在极度危险和危机之中,人真的可以灵魂出窍?或者是人类生物性本能的自我防护和幻觉?很显然,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或许是上天悲悯,或许是比上天更伟大的人类,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和所有勇敢无畏的救援之人,充当了天上神灵和人间天使!
男孩对于解放军、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天生就充满了绝对的信任。在这个男孩被人抱起的一瞬间,他认清了这处废墟,实际离自己家并不远!而且还是在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村子里!一瞬间,事实的真相,使得他变得目瞪口呆起来。
他并没有从昏迷中完全醒来。随行的医护人员快速地对他进行了简单检查和必要的救治,在确认他只是轻微受伤和昏厥以外,各项生命体征都相对比较稳定。她们都很诧异和惊奇,这样的小孩,是怎么把自己和树木的光影投射出废墟,而被救援人员发现的呢?在将男孩快速送至统一的救治区后,救援队伍没有任何的纠结和迟疑,即刻奔赴到下一处废墟实施探测和救援。
不久后,那个被救的男孩苏醒了。他继续思考着这个带有某种神性的隐秘问题:自己明明已经昏迷了,可为什么还能看到震区发生的事情?并且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些细节。“难道在人世间,人体内真的存在着灵魂和某种隐秘的力量?并能在危险时刻,实现灵魂出窍和向人求救?”很快,这个男孩在否定和肯定的纠缠较量中,相信和确定是后者——人是有灵魂的!小的,如人的一颗悲悯之心,关切之意;大的,如天地仁心,和那些永存于世的警魂、军魂、民族之魂!
从始至终,那个男孩都在隐藏自己的名字。
是的,他——哦,不!是我一直都在刻意地隐匿自己的名讳。之所以我能把整个事件描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那个男孩——就是我!至于问为什么如此?实在是因为,这一切太过于匪夷所思了。直到目前,我仍旧没有把这些问题完全厘清——但从逻辑上,的确真实存在!不然,你要么疑惑,要么感到惊奇与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