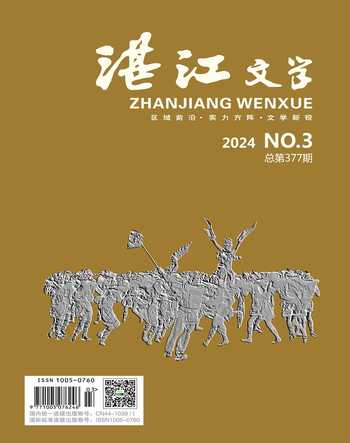银瓶山帖(七首)
徐汉洲
晚饭后在东江边徜徉
一生要走多少路
是有安排的
到了一定界限就会折返
所以有那么一阵子
你对两侧风景
以及擦肩而过的人
似曾相识
有些貌合神离
这时你是走在回头路上
一切皆有制衡
被设定的几个暗示
早已说明问题
最高的那座山爬不上去
最低的那条沟也潜不下去
再比如相生相克
哪有什么相伴相随
启明星和月亮
始终保持了对立的距离
我想说的是
有些道理明明清楚
可就是还要去冲撞
一堵围墙一张网一片刃
头破血流时写下这些分行
却还是阻挡不住
明天的鼻青脸肿
鸟儿都是隐喻的注脚
有一年我父亲特别注意
鸟儿的突然出现以及叫唤的语调
当然,我们那里素有
对鸟儿充满敬畏的习俗
布谷鸟预兆丰收
喜鹊给门楣增添喜气
燕子衔来满门和谐
每一种鸟都有自己的寓意
人们不喜欢猫头鹰的叫声
特别是后半夜啼叫像小孩子哭
那些日子我父亲还特别憎恨乌鸦
见到就扔石头
奇怪的是乌鸦对父亲也有意见
父亲一出门就冲着他叫
每次见状就默默折回家里
整天半脚门不出
又过了二十来天
父亲在井下砍坑木时手一滑
把自己的小腿剁了一斧头
胫骨几乎全断
“乖乖,如果往上半寸膝盖就粉碎了”
医生心有余悸
此后,父亲对鸟敬而远之
少年时光
实在忍不住的时候
奶奶会去割下一小块
埋进花五分钱打来的黄豆酱里
跟红薯一起蒸
虽然腊肉的香气比妹妹还显瘦
但我们仍有幸福感
那时候没什么梦想
奶奶想我们早点长大
父亲想我们早点挣工分还超支
我自己则渴望哪一天醒来
身上长出一对大翅膀
用筷子蘸一下肉香咬一口红薯
日子虽然滋润
但每当鸟儿从头顶飞过
我仍然忍不住驻足遥望
无法阻止
不喜欢两鬓斑白
然后两片飞雪就落下了
接着三片四片五片六片
然后是两座雪峰
不喜欢耳朵眼长毛
然后有一根偷偷冒出来了
接着两根三根
理发师说,要不要剪?
我说剪。最好把根剪掉
然后越来越浓密
像一坨不着调的水草
喜欢一口白牙
可近些年有些泛黄
医生说还有几颗松动了
我说那就赶紧固定啊
结果还是空了一个缺
这个缺等于我心头一个缺
这就是岁月折磨人吧
不讲套路不讲道理
目的就是要在你的外表
制造一些
强烈的、深刻的迟暮信号
再骄傲的人
也无法阻止
银瓶山帖
我不是智者
也不是仁者
也不知道它的褒贬
这两个标签不能乱贴
我喜欢与山为伍
我经常把自己遗忘在
它宽厚的怀里
我喜欢水的样子
它给我出神入化
我当过客时间久了,怕了
想要一些有分量的依靠
是可以理解的
想要过得自在一点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么多年那么多周折
依靠并不牢靠
自在并不乐哉
否则怎么一次又一次飘走
这次我可能真的靠住了
这次是心被黏住
虽然不是名山
论巍峨都排不进前序
这里不是名川
一条溪涧在冬季断断续续
至今还没有取名
我的魂被攥在了虚无
或许世上并没有什么真道理
当我的呼吸很不规则
当暗示告诉我
将碰见可遇不可求之物
越靠近,你的气势
让我的气场崩溃失律
银瓶山如果是一个人
那也是旷世美女
端庄青翠娇媚跌宕
如果非要再打个比喻
我只能想到我的老父亲
温厚朴实偏安一隅
从不出风头
沐浴阳光
有人怕
有人则相反
怕的人主要是怕晒
一白遮百丑
他们要保护美
其次是怕热
用心粉饰的容颜
出点汗就稀里哗啦
我喜欢太阳
是因为我怕黑暗
我不喜欢门窗之类机构
不要房顶更有快意
光明磊落的日子
我更能感觉到靠谱
我爷爷比我更喜欢
在盛夏的田野里
他光着膀子犁地耙田
汗珠在冒烟皮肤在冒泡
我爷爷似乎很享受
因为
他一直在哼着古戏文
歉意
一排冻死的树木
身上聋拉的花朵失去了血色
植物跟人死亡一样
此刻不仅是绿色没有了
光华也已熄灭
就像这天气,灰蒙蒙的
根本不像要下雨落雪
立冬以来,城市变得坚硬
寒冷肆虐大街小巷
裹住公园里的每棵树,每片叶
西北风抵达时小草先丧命了
这些树昨天还踌躇满志
今天无声夭折,连枯枝败叶
落地的路径也被冻僵
预报说今夜更冷明天更冷
并且宣布,今年的冬天
是本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
或许还会有更多的树木冻死吗
我遥望远处哆嗦的山峦
内心流露出一丝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