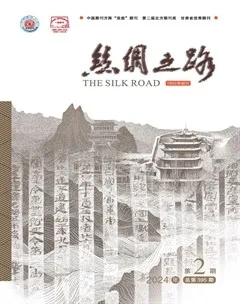丝绸之路游艺文化交流场所研究
丛振 金天
[摘要] 丝绸之路自汉时开通以来,便是我国同西域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此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唐代时,更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西域文化和中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留下了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在丝绸之路繁荣的背景下,中外游艺文化的交流频繁开展,而中外游艺文化交流中的各类场所也自然为丝绸之路游艺沟通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通过对丝绸之路游艺文化交流场所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唐宋时期中原地区对经丝绸之路而来的异域游艺文化的喜爱与重视,也从游艺交流的角度侧面说明了丝绸之路对于我国古代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 丝绸之路; 西域; 游艺文化; 游艺场所
[中图分类号] G812.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3115(2024)02-0016-09
文化传播与交流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自汉代以来,东启中原、西至欧陆的古丝绸之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的过程中,始终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沿途的农耕文明、绿洲文明、海洋文明在丝绸之路的串联下,共同造就了繁荣的人类文化瑰宝。但由于古代技术的限制,各文明间物质与文化的交流往往伴随着遥远的距离和漫长的旅途。在漫长的丝绸之路行程中,来往的使节、商人们无疑需要一种方法来消遣旅途的孤独与艰辛。而游艺在旅人的生活中,无疑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丝绸之路旅人们活跃气氛、获得愉悦的难得之法。可以说,只有在参加游艺活动的时候,他们才能暂时忘掉旅途的劳累与离乡的寂寞,享受那一刻的感官快感与精神愉悦。正因为丝绸之路上游艺活动的不可或缺,西域的诸多游艺也随着这些异域旅人们的脚步,一路相伴而来。
不论是丝绸之路沿途的旅人,还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城中的居民,在进行游艺活动时都需要一定的场所。为了使丝绸之路游艺文化交流场所研究更加全面具体,更加突出各阶层、各文化元素的不同与交流融合,本文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并在每一部分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具体场所进行分析,从而通过不同层面来了解游艺文化的传播、交流过程,以期更加全面生动地叙述丝绸之路游艺文化传播中的游艺交流场所,并深入思考不同游艺场所对游艺文化交流的作用与影响。
一、丝绸之路游艺文化研究综述
“游艺”最早见于《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衣于仁,游于艺。”[1]这是孔子对弟子们的行为规范做出的具体要求。他认为学生们应当树立远大理想,做事要符合道德规范,对万事万物要有仁爱之心,活动要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内进行。不难看出,此时的“游”与“艺”二字是分开来理解的,并不是我们当今所理解的娱乐、游戏的含义。在古代,“游”与“遊”是两个不同的字,在陆地上活动,如“遊戏”“游览”等,“游”与“遊”可以通用;而在水中活动,如“游泳”“浮游”等只能用“游”[2]。随着历史的推进,二者的含义才逐渐合一,“游艺”一词逐渐开始包含游玩、游乐的含义。朱熹在解释孔子之言时认为:“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3]这说明到了南宋时,游艺已经有了玩物适情、消遣娱乐之意。同时,游艺也逐渐成为古代儒家的一项重要的修身养性的手段,大大丰富了古人的精神世界。
但中国古代的正史资料中,并无对游艺的系统性专门记载,只是零星附属于正史之“艺文志”“礼志”“乐志”等史料中,当然也没有对此的专门研究。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与中国社会思想的变革,对于“游艺”一词的理解也逐渐通俗化、大众化,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近代第一个将游艺作为单独的分类进行研究的是杨萌深先生,他所著的《中国游艺研究》一书资料丰富,分类详尽,系统地叙述多种传统游艺活动的历史渊源与流变,为我们研究古代游艺提供了范本参考。杨先生在《中国游艺研究》中认为:“游艺就是游戏的艺术,并没有含着什么深奥的意义。其词或源于孔子‘游于艺(论语述而)一语。”[4]从此,“游艺”一词的现代含义便与游戏、玩耍、娱乐活动有了紧密联系。台湾学者陈永平更是将其准确定义为:“悠游、沉浸、涵泳在各项游戏、娱乐,或艺术(技艺、才艺)领域之中,可以让人们以娱怀取乐、消闲遣兴,达到放松、调适身心、增加生活乐趣为主要目的的一种精神文明活动。”[5]而本文所讨论的游艺,也大抵相当于现代定义的游戏、娱乐等利于身心的文娱活动。
古代的丝绸之路并没有我们当今的便捷交通手段,漫天的黄沙、极寒与酷暑、缺水缺粮、强盗袭扰等困难时刻威胁着来往路上的每位商旅。而游艺活动所带来的短暂快乐,便成为抚慰来往商旅内心孤独苦闷的一剂良药。或在奔波的驼背上,或在歇脚的驿馆里,来自各地各民族的游艺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又经由他们带到丝绸之路沿线各地,使丝绸之路成为名副其实的“游艺传播之路”。
文明间的互动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交流,早在汉代时,西域诸如杂技之类的游艺活动就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了我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6]2920而源起于中原的诸多游艺形式,也通过丝绸之路不断向西传播。现存最早的关于围棋理论的著作是1899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的北周手抄本《棋经》,可见经丝绸之路传来的围棋也是西域比较受欢迎的游艺活动之一。
不管是百戏、杂技之类的体力游艺,还是博戏、弈棋类的智力游艺,都需要在一定的游艺场所才能进行。游艺场所是承载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空间基础与载体,是人们参与游艺时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正因为有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游艺文化交流场所的存在和不断发展,丝绸之路游艺文化的发展传播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传播与影响范围。
二、统治阶层游艺文化交流场所
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7]。在我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层的范围大致是封建王朝的王公大臣及其有直接关联的群体。相较于社会其他阶层,统治阶层往往拥有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所建造的游艺场所,而宫廷便是其中的代表。
宫廷或说宫苑,是帝王及皇族们起居和工作的场所。《周易·系辞》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8]宫廷是中国古代彰显统治者权威的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其规模宏大、建筑考究,给人以强烈的精神与感官冲击。宫廷不只是统治者工作和居住的场所,在闲暇之余,统治者们往往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游艺活动以充实个人生活。宫廷类的游艺交流场所中进行的活动多以观赏性游艺文化交流为主。例如汉代时,宫廷宴会上就出现了大型百戏表演的场景。张衡在《两京赋》中,托汉武帝时期之故事,写其所处时期的百戏表演盛况:
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锯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尔乃建戏车,树修旃,倔僮程材,上下翻翩,突倒投而跟挂,譬陨绝而复联。[9]
文中提到的 “都卢寻橦”“跳丸”等活动,都带有明显的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此后,宫廷逐渐作为重要的游艺交流场所,被统治阶层所喜爱。如《后汉书·陈禅传》中提及:
安帝刘佑水宁元年(120),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主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6]1685
中外的统治者们都喜欢在宫廷中举行游艺活动,或为愉悦身心,或为招待宾客。如《法苑珠林》中就记载了“王玄策出使天竺时所见五女戏杂技”一条:
又王玄策西国行传云:王使显庆四年至婆栗阇国。王为汉人设五女戏,其五女传弄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绳伎,腾虚绳上,着履而掷。手弄三仗刀楯枪等种种关伎。杂诸幻术,截舌抽肠等。不可具述。[10]
这是天竺统治阶级在宫廷中为中国使者举行百戏表演的记载,生动展现了丝绸之路游艺文化交流的手段和场景。同样,中国统治阶级也接受了这样的游艺交流。《旧唐书》中载唐睿宗接待婆罗门进献的场景:
睿宗时,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锯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又伏伸其手,两人蹑之,施身绕手,百转无已。[11]
这种宫廷与宫廷之间的游艺文化交流表明了宫廷这一场所不仅起到了简单的提供一个观赏百戏类游艺活动的场地作用,更是一处承载游艺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质载体,没有场所这一物质载体,游艺文化交流就无从谈起,可见宫廷对游艺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作用。
频繁的中外文化交流带来的不仅仅是西域的游艺文化项目,还带来了西域的游艺文化场所的特征,并影响到了中国的游艺文化场所建筑结构。中国古代的代表性宫廷建筑,如未央宫、大明宫都是木质结构建筑。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地中海地带的埃及、罗马、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的砖石结构建筑。在丝绸之路开通后,具有鲜明异域特色的诸多游艺活动伴随着物质文明的交换纷至沓来,并衍生出了新的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特色的游艺项目。在交流碰撞中,它们也带来了独具域外鲜明特色的建筑传统与风格,并且影响了中国古代宫廷的建筑风格,使得宫廷游艺文化交流场所也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中产生了具有鲜明中外文化交流的场所特征。
宫廷游艺活动与宫廷这一游艺场所相辅相成的关系,是经得起仔细推敲且有充分史料支撑的。王振铎曾考证在秦咸阳宫殿遗址中可见中柱或“都柱”的设置,这种建筑风格似乎并不仅仅是结构上的需要,而是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秦咸阳宫殿这种高台建筑与埃及、西亚的金字塔、观象台都有着相似的四棱台(椎)几何形体[12]。同时,中外美术界早已公认,汉代中原雕刻的新因素是张骞从西域引入的[13]。除此之外,麟德殿是唐代皇帝举行大型宴会的地方,以数座殿堂高低错落结合在一起,大殿的东西两侧又有亭台楼阁衬托,其建筑造型风格丰富多样,这种建筑方式在唐代敦煌壁画中亦可以见到[14]。可见唐代宫廷场所的设计也跟游艺活动一样受到了西域的影响。而在西域的宫廷与建筑设计中,也能发现诸多中原文化的影子。如法国学者莫尼克·马雅尔认为,高昌古城是整体仿照唐都长安的平面图建立起来的,而沿城池北墙则有一座仿照中国宫廷而建造的王城 [15]。
除观赏性游艺之外,宫廷中还有可供统治阶层亲身参与的场所。马球是深受唐代统治阶层喜爱的一项游艺活动,唐代的诸多宫苑中,都有马球场的存在。如“尚食内苑、紫云阁之西有凝阴殿,殿南有凌烟阁。贞观十八年太宗图画功臣之像二十四人于阁上,帝自为赞词,褚遂良题额。又有功臣之阁在凌烟之西,东有司宝库。凝阴殿之北有球场亭子”[16]。其中提到“球场亭子”,表明此处有一处球场,还有观赏马球用的观赏亭。而当有外国使节来访时,唐代统治阶层也会邀请他们一起参加马球活动。如唐中宗时,有一场著名的马球比赛就发生于宫廷内的梨园之中:
景云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仗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时玄宗为临淄王,中宗又令与嗣虢王邕、驸马杨慎交、武秀等四人,敌吐蕃十人。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吐蕃功不获施,其都满赞咄,尤此仆射也。[17]
对抗的双方分别是吐蕃使臣与唐廷官员。前几轮比赛中,吐蕃使者皆取得了胜利。在被动情况下,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挺身而出,运用自己高超的马球技巧,帮助唐方取得了胜利。显而易见的是,这场著名的马球比赛背后,不仅折射出马球交流的诸多信息,还折射出了马球场这一游艺场所的诸多信息,如参赛双方来自不同区域,赛前必先充分沟通比赛规则和评判胜负的标准以及场地是否熟悉适合等。这既是丝绸之路马球游艺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又是丝绸之路游艺文化交流场所的生动展示。
三、社会公共组织游艺文化交流场所
这里所讨论的社会公共组织,指的是相对于统治阶层专用场所的,具有一定官方或半官方性质,但更多面向大众的社会组织或群体,一般包括寺院、官衙,或城市中的专门机构等。此类组织的服务对象范围较广,既包括政府官员、教职人员,也涵盖了百戏艺人和市民群众。这些群体既可担任游艺活动的组织者,也可以是其中的参与者。此处以寺院为例,探讨中国古代公共场所中进行的游艺文化交流。
寺院是佛教僧侣及信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但以寺院为中心衍生出的庙会、戏场等场所又体现着一定的世俗特征。因而,流行其中的游艺活动往往诞生于宗教文化,但发展于世俗生活,并最终通过世俗游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寺院、戏场、庙会等场合进行的游艺活动,既不是完全的宗教仪式,亦非纯粹的民间娱乐,而是一种有机融合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的复合文化产物。
魏晋以降,佛教在中国本土得到了广泛传播,一方面是由于其本土化改造趋于完善,另一方面则出于当时民众无法逃避现实战乱,因而寄情于超然世外的宗教文化的客观需要。这种强烈的情感需要也促使当时的僧侣更多地使用世俗化的方式,如诗歌、琴棋书画、雕塑、茶道、变文等技艺来吸引信众[18]。这种对于佛教的信仰则自然地物化为寺院文化的繁荣,《洛阳伽蓝记》中甚至记载了孝文帝之时“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19]37。
随着数量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寺院的功能与作用也逐渐超出了一般宗教场所的范畴。早期,许多寺院为了庆祝佛教节日,往往设有专门用于庆祝节日的场所。但随着佛俗与民俗的深入融合,寺院周边也逐渐演化出庙会这一时令性节庆场所(或称集会)。如唐时流行的佛诞节,最初是为纪念释迦牟尼的诞生而设立的,庆祝形式也仅限于施斋、浴佛、抄念经典等传统的佛教仪式。但随着信徒人数的增长、娱乐需求的增加以及更多教俗文化的交流,百戏演艺也逐渐融入庆典流程之中。《杜阳杂编》 载:
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四月八曰,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竞聚僧徒,广设佛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舆以载歌舞。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20]
此段描述的便是著名的唐懿宗“迎佛骨”事件。可以看到,在整个庆典过程中,除了“士女瞻礼”“僧徒道从”等基本佛教仪式之外,还出现了“吹螺击钹”、小儿“呵唱于其间”等歌舞表演。这充分说明了当时宗教活动与世俗娱乐之间存在着相互融合的现象,而这种教俗文化的交织也就意味着庙会的出现。庙会往往吸引着众多的僧侣、信徒以及普通群众前来参与、娱乐,同时这种大型的人员聚集又为百戏艺人和货郎商贩提供了丰富的客源,寺院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场所。《洛阳伽蓝记》卷1“长秋寺”条载:
长秋寺,刘腾所立也……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缘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像停之处,观者如堵。[19]43
上述即为长秋寺“行像”日庙会时寺院表演“狮子舞”与“吞刀吐火”“缘幢上索”等幻术杂技的场景。而这次表演也吸引了大量群众前来观看。
庙会中的杂技幻术大都自西域传来,如上文提到的狮子舞,据周泓考证,大致于南北朝时期由西域传入中原,这一时期亦出现了“汉人制作或扮狮”的现象[21]。狮子原产于西域,中国本土的狮子多源于丝绸之路西方诸国的进献或赠送,后由西域胡人扮演狮子进行舞蹈,创制了狮子舞这一游艺活动。《新唐书·音乐志》记载,狮子舞自龟兹传入中原,并对舞狮演员和道具进行了描述:“龟兹伎……设五方狮子,高丈余,饰以方色。每狮子有十二人,画衣,执红拂,首加红袜,谓之狮子郎。”[22]《通典》中亦有对狮子舞道具和舞姿的详细记录: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挚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衣,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戏弄之状。五狮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抃以从之,服饰皆作昆仑像。[23]
不难看出,此时的狮子舞仍然带有明显的异域色彩。但随着其在庙会等世俗场所的普及与在演出过程中不断进行的本土流变,狮子舞(亦可称为舞狮)也中和了中西文化的不同因素,最终演变为符合中原地区审美的形态,为宫廷与民间所喜闻乐见。诸多唐诗如白居易《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和元稹《西凉伎》中,都曾描写过精彩绝伦的狮子舞表演。
除了中原地区的寺院庙会之外,在西部的敦煌地区,人们也会在节庆时于寺院中进行游艺活动。S.4625《燃灯文》载:
每岁元初,灵岩建福;灯燃合境,食献倾城;福事已圆,众善遐集。其灯乃神光晃耀,炯皎而空里星攒;圣烛耀明,朗映而灵山遍晓。银灯焰焰,香油注玉盏霞开;宝火炜炜,素草至金瓶雾散,千龛会座,傥然创砌琉璃;五阁仙层,忽蒙共成卞壁。遂使铁围山内,竟日月而通祥;黑暗城中,迎光明而离苦。[24]
每到上元节的夜晚,敦煌地区的人们便会前往寺院、佛窟通过燃灯的形式来祈愿。《燃灯文》中漫山遍野的灯火,正是当时敦煌寺院节日热闹景象的最好反映,亦可借此窥见上元燃灯在敦煌以及更西地区的传播。由此可见,寺院作为中国古代的公共组织场所,在丝绸之路游艺文化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非正式游艺文化交流场所
非正式的游艺场所,不同于节令性的大型活动地点,多指的是不受时间、地点、条件制约,较为随意、方便的娱乐场所。对比与统治阶层及社会工作组织的大型游艺场所,此类场所往往规模更小,耗费人力物力较少,但却具备着纯粹的民间性,更能体现中西游艺文化交流的广泛性、深入性。此处将选取瓦舍这类游艺场所,以更为具体地剖析非正式游艺文化交流场所的特征。
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与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在一些都市内出现了服务于市民的商业性质游艺场所,俗称“瓦舍”,又名“瓦子”“瓦肆”。瓦舍之内用于表演歌舞游艺的场所名为“勾栏”,或“勾肆”“邀棚”,勾栏内设戏台、戏房、神楼等。据记载:“每座瓦舍中都有勾栏,临安北瓦有勾栏十三座。而小瓦子恐怕就只有一个勾栏撑持场面,故而勾栏有时也与瓦舍互为同义词。勾栏的原意是栏杆,由于大型瓦子内有不止一个游艺场所,各个场子四周以栏杆圈围起来,成为一个演出的场子,另一层用意则不外乎防止有人趁机看白戏。”[25]勾栏作为瓦舍中主要的演出场所,其演出内容多以音乐、歌舞等内容为主,其中的歌舞有许多便来源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如宋元祐年间(1068-1094)的“诸宫调”,是宋朝红极一时的音乐形式:“将唐宋以来的大曲、词调、缠令、缠达、唱赚、传奇以及北方流传的民间乐曲按声律高低,归人各个不同的宫调,敷衍成文而人曲说唱。”[26]33但像诸宫调这种音乐的形成,经过严格的考究应该是出现在宋之前。“经比较,宋、金、元代流传的诸调其性质与体裁同唐代变文相似,发展到以琵琶等乐器伴奏的‘弹词,又与胡曲发生一定的关系。无独有偶,在中国西部地区敦煌遗书中也发现了可称为诸宫调的3个写卷,以及黑城佛教遗址问世的《刘知远诸宫调》。”[26]34这则史料证明,早在唐代,东西方的音乐艺术交流便已经渐趋形成了诸宫调的雏形。而瓦肆作为其演出的主要场所,也承担了文明交流的重要作用。
除音乐歌舞之外,瓦舍还有许多其他的娱乐活动也源起于丝绸之路上的游艺文化交流。例如在我国深受喜爱的“皮影戏”与“傀儡戏”,就与西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生经》卷3中记载,应国王之约,“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27]。此处指印度与西域流行的木傀儡。在我国唐代,西域各地已盛演傀儡戏。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6号墓中曾清理出彩绘木俑和绢衣木俑70多件,另外,还有木马残腿、木俑手脚200件。这充分证明在唐代东西方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傀儡戏这一游艺在西域各地饱受关注。到了宋代,瓦舍中的皮影戏、傀儡戏表演更是有了长足发展,并在原有基础上演变出了新的形式。宋代耐得翁《都城纪事》有载:“弄悬丝傀儡、杖头傀儡、水傀儡、肉傀儡。”[28]另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技艺有……药发傀儡……影戏……弄乔影戏……不以风雨间,诸棚观戏人,日日如是。”[29]此处的“影戏”,即以平面傀儡取影,亦为傀儡戏的一种主要演艺形式。
除皮影戏、傀儡戏表演的形式是中外交流的结果之外,其表演的内容也与通过丝绸之路的中外游艺文化交流密切相关。据史料记载,古代印度常用影戏的手法进行表演,其中最古老的戏剧名讲述了罗摩与西多的故事,叫作“都墨伽陀”。除此之外,还擅长表演猴王“安家陀”的故事,因此,在古印度影戏也常被称为“皮猴戏”。此故事当从印度《罗摩衍那》史诗中的猴王“哈努曼”蜕变而出[30]。胡适先生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曾提及:“有一部专记哈奴曼奇迹的戏剧,风行民间。中国同印度有一千多年的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这样一桩‘伟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会不传进中国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反映中印及周边国家猴行者的根本。”[31] 由此看来,中国版的“美猴王”故事内容,多少受到来自印度的皮影戏内容的影响。据此可知,中国的游艺文化在同其他国家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兼收并蓄、取长补短。而瓦舍这种非正式游艺文化场所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不仅吸收了他国的优秀游艺文化,更衍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产品。
五、结语
场地场所是丝绸之路游艺文化交流中必不可少的基础。它不但保证了游艺活动的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游艺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综上所述,统治阶级耗资大、占地广的游艺场所不但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审美,也间接引领了整个社会的娱乐风向。而社会公共组织类游艺场所则给统治阶层之外的诸多民众提供了世俗的、大众的、开放的公共普适性游艺场所。非正式游艺场所虽从规模和档次上都无法与前两类场所相比,但它的确是广大民众最为喜闻乐见的、最常前往的游艺文化场所。其承载了最广大民众的娱乐休闲需要,在大多数时候它们是普罗大众愉悦身心、放松心灵的寄托之所。
各类不同属性的游艺场所源源不断地吸引着诸多游戏者参与到各色中外游艺活动中来,从而使他们成为了各类游艺场所中游艺文化的参与者、传播者,甚至是发展者和创新者。古代中原民众在接受、学习并享受异域传来的游艺活动时,也同样将中原游艺场所与之创意性结合,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文化的兼容并蓄。其中的许多创意最终通过漫漫丝路,反向影响了西域游艺活动的发展。通过对上文中三类游艺场所盛况的列举分析,我们也能够看到唐宋时期中原地区对经丝绸之路而来的异域游艺文化的喜爱与重视,也从游艺交流的角度侧面说明了丝绸之路对于我国古代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将游艺文化交流场所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与客观主体,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示更为立体、饱满的丝绸之路游艺文化形象,以便于更加深入地了解丝绸之路这一伟大的历史之路。
[参考文献]
[1]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述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5.
[2]左民安.细说汉字1000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389.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述而[M].北京:中华书局,1983:94.
[4]杨荫深.中国游艺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
[5]陈正平.唐诗所见游艺休闲活动之研究[D].台中:私立东海大学,2006:6.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20.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8]王玉德.中国宫廷文化集观[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2.
[9]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48.
[10]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注.法苑珠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107.
[1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43.
[12]王振.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续)[J].文物,1963,(04):1-20.
[13]常青.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38.
[14]朱永春,朱永和.中国建筑[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28.
[15]莫尼克·马雅尔.古代高昌王国的物质文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5:94.
[16]宋敏求.长安志[M].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134.
[17]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53.
[18]李斌成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76.
[19]杨衒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20]王仁裕等撰,丁如明等校点.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32.
[21]周泓.古代汉地之部分西域文化考溯[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8,(06):42-57.
[25]欧阳修等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0.
[23]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3718.
[24]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5:528.
[25]虞云国.水浒寻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227.
[26]王洁慧.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艺术研究[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0.
[27]李强,柯琳.民族戏剧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532.
[28]冯双白,等.图说中国舞蹈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51.
[29]孟元老撰,侯印国注.东京梦华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21:130.
[30]黎羌,柯琳.东方乐舞戏剧史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130.
[31]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