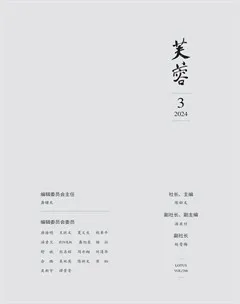海棠之吻
许冬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招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创作方向)在读硕士。散文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散文》等刊物。著有散文集《外婆的石板洲》等十余部。
一
记得那是一个南方的秋天,没有云,天空蓝得清透明白。
来找我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她坐在我对面,说话语调温柔,但温柔的言语里又影影绰绰藏着凋零。她来,为的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名叫海棠,是我的学生。
我第一回在课堂上叫海棠这个名字时,心想,为之取名的一定是女孩的母亲。海棠花美,而“海棠”两个字发音时,舌尖处似有微风和阳光的清甜和明亮。一个女人,新做了母亲,她内心甜蜜,此后的时光因为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而充盈饱满。她对女儿也许不设定太宏大的人生目标,是只做一朵海棠就好。
海棠的母亲坐在我对面,说着说着,泪终于憋不住。她恳求我帮忙,喊来她的女儿。她想见女儿一面。
他们是夫妻离婚,海棠判给了父亲。我跑到教室,找到海棠。海棠很懂事,每次见我,老远就跟我招呼。可是这一回,当我说到她母亲坐在我家等她时,海棠竟退回座位处不肯出来。我拉着她的手,贴在她耳边悄悄说:“小傻瓜,天下的妈妈都是最爱自己的孩子的。你看,妈妈这么远过来,就是想看看你。你无论如何得去跟妈妈见一面,让妈妈看看你。你还可以跟妈妈说点你的学习情况……”
不知道是出于礼貌,还是被我说动,海棠最后同意去我家。她低头走在我身后,一路沉默,沉默得像一枚不肯发芽的果核。
将海棠引到她母亲面前后,我即离开,站在楼下等,好让这一对母女贴心贴肺地说说话。可是,才不到十分钟的样子,海棠就下了楼,边走边小跑着往教室方向去。我正要拉她,想留她和她母亲多待会儿,可是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已经斜着膀子从我身边风似的掠过去了。她是低着头跑掉的,脸上有泪水。
我心里一叹,慢慢上楼。坐在桌边的,是那个看起来比刚来时更加萧索更加孤单的母亲。
海棠的母亲一边抽泣一边擦泪,过了好一会儿才艰难平复情绪,慢慢跟我说起一些事。她和海棠爸爸离婚后,就回到一百里之外的娘家那边另组了家庭,海棠的爸爸在外做生意也另娶了一个贵州女子回来。海棠母亲因为听说这位贵州女子打算过年回娘家带上海棠一道,所以格外不放心,生怕人家会将自己的女儿拐去卖掉,此番来学校,既为见女儿以慰思念之苦,也为叮嘱女儿千万别跟后妈去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但是,海棠却不认同她母亲的意见。
我后来想,这一对母女的短暂相见和不欢而散,根由大约不在去不去贵州这件事上。而是,这个算是某种程度上“失去”女儿的母亲拼命伸手想要揽回女儿,而女儿已经倔强地不肯回头倒向母亲的怀中。因为在海棠心里,她似乎已经更爱她的那位来自贵州的后妈了。
因为这件事,此后我便对海棠更多一些关注,我也像她母亲一样唯恐她后妈对她不好。海棠的长相在班上女生中并不算出众,但是她长长的辫子每天都梳得特别仔细,一点不乱,一看就是有大人帮忙梳的。大约是她后妈梳的。海棠告诉我,是自己的亲妈找爸爸离婚的,大约是怪爸爸挣钱少。关于这个,我听海棠妈妈说过,她说海棠爸爸做生意总是不挣钱,她到娘家到处借钱给她爸爸,可她爸爸总是不争气。海棠的妈妈大约对她爸爸失望透顶,终于提出离婚,可是放心不下女儿。海棠对她母亲有抱怨,所以平时不大肯见她母亲,她觉得妈妈不爱爸爸,便也是不爱她了。
后来的一次家长会上,我见到海棠的后妈。她很安静地听我说话,很小心地问我海棠在学校的情况。我后来也听海棠说起她后妈每天晚上陪她学习的事,心里也挺感动的。但是,我又始终希望海棠和她亲妈的关系能有改善。
冬天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泡脚桶,是海棠的亲妈从我同事那里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网上买来寄给我的。我一时不好退回,便收了,将泡脚桶送给了我母亲用。我心想,也许是她们母女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善,这个小母亲心里高兴,所以感谢我的帮忙。
翌年的一个海棠花开的季节,海棠的亲妈又来了,我热情接待了她,坐下一聊,我才知道这个母亲已经又有小半年没见到女儿了。女儿似乎铁了心不肯见她,她所有的方法用尽,想来女儿是最听老师话的,所以只得再从我这里求助。
这一回,我又到教室,悄悄贴在海棠耳边说她母亲来了。海棠礼貌地对我笑笑,然后一个劲地摇头表示不去见。她说,她怕见了自己母亲,让后妈知道了,后妈会伤心。她还说,后妈因为她,都放弃去生自己的孩子。她说到后妈时,眼泪儿一串串挂出来,挂满小小的微黑微红的圆脸蛋儿。她那伴着哽咽的微微沙哑的声音里,净是对后妈的爱护和疼惜。我心想,小傻瓜,哪有女人为了继女放弃去做母亲,或许是后妈自己生不了孩子呢。但是,我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我没有把自己这样一个来自成年人的阴暗的揣测告诉海棠。再说,即使是一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她能把继女视如己出,也令人尊敬。
那一天,我没能说动海棠。我一个人走回家,面对一个焦急等待的母亲,深感抱歉。
她告诉我,她想孩子实在想得难受,想得整夜不眠,抱着丈夫哭。
她把我的眼泪也说下来了,我劝她再生一个,或许多少可以缓解这无止境的思念之痛。她说他们是有这计划,但是如今年纪已大,不是想要就有的。
在那个花气蓬勃的春天,我送一个见女未着、失魂落魄的母亲出校门。我们路过校园那几棵正开花的树边,她脚步放慢。校园水泥路边那几棵海棠树上,浅粉色的花朵开得好似半天云雾从枝丛里弥漫出来,那云雾在阳光下随风变幻,仿佛又变幻成小女孩粉红的笑颜。我指指,轻轻对她说,那是海棠。她微微点头,抿了抿落到嘴角的泪珠,对我感激似的笑笑。
二
北京的鲁迅文学院里,也有几株海棠,叮叮当当地结了满树的果子。我9 月刚到时,那海棠果还是青的,猜想那味儿一定极酸。转眼两个月过去,那满树海棠果已是张灯结彩的红。我好奇摘一颗品咂,酸里已透一些甜来。
我和同学常常在这秋天的海棠树下散步,一边沐着树间漏下的日光,一边闻着若有若无的果香。一日,同学红蕾跟我说起我给她的印象。她说我初看是阳光的,是欢喜的,但再走近就不容易了,因为我身上似乎藏有一点冷和疏离。我后来细想,觉得她说的话是有几分道理,我确实是害怕和别人太近。
我看着树上的海棠果,忽想起十多年前我的那个名叫海棠的女学生,想起她和她母亲的眼泪。
最后,我想起了我和我的母亲。
我是从哪一天起,就抱着一块冰在怀里,一个人悄悄走远,害怕和别人太近呢?
我想起母亲如今常常责怪我,结婚后从不肯在娘家待上一夜,其实她是责怪我不肯落下脚、陪她一夜。
她不知,即使是母亲,我也害怕和她贴近。
成年后,我几乎不曾和母亲同床而眠过。每次回娘家,即便再晚,我都要走。母亲怕我嫌弃她的床不够干净,总是解释说特意为迎接我而刚刚换过被子,而我则解释说晚上要回家用电脑做事情。
母亲不解道:“难道有那么多文章要写?”
我一边笑着一边撤退,顺手带上母亲的门。我终究要走。
文章是写不完的。可是,我到底为什么不留下来陪母亲睡一夜,总是让她失望呢?
每一次离开母亲家,我都会感到愧疚。可是如果让我退回门口,我还是选择要走。
因为,跟母亲同睡一床,在我这里,那是陌生的。是的,我和母亲睡在一起,我觉得像是跟陌生人睡在一起。我会不敢伸脚,不敢放肆展开四肢。我更害怕,会一不小心碰到母亲的肌肤。
我想起童年时,在我们家那个临河而居的老宅里,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堂屋里逗弟弟开心,我不远不近默默站在旁边。母亲每逗笑一次弟弟,总要脸贴到弟弟脸边,啪——很响亮地亲一口弟弟。我就站在母亲身边,不远不近。母亲不曾转过身亲过我一次。
常常是那样的夏日,弟弟衣服穿得少少的,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堂屋里,坐在穿堂风里,她身子一俯一仰,以巨大的幅度抱着弟弟起伏。他们在穿堂风里用身子的俯仰起伏把小小的椅子坐成了秋千一般。母亲常常一边逗弟弟,一边幸福甜蜜地抒情:“我的心呀——我的肉呀——”
母亲抒情完毕,又会补上响亮的一吻。弟弟简直成了母亲的无上美味。我就站在母亲身边,不远不近。河水映着天光斜斜照进屋子里,到处都是明亮的,我也站在明亮的光照里,可是母亲似乎不曾看见我。我形若虚无。我不远不近,默默看着母亲一口又一口亲着弟弟。一口都不会落到我脸上来。
午后的风贴着河水吹拂,然后穿过柳树和榆树的枝叶,再穿过我们的堂屋。风把柳枝儿和榆树枝儿吹得软软的,把弟弟和母亲吹得像是起了毛,他们的笑声有谷类发酵的甜香。风把我吹得凉凉的,我要凝结了。
我凉凉的,默默看着母亲亲着弟弟。一口都不会落到我脸上来。
一口都不会落到我脸上来,我好像也没有恨意。我只有一点失落,一点当时还不能懂得其中含义的伤心。我看着母亲亲弟弟,像看着隔壁婶婶亲着堂弟一样,只是羡慕那亲吻大约像刚出锅的米饭一样冒着芳香的白气,它烙在弟弟脸上,软糯而微烫吧。我没有恨意——谁会恨一个邻居亲吻她的孩子而不亲吻自己呢。
最令人浮想的是晚上,特别是冬天的晚上。那时,母亲一边给弟弟脱衣服,一边亲弟弟。亲过,母亲睡下,将弟弟揽在怀里。弟弟像种子睡在瓜瓤里一样,睡在母亲雪花膏香气弥散的怀里。我就在对面的床上,自己静静地脱衣,然后睡在父亲身边。
我抱着双臂在冰冷的被子里,不敢靠近父亲。我弯着我的左臂,弯到身子右侧;我弯着我的右臂,弯到身子左侧。我枷锁似的自己抱紧自己,用自己的体温,慢慢焐热身上的被子。我将被子掖到耳边,依然能听见母亲啪的一声亲弟弟的声音,那宣告要关灯了,一天隆重结束,夜晚正式开始。在一日的终了之时,父亲不会亲我,母亲更不会。我沉入黑暗中,像一个没有晚餐的孩子,可是也乖乖地睡觉。我期待节日。
一到节日,我便会去外婆家。七岁那年入学读书,七岁那年的另一壮举,便是我可以独自去外婆家了。我一个人翻过高耸的江堤,穿过足有一里长的坟地,穿过狗吠相迎相送的村庄和大得没边的田野,到达七八里之外的外婆家。外婆家在长江边的一个沙洲上,那时,每到假日,小姨便会早早站在屋子西边的木槿篱笆边等我。
我远远看见平坦开阔的沙地中间立着一座并不高大的土墙房子,那是外婆家。它像江面上一只正泊岸的船,而站在木槿篱笆边翘首等我的小姨,像是船顶上一面迎风招展的庄严的旗子。
我奔向小姨。小姨牵着我的手,或者将我高高抱起。肌肤相贴的那刻,我像是一块就要摇摇欲坠的石头,忽然稳稳从悬崖边坐回来,躺倒在一块温厚可亲的大陆上。
我迎向小姨,其实是迎向一个母亲。
我其实在懵懂之年,已经不要生我的母亲了。我认小姨为母,从小姨怀里出发,把蒙古长调一样低沉悠扬的爱和惦念都给了小姨。
三
小姨大我十一岁。我懵懂时,她正值蓬勃的青年时代。那时,父亲经常要出门做手艺,一年有小半年的时日不在家。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小姨便常来我家,帮母亲照应家里家外。小姨在我家的日子,我上学路上逢人便炫耀我小姨来了的事,而一放学,我便背着书包飞奔回家,唯恐小姨在我上学时回到江洲上去。村子里有个男青年,想娶我小姨为妻,我听大人们三句两句地说起,心里对那男青年陡添了恨意,从此上学宁肯绕路也不愿再路经那男青年家的门口。
有一年冬天,父亲出门回来,路过安庆时,给母亲和小姨各买了一件很时尚的褂子,近似于年历画里的朱明瑛穿的上衣。小姨的那件浅紫色褂子,穿上身特别显粉嫩,一位正在读高中的表姨看上了,软磨硬泡要跟小姨换,小姨竟就换了。这事儿又让我暗自生气了好一会儿。我大约以为,小姨穿着我父亲买的褂子住在我家里,那神情就像我母亲。我多么盼望小姨永远住在我家呀。
在外婆家,我睡在小姨的怀里。小姨也弯着胳膊,像母亲把弟弟揽进怀里那样,把我揽进她的怀里。我不要枕头。我夜夜枕着小姨的胳膊入睡。小姨的床挨在厨房边,夜里,土灶后面堆放的芦苇叶子散发的清香,还有炊烟的余烬散发的焦香,在我们的被子边沿袅绕。我卧在小姨怀里仿佛豆粒被柔软的壳子包裹,连藤带叶地,我们一起被种植在温湿的土壤与腐叶之间。在这样温湿的空气里,我还能闻见小姨生理期时从衣服深处散发的隐约腥味,她的胸脖之间残留的香皂的香味,小姨的脸贴着我的脸,我们脸上的雪花膏香味蒙蒙融在一起……跟小姨在一起,所有的味道都是亲热而好闻的。
黑白电视机里唱《恼人的秋风》时,小姨教我唱《恼人的秋风》;大广播里唱《回娘家》时,小姨教我唱《回娘家》……小姨教我唱《妈妈的吻》,唱到“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时,我只喜欢唱“妈妈的吻,甜蜜的吻”这一句,只觉得这一句像水果,有水润润的清甜——天下妈妈的吻,都该是多汁的浆果;小姨的近在我脸边的嘴唇,以及她的歌声,也像浆果。我唱不好“叫我思念到如今”这一句,我也不喜欢唱这音调越走越低的一句。那时,我还不能体悟,时间的疆域里,会有长久别离,会有再也无法填塞的茫茫空白。
就这样,小姨用歌声铺就夜晚,小姨载着我在歌声里荡漾……而不远处的江面上,偶尔有轮船嘟嘟鸣笛,整个世界都像是在银色的月光下微波荡漾。
…………
我十岁那年,小姨开始生病了。
四
母亲对于我不肯与她同床而眠,只当是我的倔强。
年纪渐大以后,她一日日有不安,总怕我将她冷落或抛弃。她跟我说她的朋友谁谁谁买了多少保险。她听她的老姐妹们絮叨,说是儿女都不如买保险放心。我跟她说:“妈,你放心。只要你女儿我还活着,只要我有一碗饭,必定要分半碗饭给你。我留下半碗饭给自己吃,是因为我得活着,再给你去找下一餐的半碗饭。”
她大约终于放心,好些日子不再跟我提买保险或者谁家老人被虐待的事。我的就是她的。所以她相信,我的心,和她的心,一定像扣子一样紧紧扣在一起。
可是不久,她又生了新的疑虑。她的新疑虑已经从物质生活转移到精神层面,她无比关心将来她死时我是否有强烈的悲伤。她总是有意无意地跟我说起小镇上某个老太太去世,说起老太太的女儿如何悲恸地扶棺而哭。在她看来,哭声的高低和长短,可以标注女儿对母亲的忠诚之爱的程度。有一日,她在极其细致地描述人家女儿的哭态之后,不再说话。我们母女之间的谈话就这样忽然豁出一个巨大的空白来,静寂无声的空气里,除了择菜、洗碗、拖地的声音,似乎有一丝丝凉风从某个隐秘之处灌进来。母亲不说话,她在等我表态,表态她如果死去我会号啕,并且在泪水里列数她平生的美德及她之于家庭和亲友的功绩,特别是我呼天抢地的不舍和思念。她常常等了半日,我依旧不出一语。
其实,在漫长的空白和静寂里,我问过自己:有一天,母亲若故去,我会不会哭天抢地、号啕不已?
我想过了,我不会号啕。我会仔细认真地办好丧事,让她的葬礼隆重得像一场出嫁。等人群散尽,我会在一个阳光厚实的午后,一个人走到母亲的坟前。我会在坟边静静种植一棵会开花也会结果的树,陪她。我会坐在花树下,一个人默默流泪。默默流上一下午眼泪,再让太阳晒干,不惊动任何人。就像我幼时在母亲面前,看着母亲亲吻弟弟,我只是默默伤心,不会哭天抢地,不会惊动任何人。
我真是不习惯在母亲面前放纵情绪。我乖巧至今。
她终于等不及了,愤愤不平地叹道:“我就知道,我死后,你是不会哭的!”
她几乎是在逼我表态了。显然,在她那里,我不哭,便是不孝。我是不能不孝的,我在外好歹是体面有身份的人。那么我就得表态说我哭,狠狠地哭。
我一抬头,笑道:“我会下载最好听的哭丧歌,再放个大音箱,让专业哭丧的人来哭你,让半个镇的人都能听到。”
母亲也笑起来,她大约觉得那样的死亡也像广场舞一样热闹。她喜欢热闹。她在想象的热闹中,忘记再去追索我的忠诚了。
我隐藏得很好。她不知道,我的内心深处对她有疏离。
她欢喜地一步步向我靠近,不知道我自幼年起已经背叛远走,一去不肯回头。
我像我的学生海棠一样。
原来,我像我的学生海棠。我们内心深处,早不认生身母亲了;我们循着那些鱼鳞一样密布的爱的细节和肌肤相贴时的暖意与信任,去认领另外一个精神上的母亲。
在合肥,我有时会住到弟弟家里。弟弟出差时,我便顺带照应正在读初中的侄子,所以弟弟家里一直备有我的洗漱用品、换洗衣服,还有我睡觉的那张床也是弟弟专为我备的。
我不住弟弟家时,母亲有时会过去住些日子。母亲去时,我隐隐担心母亲会睡我的床。而母亲是知道我的癖性的,就是我睡的床、我穿的衣,我是不愿意别人去碰的。而我又知道,母亲一定是想碰的。她可以熬过一天两天不碰,但一定熬不过天天不碰。
我有时想象侄子上学后,母亲一个人待在弟弟家的情景。她一定是一得空就去我睡的那个房间逡巡,她会像我幼时垂涎别人家果树上的果子一样,一天数次在我睡觉的房间窥探,摸我盖过的被子,摸我穿过的衣,寻找突破口。她像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只要找到一个貌似合理的借口,就可以开向我的领地。她终于找到了。
有一天晚上,母亲跟我视频,告诉我她正睡在我睡的那张床上。“不是我要睡的,是你小侄女非要睡你的床。”母亲笑着解释,一脸甜蜜和满足。母亲有时会带我的小侄女住到合肥弟弟家,她知道我格外疼爱我的小侄女。后来,她又找到了更多借口,比如她的睡衣没洗或没带,因此可以冠冕堂皇穿我留在那里的睡衣。再后来,她得寸进尺,连我的外衣也穿。她打电话给我说:“这几天天气冷,衣服没带全,我穿你那件咖啡色毛线衣了啊?”她像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其实她早已穿上身,她只是要告诉我,她穿了我的衣。潜意识里,她大约是告诉自己,她和她的女儿,是如此心心相印地一步步贴近。我跟她说:“那件毛线衣,你若喜欢,你就穿去吧,我不要了。”可是,她后来将毛线衣洗洗,又叠好,放在原来的位置。她大约只是享受穿我的衣服,而那衣服上残留着我的味道。
她大约像我幼时渴望被她亲吻一样,渴望和我无限地靠近。
她大约想喊回女儿。喊回在时光里早已远走不肯回头的女儿。她以为能喊回来。
…………
想到母亲的那些小伎俩,我常暗自心疼,暗自愧疚不已。可是,每回陪母亲散步时,母亲想要牵我的手时,我总是下意识地想要闪躲。我不肯和她十指交扣。十指交扣,体温传递,应该像一条河流从上游流到下游,浩浩汤汤,一日千里。而我的上游在我幼时已经断流,我独自流淌,我淌成了另外一条河流。我和母亲已经是两条河流,我们不交汇,但我们同向,就像地图上的黄河和长江,同样地自西向东,不远不近地相望。
我慢慢找到陪母亲散步的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将我的胳膊搭在母亲的肩膀上,我们不像母女,倒像一对姐妹。母亲年轻时和我现在一般高,可是现在老了缩了,我的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刚刚好,我很舒服。而母亲似乎也很满足,她大约觉得我把她揽进了怀里,她的全世界都在我的怀里了。
五
小姨得的病,好像并不严重。她依然可以行走,可以跟我说笑,只是不再干活,只是一日日地消瘦。
我每放假就去外婆家,小姨不再远远站在木槿篱笆边等我。但我一进屋,我一说话,小姨就会从病床上爬起来,颤颤摇晃着,走到堂屋,拉我到她怀里。
多数时候,小姨都是睡在床上。我以为,睡睡就会好,所以小姨生病,起初我也不觉得十分哀伤。小姨只要还能让我看到就好,哪怕是一个消瘦的小姨,她也是我的小姨。
外婆和母亲常常窃窃私语,她们议论小姨刷牙也不会流血了,还有那个女人每月都会流血的事,小姨也不流血了。她们议论的内容我越来越觉得陌生,也就越来越有隐隐的害怕。我不知道我的小姨接下来会变得怎样未知。除了见过大人杀鸡杀猪,我还没见识过人的死亡。
小姨得的是白血病。她一直瘦着,瘦着,瘦到最后皮包骨。我不再枕着小姨的胳膊入睡。我睡在小姨身边,夜里听着江上轮船的鸣笛声在黑暗中颤抖成线,然后一点点在夜气里被抽走。我像是被一种潮湿而浩瀚的黑暗笼罩。我又沉在黑夜里了。
两年后的一个初冬,小姨走了。她才二十三岁,还没有经历过恋爱,就永远地走了。
小姨躺在棺材里,在一片浩茫而模糊的哭声里,她的棺材被许多人抬走。她将要被葬在离江边不远的沙地上。许多人跟在棺材后面,给小姨送行,我一个人走在这悲怆的队伍里。而身后,外婆哭得几近晕倒,她要送小姨却被人拉回。我看着恸哭的外婆,又看看那悲怆的送行队伍,忽然一个人立在半路上。我流着泪,不知要跟谁说话,不知说什么,举目荒凉。我像是悬挂在半道上,不知道是该留下来陪外婆,还是该追随那队伍去送小姨。
我悬在初冬的风里,不敢去送小姨。我怕回来时,我回来了,而小姨却不跟着我回来。
我从此就那么悬着了。既等不回来小姨,又不肯回头认领母亲……
送葬的队伍全不穿孝衣。他们说小姨死后是要上天堂的,给去天堂的人送葬,不必素服相送。可是,我却不愿意小姨去天堂,天堂太远,不如沙地上垒起的黄土坟茔近。我渴望小姨住得离我们近些。当外婆家的炊烟自屋顶袅袅升起,我伴着外婆在灶膛后面慢慢烧着柴火,芦苇叶子燃烧后的焦香弥散在轮船鸣笛过的空气里,小姨就能闻到。
我的私心后来竟然得到满足。大人们大约也不希望小姨上天堂,天堂不仅远,而且不接受清明冬至我们给她焚烧纸钱。于是,憋了一两年后,关于我小姨的去向又有了新的结论,他们说我小姨入教时间不足一年,资历浅,上不了天堂。这真是好,小姨即使死了,还未出村庄。从此我们上坟时,想想小姨就在坟里不走神地睡着,与我们只隔薄薄一层黄土,便觉得心里安妥。清明冬至焚烧纸钱时,我还可以听着大人们呼唤小姨的名字。
我带着对小姨的无尽思念,从此在父母的屋檐下一日日寂静长大,乖巧长大,不再对大人的怀抱抱有指望。而《妈妈的吻》里那句“叫我思念到如今”,我终于慢慢懂得其中滋味,并常常在心底无声唱起。
二十多年后,外婆去世。我送外婆,到她入土。外婆的坟就立在小姨旁边。那是盛夏,小姨的坟上青草萋萋,正如小姨一般,一直是二十来岁的青葱年纪。二十来岁的小姨,如果站在如今四十多岁的我面前,年龄上完全可以是我的孩子。可是,她在我心里,依然是母亲。母亲是没有年龄的。母亲是爱的矿藏,没有年龄。此刻我回想小姨坟上的青草,依然觉得后背上犹有小姨的体温。爱,让时空无界,让生死无隔。
写到这里,我自然想到生我的母亲,那个喜欢背地里穿我衣服的我的老母亲。按照人们善良的愿望,我该和她来一场情感上的大团圆。从前我凝望她,现在她贴近我,我们应该跨过三四十年的时光,执手相认:啊,这是我的女儿;啊,你是我的母亲!
可是,我想了又想,问了又问,确定自己还是不能完全做到。即使此时母亲张开怀抱,让我躺进去,我依然不能安然享受。一闭眼,我仿佛依然看见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站在我面前,不远不近,目光幽怨微冷——我惊觉,躺在母亲怀里的,还是我的幸福的弟弟。母亲,还是弟弟的母亲。
我为此苦恼了许多年月。这个深秋,我散步在鲁院的海棠树下,看着满树的红果子,忽然发现海棠和海棠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南方,海棠的果子小如天竺子一般,其味酸涩。可是,在北地的鲁院里,海棠却结得如此红艳水润,硕大如山楂大小。水土相异,让南地和北地的海棠也如此不同。同样的海棠树可以结不一样的果子,原来,这个世上,许多事情并不是只有唯一的答案。
那么,我又何必纠结于认祖归宗母女相认呢?
当我把胳膊搭在母亲的肩膀上时,我便是替小姨活着,活成母亲的姊妹。
想起十多年前我的那位名叫海棠的学生,她如今已经长大,也许也做了母亲。她和我一样,有两个母亲。如果做不到像江河交汇一样相认,也许像我这样,留下一个当作姐妹,也未尝不可。
我常想,如果小姨还活着,我大约会常常拉上她和我的母亲一道,去逛服装店,给她们一人一件地买。在伴同这一对老姐妹回家的路上,我会夹在她们两人中间——我一只胳膊搭在母亲的肩上,然后,我的脸悄悄侧到另一边去,在应该五十多岁的小姨的额上,甜蜜地印上我的口红。我的吻,像一颗北地的海棠,嫣红而多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