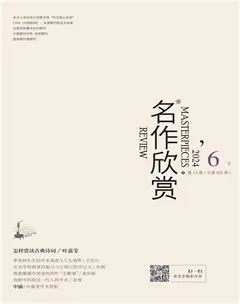人生难得是欢聚
陈漱渝
1936年2月21日,即临终前不久,鲁迅为《呐喊》的捷克译本写了一篇短序。序言说:“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整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李叔同作词的《送别》一歌,以美国为源头,流传到日本,又在中国家喻户晓,就是印证上述论断的生动例证。
《送别》的原作者是美国音乐家奥德威。1851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奥德威创作了《梦见家和母亲》这首歌,缅怀童年时代父母的爱,那是一生欢声笑语最多的时光,成年后远离了故乡,跟父母相见无期。歌词希望双亲健在时儿女能多尽孝心。这首歌仿照了黑人歌曲的格调,抒发了人类对家庭——特别是对母亲感恩和眷恋的普遍感情,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至今,成了流行歌曲中的经典之作。
《梦见家和母亲》流传到了日本,被日本犬童球溪重新填词,改编成了《旅愁》。1907年,犬童球溪正在新潟高等女子学校任教,这首歌被选入了日本的《中等教育歌唱集》,成了当时日本的流行歌曲。歌词描写一位旅人,在深秋夜阑人静时怀念故乡和父母,思绪奔涌,心情迷惘。此时风雨敲窗,打碎了他归乡途中的美梦。就曲谱和情感而论,这首歌曲无疑是《梦见家和母亲》的翻版。
关于李叔同创作《送别》的过程,我查过一些资料,大同小异。通常的说法是,李叔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跟挚友许幻园的别离。许幻园是富家子弟,好舞文弄墨,号称“华亭诗人”。他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城南文社,以文会友,活动地址就在他家——上海大南门附近的城南草堂。李叔同因征文活动结识了许幻园,许欣赏其才华,请李叔同携眷住进了城南草堂,并在他家门前挂匾,名为“李庐”。李叔同1900年刊行的《李庐诗钟》《李庐印谱》即因此得名。在城南文社活动期间,李叔同还跟宝山名士袁希濂、江湾儒医蔡小香、江阴书家张小栏结为“金兰之交”——意即友情坚如金石,跟许幻园一起号为“天涯五友”。许幻园之妻、沪上女画家宋梦仙为之作《天涯五友图诗》,其中夸赞李叔同的七绝为:“李也文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只把杜陵呼小友。”李叔同也有《清平乐·赠许幻园》一词:“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户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然而,这种“情适闲居”的好景不长。由于时局不宁,许幻园经商破产。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许幻园来到李叔同的门前,远远地喊了一句“我破产了,后会有期”,便飘然而去,携妻女到北京另谋生计……在这种伤离别的心境中,李叔同酝酿了《送别》的歌词。
遗憾的是,《送别》的手稿未存,仅存丰子恺的手抄本,最初见诸裘梦痕、丰子恺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1927年8月由开明书店初版,作为中等教材广为发行,现孔网拍卖价最高标为八千元。歌词的字句在流传中有出入,比如“一壶浊酒尽余欢”,亦作“一觚浊酒尽余欢”。“觚”与“孤”同音,是古代的酒器,也作为祭祀时的礼器,容量均为两升,是贵族礼仪文化的用品。“觚”与“壶”用途相同,形状有异;“觚”这个称谓较雅,“壶”相对比较通俗,更适合通俗唱法。据我所知,《送别》的创作时间有1913年、1914年、1915年等多种说法。我认为1915年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年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音乐课,又曾短期去日本避暑,有可能接触到更多的日本歌曲。这一时期,正是李叔同创作歌词的“金色秋天”,除了《送别》,还有不少歌词问世,如《早秋》《忆儿时》《悲秋》《月夜》《秋夜》等。还有人认为《送别》的抒情对象是他的日本情人诚子。这不大可信。因为诚子是1911年4月跟李叔同一起到中国生活,直至李叔同1918年出家。受戒之后的弘一法师,当然不会再写《送别》这样的“红尘情歌”了。
李叔同《送别》的歌词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李世珍是清同治年间进士。业师常云政、赵幼梅、唐静岩都是饱学之士。从十六岁开始,李叔同对文艺,尤其是戏曲产生了浓厚兴趣,为其日后成为书法家、画家、音乐家、诗人、戏剧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二十二岁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总教习是蔡元培,同学中有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名家,二十六岁时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创办了《音乐小杂志》,主演了《茶花女遗事》,并于三十二岁时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所以他能为《送别》的原曲填写出家喻户晓的歌词绝非偶然。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这三首歌词同中有异。共同之处就是表现了思念故乡、思念友人,特别是思念亲人的感情。中国古典诗词中不乏此类文字:“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宋〕晏殊:《玉楼春·春恨》)“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南唐〕李煜:《长相思·一重山》)“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汉〕佚名:《孟冬寒气至》)“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唐〕卢纶:《李端公》)“重来不怕花堪折,只怕明年,花发人离别。”(〔南唐〕冯延己:《忆江南》)外国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伤离别的诗歌。大学学俄国文学史时,记得屠格涅夫、阿赫玛托娃都写过此类作品。可见伤离别表达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
《送别》跟《梦见家和母亲》以及《旅愁》的不同之处,是其他两首诗对情感的表达比较直露,而李叔同的填词却是将一连串的意象巧妙连缀起来,自然流畅、深沉含蓄地抒发了惜别之情。前一段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吹拂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长亭”是古代驿站。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是送别休憩之地。李白五绝《劳劳亭》写道:“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王实甫《西厢记》中,有《长亭送别》一曲。李叔同的词《南浦月》中也有相似的描写:“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古道”即野道,给人以苍凉之感。“芳草”指香草。芳草无情人有情,目睹青绿色的芳草更增离别者的绵绵愁思。“晚风吹拂”给人以凄冷之感。李清照词《清平乐》中有“怎敌他晚来风急”之句。“笛声”也是凄切之音,催人怆然泪下。王之涣《凉州词》有一句“羌笛何须怨杨柳”,就是为了渲染离愁别绪。“夕阳山外山”,落日斜挂山头,山峰层层叠叠,夕阳欲隐未隐,山形依旧,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书写的也是不胜依依的故人情。“天之涯”“海之角”,形容别后距离遥远。“知交半零落”,并非形容友谊淡化,而是各奔一方,剩下的是孤独。鲁迅旧体诗《哀范君三章》中,也发出了“故人云散尽,我等亦轻尘”的慨叹,沉郁顿挫,令人痛惜。“浊酒”是含有杂质的普通酒。离合悲欢,尽在酒中。李叔同七绝《津门清明》中有云:“一杯浊酒过清明,肠断樽前百感生。”酒不解真愁,故余欢短暂,苦涩绵长。“别梦”是离别后的梦境。一个“寒”字,更为梦境增添了冷清、凄苦之感。
《送别》第二段的歌词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问君此去几时来”中的“来”指回来。“来时莫徘徊”中的“徘徊”指犹豫不决,表达了作者对友人重聚的热切期盼。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意思是见面机会十分难得,分别时刻难舍难分。“聚”是对重逢的期盼,“别”是对希望的播种。
根据我的体验,人生往往是一个不断离别的过程。“别”易“聚”难。“暂别”是常态,如每天下班会跟同事挥挥手,明晨又会在同一个点打卡上班。毕业分配、战友复员是“久别”。最不堪回首的是“诀别”,从此永不相见。2006年9月30日,我的母校雅礼中学举行百年校庆。我们初中的同班校友纷纷从各地聚集于湖南长沙。庆典后举行餐聚。席上敬酒时说:“五年后再聚,一个都不能少。”“你若回头相望,我必如约而至。”然而,从那时到今天,花开花谢十七载,这些祝愿竟成豪言壮语,不少发小已经驾鹤西去,“一个都不能少”的美梦转成空,令人唏嘘不已。这让我想起了张震岳创作的流行歌曲《再见》:“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当然也有壮别的场面。如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有一首主题歌,叫《驼铃》,结尾有“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这种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歌词。但这首歌开头抒发的情感仍然是:“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伤离别虽是无言的痛、涩涩的苦、深藏的泪,但不等于那种凄凄切切的颓唐,也不等于西方那种推崇情感、忽视理智的“伤感主义”,而是让人们更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次相遇、天地间的每一分温情,把“思念”当成生命的火,把“重聚”当成力量的凝结。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中有一名句:“多情自古伤离别。”鲁迅七绝《答客诮》中开头一句是:“无情未必真豪杰。”中国人是这样,外国人同样如此。
写到这里,我还想起了中国台湾女作家林海音。记得198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吴贻弓把林海音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城南旧事》搬上了银幕,影片主题曲就是李叔同创作的这首《送别》。这既是当年的一首学堂歌,一经上演,又变成了当下的学堂歌,传唱更广。1989年9月8日,林海音在台北忠孝东路青叶餐厅设宴,欢送一位女作家出国深造,我也忝陪末座。我问林海音身体状态。她说:“我身体挺好,每天早晨五点半就出门锻炼,只是有糖尿病,没有别的病。”我得了几十年糖尿病,平时并无特殊感觉,故并不在意。事后我写了一篇《人生难得是欢聚——台北两晤林海音》。文章的结尾写道:“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位老人迈着稳健的步履,在北京城南的胡同里寻觅她童年的梦,就像她六十年前背书包走出北京城南椿树胡同,穿过鹿犄角胡同,向厂甸迤北的师大附小走去一样……”20世纪90年代,七十多岁的林海音果然回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北京,逛了城南的胡同,喝了北京的豆汁,跟分别多年的亲友重逢……不幸的是,晚年的林海音糖尿病并发,于2001年12月因中风去世。我在台北跟她的欢聚,竟成了此生中的一次诀别。我现在追悔的是,她回北京时,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去拜访她呢?这更使我相信《送别》中的那句词:“人生难得是欢聚!”
——《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评介
——《李叔同——弘一大师影像》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