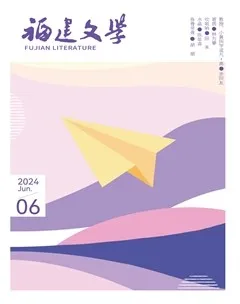格里格之书
陈元武
一、太阳升起
太阳在这本棕皮书上重新燃起了火焰,它带着一些霉腐味,纸质发黄,一些铅字从纸上剥落,一些被茶水渍过的地方洇出奇怪的图案,像楔形文字或者巫灵。挪威的冬天阴晦无光,北海狂劲的风从北极吹来,沿着地球自转产生的切变线从东北沿岸吹进挪威的森林,峡湾那边已经白雪皑皑,红松的枝丫在雪的重压下吱嘎嘎响着,不时落下,弹起一阵雪雾。雪中有一些不安分的雪鸡在鸣叫,嘎嘎嘎,沉闷而快节奏。狼在森林深处嗥叫,呜——,拖长了尾音。在卑尔根市的峡湾和湖泊中,泊着一些白色的单桅帆船,渔民们正在烧着早餐的奶茶和乳酪片,煎着鳕鱼段,哼着小曲。沿着海边的拥挤的街道走着,地上一片泥泞,未化开的雪和污水混杂在一起,成为污浊的雪水。格里格叼着雪茄烟,一边走着,一边往远处的海上看去,灰晦色的天幕底下,错乱无序的彩色房子像一堆音乐的乱码。岩石高峭的峡湾出口,似乎有一群海鸥在执着地盘旋。岩石边的少许耐寒的奥勒松像长不大的盆景似的点缀在那里,加上一些伏地的杜鹃和苔藓植物,山看上去不太裸露,仅仅如此而已。北欧的极寒夜到来之前,一切仿佛都像是轻松的前奏曲。夜晚说来就来,下午茶刚刚喝过,天就黑了下来,从上午开始的白昼迅即结束,才过去不到四个小时。于是,路边的灯一直亮着,这是老式的煤气灯,每天都有一个点灯人沿街将每盏古老铁艺灯柱上的煤气灯点燃,顺便将灯罩上的积雪掸落。煤气灯刚刚点亮时,微微地跳跃着,直到夜色降临,气量加大后,颜色从橘黄变成了雪白,照着泥泞的街道,泛起一片青色的光。我在这里短暂的旅行有了些浅直的感觉,那本书虽然罩在玻璃里,但还是给了我冲击般的印象。黑暗的夜如潮水般淹没了一切,街上昏暗的灯光说明留在这里的人口不多,冬季多半去了南方的海滩,北欧的冬天是他们的重要假期。
1874年初冬的一个傍晚,格里格走进卑尔根萨尔登码头街边一幢三层小楼的暗红色门,一股白雾趁着开门的当儿扑进屋。台阶上的雪让老仆人扫得很干净,仆人叫桑普森,一个卑尔根本土的老头,原先侍候过格里格的父亲和母亲。父亲亚历山大·格里格,一个零售商人、卑尔根市副领事,母亲是挪威著名律师和政治家爱德华·哈格鲁普的女儿珍·哈格鲁普。他来到峡湾罗浮敦小镇,是为了给易卜生的戏剧《培尔·金特》创作配乐组曲《培尔·金特组曲》:《晨景》《奥赛之死》《安妮特拉之舞》《在山神宫中》《英格丽德的悲叹》《阿拉伯舞曲》《培尔·金特归来》与《索尔维格之歌》。入秋之前,太阳已经微弱得只剩下了红光和柔和如壁炉之火的光焰,他的卧室朝向海湾。当太阳从峡湾东面升起时,先是染红了有着赤褐色植被的山峦,奥勒松低矮的树冠也被阳光所染红,在清晨的天幕中像燃烧起的一团团火苗。早上十点多,太阳已经照进他的卧室,在那张橡木桌上,摆着易卜生的戏剧《培尔·金特》,棕色的书皮上满是新鲜的印刷痕迹,烫金的书名和易卜生花样签名的字迹。内页上满是他用红蓝墨水注释的字迹。作曲,有时需要像评论家一样,对原著做出准确的判断和理解,并能够沉浸式进入其中的情节,陶醉在字里行间。音乐是再创作,也是对原著的发挥和升华。音乐更像是诗意的激情。但格里格知道,要克制、克制,克制住自己的创作冲动,冷静地将音乐融入剧情中。格里格像重新认识自己似的看那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随后进入冥想状态,偶尔有灵感,即匆忙记录下来,来到楼下的钢琴边坐下,试着弹奏以确认那种音乐的感觉。桑普森站在角落,静静地听着,然后对方才的弹奏发表看法。格里格觉得自己的音乐知音,除了母亲和老师外,就是这位忠诚的仆人了。他听得一脸微笑,半闭着眼睛,陶醉在方才的音乐节奏中。然后俯下身来,给壁炉里再添些干柴。炉外的铜水壶里喷着热气,那水是给他晚浴用的。另一只小银壶里装着他泡咖啡的水,南欧的迷迭香和薰衣草前不久刚从法国普罗旺斯寄来,路上走了近一个月。他将一些草浸泡在水里,然后和水一起倾倒到浴缸中。搪瓷浴缸也是法国的货,罗斯柴尔德的浴缸能够抵挡住北欧的严寒和冰冻,瓷白的缸里,不久被浅褐红色的香草液所淹满,浴室里,白色的雾气弥漫。格里格一边泡着香草浴,一边还在想着那段曲子,他需要将那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激情地表现出来,他选择了长笛和圆号作为主演奏乐器:长笛、黑管、圆管、小号、定音鼓、弦乐队。海边的薄雾重重的森林边,微风吹拂,卷起的雾迅即升到空中,化为云岚。太阳升起的瞬间,音乐从长管吹出,富有节奏和流水般的韵律。光影迷蒙的海面上,阳光越来越强烈,直到透过雾霭,照亮了整个森林。海洋中的鱼在海雾中穿行,像鸟儿似的飞鱼、鲾鲼和斑点鲣鱼在空中短暂地飞行,将海面变成了舞台。阳光越来越强烈,直到在天空中烧出整片的橘红。音乐渐渐从欢快的长笛转向了长笛、黑管和圆号的重奏。管弦乐是交响的灵魂,也是音乐高潮的推动者,像浪花一样。从舒缓的引子,到越来越欢快的管乐重奏,小提琴介入,将音乐往高处推。太阳升到了半空中,海水湛蓝,天空中布满了喜悦的粉红色,不断重复的节奏将浪潮的次第冲击引入更美妙的境界。风似乎停止了,然后重复长笛的漂亮而美妙欢快的乐音。但此刻,格里格盯着窗外远处的海上,那一抹曙红色的霞光。那轮红日升起,时间已经快到正午时分。海雾渐渐散去,空气中飘着微雨似的雾霰,像雨,也像雾。灰色的天空渐渐舒展开,像揭开的重重舞台帷幕,直到露出一丝浅蓝色。太阳升起,天空依旧像临近黄昏的感觉,太阳并不会从头顶上掠过,它只是以较低的高度环峡湾走一段路,即重新沉入峡湾的重山后。天空中永远有着一种玫瑰红的颜色,他桌上的书沐着这种红色的霞光,感觉那就是一本浪漫之书。
我去的那些天,经常突然间就下起雨来,北欧的天气如此怪异莫测,因此,我都带着一把透明的伞,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但那种凛冽的寒风仍然让我感觉仿佛有刀锋掠过脸颊。沿着布吕根大道一直朝海湾走去,海水灰褐色,反射着灰黄色的天幕,似乎有一种光像幽灵般穿透过厚厚的云层。女儿说,那是极光的幻影,白天也可能出现,蓝色、绿色或者玫瑰红色,像纱巾一样在天际出没,似乎有一种光更像是从神殿上看到的那样。街上没人,除了我、女儿和她的同学欧根·哈特,挪威人很少在街上闲逛,除非是夏季的音乐节和啤酒节等。酒吧也只开到下午三点多,全天只营业不到四个小时,晚上,就关门打烊了。连超市也只开到下午四点半多一点,灯亮起的时候,街上的商店都关上大门。海边码头上泊着的闲舟在海水里摇晃着,主人不在,没人打更,就任由北海的风浪来打理。船体满是海草和碰撞的划痕,船帆包裹得紧紧的,仍然进了雨水和海水,帆衣鼓鼓囊囊的,里头的积水恐怕要等船主人回来打理了。每个周末,码头上都会有一批渔船靠岸交易,主要的鱼就是鳕鱼和鲣鱼。三文鱼是人工养殖的,通常本地人不喜欢吃,而最喜欢的鳕鱼肉质细嫩无刺,煎鳕鱼是当地人的主要肉食。哈特喜欢啤酒加培根、三明治或者牛排,但挪威,鱼块比牛排便宜很多,大鳕鱼切成几块,双面煎黄,浇上豆蔻粉和罗勒或迷迭香打成的汁,里头加了块柠檬、橄榄油,夹进面包片里,就成了挪威三明治。热狗也是夹块鱼柳,而不是香肠。街灯亮起的时候,湿地上映出五彩的灯光。布吕根沿海湾边是一排大木屋,两层或者三层,外墙色彩艳丽,白色的窗框加玻璃,使得房子像油画般鲜艳。空气极其潮湿,寒冷透过厚厚的羽绒钻进来,身体明显感觉到它的威胁。所以,在这漫长的冬天里,烤火成为必要的日常。屋里有暖气外,还要加个壁炉,幸亏在大厅里通常不会待太久,卧室才是温暖而舒适的空间。
在布吕根的私人小旅馆里,拥挤着其他国家来的游客,但我们只在自己的房间里欣赏格里格的音乐,房东给了我们蓝牙音箱,说你爱听什么音乐都可以从网上直接播放。那个稍有些肥胖的大妈有着一头红发,身材魁梧,她说自己是从西班牙过来的,本来只打算度个假,结果前房东意外去世,给她留下了这幢房子,她便将它改成了私人小旅馆,租金远低于酒店。她说,太寂寞了,这里就缺少点人气,你们从世界各地来,正好填补了我的寂寞。她的挪威语里夹着西班牙语。她说,以前,人一多,她就会开酒会,然后跳弗拉门戈舞。她对着我比画了下,说现在不行了,身材严重变样,跳不动了。她朝我们挤了挤眼睛,以消除尴尬的气氛。外边那群人,应该是某个大学的学生,长相像中东阿拉伯人。他们的声音实在太吵了,我便从卧室走到日光室,这是全玻璃房,朝向天空,虽然外边寒冷,那冷透过玻璃在阳光室里积聚着,但还好,厚厚的衣服让我感觉舒适。天空中闪烁着极光,一会儿绿色一会儿就转为粉色或者蓝色,像女巫的帽子飘带似的,在天空中忽闪。天上的云似乎要散开了,但窗外仍然飘着细细的雨,像雾一样,不时打湿了玻璃。北海的风裹挟着北极的寒气,将海浪吹成了细雨,雾白的海瀣像幽灵般扑向海边。挪威的西部和北部,陆地裂成无数的碎片,像块冻裂的奶酪似的,那海瀣从峡湾的山间直吹进来。因此,在晴好的夜晚,仍然会遇到莫名的雨。
《培尔·金特》一书就在手里,英译本,易卜生的头像雄狮似的,有虬曲的头发和浓密的胡子,棕色封皮上有他的签名手迹,也镀成了银色。培尔·金特是一个病态的沉溺于自己幻想的角色,他成为权迷心窍、自大狂妄的牺牲品。年轻时,他粗野、鲁莽,经受着命运的多次捉弄,于是他离家出游,在外周游一番后,回来时已经年老,而回家途中又遭遇翻船,使得他的财富化为乌有,他又跟离家时一样一贫如洗,而他年轻时的情人,一直忠诚于他的索尔维格迎接他的归来,他筋疲力尽地倒在她的怀里,幸福地死去。1874年秋,格里格拿到了《培尔·金特》剧本后,欣喜异常,他恰好需要向诺尔德拉克证明,他除了能够写器乐小品外,还能够写歌剧、大合唱、交响曲等大型体裁。那年春夏,格里格刚好拿到了政府年金,这要归功于著名钢琴家李斯特的极力推荐,他的《F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受到李斯特的盛赞。格里格投入为易卜生的新诗剧《培尔·金特》的配乐中。那一夜,在香草浴的温和芳香中,他的灵感诞生了,像美妙的清晨的阳光和鲜花般,他的前奏曲有着诗一样的浪漫和舒缓节奏。“那浓密的鲜花丛中,海水从远处折射来阳光的暖色,罗兰的长叶上缀着露珠,索尔维格在井边汲水,但这似乎是培尔·金特的幻想,他身处万里之遥的北非,在地中海边沐浴着阳光,但他的思维穿梭在两地空间。”格里格一直写到了凌晨,老仆人困得在壁炉边的长椅上睡着了,呼呼地打着鼾,恰好像节奏器般。格里格已经忘记了时间和疲惫,他的激情像汹涌的海浪,他不断地重击着钢琴琴键,在轻盈和跳跃的音符间做着美妙的和弦连音,回旋段、复调、升A和降A。弦乐的适时插入,将音乐引向宏大的高潮段,然后,复归轻柔、舒缓、漫不经心的细节处理,节奏之后是《阿尼特拉舞曲》,节奏明快,动作欢快有力,是阿拉伯舞蹈的风格。这首三部曲式舞曲,格里格在钢琴上顺利完成了试奏,手指跳荡着,仿佛阿拉伯的温暖海边,一群人在欢舞庆祝着什么。但他使用了属于加泰罗尼亚风格的地中海舞蹈节奏,仿佛有一个身着鲜艳舞服的舞者在一群人中间跳着不属于他们的舞蹈,像波希米亚人、加泰罗尼亚人或者吉卜赛人。阿拉伯人骑着马或骆驼,腰里别着雪亮的弯刀,大胡子在脸上像一蓬沙漠上的蓬草,酒玷污了他们的白色长袍,银色的杯子狼藉一地。红毯上,歪躺着一个胖子,正搂着一个红衣舞妇。和易卜生诗剧本身的严肃相比,他的配乐多了些风趣和轻松的成分,易卜生剧本中的悲剧气氛也随着格里格的音乐而变得更像经典的歌剧。
二、奥赛之死
格里格写到《奥赛之死》段时,竟然引用到日本《樱之歌》的节奏,他运用了单音重复的节奏,将死亡表达得很完美,悲伤在内心里,像樱花开放,天空中隐隐现出奥赛那张美艳的脸庞,隔着阳光和云纱,似乎一切都将永恒,像大地和四季一样重复出现。“这是东方的古老的葬礼之歌,春天短暂,像她的生命一样,绚丽非凡,却总是宿命似的以悲剧的结局出现。人或者都要死的,只是这样的死无比诗意,给生者悲恸的同时,樱花的飘落像诗的最美结束。”我静静地听完这一段,想着和那天在某画廊里看到的那幅东方风格的绘画一样,充满着怅惘和惊喜,心情同样是复杂的,像柠檬汁里加入了一杯甜酒。我听到这熟悉的东方音乐,不免动心。格里格博取了世界各地的音乐风格,来创作他的《培尔·金特》,就像我在阿姆斯特丹凡·高艺术馆里看到大量以浮世绘风格为蓝本的绘画时,也极为惊讶。凡·高早期绘画中日本艺术因素如此之多,像他的一幅表达春天的画中,樱花、天空的蓝、东方式的桌椅后的浮世绘画、楹联上的汉字,无一不是东方元素。他曾在给弟弟提奥的信中提道,遥远东方国度的艺术如此严谨和纤细,准确而略有浮夸,似乎那里的艺术更加概括和诗意。格里格同为北欧人,性格里竟然如此相似,按格里格自己的话说,像浪漫主义诗人,兼具民族主义情怀。他跟合伙人诺德罗共同创办了演出团体尤特皮社,力主介绍和演奏北欧民族音乐,后来他创办了克里斯蒂安尼亚音乐协会,并任该协会的乐团指挥,在国外演奏自己的作品。
半夜时分,天空的云终于散去,对面街道的楼顶上,太阳房里燃起了蜡烛的光,一对年轻人在里头卿卿我我的。这是浪漫的时刻,是属于他们的,也是属于音乐和激情的。天空中的极光越来越明亮,有人说,那是北极之神在开酒会,冰雪女王和众神在神秘的光芒中释放出一颗又一颗流星。北欧人性格多半是严肃和刻板的,也沉默寡言,独来独往。平常在街上,很少遇见几个人聚在一起喝咖啡或者闲聊,只偶尔有人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着,像风似的从身边闪过。北欧是诗和童话的世界,但也不全是,冬天的短昼让人压抑,漫长的夜让人冷静和孤独,也让酒和灯光变得无比美妙和不可或缺。这里的人拒绝新式的灯光光源,白炽灯依旧是他们的最爱,彩色玻璃灯泡发出柔和温暖的光,夸张的鸭梨形灯泡里,钨丝微红,像一条神秘的经脉。工业文明的语言从来简单直接,当年发明煤气灯的人想不到,一百多年后的现代,仍然在用着他的煤气灯。同样的白炽灯给人以温暖感觉,生活味浓郁,怀旧风强烈,背景是深色的木质墙壁,墙上挂着一些简单的艺术品,照片、艺术绘画或者是一张古老的唱片。黑胶唱片一直是艺术人的最爱,听用杜比音响系列还原的音乐,如身临其境。格里格诗意音乐和丰富的想象力,让音乐存在诸多域外元素,更加让人沉醉。钢琴在某些音乐表达上更像是王子似的,在快速节奏的处理上能够做到纤细毕现,力度、节奏和音色丰富并茂。比如《奥赛之死》,前半部音乐简单重复,却能够让人心为之一动,那是简单的怀念,也是无奈的极致。
北欧的樱花更加短暂,所以,他们不种类似的树,而是种耐寒的雪松、云杉和山毛榉。但落叶树长得极缓慢,几十年了,仍然是一棵不大的树。比如卑尔根山上较多的挪威槭,秋天时满山的红艳,从金黄到橙红再到赤红。在格里格故居旁边就有着两棵挪威槭,一棵是青叶槭,另一棵是紫叶槭,和那幢浅绿色的小楼相映成画。北欧人长于思考,也在艺术上有特殊的敏感神经。在格里格故居二楼,看到一张19世纪的橡木桌台,上边放着这本《培尔·金特》,棕色的封皮已经脱漆,旁边有封打上火漆的信件,纸质均已发黄。据纪念馆的管理员尼特森·贝克尔说,格里格在这里度过了余下的时光,他在楼上这张橡木桌上创作音乐,然后将谱稿拿到楼下弹奏。那时候的特罗豪根尚极具山野气象,本身卑尔根的人口就不多,多半是渔民。这是个小山坡,木屋建成以后,他和妻子就在这里生活。米色的外墙漆是后来才刷上去的,原本的木头本色让风雨侵蚀成灰褐色,门口的斜坡边有一丛野蔷薇,春天的时候,开满了白花,芳香在风中传得很远。现在钢琴和照片都在二楼的原工作室里,一扇窗户朝着海湾的水面,阳光和风能够从窗户透进来。当春天来临时,远山开着白色的槭花,山毛榉树鹅黄鹅黄的新叶舒展开,像春天的信使。夏天,他都在创作中,傍晚从家中出来,沿着缓坡走向海边。这海像一湾湖,海水湛蓝,和远山相映出安静宁谧的如诗画面。仲夏节,人们在海边狂欢,在太阳不落山的氛围里尽情发泄着身体里积压已久的激情。音乐节往往很简单,在海边酒馆里,或者在船上,或者在山间野营地。现在的啤酒音乐节更加狂欢,摇滚音乐成为主体,而一百多年前,主要以手风琴、钢琴和当地一种说唱艺术为主,加上民族服装的舞蹈Hallingdans,类似于踢踏舞,一个小伙子旋转着舞步,像鞑靼舞,下蹲、转身、击掌、踢踏,一个姑娘手持桦木棒(用于驯鹿)站在圆凳上,小伙围绕着她不停地以舞蹈献殷勤。音乐比较简单,有风琴、口琴和弹拨乐器。格里格较常参与这样的音乐节,他的乐队还演奏他的音乐。另两种民族舞曲为哈林格舞曲和斯普林舞曲,类似于Hallingdans,节奏欢快,不停地旋转和击掌。格里格个子不高,一头卷发,动作敏捷准确。烤鹿肉和炫耀渔获成为人们的主要娱乐消遣,三文鱼、虹鳟、鱼子酱和腌鲱鱼(臭味惊人)、鹿肉在烤架上吱吱响着,三文鱼段在烤叉上旋转着,鱼油滴在炭火上,冒起阵阵青烟。天空中,那轮不落的太阳斜斜地擦过山冈,就重新升起到天空中,夜晚几乎不复存在。我和他们一起坐一条小游轮到峡湾里看风光。但现在看到的只有皑皑白雪。风不算太冷,山顶不时有雪滑落,激起一阵雪烟,高大笔直的云杉像图腾一样直指苍穹。船开了一小段,便折返,按法律规定,现在的天气,不能进峡湾深处。在相对开阔的湾面上走着,仿佛在某个湖上。听着听不懂的语言,他们有说有笑,我静静地看,静静地听。有个本地的小伙,会摇摇铃,一路上摇着,沙沙沙地响,似乎有某个音乐在无声地配合着他。马库斯·米勒的爵士贝斯,和他的摇铃比较相配。
一个高个子北欧中年男人,络腮胡子,灰色的头发和灰蓝色的眼睛,在看一本书,我一看,正是易卜生的著作《玩偶之家》。他似乎很投入,也许他是个跟我一样的人,但限于语言,我只能看着他静静地读书。奇怪,他怎么挑在喧闹的游船上看书?也许吧,这会儿他有空看书,或者,风景实在单调了,抑或是我们这些俗人让他厌烦了。北欧人是不喜欢太过闹腾的环境。也许是漫长的冬季把他们的性格塑造成冰雪的模样。我记得《奥赛之死》篇章里这么说:“那些悲哀总是短暂的,就像冬天,再漫长也将过去,桦树和榉树按时发芽,而她的尸体也将在花开时变成一缕尘烟。”我们拜谒格里格墓地的那天下午,天下着淅沥的小雨,这里虽然寒冷,却多是雨而不是雪,或许,北海的暖风能带来一些改变。墓园里静谧无声,落叶在湿滑的石头甬道上黏附着,脚步经过,也未发出声响。他和妻子的墓碑嵌在一堵石墙上,离他的故居不远。黑色的玄武岩上刻着“爱德华·格里格:1847—1907”。在这个叫诺达梵涅的湖畔,他和妻子妮娜长眠于此。没有鲜花,只有湖水,四时的阳光不时穿过森林落在那堵石头墙上。
想起拜伦的一首诗《洛钦伊珈》:“去吧,你艳丽的风景,你玫瑰的花园!/让富贵的宠儿在你的眸子里徜徉;/还给我峻岩吧,那儿有积雪的安眠。”我女儿速写了一张我和石墙的画,我的表情肃穆庄重,而在画的下面,我题下了自己的诗句:“天空因为你而绚烂无比/叶子上有着跳跃的音符,阳光挥着指挥棒/《阿尼特拉舞》欢快地旋转着/时针随着时空旋转着/索尔维格的无奈和悲楚显得苍白无力/他躺在怀里,紧闭双眼,无能为力。”
责任编辑韦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