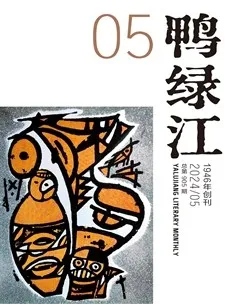月亮掉到水盆里
中秋节这天,天气预报说阴,应该白天见不到太阳,晚上也见不到月亮。一年当中月亮最圆的时候,就这样要被一片云给毁了,常亮觉得多少有点儿可惜。孰料,不愉快的事儿远不止这,早晨起床,他的右眼皮就一直在跳,像有人从天上垂下一根绳子,无端拴住他的睫毛,紧一下松一下拉拽着。他从小就听大人讲,右眼跳灾,学别人在右眼皮上贴了一小片白纸,寓意白跳,以此化解莫须有的灾祸。
昨晚白乐就开始嘀咕,你爸和你妈连个电话也没打,明天我们到底该不该回去吃团圆饭?他肯定地回应道,明天才过节,明天他们一定打。他嘴上是这样说的,可心里却不是滋味,父母已是古稀之年,理应由儿女呵护孝顺,可他们还在一味地索取,别说平日嘘寒问暖、主动分担了,就连逢年过节,也得是父母张罗好丰盛的饭菜,他们兄弟两家连大带小八口人赶着饭点儿去挤父母那间小公寓。在北方,但凡团圆饭,一定少不了饺子。在常亮的记忆里,吃饭时母亲一般不上桌,夹些菜在碗里,一手端碗,一手搅动煮在锅里的饺子,趁饺子上下翻滚的间隙,匆匆吃上几口。他知道,母亲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让一大家子能吃上现煮的、热气腾腾的、烫嘴烧牙的、暖心暖胃的大肉饺子。每次,母亲都会在饺子里包一枚硬币,她边捞饺子边嚷嚷着鼓励大家努力吃,说谁吃出硬币,谁一年就想啥啥来、干啥啥成。等到饺子上桌,团圆饭也就快圆席了,大人们已被一桌鱼肉喂得差不多了,象征性夹几个放在碗里,再夹一个塞进嘴里,半张着冒着腾腾热气的嘴,卷着舌头赞叹母亲的手艺。孩子们则一个接一个地往碗里夹,也不吃,“开膛破肚”地找硬币。母亲在一旁笑嘻嘻地说,要吃到才算,这样找出来不算。可孩子们不管这些,规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句空话,非得找到那枚硬币才算完事儿,有时一整盘饺子都会遭殃。母亲依旧笑嘻嘻的,端起皮子、馅儿和在一起的“大杂烩”,一大口一大口往嘴里扒拉,满脸慈爱。大家伙儿吃完饭筷子一撂、碗一推,两手一抹油光锃亮的嘴,打着饱嗝刷手机、打扑克、侃大山;母亲又开始忙着收拾残局,她不让孩子们帮忙,说你们年轻人平时工作那么忙,好不容易过个节休个假,好好休息休息,想干啥就干点儿啥。
常亮这一想就到十点多了,父母还是没打电话来,他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心里一阵慌,担心二老会不会是身体又不舒服了。他想主动给父亲打电话,却被白乐伸手拦住,说,大过节的,你不要找不痛快,他们今天不打电话,我们就不回去,人家有二儿子、二媳妇和孙子就够了,有咱没咱一样团圆。一直以来,白乐都认定公婆偏亲,有啥好处都先经着老二家,尤其是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影响,对老二家的两个儿子是真亲,对他们家的两个女儿却是虚情假意。
右眼皮跳得更欢实了,像浮在水面上的浮漂,一上一下不停地抖动。常亮心不在焉地蜷在沙发上,干脆拿一张白纸遮住整张脸。白乐见状气不打一处来,伸手夺过白纸撕成粉碎,骂骂咧咧地说,大过节的,你干啥呢,死人才往脸上盖,你不想好我还想好呢,我才不想年纪轻轻就守活寡呢。
常亮笃定如果母亲身体无恙,父母一定会打电话来,出现这种状况,一定是有原因的。他用手捂住右眼,眼皮好像不跳了,心却七上八下地跳了起来。他一边在默默祈祷父母安康,一边在给自己暗暗打气,下决心再等半个小时,也就是十一点,要是父母还不打电话来,哪怕是跟白乐闹翻,他也要主动打电话过去,毕竟在他心里父母的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等待的时间显得特别漫长,一秒堪比一秒,眼看就快要到十一点了,常亮的心跳开始加速,摩拳擦掌地准备跟白乐大干一场。或许是心有灵犀,或许是冥冥之中二老一直在努力守护着家的和谐,正当常亮拿起手机要拨号时,父亲却先一步打来了,老人急喘喘地问,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常亮回答说,等您打电话请呢。
父亲说,我一早就给白乐打电话了呀。
父亲这样一说,常亮心里直犯嘀咕,白乐明明说没有打电话啊,这家伙又在搞什么鬼?为让白乐也能听到,他点了免提,提高嗓门儿说,白乐说没人给她打电话。
父亲肯定地重复道,打了,我打的,一早就打了。
正在化妆的白乐一蹦三尺高,从卫生间冲出来,对着手机吼道,你几时打的电话,我要是接过你的电话,出门就被车撞死。
常亮一看事态不妙,害怕矛盾会激化,不等父亲回应,就急慌慌地挂断电话。
白乐气呼呼地把她的手机丢给常亮,说,眼睛没瞎的话,你自己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常亮从头到尾查了一遍通话记录,发现果真没有。
一个说打了,一个说没打,究竟是谁在扯皮?常亮脑袋一阵疼,分不清孰是孰非。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白乐说的应该是真话,当然前提是她不是趁过节在故意找碴儿,提前把通话记录给删了。既如此,可父亲又为什么要说假话呢?他没有理由要说假话啊!难不成他又犯迷糊了,打错电话了?
白乐木桩一样站在常亮的面前,看似呆滞的眼神里泛着熊熊燃烧的火。常亮的心被搅得七零八碎,疲软到好像连跳动的力气都没了,他更不敢看白乐的眼睛,怕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
白乐咬牙切齿地问,他给我打过电话吗?
常亮瓮声瓮气地回答,他可能又犯迷糊了,你不要跟他计较。
白乐不依不饶,犯迷糊了?怕是光顾二儿子和二媳妇了吧,不信你打电话问问老二,人家一准儿已经被请回去了。
常亮无言以对,沉默几秒钟后说,马上到饭点儿了,你赶紧收拾吧。
白乐心里一阵委屈,觉得老人这是偏心到家了,不光平日在钱财、带孩子上偏向二儿子,就连叫吃顿团圆饭也能把他们给忘了。她越想心里越憋屈,忍不住抽泣起来,泪水冲刷着刚抹在下眼皮的红色眼影和涂在脸上的粉底,形成一道道红白相间的条疤,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心生恻隐。
常亮最反感女人哭哭啼啼,尤其是见不得白乐哭。她这一哭,不仅没有引起他的怜惜,反而冲淡了他心里替父母升起的内疚,甚至无端对她愤恨起来。
白乐一直哭,浓眼泪、清鼻涕混在一起,顺着下巴滴滴答答落在地板上。常亮越看越不是滋味儿,不耐烦地吼道,哭哭哭,多大点儿事啊,值得你大过节的哭丧似的。
常亮这一吼彻底惹怒了白乐,她狠狠抹了一把脸,眼泪、鼻涕、眼影、粉底全部和在了一起,脸上红一片、白一片的黏黏糊糊的。她不管这大花脸了,也不管披头散发穿着睡衣了,气冲冲地要大闹天宫,去找二老问个清楚。
常亮一看这架势就怂了,紧紧抱住白乐的腰,乞求道,都是我不好,老婆你消消气,我们不回去吃了,咱去下馆子,犒劳你吃顿好的。
白乐正在气头上,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此刻竟如大力士一般,一扭腰一甩胯,就挣脱了。常亮不甘心,又迅速抓住白乐的手。白乐使出女人的独门功夫,以猝不及防的速度一口咬住常亮的手背。常亮疼到撕心裂肺,啊一声惨叫,捂着一手牙印龇牙咧嘴地原地蹦高。
正在写作业的小女儿痴痴地看着他们,刚才发生的一切令她惊慌失措,不知该不该加入劝解妈妈的行列。
白乐夺门而出,常亮也顾不得疼了,紧紧跟在她身后,他再不敢轻举妄动了,怕进一步激怒她。
车就停在门口,白乐一出门就上了车。不等常亮做出反应,她就反锁了车门,任常亮拳头雨点儿般地敲打车窗,她还是一脚油门,车子以赛车加速的速度冲了出去。
每逢过节出租车就紧张,常亮等了好长时间才拦下一辆纯电比亚迪。等他火急火燎地赶到父母家时,却发现家里一派平静,二弟一家正躺在沙发上齐刷刷地刷手机,母亲在忙着炒菜,父亲在包饺子。
父亲见常亮气喘吁吁的样子,不解地问,你这着急忙慌地干啥?回头见是他一个人,又问,白乐和孩子呢?
常亮反问道,白乐没回来吗?
二弟一家也不刷手机了,齐刷刷看向常亮,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啊。
母亲回头问,你们不是一起走的吗?
常亮木木地摇了摇头。
母亲看出了异常,追问道,怎么啦?你们吵架了吗?
常亮依旧摇了摇头。
母亲急了,说,到底怎么啦?你倒是说话啊!
常亮一边庆幸自己赶在了白乐前面,一边又担心白乐会出事儿,无心对父母解释,丢下一句回头再跟你们说,就跌跌撞撞地出了家门。正是午间高峰期,电梯走走停停,常亮等不及,小跑着下楼梯,他想要在小区门口堵住白乐。
常亮在小区门口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始终不见白乐的影子。小区不大,就一个门,白乐要是回来,没理由会逃过他的眼睛。虽已是中秋时节,但“秋老虎”依然肆虐,幸亏黑云遮住了太阳,没有炙烤,只是闷热。常亮在额头抹了一把汗,内心的焦虑令他既生气又不安。饭点儿到了,空气里飘荡着炖肉、炒菜的香味儿,一股脑儿往他的鼻孔里钻,不失时宜地挑逗他的饥肠,发出叽叽咕咕的抗议声。
父亲又打来了电话,还是问,找到白乐了吗?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常亮舔一下干裂的嘴唇,费力地吞下一口唾液,回答说,白乐不知跑哪儿去了,你们吃你们的,别管我们了。
父亲又问,给她打电话了吗?
常亮答,出来时走得急促,没带手机。
父亲叹口气,像是在自言自语,我给人家打了好几个,电话通着,可就是不接。
大十五的,她能去哪儿呢?回娘家?是万万不可能的,白乐娘家最讲究习俗,一向不肯逾越半步,中秋节、春节出嫁的姑娘不能回娘家的旧俗已经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虽然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和观念的更新,开放的家庭已经开始突破,女儿带上女婿、外甥回娘家团圆已不再是新鲜事儿,可在他们家却仍是禁忌,不仅白乐的父母、兄长不能接受,连白乐自己也不能接受。开车去外地了?应该也是不可能的,虽然她拿本已经六年了,但一次高速也没上过,她应该没胆量去独自尝试。可常亮还是担心,要是她真的逞一时之气,独自一人开车上了高速呢?
右眼皮跳到常亮无法正常睁眼,心也慌得厉害,他六神无主地拦下一个急匆匆的路人,借手机给白乐打电话,连续打了三次都不接;他想一定是陌生号码的原因,发信息说,我是常亮;再打,还是不接。
欢声笑语潮水似的一波又一波从开着的窗户飘出来,碰杯、祝福的声音一家高过一家,常亮听着心越揪越紧,他断定白乐不会回来吃团圆饭了。此时他们一家四口却分散在四地,大女儿跟着前妻在外地,中秋假期短,不值得回来团聚,小女儿一个人在家,白乐更是杳无音信。想到小女儿,他不由得心疼起来,孩子还小,一个人在家还没吃午饭,他得赶紧回家去安顿好孩子,再做寻找白乐的打算。
出租车不好打,常亮扫了共享单车,把电门拧到最大,一路狂奔。他一进家门,小女儿就看着他可怜巴巴地说,爸爸我饿了。
常亮差点儿没控制住眼泪,问,听到爸爸的手机响了吗?你妈妈打电话了吗?
小女儿说,没响也没打。
父母没再打电话来,常亮的心也不平衡起来,难怪白乐会生气,父母有时候做得也的确不到位,就拿当下来说,明知白乐不知去向,他肯定是要去寻找的,也不懂得来关照一下小孙女或安排老二过来接一下。
埋怨只是一闪而过,最要紧的还是要先找到白乐。常亮打她的电话,通着,一直不接,反复打,还是不接;给她发微信说了一大堆软话、好话,也不见她回一个字。
联系不上,只能去找,找又是大海捞针,也只能是碰运气。不管如何,常亮还是决定安顿好小女儿去找白乐。他给小女儿泡了一碗方便面,切开一个月饼,说,大十五的,让我娃吃方便面,真是罪过。
小女儿倒是很开心,方便面对她来说胜过一切大鱼大肉,平时想吃白乐高低不答应,在她看来,方便面就是发明来害人的,把一些人惯懒了不说,谁吃谁胖,尤其是女性,从小就应该保持完美体形,坚决不能碰它。
方便面独特的香气令常亮觉得更加饥饿,但光是肠胃在作怪,嘴巴却没有想要吃的冲动。他看着狼吞虎咽的小女儿说,你吃完饭一个人在家好好写作业,爸爸去找妈妈,好不好?小女儿懂事地点了点头。
他担心白乐在气头上开车,出了交通事故,就打车沿能回父母家的几条路来回绕。因过节,人们都在家团圆,中午的街道十分清静,鲜有车辆和行人。看着空空荡荡、平静如水的大街,他的心也被掏空了,对白乐的担忧溢满整个心脏。随之他惊奇地发现,随着紧张感的不断加剧,右眼皮竟不跳了,心跳也没那么厉害了。
常亮指挥出租车司机满大街绕。司机就快被绕晕了,半乞求半劝解道,大哥,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这不等于是瞎猫想碰死耗子吗,哪有那么多巧合啊;再说,这大过节的,老婆孩子还等我回去吃团圆饭呢。
其实在绕完回父母家的几条必经之路后,常亮就不抱多大希望了,只是他不甘心,更不愿意回家没头没脑地等。
出租车司机见他不吭气,又说,大哥,听我一句劝,咱回家等吧,女人都一个样,能放下男人也放不下孩子,耍耍小性子就没事儿了,今晚嫂子一准儿回家。
常亮说,你不懂,我家这个不同,在娘家惯坏了,啥都得由着她,一旦不合她心意,心瓷着呢。
出租车司机无奈地叹口气,说,那我们也不能就这样一直绕下去哇,就这么大个地方,已经来回绕两圈了,再绕下去也没意义了吧,你倒是可以不心疼钱,可我还得回家吃团圆饭,好不容易过个节,下午也想给自己放个假。
话说至此,常亮也觉得确实有点儿不合时宜,虽说出租车是服务行业,可人家不想为你提供服务了,你总不能山大王一样强迫人家吧;再说,人家说得也不无道理,自己这般没头苍蝇似的找下去,的确不是个办法;再说了,孩子一个人在家,等得时间久了搞不好会做出不安全的举动。几个现实状况加起来,到底还是破解了他的固执,他心不甘情不愿地对出租车司机说,那好吧,麻烦你靠边停下,我走着去找。
出租车司机面露一丝笑容,无奈地摇摇头,像是在说给他听,更像是自言自语,跑车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见这样死犟的男人。
扫码付过车费,常亮昏昏沉沉地走在大街上,饥饿导致他血糖低,先是手脚无力,再是胸闷心慌,不一会儿就发展到浑身颤抖。他就地坐在马路牙子上,摸索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水果糖,塞进嘴里用舌头上下左右搅动着快速吮唆起来。
一块糖快要吃完时,常亮觉得没那么难受了,可身体仍处于原始的自我保护状态,使他还不想站起来行动;他干脆把腿支起来,呈半蹲半坐状态,头垂趴在膝盖上。
天上的云层尽管看起来很厚实,可太阳毕竟是太阳,它午间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还是让天空白亮起来,闷热中夹杂着丝丝炙烤。常亮迷迷糊糊的,感觉像是睡着了,却明明是醒着的。在这种状态下,他原本全部朝向父母的心,开始一点点发生倾斜。尤其是当他回想起白乐嫁进门几年来发生的几件事,觉得也不完全是白乐矫情,父母确实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
先说结婚买房这件事儿吧。他们结婚买房时,父母推说没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东拼西凑付了首付,婚后两口子扎紧裤腰带还债、还房贷。可没过两年,老二结婚,父母就一下子拿出二十多万首付。这不叫偏心叫啥?白乐气不过,揪着他回家跟父母理论,父亲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两口子挣钱能力比老二他们强太多,买房欠那点儿钱,对于你们来说,那就不是个事儿。更让白乐不能接受的是,母亲竟然以他们是老大为由,借口说,长兄为父、长嫂为母,要不是我们这两把老骨头还在,你弟弟结婚,还不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吗?这话一出,让白乐觉得敢情小叔子是他们为她而生的,反倒是叫她庆幸、感激他们老两口的健在了,真是岂有此理。那天闹腾到很晚,白乐暴跳如雷,常亮则活脱脱一只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装受伤严重,直到最后也没闹出个结果,白乐只得哭哭啼啼地回了家。过后几天,常亮化身没筋骨的墙头草,无须有风,在白乐和父母两边倒,一边安慰老的不要伤心上火,一边劝老婆何必斤斤计较,言辞凿凿地说,自己的日子自己过,父母不能跟一辈子,靠天靠地靠父母,说到底,靠谁也不如靠自己。浅显的道理白乐也明白,给你估的,不争也是你的,不给你估的,争来的也都是气,也就没再继续争较,认了现实,不得不哑巴吃黄连——全苦在心里了。也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白乐跟公婆的矛盾开始萌芽,常亮时刻会提心吊胆地嗅到浓浓的火药味儿。
再说带孩子这件事儿吧。他们虽结婚在先,但婚后二人忙于工作,要孩子的事儿就往后推了好几年。老二两口子结婚第二年就生下一个小子,紧接着又生了二小子,父母一手把两个孙子带到上小学。其实后来他们也想要孩子了,可考虑到父母正在帮老二带孩子,不想让老人太劳累,又担心老人应付不过来,就商量着又往后推了两年。挨到老二的两个儿子前后脚进了校门,他们终于敢精心备孕了,生下了小女儿。本想着父母也一定会帮着带到上学,没想到只带了不到两年,在孩子还不到两岁时,母亲要不就今天喊头疼,明天喊肚疼,要不就埋怨小孙女太难缠、太累人,她一把年纪实在是应付不过来,推脱着不想给好好带。说得次数多了,常亮嫌烦,也确实心疼母亲,试探着跟白乐商量请个保姆。白乐一听就火冒三丈地反对,他们能帮老二带大两个,轮到我们头上,就连一个也带不了了吗?请保姆能有自己照顾得好吗?你没看过新闻吗?有多少孩子不是被保姆虐待吗?请保姆不用花钱吗?我们的房贷、车贷还没还完呢!没过多久,母亲就真生病住院了,正赶上他们工作最忙的时候,跟公司请假肯定是不可能的事,不得已,只得花钱请了一个亲戚带孩子,没想到母亲这一病就再没好利索,三天两头地往医院跑,说好的临时保姆成了长期保姆,直到把孩子送入幼儿园。母亲是真病也好,装病也罢,在白乐看来,就是找理由不想帮他们带孩子,婆媳之间的隔阂和矛盾进一步加深,甚至到了无法调解的地步。
还有两件事,白乐也耿耿于怀。一件是,那年农村老家风电占地,得了两万多元补偿款,表面上父母把钱分成了三份,两个儿子一家七千,他们老两口留了六千,可暗地里父母把那六千也给了老二。这事儿不知怎么就传到白乐耳朵里了,她揪着常亮去找父母理论,让父母要么也给他们六千,要么问老二把那六千要回来,一家分三千。父母自是不会同意跟老二往回要钱,也找不出理由推脱白乐,母亲使出缓兵之计,答应过年时给白乐包一个六千块钱的大红包。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也许只是为了安抚白乐,也仅仅是说说而已,可白乐却牢牢记在了心里。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吃过团圆饭,白乐见母亲迟迟没动静,就当着老二一家的面跟母亲要红包。母亲依旧推脱说,他们老了,又没有退休金,就那几个可怜的老年救济款,连平时吃药和吃饭都不够,言外之意就是,她没钱。白乐一听,差点儿没被气到倒地身亡,她吊起了脸子,心里发誓跟父母老死不相往来。另一件是,父亲未经他们的同意,就将登记在他们名下的城中村的房子租给了别人,租房所得的两千元钱也没给他们。这还不算,租房的人因生炭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险些丢了性命,一纸诉状把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官判他们承担30%的责任,无辜赔了对方几万元医药费、误工费。这件事让白乐认定,公婆就是她的宿世冤家,不像别人家的父母,是来度儿女的,他们分明就是来祸害自己一家的。
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回忆也很费力气,尤其是针对不愉快的事儿,常亮觉得身心疲惫,脑袋有点儿蒙,还阵阵透着针扎般的疼。无头绪的情思在他的脑海里恣意乱撞,他努力克制着不让它出圈,想让它停下来,可越是这样就越乱,不安、惊惶、急躁、胆怯、无奈、虚脱一股脑儿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将他团团包围。为缓解症状,他又往嘴里塞了两块糖。若不是刺耳的手机铃声解围,他说不准会就此抑郁。来电是陌生号码,他幻想是白乐,接通却听到是小女儿略带哭腔的声音。孩子在家等不到父母,就一个人下楼借小卖部的电话先给妈妈打,不接,才又拨了他的号。他在电话里听到,小卖部的老板在替孩子埋怨他们,这家大人真不靠谱,大过节的闹什么矛盾,把小孩儿一个人丢在家里,这鸡飞狗跳的日子能过好吗?常亮在电话里安抚小女儿先上楼回家,说他马上就回去。小女儿说,出门时不小心把门给带上了,想回也回不去了。常亮这才想起,自己也没带钥匙,备用钥匙在车上,联系不到白乐,就进不去家门。常亮千叮咛万嘱咐小女儿一定乖乖待在小卖部等他,不要出去随意走动。他拦下一辆出租车,念经似的催促司机快点儿再快点儿。路上,他又给白乐打了几次电话,起初通着,没人接,后来语音提示已关机,他搞不清是她故意关的,还是手机没电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好兆头,他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上,大脑沉沉麻木,四肢微微战栗。
回到楼下小卖部,常亮见小女儿正坐在凳子上吃老板给的月饼,忙作揖道谢。
老板不领情,劈头盖脸地数落开了,平时看你两口子文质彬彬的,好有礼貌和涵养的样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大十五的闹意见,把这么小的娃一个人丢在家里,娃中午连饭都没得吃,你们做父母的于心何忍。
常亮说,给吃了,给吃了方便面。
老板说,方便面?大十五的给娃吃方便面,那也能顶饭吗?
常亮想不出该如何跟老板解释,只一个劲儿点头称是,嘴里重复着,谢谢您了,多亏您了,这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
老板半打趣半认真地说,啥远亲不如近邻,你们不也经常在外面超市买东西回来吗?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价格,也不想着照顾邻居,还远亲不如近邻呢。
老板的话让常亮一阵脸红,老板也觉出了尴尬,忙圆场说,玩笑话,玩笑话,消费自由,消费自由,跟邻居不邻居的没关系,跟情分啥的也没关系。
小女儿听明白了他们的对话,拉着常亮的手说,爸爸,咱以后买东西哪儿也不去,就在阿姨这里,好不好?
常亮重重地点了点头。
老板摸着小女儿的头说,童言无忌,还是孩子好啊,心比水晶还要透明、纯净,不像大人,整天心贴心睡在一起,都尿不到一个夜壶里。
常亮看着小女儿清澈如水、不含一丝混沌的眼睛,心想,人为什么一长大就会变得复杂,到老就会变得令人难以捉摸,难道一直这样不好吗?他因此也彻底想明白了,今天的白乐跟今天的父母一样,他们都活在自己想当然的世界里,都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想问题,所以才会导致今天的结局。
老板见常亮一直在愣神儿,就安慰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夫妻之间磕磕碰碰,闹点儿别扭很正常,不要太往心里去。
常亮想跟老板说实情,想一吐为快,也想让老板给评评理,又觉得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扬,也就作罢了。
虽暂时回不去家,但也不能一直待在小卖部,影响人家做生意,常亮再三谢过老板,牵着小女儿的手跟老板告别。回到小区里,父女二人并排坐在小公园的长条凳上,这里能一眼看到小区门口,若是白乐回来,他们会第一时间发现。
小女儿的肚子一阵一阵咕咕咕地叫,常亮问,宝贝,你是不是还饿呢?
孩子吧嗒着嘴巴点头。
常亮又问,那你想吃什么呢?
孩子脱口回答说,汉堡、薯条、可乐,又强调可乐要加冰的。
常亮觉得小女儿这是在趁火打劫,平时白乐是绝对不允许她吃这些的,尤其是可乐,别说加冰的了,连常温的碰都不让她碰一下。父母帮带孩子那两年,因为孩子的饮食问题,白乐也没少跟他们理论过。常亮后来想,这可能也是父母不想继续给带孩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毕竟他们老了,对孩子更加溺爱,孩子想做的事,他们一般拗不过,更多时候,是他们主动妥协,甚至是主动去满足。其实常亮也觉得孩子吃油炸食品、喝碳酸饮料不好,可今天不同,一来过节,二来作为补偿也得满足孩子,他咬咬牙,冒着被白乐知道后批斗的风险,上美团点了一份肯德基单人餐。点过餐,他跟小女儿说,你得向我保证,吃肯德基的事情不能告诉你妈妈。小女儿伸出小指跟他拉钩,信誓旦旦地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变谁是小狗。
孩子吃饱喝足,一个人在小花园里玩,常亮活体雕塑般坐着发呆。天沉沉黑时,孩子玩累了,回到他身边说,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我肚子又饿了。
常亮试着打白乐的电话,还是关机,看来今晚想要回家,只能请开锁公司帮忙了。他打114转接通开锁公司的电话,对方说,开锁平时80元,今天过节最低100元。常亮没有讨价还价的心情,刚想说多少就多少,能快点儿过来就好,突然觉得眼前比前阵子亮了,他下意识地抬头,一轮白月正圆圆地挂在空中,发出冰冷却柔和的光。几乎在同时,小女儿嘴里喊着妈妈、妈妈,奔跑着冲出小花园。一片云飘来,又遮住了月亮,光却没有暗下来,是小区点亮了路灯,朦胧中,常亮看见白乐跟小女儿紧紧拥抱在一起。另一种担忧在他心头蔓延开来,小女儿会不会一时激动,忘了承诺,把吃肯德基的事情告诉她妈,要是那样的话,对他来说,这注定会是一个更加悲惨的中秋节。
见到白乐,他关心地问,你这一天去了哪里?有没有吃饭?
白乐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搞清楚了吗?我和你爸到底谁在说谎。
他生怕再刺激到她,小心翼翼地说,这个重要吗?你何必跟老人斤斤计较,一家人和和睦睦的不好吗?
她脸色煞白,咬着嘴唇,不容商量地命令道,你现在就打电话问清楚,到底是谁在说谎。
常亮本不想这时候再给父母添堵,可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把她给盼回来了,更不想让她再生气,违心默念,爸爸妈妈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儿子这也是被逼无奈,看在孙女儿的分儿上,你们二老就担待着点儿吧。父亲的电话接通后,不等常亮开口,父亲就开始自我检讨了,说,早上我确实没给白乐打通电话,是给明月(老二媳妇)打了两次,人老了,糊涂了,你跟白乐解释一下,道个歉。常亮安慰父亲不要太自责,并违心说,白乐已经不计较了,你们早点儿安心休息吧。跟父亲通话时,白乐要求把电话调成免提,父亲的话她自然听得直直白白,无需常亮再拐弯抹角或添油加醋地转达。
挂断父亲的电话,白乐说,这下你清楚了吧,看清你爸妈的本质了吧,人家心里只有老二他们一家,打电话都是先打给明月,而且还是连打两次,你是老大,理应不得先打给咱们吗?
常亮无言以对,觉得白乐说得也不无道理,凡事是得有个先来后到,他是家中长子。这样想着,他心生莫名其妙的不痛快,说不出是哪个细胞、哪根神经出了问题,酸溜溜地、不疼不痒地难受。
一进门,小女儿就一直喊饿。孩子是心头肉,白乐顾不得别的了,在厨房叮叮哐哐张罗晚饭。小女儿趁机躺在沙发上明目张胆地玩常亮的手机——平时白乐连碰都不让她碰一下。一切似乎又回到如常,可常亮觉得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七上八下地作怪。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常亮感觉心里越来越憋屈,曾经对白乐的种种抱怨在一点点化解,相反,曾经对父母的种种包容却在一点点凝固,直到拧成一个硬团。
在常亮失魂落魄发呆的时候,一直安安静静看手机的小女儿突然大叫起来,说,爸爸妈妈,爷爷发信息了,原来他昨晚洗漱时,不小心把手机掉进水盆里了,今天早上手机就失灵了,明明拨的是妈妈的号,却打给二妈了。说完又自言自语地补充道,我就说嘛,爷爷不打电话叫咱们回家吃团圆饭一定是有原因的,不是故意的。
常亮一听就觉得这是父亲编出来的借口,想想啊,手机掉到水盆里还能用吗?父亲这不是越描越黑吗?好在白乐在厨房忙活,注意力不在他爷儿俩身上,小女儿的话她应该没听真切,这要是让她听见,不仅不会释怀,反而可能更加激发她的不满,将矛盾进一步激化。常亮赶紧跟小女儿要过手机,做贼似的迅速删掉跟父亲的聊天记录,小声嘱咐小女儿一定不能将刚才的话说给妈妈听,并许诺只要她听话照做,周末奖励她吃肯德基。
没多久,白乐就整出几个菜,还煮了速冻水饺,家里竟然也有了几分团圆的味道。
吃过晚饭,楼下小花园里有人放烟花、摆台供月亮。常亮讨好地对白乐说,你今天心情不好,我们下去走走,看看烟花、拜拜月亮吧。
白乐没理会他,想起什么似的问小女儿,你那会儿说啥掉到水盆里了?
常亮抢着说,是月亮。
小女儿赶紧在一旁附和说,今天是中秋节,为什么看不见月亮,原来它昨晚就掉到水盆里了,哈哈哈。
常亮也跟着哈哈哈大笑起来,白乐一脸懵懂,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作者简介>>>>
党永高,1982年出生,山西省朔州市人。作品散见于《山西文学》《都市》《青年作家》《小说月刊》《雪莲》等报刊。
[责任编辑 陈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