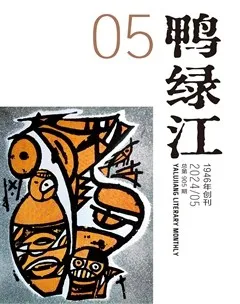戏里春秋(外二篇)
太阳刚冒出东山顶,九叔就来看金凤。
金凤没在屋。九叔从屋里出来,去了猪圈,两头小猪正哼哼唧唧地围着猪槽吃食;九叔又去了鸡窝,鸡窝里只有鸡毛和未铲除的鸡粪;九叔便去了菜园,菜园里连点儿带绿的菜叶子都没有……
九叔站在菜园边上发呆。
这么冷的天,她能去哪儿?就那腿脚,多站一会儿两腿都打战。九叔想到这,心也跟着颤起来。
九叔找啊找,从村东头第二个胡同进去,见大石头上坐着一个人。看外形,就知道是金凤,走近时,九叔愣了。
金凤端着身架,身上竟然穿着一套戏服!上身是件月白色带刺绣靠身小袄,下身是件捏百褶的云霞绉八幅裙。金凤没有上行头,两手交叉,放在膝上,眼睛看着前方,平时佝偻的腰身竟也挺直很多。她的前面就是土戏台,没有幔布,只有几根钢筋固定在戏台四周,孤零零地竖立着。
九叔没吭声,站在金凤身后。金凤没回头,半晌,颤巍巍地起身,一抖裙摆,说甭拦我,今儿我就是想登台唱一段……
九叔伸出的手停住,金凤已慢转腰身,一步步向戏台走去。九叔把双手拢进袖筒,看金凤的背影。
风起,钢筋架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像是在给金凤伴奏。
九叔坐在金凤刚才坐的大石头上,愣神。
金凤长得漂亮,却红颜薄命,刚嫁过来不久,丈夫就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留下一个还在吃奶的娃。九叔是村里唱戏的台柱子,青衣小生花脸样样都能拿得起。因为喜欢唱戏,对什么都不上心,包括他的婚姻。介绍给他的姑娘们都认为九叔“不务正业”。这名声一传出去,就把他给耽误了,因而过了适婚的年龄。有热心人给九叔和金凤牵线,金凤婆婆泪眼婆娑的,哭喊着说儿子没了,媳妇再走了,让一个老太太怎么活?
金凤也掉了泪,说你放心,我这辈子就守着你和孩子,守着这个家,哪儿也不会去。
九叔和金凤的家里都养着羊,但是两个人从来不去一个地方放羊,一个在山这边,一个在山那边,中间隔着几个山梁梁。
放羊是个寂寞的活儿,再加上满山的枯黄萧瑟,九叔的心更是孤寂。他把羊群圈在山窝窝里,人站在高冈上,踮着脚往山那边望。没事就挥舞着羊鞭,对着白亮亮的太阳开始喊山,便有咿咿呀呀的戏腔在群山之间响起。
山那边传来“咩咩”的回应,九叔的声音更加高亢。
金凤放了几年的羊,九叔就在山上号了几年的戏文。到了正月,村里白天晚上都要唱戏,九叔就会把羊群赶到山窝窝里,自己忙着跑回去排戏唱戏。山梁上只有金凤一个人站着,抱着鞭子望向村里。隐约中,有铜器声响起,随风飘到金凤的耳朵里。金凤就像九叔那样大声地唱,羊也跟着大声地叫。山梁上便热热闹闹,像是在唱戏。
等晚上回了家,开场锣一响,金凤饭也顾不得吃就往外跑,很晚了再踩着细碎的月光回家。婆婆用拐杖敲打着炕沿,嘟嘟囔囔地指桑骂槐。
金凤也不理会,依旧去看戏。
九叔站在台上,金凤站在台下。
金凤用嗓子眼儿跟着哼戏文,眼睛里波光潋滟。
九叔演秦香莲,苦命而又坚韧;金凤泪水涟涟,双拳紧握。九叔演王俊卿风流俊雅。金凤脸颊绯红,嘴角一会儿下弯,一会儿上翘。
九叔一举一动都如风过荷塘,在金凤心里荡起一圈圈涟漪。
看着听着,哼着唱着,金凤的心思活泛起来,也想上台跟着唱一场,哪怕演丫鬟和仆役都行。婆婆便拉下脸子,说真是疯癫,这家搁不下你了?
婆婆去了后,金凤也已两鬓染霜,有人就又给九叔和金凤牵线。金凤的儿子却把媒人撵出去。金凤的眼神黯淡下来,索性也就没了再走一步的想法。
村里原来爱唱戏的老人越来越少,就连九叔也唱不动了,没等开嗓,一口痰已经把气脉压住。年轻人更是没什么兴趣,戏台逐渐冷清下来。九叔把那些戏服和行头收拢到几个大箱子里。有人说都没人唱了,就扔了吧。九叔瞪了一眼,却不知该如何处置,只是坐在箱子上发愣。
金凤说那就放到我家吧,儿子不在家,我一个孤老婆子,东西多点儿,省着冷清。
安置好木箱,等人散去后,金凤看着墙角处的几个木箱,便翘起兰花指,愣了一会儿,又放下,痴立着……
九叔偶尔过来,不说话,两个人的目光落在箱子上,任凭太阳光线一点点地从上面飘过去。
月上中天的时候,九叔常在村里踽踽独行。走到金凤家门口,隐约听到有咿咿呀呀的声音传出,窗户上,摇曳着一个宽袍大袖、绰约多姿的身影……
一声高腔,把九叔从回忆中惊醒过来。九叔揉着眼睛,愕然地看着金凤。他没想到,金凤穿上这套半旧的绣花裙子绣花袄,竟然精致地攒出另一个人来,一个他好像从没见过的人。
欢笑一堂喜气浓,
与表弟今日喜相逢。
遵父命人前要端重……
金凤声音清亮,唱词婉转地在她唇中吐出,无风,似乎一切都在凝神倾听,戏台边上围拢越来越多的人。人群里突然传来长长的叫好声:好!好!唱得好!
是九叔!
他分开人群,一步步向台上走去,脚尖翘起、亮相,眼神深邃地看着金凤唱:
三年前与表姐两小无猜幼年的情景,
一霎时涌现在我的心中……
九叔的上台并没有让金凤分神,她不是自己,是戏里的那个“她”;九叔也不是自己,而是戏里的那个“他”。
我这里看他他看我,
我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
他们在台上挥洒自如,虽然没有乐器托着,却唱得毫无生涩之感。
好容易此刻得亲近,
话到舌边难启唇。
这天气真是好……
太阳应景似的,越升越高,热烘烘地照着戏台。把台上的两个人照得通体发亮,熠熠生辉,目光流转之中,唱得愈发清越激扬。
倘若有缘结秦晋,
莲花并蒂不离分……
戏魂
弦声幽怨、苍凉,在院子里回荡。
“咣当”一声门响,三爷赶紧挂上弦弓,身子靠在椅背上,望天。
三奶拿着猪食盆走出来,白一眼三爷,说吃饭还得我请?天天哭丧,早晚有一天,我把你这个破玩意儿给塞灶坑里。
三爷佝偻着腰身,拎着胡弦进屋,把三奶的絮叨关在门外。
三奶依旧愤愤的,把猪食一股脑儿倒进猪食槽里。进屋,看到饭菜一口没动,三爷正抱着胡弦,直愣愣地盯着北墙发呆。本快要熄灭的火气,又腾地着起来:
你的魂儿是让你的那些“老婆”给勾走了吧?这日子还过什么过!赶紧走,回你的那个家……
墙上,是几张发黄的黑白照片,边缘破旧。照片上的几个人,都穿着戏服,面貌模糊不清。
三爷收回目光,盘腿上炕。
三爷外面有“家”,还经常换“老婆”。三奶为这很生气,说三爷的魂儿被那些“老婆”勾走了。
那个“家”就是村里的小剧团,“老婆”是和三爷配戏的女人们。“家”里不只有三爷,还有九叔、金凤和村里很多老老少少。
三爷在剧团里不只拉弦,还会经常客串个角色。三奶挂在嘴上的“老婆”不单指那些女人,有时也暗指向金凤。
金凤守寡,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可三爷不避嫌,还是会去。再说了,剧团里的那些旧戏服,还不是靠金凤经常缝缝补补,九叔也会去,排戏练唱对戏词,哪来那么多事!
但是三奶认定,三爷就是被外面的人勾了魂儿。
她怨怼、暴躁、不管不顾地又吵又闹,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男人和别的女人“眉来眼去”,哪怕是在戏台上也不行!
三爷人是回来了,可是时间不长,三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三爷的魂儿丢了!终日坐在院子里,拉着胡弦,弦声如诉如泣。
不只这些,三爷的行为更是反常,不拉胡弦时,就会在村里村外到处转悠。看到谁家丢的废纸壳旧麻绳,会捡回家;去村头的理发店,有女人剪头,也赖皮赖脸地要来头发;有时还会带回树枝和树根,然后躲在西屋里,整天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你这儿有病!三奶指着脑袋,愤愤地说。
三爷只是沉默。三奶也死了心,便也沉默下来,心想只要不跟那些人搅和,任由三爷折腾了。
这不,三爷几口扒拉完饭,又去了西屋,门依旧关得紧紧的。
三奶张张嘴,却什么话也没说出来,闷闷的,把碗筷弄得叮当响。
九叔来了,打声招呼,也一头钻到西屋。敲门不开,灯亮一宿。第二天快晌午时,两人才走出来,满脸兴奋,眼睛里虽是布满红血丝,但却闪着光亮。三爷披着一件新戏衣,九叔手里端着几顶帽盔,戴着髯口,拉着戏腔对三奶说:哎呀呀,三爷的手哇真是巧,你看这些行头……这戏服,这布料……哎呀呀,我就说嘛,他的这根弦儿嘛,是断不了的,那是他的魂儿……
纸壳做的帽盔、树枝做的刀枪、烂麻纰和头发做出来的各色髯口……花花绿绿,很是齐全。
三奶愣愣看着三爷,脸色骤变,“嗷”地一嗓子:你把我的那点家底给祸祸了?
那还是娘临去时,给她的一块压箱底的上好布料,她没舍得用,一直精心收藏着,说是留个念想。没想到会让三爷给翻了去,做了戏衣!
三奶血往上涌,疯了似的抢过戏衣,随手把一个帽盔摔在地上。
九叔一看不好,拽着三爷跑了出去。
三奶抱着戏衣,大腿一软,坐在台阶上。
其实,她当初答应嫁给他,正是因为看过他在台上拉胡弦。那轻巧熟稔的指法,拨动了她的心弦,再加上他穿上戏衣时风度翩翩的样子,瞬间俘获了她的心。娘却说死说活不同意,可是她喜欢。最后,娘还是依了她。
后来娘在临终时,告诉她一件事,这才知道娘的苦痛。爹在年轻时,也是梨园行的人,因念白唱腔专学白玉霜,几可乱真,只是气派风度还差着火候,神态更没法与白玉霜相比,所以没有走红,不过却也因外相俊美,拥有很多戏迷。但是在一次远赴外地走场时,就失了联系,再也没有回来。听人说,是跟戏班子里另一个唱青衣的一起消失的……
而那时的三奶,还是个襁褓中的婴儿。
所以,自打娘去世,三奶就开始拦着三爷,让他远离唱戏的那些人。她忘不了娘那双快要哭瞎的眼睛。
当年三爷在县里剧团拉胡弦的时候,她连哭带闹地把三爷给带回村。即使三爷失魂落魄,大病一场,她也不在乎。她只要三爷常在身边守着就行,只要天天看到他就行。没想到,他又跑到村里的小剧团和那帮人混在一起。
三奶没办法,只能是豁出去了,当着一群人的面,把一包东西倒进嘴里,说再上台我就死给你看!然后双眼一闭,嘴吐白沫,躺在地上。
三爷吓得脸上发白,又是掐人中又是喊人。这一招很好使,三爷不再去剧团也不再排戏。
但是打那后,三爷眼里的光消失了,整天失魂落魄的。
可他哪知道,三奶就是吓唬他,喝的只是洗衣粉啊……
其实,三奶何尝不喜欢看他在台上光彩照人的样子啊!三爷就像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在舞台上演绎着刀光剑影、爱恨情仇。三爷眼睛里的光,把她的心照得亮堂堂的;三爷的弦声,把村子带得热热闹闹的。三奶只是害怕,怕三爷会和爹一样,怕自己像娘那样……
可如今,戏没人张罗了,村子静得让人心里发慌。三爷的魂儿没了,她的魂儿也没了。
三奶的泪流下来,一滴滴落在戏衣上。天知道,她有多后悔,可是她不输嘴。有一次三爷喝醉酒,把刚从别处讨来的唱本弄丢,她拿着电筒,一直找到月上中天。回来后,她偷偷地把那些唱本给整理好,熬到后半夜,才把缺失的唱词给补上。这一点她感谢娘,拼死拼活地让她读书认字……可那个老东西,竟然一点也不记得喝醉后发生的事,一大早就拿着唱本乐颠颠地往金凤家跑……还有那件戏服,估摸就是按着金凤的腰身做的。没良心的,我虽然没有金凤高,也没有金凤苗条,难道就不能穿戏服吗?
三奶轻轻地抚摸着,良久,慢慢把戏衣抖开。
阳光下,一块暗沉的布料,做成戏衣,竟然有了灵魂,有了生命,灵动而又饱满,还带着她最熟悉的体温和味道……
三奶好像忽然明白了三爷。可是,他明白她吗?
三爷从未理会她内心的渴盼,她曾经无数次隐在黑压压的人群里,看着台上的三爷,心里的欢喜糅杂着酸涩,她多想和他对戏的是自己……
要知道,那些角色里的唱词,她也能倒背如流……
三奶的心颤颤的,赌气般地把衣服穿在身上,她忽地愣了,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眼泪唰地流下来。
立腰、沉肩,双脚抬起,脚掌着地……
一个云手,掩袖、捧袖……三奶就像在戏台上一样,在院子里一板一眼地比画起来。
三奶发现,那件衣服竟然不肥不瘦不长不短,穿在身上是那么妥帖,就像是给她量身定做的。
晒戏
箱子排列整齐,箱盖上斑斑驳驳。
金凤把木箱一一打开,眼神有些黯然。
木箱里,堆放着戏服行头,散发着陈年的味道。
九叔和三爷叹口气,弯下身,开始动手。
阳光里,细小的灰尘翻滚着,在每个人身上起起落落。
六月六,挂锄钩。每年到这个闲时,小剧团里的几个“老人儿”会不约而同地跑到金凤家里,商量着排戏学戏的事。所谓“老人儿”,就是在剧团里能唱能张罗的人。“老人儿”中没有科班出身的,只有三爷,曾经在县剧团里拉过胡弦,经常讨来人家弃下的残本,凭着记忆,补上唱词,然后拉着调门,教大家唱腔。
“老人儿”不是按年龄来算的,其中也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比如八岁红,八岁开始登台,凭着出众的扮相、唱腔和台风,成为剧团里的台柱子,再加上经常到各乡镇演出,可以说是声名远播。成年后,八岁红打工去了城里,就很少再回来排戏唱戏。
金凤出面也叫不回,虽然八岁红是金凤的儿子。
因为没有年轻人,剧团也就渐渐塌了架。那些“老人儿”即使精心上了妆,也难掩满脸的皱纹夹着胭脂水粉,看着滑稽,唱得也是没精神头儿。隔年后,九叔和三爷再怎么张罗,因人手不够,说来年再唱吧,不差这一年。等到了来年,人还是不够,意趣也更加淡了,只说下一年吧。拖来拖去,人越拖越少,也就没人再提及唱戏的事了。
眼瞅着又到了六月份,九叔和三爷来到金凤家。金凤炒了几个小菜,三个人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说起戏团里的往事。
好久没喝这么畅快了,要不来两句?三爷有点醉眼蒙眬。
你要是有这个兴致,来两句就来两句。九叔看一眼金凤,清清嗓子。
三爷用手在桌子上轻轻拍打着节拍,哼着慢板过门。九叔站起身,咳两声,略一思忖,很快就入了戏:
清晨起别娘子把柴扉掩,
进城去找一座酒馆解解馋。
走过了三里桃花店,又来到五里杏花园。
路旁边绿柳红花多娇艳,翠鸟儿枝头叫声喧……
九叔的声音低沉沙哑,丝毫没有往昔的清亮愉悦,尤其是到了高腔,气脉提不起来,好像气力被谁抽掉了一样。三爷摇摇头,九叔自嘲般地干笑一声,端起酒杯,仰脖一饮而尽,然后低着头,只是摆弄着手中的空杯不再言语。
三爷打拍子的手停下来,在膝盖上来回摩挲。
金凤首先打破沉寂,说“六月六,晒龙衣”,那些戏服堆了这么久,眼瞅着快雨季了,可别生了虫子,趁着天儿好,拿出来晒晒,省着发霉。
要晒你晒,都霉掉了倒也省心!
话虽这么说,九叔还是跟着三爷和金凤身后,来到西屋,整理那些戏服行头。
金凤将鞋靴盔冠一件件拿出来,摆在院墙上,又把那些蟒袍、对帔、开氅、斗篷、云肩、裙子、小袄一一挂在晾衣绳上。戏服历经了几代人,有的已经十分破旧,还打上了相同色调的补丁。不过在阳光的照耀下,花花绿绿的依旧灵动和飘逸,好像所有的演员正在台上集体谢幕。
三爷和九叔呆呆地看着,金凤也有了刹那的失神。他们熟悉这些戏衣,穿上它们,就成了戏文里的生旦净末丑。无论是才子佳人、官商富贾、丫鬟仆役……每个人都赋予不同的角色和故事,通过一件衣服,去重现和演绎人间的世事无常和悲欢离合……但此刻,它们回归本真,只是一件件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戏服,在阳光下静静地晾晒着。
金凤轻轻地摸着戏服,想把上面的褶皱抹平,可一松手,戏服又恢复了原样。金凤的心便也跟着起了褶皱,她想不通,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怎么说消失就消失了呢?
金凤喜欢看他们在台上青衫鼓荡的表演,那流转的眼波、轻颤的水袖,瞬间就把她的心掠住,在一咏一叹中缱绻入戏了。她守寡多年,婆婆去世后,儿子想让金凤去城里养老,金凤说什么也不去,她舍不得,总觉得这里有什么东西牵绊着她,是什么,又说不清。
后来不唱戏了,那些装戏服的箱子就堆放在她家里。金凤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打开木箱,穿上戏服,走着台步,哼着戏文,让家里变成自己的戏台。
可如今,只能是晒晒戏服,等他们这些人没了,连晒戏服的人都没有了,然后霉了烂了扔了……想到这,金凤的眼泪就落下来。
金凤擦了擦眼睛,低头拿出一件古铜色软绉蟒,小心地挂在衣绳上。阳光很烈,金凤的眼睛不由得模糊起来,她恍然看到那些唱过戏的人,穿着这些戏服,正在咿咿呀呀地排戏唱戏。而她也穿上戏衣,和那些“老人儿”一起登台亮相……
想那些事干吗?都过去了,咱们也老了,以后也不操心这些了,享清福岂不更好?九叔过来,站在金凤的身边。
说得好听,你能放下?金凤瞪了九叔一眼,转身去抻戏服上的折痕。
九叔脸上一暗,梗着脖子说,有啥放不下的,这一晃都几十年了,我从十五岁登台,唱了一辈子了……
“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身上再脱他的蟒龙袍……”三爷忽地从身后唱起来,打断九叔的话,满脸促狭地看着九叔。
你、你给我闭嘴!九叔变了脸色,有些恼怒地看着三爷。
人家唱两句碍你啥事!金风满眼困惑,不解地看着二人。
哈哈,他还好意思说十五岁登台,你不知道,当年他演一个小配角,却给演砸了……
演砸了?我不信。金凤瞪大双眼,要知道,九叔在十里八屯的可算是个名角。
你给我闭嘴,不许说!九叔的脸糗得像猪肝。
人家“包拯”唱到“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你猜他咋做的?他颠颠地跑过去把“陈世美”的胡子给摘下来了,这把“陈世美”急的,捂着胡子喊:帽子!是帽子!
金凤“扑哧”笑出声,看着九叔问:那后来呢?
到底把人家的胡子给硬摘下来了,气得“包拯”踹了他一脚……台下可就笑疯了,台上也都笑场,一直到剧终……他这算是一摘成名!打那后,人家“陈世美”说啥也不和他对戏了……
哈哈哈……
那不是第一次登台,有点紧张嘛……九叔也忍不住笑起来。
哎呀,没想到你还有这些光荣历史。金凤乐不可支,一低头,看到手机有来电显示,赶紧说,别逗嘴了,你们先忙着,我儿子来电话了。
这一晃,也过去几十年了。九叔看着金凤打电话的背影,叹口气说道,以后就是想对戏也对不成喽,就连那“陈世美”也都过世十多年了……就是在,这戏也没人唱了,留着这些行头啥用?还不如烧了卖了,省着堵心……
你说烧就烧?这可是几辈人攒下的家底,我看你真是疯了!三爷立刻变了脸色。
留着有个鸟用,你还能带到棺材里?看三爷发火,九叔的气势顿时减了大半,嘟嘟囔囔地说,放也得放发霉,我不动别人也得动……
我看谁敢动!三爷的拳头捏得嘎巴作响。
“这么一会儿工夫,你们咋还吵起来了!”听到火药味儿,金凤赶紧挂断电话,横在两人中间,却掩不住满脸的兴奋,儿子来电话说县里有一家职业高中,成立了戏曲专业班,他被聘请做了顾问,还要送戏下乡,并且邀请咱们去学校讲戏呢……
真的?
真的!
那还等什么,把戏服检查一遍,脏了的洗洗晒透。九叔的身体里像被注入什么东西,腰板儿忽地变得挺直,瞬间就有了精气神。
这戏嘛,也得晒晒,以免发了霉……三爷双手上下抖动,迈着方步,来了一句道白,大声唱道:
人常说美景良宵人人称赞,
我却道把酒高歌胜过那神仙。
哈哈哈……
作者简介>>>>
阎秀丽,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安徽文学》《山西文学》《延河》《广西文学》《百花园》《天池小小说》《小小说月刊》《小说月刊》《少年文艺》等省市级报刊上发表作品,有小说被《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转载。出版长篇儿童小说《梨花盛开的时节》《山海传奇》《宝塔山下的少年》。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