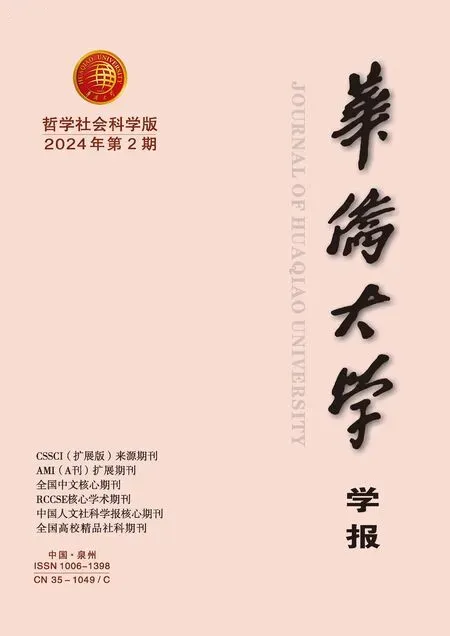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类型与法律规制
○周梦懿
一 问题的提出
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的核心载体。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迅猛,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根据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平台经济发展观察(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市值超百亿美元的数字平台企业有28家,全球占比40%,总市值约2万亿美元,全球占比21.74%,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平台经济主体。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平台经济发展观察(2023年)》统计数据显示,在超百亿美元平台企业方面,中国企业数量比美国多2家,但总市值却仅为美国29.4%。二是有不健康发展的苗头和趋势。尤其是数字平台借助算法数据、平台规则、资本优势从事反垄断行为,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这两个问题互相关联,只有强化反垄断,才能促进数字平台健康发展、做优做强。
当前数字平台反垄断的一个热点问题是“自我优待”(self-preference)。所谓自我优待指平台为自己或关联公司的商业活动提供相比其他经营者更为有利的条件。自我优待是竞争法领域的新来者,“在十年前很难在课本或著作中找到关于自我优待的讨论,但现在如果不谈及自我优待将无法理解最近以及正在进行的反垄断执法”(1)PabloIbanez Colomo,Self-preferencing:Yet Another Epithet in Need of Limiting Principles,World Competition,2020,Vol.43,No.4,pp.417-418.。关于自我优待的讨论源于“谷歌购物案”,欧盟委员会2017年判定谷歌的自我优待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罚款2.42亿欧元。(2)Commission Decision of 27 June 2017 in case AT.39740-Google Search (Shopping).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对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表示关切。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2020年发布的《数字市场竞争调查》(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将自我优待定性为平台进行市场力量传导的手段,与掠夺性定价、排他性交易等并列,并指出谷歌、亚马逊等存在自我优待行为。(3)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Commercial,and Administrative Law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2020,117 Congress 2d Session,p.187、pp.310-315.2022年,欧盟出台《数字市场法》(Digital Market Act),其中第6(5)条规定平台守门人“在排名以及相关索引、搜索方面,不应对自己的服务和产品提供比竞争对手相似服务和产品更为优惠的条件。守门人在这种排名以及相关索引、搜索方面应采用透明、公平和非歧视的条件。”(4)Regulation (EU) 2022/1925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4 September 2022 on contestable and fair markets in the digital sector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EU) 2019/1937 and (EU) 2020/1828 (Digital Markets Act),Art.6 (5).虽然这一法律条文没有明确提及“自我优待”,但学者指出,该条文的法律效果相当于是禁止自我优待行为。(5)Viktorija Morozovaite,The Future of Anticompetitive Self-preferencing:Analysis of Hypernudging by Voice Assistants under Article 102 TFEU,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2023,Vol.19,p.423.
我国也面临数字平台自我优待问题。例如,京东是否对自营商户和他营商户一视同仁?百度是否在搜索结果页面优先展示百度地图、百度云等自有的纵向衍生服务?如果存在自我优待,我国法律该如何应对?2022年6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0条拟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无正当理由在与该平台内经营者竞争时对自身商业活动给予优待。不过,2023年3月正式发布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删除了这一规定。自我优待法律规制被写入征求意见稿,这表明我国立法执法者已经关注到了自我优待问题。最后,自我优待法律规制又被移除出最终法律文本,这表明我国立法执法者对自我优待问题还存在疑惑,尚未形成共识。“平台经济不仅正在改变商业模式,而且也正在改变法律理论”(6)Orly Lobel,The Law of the Platform,Minnesota Law Review,2016,Vol.101,p.91.,它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包括自我优待在内的新的竞争方式及其垄断影响。鉴于此,本文拟立足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法律实践经验,探究自我优待的概念和类型,并以此为基础对自我优待的法律规制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数字平台的法律治理有所裨益。
二 概念厘定:数字平台和自我优待
(一)数字平台:平台经营者及其双重角色
关于数字平台概念,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2021年2月发布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第2条进行了明确规定,即“通过网络信息技术,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据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数字平台:第一,平台是信息提供者、交易撮合者,提供市场信息服务、市场交易服务。第二,平台具有双边或多边市场,既面向经营者用户,也面向最终的消费者用户。第三,平台是规则制定者、规则执行者,经营者用户和消费者用户均受平台规则约束,平台对平台内市场主体具有组织和管理职能。不过,数字平台的角色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日益多元。实行自我优待的数字平台是典型的“双角色平台”(dual-role platform),这里的“双”指数量多。双角色平台,也被称为“混合平台”(hybrid platform)、“垂直一体化平台”(vertically-integrated platform),指一个平台企业既是信息提供者、交易撮合者,也是产品经营者、服务经营者。(7)Yuta Kittaka,Susumu Sato,Yusuke Zennyo,Self-preferencing by Platforms:A Literature Review,Japan &The World Economy,2023,Vol.66,p.1.换句话讲,数字平台拥有“平台服务提供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两种角色。两者不必是一个公司,只要平台运营公司与从事自营商业活动的公司同属于一个商业意义上的整体,我们就可以称其为“双角色平台”。我国《电子商务法》已经注意到了平台的双重角色,第37条强调电商平台应以显著方式向消费者区分平台内的自营业务与他营业务。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平台自营业务如京东上的京东自营、淘宝上的天猫超市、抖音内的西瓜视频等。通常来说,兼有平台服务和平台自营的“双角色平台”有两种形成逻辑。
其一,平台角色发生转变,从“平台服务提供者”到“平台内经营者”跨界发展。传统意义上,平台只是作为一个交易中介或者交易场所存在,主要业务是提供信息、撮合交易,收取手续费。但经过多年发展,数字平台新增用户数、新增商户数、新增交易量逐渐见顶,为了保持并扩大盈利,数字平台开始相继下场亲自参与产品或服务交易。例如,天猫是一个向第三方经营商户开放的电商平台,但近几年开始上线经营“天猫超市”。又如,苹果既是应用商店的提供者(APP Store),同时苹果也是各类应用软件的开发经营者。其二,商户角色发生转变,从“经营者”到“平台服务提供者”跨界发展。例如,最初亚马逊是一个线上零售商,与沃尔玛类似,从厂商处以批发价购进商品然后再以零售价出售给最终消费者,赚取中间差价。后来其线上市场向其他经营者开放,邀请其他经营者进驻,逐步发展成为一个自营商户与他营商户共存的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他营商户的销售额在亚马逊平台销售总额中的占比从2011年的36%增至2015年的50%。(8)Lina M.Khan,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Yale Law Journal,2017,Vol.126,No.3,p.781.与亚马逊相似,我国京东也是从一个封闭的单一经营实体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向第三方经营商户开放的电商平台。
总的来说,自我优待是数字平台纵向整合的产物。当“平台服务提供者”兼具“平台内经营者”角色时,其利益冲突就会通过自我优待表现出来。从平台角度来看,拥有双角色可能是一个有经济效率的商业战略。然而,从竞争法角度来看,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拥有双角色可能会影响其中立地位,出现自我优待、排除异己的反竞争行为。
(二)自我优待:在平台内部对自营业务给予优待
最先提出“自我优待”这一用语的是2011年的《惩罚、自我优待和熊猫算法》。(9)Adam Raff,Shivaun Raff Penalties,Self-preferencing and Panda:Why Google’s Behaviour Makes Antitrust Sanctions Inevitable,http://www.foundem.co.uk/Google_Conflict_of_Interest.pdf.这个算法中使用“panda”是因为设计这个算法的工程师叫“Navneet Panda”。虽然自我优待的提出已有十余年,但其为人所知是最近几年,仍属于数字平台市场竞争中的一个新兴事物,学术界、实务界对其概念及基本特征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自我优待”不是一个明确的、有确切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学者帕布鲁(Pablo)将自我优待界定为“一家综合性企业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偏袒其关联企业”(10)Pablo Ibanez Colomo,Self-preferencing:Yet Another Epithet in Need of Limiting Principles,World Competition,2020,Vol.43,No 4,p.418.,同时指出“自我优待是一个试图捕捉多种场景的形容词”,不是一个有用且可靠的法律概念。(11)Pablo Ibanez Colomo,Self-preferencing:Yet Another Epithet in Need of Limiting Principles,World Competition,2020,Vol.43,No.4,p.428.概念是理性得以支配经验材料的思想工具。(1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3页。如果没有概念我们就无法对经验事实、案件材料进行整理、讨论,无法在混沌的事实中理出秩序。因此,当务之急,不是虚无地否认、怀疑自我优待概念,而应务实地肯定并解析自我优待概念。
作为一个“伞式概念”(umbrella concept),不同的文献用其指代不同的竞争现象和竞争行为。但总的来说,自我优待的概念使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自我优待,仅指在平台内部相比于他营商户给予自营商户更多的优待。有学者将平台的“对外彼此封禁”和“对内自我优待”分开讨论,认为自我优待仅指涉平台内部的竞争行为,而不涉及平台之间的竞争行为。(13)黄尹旭:《Web 3.0时代重构竞争法治的开放和统一》,《东方法学》2023年第3期,第101页;杨东、傅子悦:《社交平台自我优待反垄断规制研究》,《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51页。在该语境下,自我优待的例子,如电商平台给予自营产品或服务更为显眼的展销位置,又如搜索引擎等对自营产品或服务提供更靠前的搜索排名;广义的自我优待,不仅关涉平台内部自营商户相比他营商户的优待问题,还涉及平台之间的自我优待问题。在广义语境中,有学者认为某个平台对另外一个平台的封禁行为也属于自我优待。(14)周围:《规制平台封禁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基于自我优待的视角》,《法学》2022年第7期,第163—178页。在该语境下,腾讯在微信中封禁淘宝链接是对其关联企业如京东的自我优待,腾讯在微信中封禁抖音链接是对其自营短视频产品微视的自我优待,腾讯在微信中封禁支付宝支付是对其自营支付服务微信支付的自我优待。
总的来说,自我优待的概念使用有两类,一类是仅狭义地指涉平台内部的纵向竞争行为,另一类广义地关涉平台内部的纵向竞争行为和平台之间的横向竞争行为。一个恰如其分的概念定义,有助于学术交流并形成共识。概念指代行为越多、适用场景越宽泛,其认知就越模糊,因此应给自我优待概念“减负”,将其限定在平台内部,不指涉平台之间的竞争行为。本文认为,自我优待应采狭义定义,将其限定在平台内部中讨论,不宜泛化讨论。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狭义定义更能契合自我优待概念的语义范围。自我优待,顾名思义,是平台对自我的优待,优待的直接行为对象是自营商业活动,而不是他营商业活动。具有市场主导地位的平台对其他平台的封禁行为,直接指向的是他营商业活动,对自营商业活动的优待只是间接的反射性结果。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有两大类:一是平台对平台的垄断行为,包括大平台对大平台的封禁、大平台对中小平台的并购;二是平台对用户的垄断行为,包括平台对终端用户(平台内消费者)的杀熟、平台对商业用户(平台内经营者)的限定交易(二选一)和自我优待。在这个谱系中,自我优待明显有别于平台封禁。第二,狭义的自我优待是当前平台法治的关注重点。相比于平台经营者之间的封禁型自我优待,平台内部的自我优待是新事物,是法律规制的重点所在。有学者将自我优待分为“强制型”和“诱导型”,前者指平台封禁(强制限定交易主体)、搭售(强制限定交易对象)等完全排除异己竞争者的行为,后者指并未完全排除异己竞争者,但诱导消费者更多地消费自营产品或者服务的行为,并指出诱导型自我优待是反垄断法中的新事物,应给予更多关注。(15)曹汇:《平台自我优待的竞争法规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19页。无独有偶,另有学者分别讨论“平台对商家的自我优待”和“平台对平台的自我优待”,并强调前者滥用平台的市场组织和管理职能,应严格规制。(16)侯利阳:《〈反垄断法〉语境中自我优待的分类规制方案》,《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3期,第34页。学者侯利阳认为,平台之间自我优待(通过封禁行为实施)的反竞争问题,因为双方地位、力量较为接近,所以在实践中更为容易通过双方协商合作等方式予以解决,而不单纯依靠法律介入;而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地位、理论相差悬殊,且平台对平台经营者具有组织、管理等职权,因此平台内部自我优待的反竞争问题对法律介入的需要更明显。此外,欧盟2022年《数字市场法》第6(5)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2年《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0条等立法文本所涉及的自我优待均是狭义的。
三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行为类型
数字经济竞争呈现出“算法—数据—平台”三维结构,(17)杨东:《论反垄断法的重构: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第209页。具体来说,竞争行为通过算法实施,数据成为市场竞争的关键要素,平台打破市场藩篱进行跨界竞争。数字平台可以使用不同的机制来偏袒自营业务、歧视他营业务,自我优待行为具有多样、复杂、隐秘的特点。在数字经济“算法—数据—平台”三维竞争结构下,自我优待的实践样态可归为三类:算法操纵型、数据利用型、平台规则支持型。
(一)算法操纵型自我优待
数字经济是一种算法泛在且算法主导的经济形态,“无处不计算”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作为数字平台向相邻市场传导市场力量的一个商业策略,自我优待通常借由算法予以实施。平台内经营者互相竞争的对象用户注意力的争夺,或者称之为流量竞争。流量是平台内经营者开展商业活动的命脉,可以说“得流量者得天下”。作为数字平台的基本技术构件,算法被数字平台用来操控流量,操纵产品或服务的排名和推送。作为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数字平台通过算法设计来增加自营产品或服务的曝光率,以增加交易机会,同时对他营商户的平台服务进行降级。本文称之为算法操纵型自我优待。
算法操纵型自我优待的典型案例是“谷歌购物案”。该案是欧盟竞争法律、竞争政策变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Pablo Ibanez Colomo,Google Shopping:A Major Landmark in EU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2022,Vol.13,No.2,p.61.自2008年开始,谷歌修改算法,操纵搜索结果,一方面在显眼位置优先展示并用图文更详细地介绍自己的比较购物服务,而另一方面对竞争对手的网页链接进行降级处理,如搜索排名靠后、取消图文介绍等。统计数据显示,95%的用户会点击搜索结果的第一页,35%的用户会点击选择搜索结果第一页的第一项。(19)Commission decision of 27 June 2017 in case AT.39740-Google Search (Shopping),p.457.谷歌的这一算法操作显著地增加了自己服务产品的交易机会,同时明显地降低了竞争对手的交易机会。经过长达7年的调查,2017年欧盟委员会认定谷歌的上述行为违反《欧盟运作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 of European Union,TFEU)第102条(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并对谷歌作出2.42亿欧元罚款,要求谷歌停止自我优待行为,确保第三方平等地接入其搜索网页。谷歌不服,向欧盟普通法院(the General Court of the EU)起诉。2021年11月,法院维持了欧盟委员会的处罚决定,指出谷歌的自我优待行为违法欧盟竞争法。(20)Google and Alphabet v Commission,Judgment of the General Court of the European Union,Case T-612/17,10 November 2021.
算法操纵型自我优待具有隐秘性。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运行设计黑箱问题。所谓算法黑箱,指算法的设计和运行不公开、不透明。之所以有算法黑箱,一是因为算法代码在事实层面上晦涩难懂,二是因为算法代码(尤其是源代码)通常被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21)李安:《算法影响评价:算法规制的制度创新》,《情报杂志》2021年第3期,第147页。因为存在算法黑箱,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来操纵商品或服务的曝光度及交易机会,难以被发现且予以证实。这使得数字平台的算法操纵型自我优待,对内具有强制性,对外具有隐秘性。欧盟2022年《数字市场法》第6(5)条所禁止的自我优待主要指算法操纵型自我优待。不过,学者马汀指出,《数字市场法》除了第6(5)条,第6条还涉及其他类型的自我优待,(22)Martin Peitz,How to Apply the Self-preferencing Prohibition in the DMA,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2023,Vol.14,No.5,p.310 &footnote 5.如第6(2)条数据利用型自我优待。
(二)数据利用型自我优待
数据是数字平台实施自我优待的另外一个资源,具体来说,数字平台利用平台内经营者的销售数据和消费者的购物数据,来实时掌握市场的发展趋势,优化其自营业务的产品选择、采购渠道、销售策略、市场定价、售后服务等。最常见的是,平台经营者运用算法侦测哪种商品销量更好,以此决定自己销售哪种商品。也就是说,数字平台将其线上市场作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凭借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数据来发现新款商品、预测销售前景,形成价格模型,以便对自营商品或服务的选择、销售和定价作出最优决策。
数据利用型自我优待典型例子是亚马逊颇具争议的商业模式。例如,宠物抱枕(Pillow Pet)最初是亚马逊平台内某一他营商户销售的产品,销量高达每天100件。后来,亚马逊的自营商户也开始销售同款枕头,并且摆在更加显眼的位置,结果导致上述他营商户的销量降至每天20件。(23)Lina M.Khan,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Yale Law Journal,2017,Vol.126,p.781.另外,一个铝制笔记本支架的制造商在亚马逊平台上经营了十年,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后来该制造商发现亚马逊自有制造商品牌“亚马逊基地”(Amazon Basics)最近几年也开始以低价(将近50%)在亚马逊平台上销售同款支架。“亚马逊基地”创立于2009年,最初业务是制造销售电池、空白DVD等,之后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但近年突然推出了3000多类产品。很明显,亚马逊平台内的交易数据在“亚马逊基地的再次活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4)Lina M.Khan,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Yale Law Journal,2017,Vol.126,p.782.2019年7月,欧盟委员会对亚马逊的这种商业数据使用行为展开调查。2020年底,欧盟委员会声明,亚马逊利用平台内非自营商户的非公开商业数据获取对其平台内非自营商户的不正当竞争优势,有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嫌疑。(25)European Commission,Antitrust: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mazon for the Use of Non-public Independent Seller Data and Opens Second Investigation into Its E-commerce Business Practices,10 Oct.2020,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2077.
数据利用型自我优待,实质上是“对第三方卖家长期以来积累的各方面竞争优势的掠夺”(26)李鑫:《平台数据型自我优待的反垄断法分析》,《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104页。,削弱第三方商户的创新动机,从长远来看损害消费者福利,因此具有反竞争性。对于数据利用型自我优待,非歧视规则指导下的矫正方法有两种:一是平台内的交易大数据向平台内的所有商户开放;二是禁止平台以市场竞争为目的使用他营商户的交易大数据。因为经营者的交易数据被视为商业秘密或其他数据产权,对外开放数据会与数据之上的私人权利相冲突,因此第一种非歧视矫正方法不可行。(27)Mikaela Pyatt,Rulemaking to Bar Self-preferencing by Technology Platforms,Stanford Technology Law Review,2023,Vol.26,p.181.也就是说,非歧视规则下,数据利用型自我优待的可行方法是禁止平台以市场竞争为目的使用他营商户的交易数据。
(三)平台规则支持型自我优待
平台对平台内的经营者具有组织和管理职能,包括审查经营者资质、信用、产品质量等等。为顺利开展市场组织和管理工作,平台会制定并执行一系列平台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平台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或准公共权力),通过平台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来行使“准立法权”“准行政权”“准司法权”,塑造有组织的私人秩序。平台具有政治权力、公民权利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被称为与公权力相对、与私权利相异的“私权力”。也就是说,数字平台兼具私利性和公共性。作为一个理想经济人,数字平台对私利的盲目追求会引发公共性的滥用,出现各种排斥、限制市场竞争的垄断行为,(28)张晨颖:《公共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151页。如对自营商户和他营商户区别对待,平台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出现“优于待己、劣于对人”的情况。
平台规则支持型自我优待的例子是苹果应用商店(Apple Store)的规则设计。一些手机应用软件开发商(包括Spotify在内)向欧盟委员会起诉,称苹果应用商店的规则设计更偏向于苹果自己开发的应用软件。苹果要求应用商店内的所有应用软件开发商采用苹果自己的支付系统,同时阻止他们让消费者知道还有其他的支付方式以避免其绕开苹果应用商店与消费者达成交易。此外,苹果应用商店收取平台内应用软件销售额的30%作为服务费(被称为“苹果税”),这使得第三方应用开发商在与苹果自己开发的同类应用软件竞争中处于成本劣势。(29)European Commission,Antitrust:Commission Opens Investigations into Apple’s App Store Rules,Brussels,16 June 2020,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0_1073.在经济学中,某一经营者获得以及维持垄断地位的手段,除了排挤市场内的已有竞争对手、提高市场门槛排斥潜在竞争对手,还有提高竞争对手经营成本。(30)Thomas G.Krattenmaker,Steven C.Salop,Anticompetitive Exclusion:Raising Rivals’ Costs to Achieve Power Over Price,The Yale Law Journal,1986,Vol.96,No.2,pp.209-293.2020年6月,欧盟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2021年4月,欧盟委员会向苹果发出一份反对声明,称其平台规则可能违反《欧盟运作条约》(TFEU)第102条(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31)European Commission,Antitrust:Commission sends Statement of Objections to Apple on APP Store rules for music streaming providers,30 Apr.l 2021,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2061.
一个平台企业开展自营业务,类似于裁判员同时也是运动员,会导致“利益冲突”,而自我优待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平台可以凭借其担任裁判员所拥有的平台权力,如规制制定、解释、执行等,进行一系列暗中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实践中,平台规则的制定和执行由数字平台主导,代表的是数字平台的利益,有时候会迎合、服务平台的跨界竞争和自我优待。数字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如果不接受平台规则,那么经营者就无法在数字平台内开展商业活动。平台内他营商户对于平台的自我优待,往往无力反对、默默接受。数字平台内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公平的平台规则予以塑造。因此,平台规则的公正与否,对于经营者而言非常重要。
四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法律规制
数字平台的法律治理应坚持“在规制中发展,在发展中规制”,既要包容审慎又应积极有效,一方面要避免失之于宽、过度包容,另一方面应防止失之于严、过度规制。就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法律规制而言,应充分认识规制缘由、奉行科学的规制理论、采用多元的规制方法。
(一)规制缘由:双轮垄断及其竞争损害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有“双轮垄断”的竞争特点。具有市场主导地位的数字平台可通过优待自营商业活动,将其在轴心型市场(平台服务市场)已有的市场力量延伸至辐射型市场(某一产品或服务市场),进而在辐射型市场形成双轮或多轮垄断。之所以讨论自我优待并呼吁法律规制,原因是人们担心自我优待可能会导致数字平台已有的市场支配地位从平台服务市场延伸到其他相邻市场,进一步扩大并稳固其市场垄断。双轮垄断是杠杆效应(leverage effect)或传导效应在平台经济领域的表现。学者刘晓春将自我优待描述为:“平台同时在两个及其以上具有相互关系的市场上开展经营活动,平台利用其在一个市场上的影响力,在另一个市场上为自己或关联公司提供相比其他经营者更为有利的条件。”(32)刘晓春:《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法律规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第71页。无独有偶,学者盖尔盖伊(Gergely)指出“数字经济中的自我优待不是什么新鲜事,自我优待背后是杠杆作用”(33)Gergely Csurgai-horvath,Is It Unlawful to Favour Oneself?Hungaria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2021,Vol.62,No.4,p.307.。市场支配力的跨界传导是反垄断执法所关注的重点对象,如我国商务部2009年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理由之一是:如果允许收购,可口可乐有能力将其在碳酸饮料市场上的支配地位传导至果汁饮料市场,对现有果汁饮料企业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进而损害饮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34)《商务部关于禁止可口可乐公司收购中国汇源公司审查决定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2009年第22号。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杠杆效应或传导效应相比,数字经济环境下平台企业算法技术成熟、数据资源占优、规则权力强大、资本实力雄厚,通过自我优待等杠杆方式实现双轮垄断,成本极低、效率极高,加速累积效应尤甚。(35)段宏磊:《巨型平台企业双轮垄断的生成机理、规制困境与未来改进》,《经济法研究》2023年第24卷,第230—232页。竞争损害是反垄断法律分析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起点和核心问题。依据《反垄断法》第7条,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损害是“排除、限制竞争”。这是较抽象的竞争损害标准,根据《反垄断法》第1条之立法目的,实践中竞争损害因素的具体分析包括对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影响、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对创新的影响等。总的来讲,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竞争损害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数字平台自我优待会对平台内其他经营者产生排除、限制影响。平台自我优待是以减少平台内其他经营者交易机会(以算法操控型、数据利用型为典型)、提高平台内其他经营者经营成本(以平台规则支持型为典型)为代价的。消费者用户新增数见顶,交易撮合手续费收益见顶,为保持并扩大盈利,平台企业开始下场参与经营,其实质是与其他经营商户抢夺消费者。因为平台掌握算法设计、数据利用、规则制定等优势资源,所以相比平台自营商户,其他经营商户处于一个不公平的交易环境。迫于生存压力,下游的产品或服务经营者要么退出市场,要么通过股份转让或经营合同等依附于大型平台企业。如此,平台企业将其在平台服务市场中的市场支配力量传导至下游的产品或服务市场。第二,数字平台自我优待会减损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一直以来都是反垄断法的重要立法目的。在反垄断法中,消费者利益表现为“消费者福利的增加”和“消费者选择的多样”(36)焦海涛:《反垄断法上的竞争损害与消费者利益标准》,《南大法学》2022年第2期,第1页。。近期来看,平台企业下场经营、参与竞争,能够降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增加产品或服务的选择。但长远来看,平台自我优待会通过减少交易机会、提高经营成本等方式将其他经营者逐出市场,排除竞争对手之后提价将消费者剩余转为生产者或销售者剩余,减损消费者福利;另一方面,因为平台自我优待,其他经营者迫于生存压力会陆续退场或依附于平台,怠于创新,这会减少新产品或新服务的上市,进而限缩消费者未来可选择的产品或服务种类。第三,数字平台自我优待会损害创新活动。2022年《反垄断法》修改,将“鼓励创新”作为立法目的写入第1条。与传统反垄断法关注静态效率(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损害不同,创新这一立法目标着眼于长期利益更加强调动态效率损害。(37)方翔:《论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创新价值目标》,《法学》2021年第12期,第168—169页。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特别是数据利用型自我优待,会对平台内其他经营者的商业模式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产生反竞争影响。某一产品或服务的潜在需求(销售)有高有低,平台自营商户所模仿的产品是已被他营商户交易数据证实销售前景可观、已获市场认可的成熟产品。这些产品之所以取得市场成功,大多是凝结了其他经营者创新投入的产品。如果放任数据利用型自我优待,那么会打击其他经营者的创新动力,降低其创新激励和投资预期。
(二)规制理论:基于行为效果分析的行为主义
反垄断规制的理论流派众多,以结构主义/干预主义、行为主义/自由主义为界分为保守、激进、折中三大学说。学者卡尔(Carl)将当代反垄断理论之争归结为三个阵营:一是芝加哥学派,行为主义的旗手,主张限缩反垄断法的适用,只有当竞争行为有损经济效率时才需要被禁止。二是民粹主义或新布兰代斯(New-Brandeis)学派,属于哈佛学派结构主义的复兴,主张经济民主、减少经济不平等、分散经济权力为中小企业创造机会等。三是现代派,属于中间派,一方面主张强化反垄断执法,另一方面仍坚信反垄断应继续专注于提高经济效率。(38)Carl Shapiro,Antitrust:What Went Wrong and How to Fix It,Antitrust,2021,Vol.35,No.3,pp.33-34.布鲁代斯曾于1916—1939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强调民主不仅包括政治、宗教民主,还包括经济民主和自由,不能允许私人经济权力过度集中。以此为背景,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存在两个理论之争。
其一,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规制应采结构主义还是行为主义?美国著名反垄断法学者、现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可汗(Khan)主张对平台企业进行结构性拆分(structural separations),将企业的“平台服务业务”和“商业经营业务”予以分离。(39)Lina M.Khan,The Separation of Platforms and Commerce,Columbia Law Review,2019,Vol.119,p.981.将平台企业的“商业经营业务”剥离出去,可以使平台企业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利益冲突”中脱身,尽可能地恢复其中立性。结构性拆分有两种途径:一是功能性拆分(functional separation),即在企业内部拆分不同的业务,由相对独立的附属企业分别经营。二是完全的结构性拆分(full structural separation),即拆分企业的不同业务,由完全独立的不同企业分别经营。(40)Lina M.Khan,The Separation of Platforms and Commerce,Columbia Law Review,2019,Vol.119,p.1084.无独有偶,国内学者李剑认为具有网络效应、规模效应的部分平台企业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主张将这些数字平台的自然垄断业务(主要是平台服务)和竞争性业务进行结构性剥离,如此可以根本性地解决利益冲突问题,消除平台企业歧视平台内异己经营者的内在动因。(41)李剑:《数字平台管制:公共性理论的反思与经济管制的适用》,《法学研究》2023年第5期,第38页。不过,应认识到,在芝加哥学派兴起之后,结构性救济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领域逐渐退出历史。在数字平台自我优待问题上,再次启用结构性救济应慎之又慎。最重要的是,结构性救济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假阳性错误,而反垄断错误规制可能会导致企业丧失发展壮大的机会,损害经济效率。总的来说,结构性救济之于数字平台反垄断不属于主流观点,大多数观点认为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应采用行为主义理论框架。其二,若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规制采取行为主义,那么应基于行为本身违法予以一般性禁止,还是基于行为效果分析予以个案禁止?有学者认为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法律规制应坚持行为主义,而坚持行为主义的观点又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行为本身违法的规制思路。该观点认为,如某数字平台具有某些竞争特征则应禁止其实施自我优待行为。换句话讲,该思路认为特定数字平台(例如欧盟2022年《数字市场法》第6(5)条之“守门人”、德国2021年《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之“有显著跨市场竞争影响者”)实施的自我优待行为本身就是违法,应该予以禁止。二是基于行为效果分析的规制思路。该思路认为,即使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有自我优待行为,也不一定违法,只有其自我优待行为造成了竞争损害才违法,应予以禁止。也就是说,自我优待的法律规制应重行为效果而非行为本身。自我优待行为不一定造成竞争损害,反而其商业模式创新、产品价格竞争有增进消费者福利的可能,因此,自我优待行为是否违法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42)Patrice Bougette,Axel Gautier,Frederic Marty,Business Models and Incentives:For an Effects-Based Approach of Self-Preferencing?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2022,Vol.13,No.2,p.43.。
本文认为,即使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其自我优待行为不能予以概括性禁止,而应立足于行为之竞争效果予以个案分析。应明确一点,自我优待本身并不违法。自我优待是企业竞争优势的表现。企业没有向竞争对手分享竞争优势的一般性义务。也就是说,一些企业比竞争对手有竞争优势,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企业有权利去利用其自身的竞争优势。(43)Pablo Ibanez Colomo,Self-preferencing:Yet Another Epithet in Need of Limiting Principles,World Competition,2020,Vol.43,No.4,p.421.我们应维护竞争过程,确保企业能保留其竞争能力、竞争激励,使企业能够利用其竞争优势,而不是干预市场以抵消或消除这些优势。正如欧盟普通法院前任主席学者韦斯特道夫(Vesterdorf)所言,“优待自己的产品或业务不是反竞争,即使这会导致某些个别竞争对手的边缘化甚至消失,只要这种优待是依据法律(on the merits)的竞争。”(44)Bo Vesterdorf,Theories of Self-preferencing and Duty to Deal-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Competition Law &Policy Debate,2015,Vol.1,No.1,p.6.进一步来讲,自我优待不能被推定为违法。“自我优待作为一个标签,有时可能会传达这样一种印象,即综合公司偏袒其附属公司本身就有一些可疑之处”(45)Pablo Ibanez Colomo,Self-preferencing:Yet Another Epithet in Need of Limiting Principles,World Competition,2020,Vol.43,No.4,p.421.。应纠正自我优待这种标签化认知,应认识到“一家具有主导地位的企业没有义务以对待自营商业活动同样或实质性一样的方式来对待下游或相关市场的竞争对手”,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综合公司才承担不歧视义务。(46)Bo Vesterdorf,Theories of Self-preferencing and Duty to Deal-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Competition Law &Policy Debate,2015,Vol.1,No.1,p.9.
(三)规制方法:惩戒性规制与激励性规制相结合
数字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自我优待排除、限制竞争,会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的利益以及破坏创新环境,因此应对其进行合理规制。数字平台自我优待法律规制应拓宽规制方法,首先就是要坚持惩戒性规制与激励性规制相结合。惩戒性规制硬化、激励性规制软化是拓展自我优待法律规制路径、提升自我优待法律规制能效的关键措施。
第一,完善惩戒性规制。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自我优待的法律规制应加强执法监管力度,优化并遵循以下两个分析步骤:一是实施自我优待的数字平台在相关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自我优待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因此应首先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自我优待语境中的相关市场,应兼顾平台服务市场和平台跨界经营所涉及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以前者为主、以后者为辅。相应地,数字平台实施自我优待所凭借的市场力量是其在轴心市场和辐射市场中影响力的加总,可称之为“统合型市场支配力”(47)翟巍:《超大型数字平台企业双轮垄断的规制范式》,《财经法学》2021年第1期,第21页。。与“统合型市场支配力”相似,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修正案(第19a条)提出了“显著跨市场竞争影响力”。与德国传统反垄断法规则体系中的市场优势地位、市场支配地位相比,跨市场竞争影响力是一种更加强大的市场力量;(48)德国《反限制竞争法》(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禁止滥用三种市场力量: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19条)、禁止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第20条)、禁止滥用跨市场竞争影响力(第19a条)。二是数字平台无正当理凭借算法、数据、平台规则等实施了自我优待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如上文所述,不是所有的自我优待都是反竞争的,应基于自我优待行为竞争损害的个案分析来判定自我优待的违法性。前文已述,自我优待的竞争损害应从其他经营者利益损害、消费者利益减损、创新环境影响等方面展开。自我优待与拒绝交易、搭售、差别待遇相似,但又存在差异。(49)孟雁北、赵泽宇:《反垄断法下超级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合理规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73-76页;侯利阳:《〈反垄断法〉语境中自我优待的分类规制方案》,《社会科学辑刊》2023年第3期,第27—29页。我国《反垄断法》第22条目前尚未将自我优待单独列为一项滥用行为,因此应注意发挥第22条第7项兜底条款的作用。此外,应注意,自我优待的反垄断执法应避免运动式、选择式执法,而要取向于公平公正,形成常态化执法监管制度。第二,重视激励性规制。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执法监管属于压力型规制,具有事后性。过分倚重执法监管,会增加规制成本、降低规制效能,难以达到预期规制效果。故此,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法律规制还应重视激励性规制。所谓激励性规制指通过非强制性评价、奖励等方式激励企业自我规制、自律合规。(50)倪正茂:《激励法学探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学者马汀(Martin)认为“自我优待可以被视为平台设计决策的一部分,即平台如何管理其生态系统,其中包括如何处理第三方产品服务于自身相似产品服务之间的关系。”(51)Martin Peitz,How to Apply the Self-preferencing Prohibition in the DMA,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Practice,2023,Vol.14,No.5,p.310.可以说,数字平台自身具有技术优势和组织能力,在自我优待法律规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因此,应采取激励监管方法调动企业自我规制的内在动力,使数字平台与监管部门相向而行,形成共治局面。激励性规制着力引导企业做优做强,走创新发展道路,而非仅仅做大,走垄断扩展道路。激励性规制包括柔性温和的监管手段,如教育引导、行政指导、约谈等,也包含商业信用机制、商业声誉评价等市场机制。
企业的自我合规审查是一项积极有效的激励性规制措施。目前,我国法律以及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已经就数字平台的反垄断作出了规定,但尚未明确涉及自我优待。在激励性规制思路下,我们应以数字平台反垄断原则性规定为指导,鼓励并引导数字平台就自我优待行为建立强健有效的合规审查机制。事实上,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非常重视企业自主合规审查的作用,例如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2020年9月发布《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3年9月发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合规指引》等。依此先例,本文建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可适时出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垄断合规指南(或指引)”,并在该规范性文件中将“自我优待行为守则”柔化为“数字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如此,可激发数字平台建立自我优待合规审查的内驱动力,引导数字平台自主建立强健有效的自我优势合规审查制度,促使数字平台履行社会责任。
五 结 语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夸张”的同时,提出“国家支持平台企业创新发展”(5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9日,第1版。。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5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李强作重要讲话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22年12月17日,第1版。。作为全球第二的平台经济大国,我国应强化包括自我优待在内的反垄断监管,以促进数字平台的健康发展、做优做强。自我优待不宜泛化讨论,应将其限定在平台内部讨论,具体指“双角色平台”对平台内自营商业活动的优待。在数字经济“算法—数据—平台”三维竞争结构下,自我优待的实践样态具体表现为三类,即算法操纵型、数据利用型、平台规则支持型。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法律规制应遵循积极有效的包容审慎原则,既不可失之于宽也不能失之于严,具体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深刻认识自我优待的“双轮垄断”竞争特点及其对其他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创新等产生的竞争损害;二是坚持行为主义理论,基于行为效果的个案分析来认定自我优待的反竞争性;三是坚持惩戒性规制与激励性规制相结合,尤其要鼓励并引导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自我审视和合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