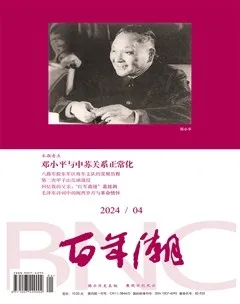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点滴回忆
陈道仪 刘昊 邢辉燕

1953年3月,陈道仪在朝鲜元山
陈道仪,女,四川宜宾人,1930年3月生。1949年12月在重庆入伍,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一军军政大学短暂学习,同年秋赴贵州剿匪,立二等功。1951年3月赴朝作战,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宣传隊宣传员、师野战医院护理员、师后勤政工室工作员(正排级)、政治部组织科干事(正排级),受师政治部通报表扬。1953年4月参加长春东北干部补习班学习,同年10月考入大连工学院化工系。1959年8月,分配到北京化工大学工作。1988年3月退休。
参加人民解放军
1947年以前,我是在长江上游的宜宾长大的。家里的房子很大,我记得房子外面大门上有“紫气东来”四个大字。
在我的记忆中,国民党很腐败,几乎是所有官员都贪污,而且烟馆多、妓院多,贩卖鸦片的人多,土匪横行祸害百姓。老百姓穷得一塌糊涂。过去我家住在重庆临江路,后门下面就是长江。很多人家的房子,就是用竹棍搭起来的棚子,长江一涨水可能就被大水冲垮了。
我的父亲算是工商业者兼地主,也做一些实业。1947年,父亲到重庆一个钱庄工作,全家跟着到了重庆。到重庆后,我刚开始上的是清华中学,校长叫傅任敢,毕业于清华大学,不是地下党,但他思想很进步。那段时间,重庆清华中学地下党很活跃,我也是那个时候受到地下党的影响。
有一次我在重庆看演出,解放军文工团打腰鼓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印象特别深。解放军的纪律很严,怕打扰老百姓,经常睡大街。参军后我在文工队时,经常要演出一个小剧,叫《红布条》。这个剧讲的是解放军进到一个村庄之后的故事。当地有个风俗,家里有喜事了,就在外边门上挂一个红布条。部队到了那家门口看到红布条,坚决不扰。类似的事情很多,对比太明显了:国民党腐败,共产党好。老百姓心向共产党,清华中学很多同学参加了解放军。
清华中学位于重庆郊区,上学的路全是土路,一下雨很泥泞,而且重庆老下雨,上学非常不便。我们家就把我转到市内的巴蜀中学念书。
1949年夏,我从巴蜀中学毕业了。没有考上大学,在沙坪坝补习,正好解放军到沙坪坝来招生。我想到部队学新知识。同学告诉我,你知道怎么才能被解放军录取吗?你去报考的时候,对方问你为什么来参军,你就说我是来为人民服务的。那时候哪懂什么为人民服务,就是因为说这句话能考上,更是觉得共产党伟大,解放军很好,所以要跟解放军学新知识。
1949年12月,重庆刚解放,我就参军了。大家参军非常踊跃,好多人参军走了,以致1950年重庆有些大学完不成招生指标。后来,我们坐了三天木船,到万县的十一军军政大学(以下简称“军大”),学习半年左右,分配到九十一团。
在军大期间,有几件事情我印象特别深。我们住在一个地主家,有一次我们四个女同志(都是新兵)晚上去守大门。夜里,有人过来检查。我们四个人都瞌睡了,迷迷糊糊在那儿坐着睡。战士一看这个情况,就说:“你们怎么了?”黑咕隆咚中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们女兵紧张得不得了。有个女兵胆子比较大,指着那人问:“你是谁?”我们以为是坏人来了,吓坏了。毕竟都是十几岁的女孩子,还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胆小。
军大训练大家打枪和扔手榴弹,为了安全,都是从山坡上往下打枪和扔手榴弹。因为担心出事,都有人指导我们。我和一个姓李的战友一起练习打枪,虽然往山坡下打很安全,但是很紧张,一枪打出去,李同志吓得哭起来,实在太紧张了。
新中国刚刚诞生,经济很困难,我们吃的菜只有白萝卜,炖白萝卜,炒白萝卜,烧白萝卜,反正一天到晚都是白萝卜。军大说要培养干部,大家说怪话:干部,干部,就是干白萝卜。后来我们开荒,我去浇地、养猪。快毕业的时候,我们的伙食就很好了。那时候都是瓦盆装菜,一瓦盆装一大堆红烧肉,大家吃得很香。
贵州剿匪、紧急赴朝
军大毕业后,我被编入二野三十一师九十一团,1950年秋天开赴贵州剿匪。那里的老百姓苦得不得了,基本上是饥寒交迫,有两件事至今难忘。
一件事,是到一个村里头见到的。这个村庄在山上,有400多人,全村只有村长有一件棉衣,其他人都没有。好在那个地方有露天煤矿,到了冬天老百姓都是烧煤来取暖。解放军进驻村里,全村人围着解放军,要求给一件棉衣,因为多年都没有棉衣穿了。
还有一件事,是老百姓普遍买不起盐。那时候,农村都是大锅做饭。过去贵州都是用岩盐,结成硬块吊起来,家里条件好的,菜煮完了,端起来拿到盐块那里转一下,就算有盐味了,菜里基本上没有油水。更穷的人,一点盐都吃不上。

1950年12月23日,陈道仪在剿匪作战中荣立二等功的喜报
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我们走路,一天不知道摔多少跤,即使穿上草鞋也不行,因为老下雨。贵州剿匪很艰苦。说是土匪,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很猖獗。贵州山高林密路难走,这些土匪藏得很深,不容易找。许多国民党兵还是“双枪兵”,一手烟枪,一手钢枪,打起仗来也会拼死抵抗。
完成剿匪任务,我们从贵州返回重庆,要经过一段叫“72道弯”的路,盘山路,非常陡,走不了多少路,就是一个弯。那个时候路况非常差,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一旦车开不好掉下悬崖,肯定全完了。那天司机很尽责,但开得很急。
到重庆后就待了一天一夜,上级通知有紧急任务,我们马上坐船到汉口,紧接着坐闷罐火车继续走。火车一路奔驰,我们很快抵达辽宁安东(今丹东)。
1951年3月21日,第十二军在军长曾绍山、副军长兼参谋长肖永银率领下,由长甸河口入朝。过了鸭绿江之后,看到朝鲜满目疮痍,被美军轰炸得一塌糊涂,到处是废墟。所有城市、村镇根本认不出来,偶尔看到一段烟囱,我们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城市。
入朝之后,我们连续走了18天,天天夜里走,白天不敢走,因为当时敌人军机很疯狂,白天轰炸得很厉害。敌机一旦发现一个目标,就俯冲下来扫射。白天我们就在野外找个隐蔽地方睡觉,恢复体力。入朝时每个人要背一块绿色雨布。雨布是橡胶做的,背着真沉。朝鲜很冷,雨布是垫在地上用的,可以防潮。我们女兵集中编在卫生队,要去做护理工作。
过江没几天,碰到敌人丢照明弹。照明弹亮到什么程度呢?夜里头照得跟白天一样,指甲盖里头的脏东西都看得见。大家迅速地跳到路边的沟里头,隐蔽起来,免得被敌机发现。我们没有制空权,实在太被动了。
天天夜里行军,太疲乏了,出现了掉队现象。身体素质好的人走在前头,后边人拉着前边人的衣服,以免掉队。有一次,大家实在是太困了,迷迷糊糊连走路带睡觉,结果前面一个人摔到沟里头,连带五六个人跟着摔到沟里头去了。
走到驻地谷山,我们有点麻痹大意,白天也开始活动,敌机发现后过来扫射。到驻地当天,有一个通讯员上厕所途中,一颗子弹从他膝盖穿过去,腿被打断。还有一次,三个炊事员在睡觉,每个人都盖了薄棉被。敌人扫射的一颗子弹,从隔壁房间先穿过一桶油,又穿过一堵墙,射到中间那个人的被子里头了。这几个炊事员幸免于难,但都被吓了一大跳。
我到现在都记得,到谷山后发给我们的粮食是黄豆和麦子。我们拿到后都傻了,说这怎么吃呢?有人想出一个办法,到朝鲜老乡家把黄豆泡了磨成豆浆,把麦子磨成粉,和在一起发酵,做成全麦馒头。18天吃不上正经东西了,尽管没有菜,就只吃这个馒头,我们也觉得很好吃,特别甜。
当时美国人吃的穿的,比我们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他们吃罐头,过感恩节还特地从美国运来火鸡,睡觉都是用羊绒睡袋。我们的侦察兵曾经抓他们的俘虏,就是把睡袋一下拎起来,把睡袋里面的人抓回来了。
我们的通讯条件也很差。架电话线的战士,经常要背很重的电线建联络线。为让首长的指挥能够到达前线,牺牲的战士特别多,因为他们暴露在外面。有的战士手被打断了,腿打断了,就跪在地上用嘴咬着两根线接上。
装备就更悬殊了,美国人是飞机大炮一起来,我们是小米加步枪,有时候还没得吃。敌人侦察机飞得很高,一旦发现一个目标,哪怕一个小黑影,就俯沖下来扫射。哪怕见了一头牛,他也要打死,只要地上有活物,敌机就会俯冲下来打死,因为他们没有顾忌,他们知道那时候我们没有制空权,我们拿他没有办法。
如果单看武器,这个仗是没法打的。但是,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有一个炊事员特别勇敢,他碰上美军,美军拿刺刀把他肚子戳穿了,肠子流出来了。炊事员把流出来的肠子往肚子里一捂,然后用他的围腰系上。他没有武器,抄起一根扁担就朝敌人打过去,对方吓坏了,不知道是什么新武器,因为中国扁担他们没见过。最后炊事员把美军打倒俘虏了。
参加第五次战役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挫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韩国军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反击战。我们入朝仅一个月,就赶上动员参加第五次战役。当时,我做卫生员,还参加文工团的工作。
我先说说这期间发生的传口令趣事。过去部队传口令,就是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往下传,传达命令。有一次传口令时,最后稀里糊涂说成“不准马打屁”。我们是有几匹马,装首长的办公用品和部队卫生用品。最后传成这句话了,走样走得厉害。饲养员犯了难,就说怎么办?管不了牲口啊!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话,当时大家实在累得困得不得了,以至于口令传错了。
我们每个人还要背很多东西,有铁锨、雨布、炒面、水壶、洗脸盆,这几样东西加起来差不多有40斤重。刚入朝的时候我们还有被子,第五次战役时就没有了。晚上也没房子可以睡觉,只能睡在外面,就靠穿的衣服和雨布来御寒。我记得跟我合伙睡的女同志叫李以群,我们用一个人的雨布铺在下面,另一个人的雨布盖在上面当被子。当时供应粮食的,是我们的兵站,隔一段路有一个兵站。有时候兵站比较密,我们就可以背少一点,如果兵站距离远,就多背一点。最近几年,我老是背疼,后来发现脊柱弯了,骨头都变形了,医生说与年轻时经历的重压有关。
第五次战役时的伙食依然很差,根本见不到油星。我们背的洗脸盆,吃饭时候就是锅和饭盆。垒几块石头,找点干草当柴火烧,上面放上脸盆,倒上水壶里的水,再把炒面倒进去,既没有盐也没有油。碰到首长的炊事员,偶尔可以要点盐,要不到油,因为首长的炊事员带的东西也有限。敌人是汽车送饭,我们是扁担挑着大萝卜,每个人自带干粮,双方后勤的差距可见一斑。
我们师里最能打的一个团是九十一团,团长是李长林。李团长吃得也很差,有一次他的警卫员想方设法搞了点玉米,可是根本没有条件把玉米磨成粉,就把玉米煮了给李团长吃。伙食差,身体肯定不行,警务员就搀着李团长走。
有一天傍晚,看到我们住的防空洞附近在燃烧一堆东西。我跟另外一个人很好奇,胆子也大,说过去看看。看到一个罐,撬开以后发现是美军销毁东西时剩下的糖,罐里是一个一个的小糖块,大半罐糖还没烧完。我们捡回来,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当时根本吃不上糖。战友说:“你俩胆子真大,万一里头埋的有炸弹,你们一掏不是马上就炸了吗?”那时候我们没有想那么多,实在馋得没办法。1952年我们的伙食就改善了,记得有一次吃饺子,入朝第一顿饺子,我连吃40个,现在想想都吓人。
我跟着部队抵达汉城郊区。我的任务是照顾一批伤员,看到这些伤员真难过。他们都很年轻,20岁左右,缺胳膊断腿的。当时医疗条件又很差,我们能做的事就是给他们包扎一下,照顾他们吃饭、拉屎撒尿。看到这些年轻的伤员,深感战争的残酷。
到了汉城才发现,我们师孤立于三八线以南,被敌人包围了。所以,部队要往回撤,向北走。途中,我们在一个朝鲜老乡家找点水喝,从老乡家出来以后,由于思想麻痹,在天还未全黑时,部队就动身行军,被美军飞机发现。敌机马上就俯冲下来扫射,敌机飞得特别低,我都看见美军飞行员了。我们赶快分散,我找了一个稍微有点坡的地方蜷着,根本不敢动。敌机扫射的子弹就在我身边炸开,冒着金星,我想必死无疑了,幸运的是未被子弹击中。大概没有发现更多的目标,敌机就飞走了,我死里逃生,回想起来这次是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遭遇的最危险的经历。飞机俯冲下来有个声音很难听,很刺耳。回国以后很长时间,只要听到类似的声音,我都紧张得要命。
我们师九十一团跟师部失去无线电联络,师长赵兰田派人历经艰险终于把信送给团长李长林。但是,战场形势变化很快,信里“原路返回”的方案已经很难执行了。李团长很有经验,决定执行“绕经下珍富里以东北返”的方案,趁着敌人不了解我军意图和山林地带方便隐蔽作战的有利条件,找机会跳出包围圈。李团长带着部队巧妙地装成韩国人,白天可以在大路上走。美国人以为是盟军,自然不攻击;遇到敌人就让翻译回答,对方以为是自己人。有时候,九十一团甚至还和敌人并肩同行,一路上我们也不敢说话。经历艰难险阻,九十一团终于和师里会合了。
我们这些女兵,还捎带着做文工队的工作。1951年,有一次我们师文工队去慰问演出,下午回来时遭遇敌人的炮火封锁。有一个必经的小河沟,小河沟有几块石头,可以踩着过去,但是天黑了看不清,天又很冷,河里已經结了薄冰了。为照顾女同志过河,有位男同志打了下手电筒,让女同志踩着石头过去。这一下暴露目标了,美军炮火马上打过来。大家赶快分散,等炮火没有了,又集中起来了。
文工团有个河南籍的女同志叫刘文,她是文工团的创作员,才19岁,她本来几乎已经过小河了,再往前走几步就突破炮火封锁线了,但她又返回来接应其他同志。就是那时候,她负伤倒在水里的。战友们把她从水里捞起来,发现她的左腿从大腿根被炸断了,断腿和身体只连着一层皮。为防止流血过多,战友在背她的时候改为爬着走,别的同志帮着抬她的伤腿。抬她伤腿的同志,把刘文的断腿揣进棉衣。第二天洗衣服时,发现棉衣里有两块带血的碎骨片。这位同志把碎骨片洗干净,连同刘文的断腿一起埋到山坡下的小河旁。
那一次文工团穿越炮火封锁线,我们牺牲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牺牲的女文工队员,叫戴儒品,长得很漂亮,大眼睛,很爱笑。戴儒品是重庆籍,出身书香门第,毕业于重庆女师音乐系。重庆一解放,她就参军了。她是女班的副班长,总是帮体弱的战友背粮袋,给脚上磨起血泡的战友挑血泡,大家都非常喜欢她。那一次,一发炮弹在她身边爆炸,她不幸牺牲,战友们就把她埋在当地。
还有一件事情,一想就难受得不得了。大概是第五次战役结束了,我们12军已经撤到相对后方了。有一天,需要工作人员去另一个地方整理材料,本来是让我去的,后来因为我是个女同志不方便,就让我们科里另外两个男同志去了,一个好像姓肖,另一个姓秦,是干部处的。当天他俩忙完事往回走时大意了,天色还看得见,被美军飞机发现了。敌机马上俯冲下来扫射。他俩迅速跳到马路旁边沟里头躲藏。等到晚饭都吃完了,他们还没有回来,我们就派人去找,发现他俩已经牺牲了。姓秦的战友曾用津贴买了一支挺宝贵的钢笔,他牺牲时子弹打断了他胸前的钢笔,穿过他的胸膛。
血战上甘岭
1951年冬天,朝鲜很冷,我们用来漱口的热水吐出来,还没有落到地上就结冰了。我们3月份入朝,算是入朝比较晚的。后勤各方面已经有些经验了,供应相对好一些了,但我们的条件还不行。我们住在矿洞。男同志在矿洞里头,女同志住在矿洞靠外面一些(空气流动稍好一些)。就一条矿洞,也不分房间,连办公带睡觉都在矿洞。我们在矿洞外边挖了一个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通道,根本直不起腰,出来进去都是蹲着。
我记得和我搭一个被窝的女同志叫徐建文(80年代去世)。我俩被窝底下垫的是棉衣和棉裤,上头再盖层雨布取暖。实在太困了,早上我们经常醒不过来。小号兵在外面吹号我们都听不见,有时候他就把我们的帘子掀起来,对着矿洞里头猛吹,才把我们唤醒起床。现在想来是很苦,但时不时看到战友牺牲,这些苦我们也不怕。经过战火的考验,我们也不怕死了,甚至都没想到能活着回去。
1952年,我在十二军三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工作。那年夏天,我们师在金城前线担任坚守防御任务。师部驻白易山峡上一个名叫曲德里的地方,司令部和政治部分驻两条山沟。一天,敌机突然空袭师部。司令部损失不大,政治部却损失很大。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修了防空洞,防空洞基本上就是土堆起来,三根木头搭起来,然后加土,防空洞一小半在地底下,一大半在地上头。那天不知道怎么暴露目标了。敌人飞机发现目标,一下就俯冲过来,又炸又扫射。我比战友刘群就跑得稍微快了一步,躲到一个石洞里头去了。刘群就慢了一步,结果她所在的防空洞被震塌了,就把她埋在里头了。
我们一个姓贾的战士很不简单,他一看出来的人少了,就带着两个战士去挖刘群所在的防空洞。当时,敌机还在天上飞,大家也顾不上,最后把刘群挖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已有高射炮了,空中稍微有些制空权了,敌机不敢多停留,炸完了就赶紧飞走了。那一次,刘群死里逃生,她的右眼角、右脸颊到右嘴唇被机枪子弹射中,子弹再往里一厘米甚至半厘米,她可能就没命了。从那以后,刘群脸上永远留了一道疤。
1952年10月,我们十二军在金城地区防御一年后奉命将防务交给六十七军,到后方谷山地区休整。刚刚撤出一线阵地,正向后方开进途中,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北进,掉头南下,转赴上甘岭。当时,上甘岭战场上的十五军已经消耗得很厉害,我们十二军三十一师紧急赶赴上甘岭接替十五军在597.9高地主阵地防御。10月20日,先调九十一团,25日继调九十二团,11月1日再调九十三团,至此,我们三十一师就全部抵达上甘岭。
我记得有个晚上,要到达主阵地某一个地点,向导带错了路,我们不要命地走,一晚上爬了两座山,走了90里地。最后所有人困得累得不行了,坐下来就睡着了。我们后勤处长姓徐,是个老革命,他比较谨慎,先派侦察兵下去看看马路能不能走。侦察兵下去一看,美军坦克车队正在山下公路行驶,部队立即停止下山的计划,避免了不必要的危险,我们要是直接下去肯定被俘虏了。
上甘岭那个地方条件很困难,我们政委一般都不让女同志去,不管你是哪一级干部,都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头。但是我们师里的文工队员还是去上甘岭慰问演出,我记得打快板给战友们打气。
上甘岭战役打得很惨烈,阵地上什么都没有了,石头都打碎了,树也沒有了,战场上全是浮土。上甘岭战役中,我们修了很多坑道,我们取胜很大程度是坑道发挥的优势。有时候石头很硬,坑道挖完了铁镐都磨光了,只剩下木头那一段。
从1950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在朝鲜战场待过的人基本上都是九死一生,因为那时候没有前方后方,敌军飞机整天在天上飞,一旦发现目标,要么就是炮弹打过来,要么就是飞机俯冲下来直接扫射。我记得有一个男文工队员跟我们说:“我每天都在生死鬼门关过的,因为随时可能被敌人发现,炮火就跟着打过来了。”

2020年10月2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七休养所,陈道仪受领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证章
投身教育事业
1953年,我们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大量人才,凡是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都要回来考大学。我是4月份从朝鲜回来的,再过三个月就要停战了。那一次,我们终于不用步行了,是白天坐大卡车回国的,白天已经敢走了。
回国以后,我先到长春去上补习班。学了几个月,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我考到大连工学院无机专业。本来应该是1957年毕业,结果大连工学院缺辅导员,又把我调出来做辅导员,1957年大连工学院本科从四年制改成五年制,所以我1959年才毕业。毕业后我被分到北京化工学院(今北京化工大学)。我当了30年老师,一直工作到退休。
(责任编辑 崔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