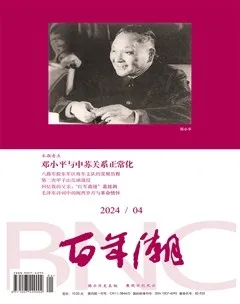九死一生如昨
一个八十七八岁的老人,却要写点七八岁时的故事,勉为其难了。但是只要去想,早期的记忆就像蹦出来一样,愈来愈多,愈来愈清晰。写下来破破暮年孤寂之闷,别无他想。
在沦陷区
我的爸爸在1933年、我的妈妈在193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在京津唐一带做地下工作驻机关时结婚,生活危险而又清贫。我快要出生了,妈妈还在等待着四处找住院钱的爸爸,找到钱才能到医院待产。我是1936年底出生的,再过半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正是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急的时刻。为纪念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抗日英雄邓铁梅,爸爸为我起名铁梅,希望我背负起民族兴亡的责任,成为邓铁梅那样的抗日英雄。我几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就抱着我作为掩护,去做接关系等工作,这可能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同爸爸一起面对危险。
在我刚会说话的时候,父母在海滨执行任务,有一个后来叛变的人,曾把我抱到海边的深水区,问我老家在哪儿、姓什么、爸爸的真实姓名。我没回音,他就把我倒提起来,头浸着海水,我那时什么也不知道,好像也不会完整地说那么多话,只能哇哇乱叫,惊动了妈妈,把我抢了出来。那人说:“二姐,你急什么?我是同孩子闹着玩呢。”

吴铁梅一岁左右时在唐山
80年代初同学们谈起办离休的事情,我总凑热闹讲起这段历史,证明自己30年代就参加了革命。爸爸听了只说:“你真招笑,那么小你懂什么革命工作。”我又讲在晋察冀边区城南庄上小学时,正值土改,我和同学们打着霸王鞭,唱着“灯碗里没有油灯不明,农民们没有地辈辈受穷……”的歌,四处宣传土改,这算参加革命工作了吧。聂荣臻伯伯身边的魏叔叔还要给我写证明呢。我把这些情况告诉爸爸后,他严肃地说:“1949年前你太小,一直在读书,没有参加过革命工作,不要跟着你们那群同学起哄,你根本就没有离休的资格。”我只能作罢,谢绝了好几位要给我写参加土改工作证明的长辈。他们去世多年后,我也退休了,有一次和张明远伯伯的女儿小霁聊天,又一次问她到底怎么办的离休。这次她说:“告诉你吧,是吴叔叔签了字,我们单位才给我办了离休,吴叔叔让我保密,不要告诉你。”我听了哭笑不得。记得追悼会上发的吴德生平中有一句“严格要求和教育子女”,我就是被严格要求的了。
1940年爸爸要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难知归期。妈妈被安排到冀东游击区参加抗日斗争。我成了无处安放的“累赘”。在老家唐山的奶奶去世了,只剩下爷爷和在家尽孝的三叔、四叔,谁也照看不了孩子。我还有个妹妹小二,因无力抚养送给了唐山的一个工人家庭。抗战胜利后爸爸回到冀东,又带着部队和一批地方干部接管了唐山市。物是人非,寻找到了收养妹妹的人家,说我可怜的妹妹两岁时就病死了。
当时爸爸只好把我送到姥姥家抚养,那时我只记得过姥姥家大门的门坎,我要先爬上去,再从门坎上滚下来。姥爷王家在沦陷区滦县南关村,距县城和滦河都很近。王家是个破落的大家庭,姥爷是老大,在外面娶了小老婆遗弃了姥姥。院子人口不少,是非热闹也不少。
姥姥是个安分胆小的农村妇女,没什么经济来源,有二亩沙地却无力耕种,全靠娘家和我妈妈的接济过日子。本来因遭遗弃,又没儿子,饱受家族白眼,我的到来更惹起了风波。那个时代哪有把孩子放在娘家抚养的,甚至有人说我的来路不正。在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胆小的姥姥不敢和家族人争执,把我关在屋里不许出去。救星很快来了,唐山的爷爷不放心我,派三叔和四叔扛着一袋白面来看我。于是舆论大转,原来妈妈嫁了唐山的正经人家,铁梅的叔叔送白面来了。现在的人很难懂,当年的农村白面有多金贵,何况还是整袋的。我也翻身成了王家可爱的外孙女。姥姥又允许我出去玩,爬过大门的高坎看外面的世界了。
大概是1943年,妈妈回来了,我扑到妈妈怀里,高兴地蹦跳。妈妈说,爸爸出远门做生意,她回娘家看看。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在冀东游击区坚持抗日斗争,她所在的部队被日军打散了,斗争很残酷,三个女同志躲在山洞里,靠着老乡送的一罐生鸡蛋坚持了三天。出来后找不到队伍,又和组织接不上关系,只好各自回家,等环境好一点再说。
好景不长。有一天妈妈去滦县城里找组织关系,在城门口被叛徒指认,日本宪兵队抓走了她。消息传来我和姥姥吓得大哭。很快日本人来了,看着家徒四壁和又老又小两个人,没什么油水可捞,布置族人监视我们。这可吓坏了族人,没有一个敢理我们,更不要说帮忙。那一段是我记事以来最难过、最无助的日子,至今深深印在脑海中。
妈妈不在家,钱花完了,米面吃完了,真的是揭不开锅了,我和姥姥饿着肚子只会抱头大哭。姥姥急中生智,拉着我到村外那二亩沙地。地里的庄稼已经结穗了,姥姥掰了几穗灌浆尚不饱满的玉米,又摘了点毛豆,在地里挖坑点火烤得半生不熟给我吃。我现在已年近九旬,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了。姥姥好像什么也没吃,拉着我往回走。我实在走不动了,姥姥便背着我。腹内无食又是小脚的姥姥也走不动了,便背着我在地上爬,爬了很久,不懂事的我竟然在姥姥背上睡着了。爬到村头已到了快上灯的时候,姥姥才叫醒我。现在想起这件事都想哭,为什么我那么不懂事。
几天后,一个我叫舅姥姥的亲戚送来一袋小米,劝姥姥千万不可吃青,秋后才能有点嚼谷。后来她又来了数次,送来钱和粮食,我们才没有饿死。姥姥感谢娘家兄弟救命之恩,也给后面发生的事埋下伏笔。后来妈妈告诉我,舅姥爷家在游击区,同八路军有些联系,组织上知道了妈妈和我们的情况,通过舅姥姥送粮送款接济,我们的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
過了一段日子,日本宪兵队放妈妈回家了,又拿来一些礼物,并说已经给妈妈安排好小学教员的工作。礼物妈妈没有收,说家中还有事暂拒了小学教员的工作。只是把不到六岁的我,更名李紫荆送到滦县第一小学去读书。这所小学在日本人控制之下,其实我是当了人质。后来我才明白,妈妈被日本宪兵抓去,并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未泄露组织秘密,更没有出卖同志。日本人把她当作家属,想放长线钓大鱼,抓到爸爸或组织的其他人,要求妈妈给他们做事。妈妈答应出去后当小学教员。日本人便把妈妈放了出来,族里的人负有监视的责任。
妈妈安心在家过日子,收拾房子,淋灰水洗被褥,纺棉花卖线,又带着我到涨过水的滦河边捞淤柴晾干备过冬。妈妈向周围的人说:“我不能再走了,这次这一老一小就差点饿死。”她安了所有人的心,日本人也放松了监视。

1943年,吴铁梅(右)在姥姥家和滦县来的亲戚合影
有一天妈妈从集上买回二斤肉炖在灶间锅里,也没让我去上学。那时在农村除了年节谁吃得起肉,四溢的香味吸引了四邻的注意。妈妈说:“累了,出去转转。”过了一会儿肉炖熟了,姥姥抽掉灶间的柴火,等着妈妈回来。我闹着要吃肉,姥姥一反常态不许我吃。周围人说:“你带着孩子找找她妈吧,有人看见她在滦河边上转悠呢。”姥姥拉起我就往外走,并没有去滦河边,而是背道而驰,走进了庄稼地,越走越远。我想着家里有肉用不着吃青啊,问姥姥话她也不理我,只是急慌慌地往庄稼地深处走。走到小路边一个沙土坎上,姥姥说“就是这了”,便拉我坐在坎上。过了一会,出现了一个背篓子的中年男子。他对姥姥说:“大娘等急了吧,有点情况,咱们要快走。”说着一把抄起我背在背上,大步流星地走出庄稼地,姥姥一溜小跑跟在后边。走了很长时间,对面又走出两个背篓子的男子,对先前那个人说:“人交给我们,你赶紧回去。他们家里可能已经报告了日本宪兵队。”这两个男人带着我和姥姥走了很远的路,进了一家农户,对姥姥说:“大娘,别害怕了,平安到家了。”又对那户人家说:“这就是我和你们说的抗属,先在你们家住几天。”这家的大爷大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又饿又累的我吃完饭就睡着了。
就这样,妈妈在日本人失去警觉后,和组织接上关系,带着我们从日本人鼻子底下溜了。
在游击区
从那以后,我和姥姥就在冀东游击区当起了抗属,不时从这个村转移到那个村,几个月过去了,妈妈也没露面。虽然经常转移,但不用为吃穿发愁。我和村里的孩子一起唱抗日歌曲,还能拿起红缨枪跟着大孩子站岗放哨,觉得天地豁然开朗。姥姥却不同,天天发愁,惦记一贫如洗的家,经常和我说,“都是你妈闹的,有家也回不去了。”
当我们转移到一个离姥姥娘家稍近的村庄时,有天姥姥忽然不见了,急得我大哭。房东大爷大娘说:“姥姥临走时留下话,回家看看就回来。已捎信给你妈,她很快会来接你。”我哭喊着说都不要我了。他们说:“鬼子‘扫荡很残酷,你妈如果来不了,我们认你做干女儿,养活你长大。”当天就让我鞠躬认了干亲。有了爹妈,大哥、大嫂、小姐姐也改口叫我老妹子。那段没有亲人在身边的日子里,是冀东农村的老百姓养育了我。就连左邻右舍熬碗豆粥都从墙头递一碗给我,更别说干爹一家了。
有一次日军“扫荡”围了村,是小姐姐带我跑反,在村口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在拦人,不许出村。也许看我们俩太小,没人理会,才跑出了村。我们回到家后,受了惊吓的干爹说:“小丫姥姥可能出事了,这次鬼子到咱们家四处搜查、盘问,以后不能领着她跑反了。”于是半夜里全家动手改造菜窖,不但扩宽,还挖了气孔。过了不久,日军又来围村了,干爹把我藏在地窖里,又放了些水和干粮,嘱咐我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要出声。我躲好了,他们全家才跑出去。地窖里真黑,由于搁了吃的东西,
几只老鼠围着我转,真吓人,但我记住干爹的嘱咐,一声也不敢吭。日军真的到家里来了,皮靴踩地声、说话声、翻箱倒柜声在我头顶上响着。我不敢出声不敢动,竟然吓迷糊过去。只记得大哥抱我出了地窖,阳光和干爹一家的说话声才惊醒了我,我也只会放声大哭。从此我彻底成了这家的老闺女,如果妈妈和姥姥不来找我,我就是这家的老丫头了。很多革命前辈的子女,就这样融化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了。
姥姥回来了,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抱着我哭。原来我们深夜不归后,负责监视的族人第二天向日本人报告。他们受到严厉逼问,有人供出姥姥有个亲弟弟可能知道我们的下落。日本人很快找到了舅姥爷,抓到宪兵队下了大狱,拷问不出我们的下落,无奈放了他,但严令他务必找到我们,不然再把他抓回去。滦县地方不大,很快他就知道了我们的音信,托人来传信。姥姥心疼弟弟,又感念断粮时救助之恩,就回去探亲了。来人还让她带上外孙女,好在当时我在街上玩,姥姥说我跟八路军队伍走了,她也不知我在哪,在关键时刻保护了我。姥姥到娘家后便被弟弟出卖给日本人,抓到大牢里受刑,但姥姥咬定不知道我妈妈和我的下落。日本人对这个农村老太太没有办法,又不是抗日分子,就放她回了家,交代族人监视。姥姥平时就在屋里待着,实在没有饭吃了,才出门四乡讨要。日本人渐渐放松了监管,姥姥终于敢要饭要到干爹所在的村。姥姥嘱咐干爹把这些情况转告我妈,把我赶紧带走。
姥姥要赶回滦县南关村,不管我如何哭闹,干爹如何劝阻,姥姥还是走了,她怕回去晚了连累族人。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到姥姥。后来妈妈设法把姥姥安排在邻县,与一个孤老太太同住。抗战胜利后,妈妈去找姥姥,她已去世。同住的老人说,姥姥临死前满炕地摸,找铁梅,还埋怨妈妈不应该把我一个人送走,怕受别人欺负。我活了80多岁,经历不可谓不多,但知道最疼爱我的人是姥姥,思念至今。
日军的“扫荡”过去了,我们的队伍又回到滦县。妈妈要把我带走。我和干爹一家依依惜別,妈妈向干爹一家反复道谢,让我永远记住他们一家人对我的救命之恩,记住冀东游击区的老百姓同抗日队伍血肉相连的关系。
我跟着妈妈、跟着部队,开始了同日本人战斗打游击的日子,经常行军转移。冀东的老百姓真好,每到一个村,坐在炕上,端上来的总是烙饼摊鸡蛋,热腾腾的豆粥、棒粥。这些吃食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无比珍贵。冀东老百姓苦啊,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却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抗日队伍。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冀东的抗日队伍才能够在游击区坚持同日本人战斗。
1944年,冀东的党政领导机关和一部分部队,被日军包围在丰润县杨家铺村、夏庄子村一带。我们的队伍只能强行突围,战斗打得很惨烈,很多同志牺牲了,我熟悉的地委领导丁振军叔叔、周文彬伯伯都在突围中牺牲了。我和妈妈骑着驴随大部队突围,我坐在她身后,两手紧搂着她的腰。急行中,驴跳过一个壕沟时颠簸太大,我掉到壕沟里。奔跑的队伍停不下来,妈妈骑着驴继续奔跑突围。到了安全地方清点人员,妈妈为牺牲的同志难过,明知我掉到壕沟里不知死活,但什么也没说,不想让刚突围出来的同志再涉险。清点人数的警卫人员发现我不在了,大声地喊铁梅。这时妈妈才说“别叫了,铁梅在突围时掉到沟里了”。一位叫程义的警卫员转身就往回跑,妈妈阻拦说:“敌人可能还在那里,有危险,等了解一下情况,我带人去找。”程义说:“天就要黑了,找不着孩子,出了事怎么办?”天擦黑时程义把我背回来,说:“孩子可能摔晕了,一动不动在壕沟里睡着了。”四周的叔叔阿姨都说铁梅又捡回一条小命。这已经是第二次在生命最危险时睡着了。妈妈嘱咐我要像记住干爹一样,永远记住这位程义叔叔。以后行军妈妈用布带把我绑在她腰后,再也没发生过掉下去的事了。
去根据地
这件事情后不久,上级来了指示,调妈妈去晋察冀边区。我和妈妈要分两路走。我被交给一位孙姓的老交通员,他长着长长的花白胡子,驼着背,穿着破旧的衣服,安排说他是我的爷爷,要带我到北京去。他说只要我听话,到北京后带我去逛北海公园,我自然是心向往之,不敢不听话。我们坐火车顺利到了北京。车站上的日本人虎视眈眈盘查每个行人,却没人理我们一老一小。孙爷爷告诉我,鬼子查“良民证”,60岁以上、12岁以下的人不发“良民证”,故而不查我们。后来爸爸告诉我,当时孙爷爷是冀东有名的交通员,专跑敌占区这条线,他只是看着老,其实没有60岁。
夜晚我们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下了车,走出车站,站外广场上一片灯海,我这个乡下丫头惊奇得一动不动,到现在我都记得嘈杂的人群在如海的光影中涌动。孙爷爷告诉我那是瓦斯灯的亮光,做买卖的摊贩都点着这种灯照明。他带我在一个小摊上吃了顿饺子,之后入住前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他嘱咐我的名字叫腊梅,不能告诉别人铁梅二字。我一直很护自己的名字,就喜欢大家叫我铁梅。爷爷看我嫌腊梅难听,就耐心地给我讲:铁梅这个名字叫的人太少,有进步嫌疑,搞不好要暴露身份的。
我这个名字的确特殊,上大学时,在北戴河与长影的编剧沈默君一起玩,他也问起铁字和梅字不搭调,父母为什么给我起这个名字。我告诉他是为了纪念抗日英雄邓铁梅。沈默君后来写了个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就是后来的《红灯记》,女主人公名字就叫李铁梅。“铁梅”名声大震,耳边总像有人在叫你一样,实在受不了(爸爸本姓李,我从小一直叫李铁梅)。我就到派出所去改名,可是大家对新名字不买账。后来爸爸说:“咱们俩还是都姓吴吧。”我想也对,我不当李铁梅,而是吴铁梅,没有了冒充英雄之嫌。就这样我跟着爸爸的化名还姓吴。爸爸吴德这个名字是在参加七大的路上改的,因组织上规定,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要改用新名字,再回白区工作就不容易暴露身份。黄敬伯伯和爸爸开玩笑说:“我起个名,你敢叫么?”爸爸想反正叫不了几天,回白区就不用了,便说:“敢叫。”黄伯伯在手心写下了“吴德”两个字,爸爸只好认了并报上去。谁知他留在延安工作了五年半,此名也从此叫了半辈子。不过还好,毛主席数次说“吴德有德”,算是给这个名字“平了反”。
再说回北京前门的小旅馆,第二天孙爷爷一大早出去,把我锁在屋内。不到中午他就回来了,急匆匆拉着我从前门火车站上车,问什么都不让我说话。从一个很小的县城车站下了车,又拉着我在乡下的路上疾行,我又饿又累走不动,好不容易到了二分区的一个村。进到屋里,一位叔叔拉着我手说:“这就是铁梅吧?许建国同志今天还问呢。”孙爷爷说:“这是我完成的最难的
任务,现在交给你们了。”后来爸爸告诉我,当年孙爷爷到北京的任务是和一位倾向抗日的伪军头目接关系,带我到二分区是捎带的。但是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没见着人,根据地下工作的经验他怀疑是出了问题,如果此人告密,可能带敌人来抓人,就很危险了。我才明白为什么带我匆匆逃离北京。后来那人果然叛变,亏了孙爷爷警惕性高,跑得快。我又与死亡擦了一次边。
去延安
二分区是党在京西建立的根据地,我在那里待了些日子,他们派马夫赶着骡子把我送到晋察冀分局许建国伯伯处。不久妈妈也到了晋察冀,把我接到她学习的党校。所谓学习是审查她被捕的问题。妈妈的问题一时查不清,她决定让我一个人到延安去找我爸爸。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经离了婚,因妈妈被捕问题审查不清,爸爸又在中央社会部做情报工作,组织有规定,也只好如此了。
1945年初,冀热辽的高敬之伯伯、钟子云叔叔要去延安,路經晋察冀,他们是有部队护送的。妈妈就把我交给了他们。我骑着毛驴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高伯伯还带着15岁的女儿高凤琴和一个叫小潘的17岁男孩同行。我们三个孩子一路有吃有喝有牲口骑,平安顺利。行军到同蒲铁路一侧,铁道本身及其沿线是日本人控制地区,过铁道就是过封锁线,十分危险。高伯伯对我们三个孩子说:部队被敌人发现了,只能强行通过封锁线,带着我们太危险,已经把我们托付给冀中送孩子去延安的队伍,等部队打过去后再把我们接回来。
午夜,我们随着新的队伍出发了,大的孩子拉着,小的孩子背着,冲刺越过封锁线。记得那位专门带人过封锁线的交通员,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与我年龄相似的男孩,靠近了铁道线,告诉我们一个地址,说如果被敌人打散了就到那集合。我们两个打着瞌睡的孩子根本记不住,急得交通员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松开你们的手。”我瞌睡着,被拖着,小跑着通过了封锁线,什么事都没有。大家放松下来,正觉得平安无事时,听见了身后的枪声,是高伯伯带的队伍与日本人打起来了。第二天冀中送孩子队的队长告诉我们三个,冀东的队伍被打散了,一个人都没过来,我们这群孩子安全过封锁线是日本人有意放过来的,他们集中人员对付冀东的部队。我们三个人也只能跟随这支队伍去延安了。以后的行军就苦了,早上在兵站吃过饭,中午无食,饿得前心贴后心,晚上到了兵站才再有饭吃。而且我们没有牲口骑了,像大人一样一步一步走,一天走一个兵站的距离,怎么也有几十里。我是最没有出息的,常常又累又饿走不动,小潘就向途中遇到的骑着牲口的叔叔阿姨求助,带我一程。一路上我被人抱着,骑过驴、骡、马,甚至骆驼,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走到了黄河岸边。

1945年,吳铁梅(前排左二)在延安枣园参加李克农父亲李哲卿(二排中)七十寿辰纪念留影
正值夏季,浑浊的黄河水波浪翻滚,发出轰鸣,作为孩子的我不觉得它雄伟,只有几分紧张甚至恐惧。要过黄河了,孩子大人登上木船,船老大操着木桨用力划着。船到河心,颠簸得厉害,我紧张得一动也不敢动。忽然一个小男孩惊叫:“船要翻了。”谁知船老大提溜起这个孩子就要往河里扔,亏了队长机警地掏出枪,顶住船夫的头:“你敢扔,我马上枪毙你。”船夫说:“船行至半不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河神听见要翻船的,只有用这个孩子祭神,大家才能平安。”队长说:“你只管划船,如果船要翻,你只要跳水跑,我先毙了你。”枪一直顶在船夫头上,他也只好划船前行。好不容易船靠了岸,队长才收回枪,最后一个跳上岸。后来队长说这些以黄河摆渡为生的老乡都很迷信,他如跳船逃走,我们一船人都要命丧黄河。
我们走到了延安,在中组部大院里,排着队坐在墙根地上,等着谈话。终于叫到了我的名字,进屋看见桌前坐着一位阿姨,是夏之栩。她一本正经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又说:“欢迎到延安来参加革命。”我没听懂,瞪大眼睛看着她。她又说:“你个人有什么志愿?”我还是没听懂。她接着又说:“你愿意学习还是参加工作?”我还是瞪着眼看着她,答不出话来。她急了,一拍桌子大声说:“你到延安来做什么?”这次我听懂了,忙说:“我来找爸爸。”“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吴德。”她听罢仔细观察了我半天,然后哈哈大笑说:“像,真像。”马上打起了电话。我听见她在电话里大声说:“你女儿来了,赶快来接!”便让我在外面等着。很快一个人牵着马喊着:“谁是铁梅?”便把我接到了枣园。在枣园几个叔叔阿姨等着我,告诉我爸爸正在开会,马上就来。海宇阿姨把我领到她屋里给我洗了澡换了衣服。她事后说,当时我头发打着结,脸和手黑乎乎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她怕爸爸看见孩子这样心里难过。干净整齐的我终于见到了熟悉又陌生的爸爸。爸爸心疼地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头,半天都没说出话来。
不久,爸爸送我到延安抗属子弟小学二年级读书,从此我开始了在革命大家庭中成长的经历。
(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