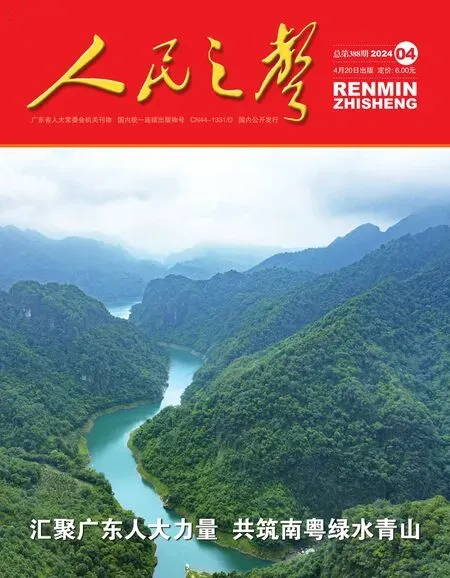三十年未大修 劳动法亟需突破滞后僵局
随着“五·一”劳动节的到来,劳动者权益保护再次引发社会热议。屈指数来,劳动法作为劳动领域的基本法,出台至今已历30年之久,其间除了两次呼应机构改革等情形的技术性修正,从无实质性修改。在立法不断更新升级的时代大势下,劳动法守成不变数10年实属罕见。近年来,要求大修劳动法的呼声正不断高涨,劳动法如何突破滞后僵局,已成为劳动法制建设的紧迫议题。
追溯起来,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立法的系统性构造,正是以1994年出台的劳动法为起点。劳动法不仅确立了劳动权利的具体类型、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也为各项劳动制度奠定了基本框架,成为日后多层次劳动立法不断演进的源头所在,并由此开启了劳动制度日趋法治化的进程。劳动法的历史贡献,堪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然而,劳动法诞生之际,正值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劳动力市场亦发育伊始、开放不足。因而,劳动法尽管扮演了推动改革的法制先锋角色,却难以对改革转轨期的诸多变迁作出全面清晰的预判,这就难免埋下制度设计过于原则、适用范围覆盖不足等先天不足,施行不久即已暴露立法空白、立法冲突等问题。而这种立法滞后性,又伴随着用工方式的日益多元化、劳动关系的日趋复杂化不断加剧。比如,我国劳动法的设计基础和适用对象,是以工厂劳动为模型的典型劳动关系,但近年来蓬勃兴起的平台用工等新就业形态,以及共享用工、远程办公等新工作模式,往往并不具备劳动法所规定的传统劳动关系的全部要素,大批从业者因此游离于劳动法的保护羽翼之外,频频陷入劳动权益受损的困境。
与劳动法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劳动法出台后,职业教育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等劳动领域单行法及相关法相继问世,细化劳动法原则规定的同时,也极大弥补了其立法缺陷,但随着劳动合同法等单行法成为高频适用的主角,本应位居核心地位的劳动法却日渐虚置。另一方面,劳动法经年不修所固化的基础性制度规范,以及相关单行法不得与之抵触的禁忌,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劳动立法的变革,难以解决制度供应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比如,面对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维权难题,目前主要依赖政府指导意见等政策性规范加以应对,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回归更具强制力的法律层面,而这首先取决于劳动法能否突破传统劳动关系的局限。
当下,我国劳动立法已迎来第二轮高潮,劳动合同法等既有法律面临修法调整,劳动基准法、集体合同法等立法短板亦已提上补齐议程。在此进程中,劳动法不应再沉默失语,而是应当尽快启动大修步伐,担负起劳动领域基本法的应尽使命,拆除旧制障碍,开辟创新通道,进而为未来劳动立法提供基础支持和方向导引。
具体而言,劳动法修改应当立足现实变迁,进一步细分劳动关系,明晰认定标准,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保障劳动权利、协调劳动关系、处理劳动争议等各项制度的顶层设计。尤其是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及各类灵活就业劳动者等群体,有必要区分用工类型等要素,设立分类分层的权益保障机制,最大程度地将更多的劳动者纳入劳动立法的保护之列。
除了具体制度构架,劳动法修改还应在宏观层面塑造劳动立法的原则、理念和精神。比如,劳动立法在倾斜保护劳动者与合理平衡劳资利益之间,如何把握恰当的尺度?劳动立法兼容公法与私法、实体与程序规范,如何真正融合成社会法的品质?劳动立法尽力回应当下劳动关系变迁的同时,又该如何为未来的制度创新预留足够的空间等等,都有待劳动法以基本法的姿态,提供清晰的答案和范本。
劳动法能否打破滞后僵局?可资参照的是,1989年出台的环境保护法作为环保领域的基本法,曾因20多年未曾修改而几近废弃,直到2014年大修后才活力复苏,并引领了其后环保立法的深度变革。有理由期待,劳动法也能复制同样的重生之路,再现历史的荣光。说到底,劳动法的修法改造,不仅是保护劳动权益、调谐劳动关系的责任担当,也是完善劳动立法、编纂劳动法典的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而言,劳动法的再出发,既时不我待,更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