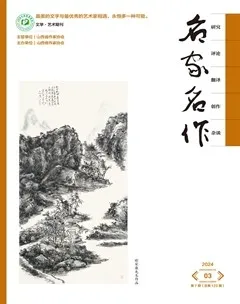明清小说中的砒霜叙事及其文化意义
李仇毅
一、明清小说中砒霜叙事形成的社会背景
纵观砒霜的源流史,知识体系的完备程度决定了大众了解砒霜的广度与深度,这直接影响着从社会生活中借鉴、汲取素材的小说家的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受道教文化的影响与科技水平的限制,砒霜尚未得到正式定名;唐宋时期,大量官修医书和医学实践逐步构建起有关砒霜的科学知识体系,但受众范围较为有限;明清时期,砒霜破“圈”成为“家喻户晓”的毒药。究其原因,一方面可归因为前代的知识发展奠定了传播基础,同时北宋后期对于砒霜毒性的重视也进一步推动了大众认知的转变——由医药转变为毒物,如《政和本草》中记载:“今定砒霜味苦、酸,有大毒是矣。”另一方面,宋代以后的文化与文学发展日趋世俗化、平民化、日常化,信息流通的变革带来了知识传播的便利,这既是砒霜融入文学叙事的物质基础,也为小说家提供了贴合实际的创作内容。[1]
二、明清小说中砒霜叙事涵盖的表现形态
明清小说中的砒霜叙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表现形态,它们因人物使用砒霜的目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表达效果,以跌宕起伏的剧情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
(一)服砒自杀
这类情节以《醒世恒言》第九卷中的陈青和朱氏为代表,因多年恶疾缠身,难以使妻子拥有幸福的生活,陈青心怀愧疚,故心计服砒自杀,而朱氏也因深爱陈青,决心与其同生共死。两人服砒自杀的情节鲜活地刻画出恋人间“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深意切与厚笃羁绊。这样的人物形象取法于中国传统小说中惯于书写的爱情故事,富含着突破封建礼教束缚、忠贞爱情超越生命的叛逆精神。
同时,以砒霜融入此类叙事情节,对原有的故事发展做进一步的创造性点化。下毒后的悲剧性结局最终于人性光辉的升华中得到化解,契合传统儒家思想中两极中和的原则,而此种叙事法则在清代刘熙载的《艺概·文概》中也有所体现:“叙事要有尺寸,有斤两,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砒霜剥夺生命的残忍冷酷以儒学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为皈依,在调和冲突中赋予了文本深刻的艺术张力,也给予读者探索生命意义和追求美好道德的思考。
(二)下砒谋杀
这类情节占明清小说砒霜叙事中的绝大部分。例如《水浒传》中潘金莲、西门庆与王婆合谋毒杀武大;《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欲市砒霜毒母死”;《醒世恒言》中赵完赵寿父子欲借砒霜灭口;《老残游记》中贾大妮子和吴二浪子因被贾魏氏打破说亲,便用“砒霜”害死全家;《醒世姻缘传》中心怀不善、妄图报复的小人吕祥,利用官员宴请的契机下毒菜食等。创作者惯于通过种种情节塑造反面人物形象,或出于家族纠葛、或出于风流多情、或出于自私自利,借助砒霜的毒性实现个体的毒念,人物下场也多以悲惨结局告终,也就印证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儒家思想。潘金莲、西门庆双双被武松手刃;王婆因犯唆使罪在刑场被活剐;“一人”在下毒前即因雷震而亡;赵完赵寿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贾大妮子和吴二浪子被绳之以法;吕祥“夹棍上又敲了一百,重责了四十大板,发驿再徒三年”。此外,这类情节除反面人物的塑造给予读者强烈的道德冲击外,也会树立一个或多个正面形象,以形成鲜明对比。探其缘由,是为了揭示在人性之恶的驱使下,砒霜的毒性给善良之人带去的深重苦难。反道德的行径与造成的后果具有强烈的反差性,使读者进一步反思善恶人性论,获得切实的阅读感受。这类人物主要有《水浒传》中的武松、《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其妻”、《老残游记》中的贾魏氏、《醒世姻缘传》中的李驿丞等。
3.误食砒霜
误食砒霜可以看作是第二类型的衍生,两者的叙事内容具有一致性——反面人物欲借砒霜毒害他人,却不料害死了自己或亲人。误食砒霜不注重从正面突出善恶矛盾,而是将重心放在揭示佛教思想中的因果宿命论上,便于读者在阅读时获得更加深入的情感净化和道德体验,起到警醒和训告的作用。
综上所述,明清小说中的砒霜叙事主要涵盖三种类型,分别是服砒自杀、下砒谋杀、误食砒霜,不仅通过砒霜这一物体媒介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与道德品质,塑造出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也在叙事结构的精巧排布中昭示了明清小说家所继承与延续的儒家思想传统,以及中国叙事原则共同蕴含的对于“致中和”的审美追求和哲学境界,体现着中国传统小说所宣扬的正统观念。
三、明清小说中砒霜叙事发挥的情节作用
明清小说中来源于社会现实的情节,是对日常生活事件的进一步加工,常以清晰、具体的细节为故事的发展牵线。“人生经验和历史事实都只是‘原料’,叙事作品的作者要将它变成‘成品’,就要遵循某种既定的内在规则去操作”,内在规则的落实往往需通过具体的叙事元素去呈现。而明清小说中的砒霜叙事则通过砒霜的使用,关联主要人物,借人物的联系推动情节的发展,使小说的叙事节奏一波三折、起伏跌宕,进一步突出了小说的主旨,显示作者所秉持的道德倾向。以此视角来分析明清小说中的砒霜叙事,体现的叙事结构意义可以分为对情节的过渡功能、收束目的与线索作用。
对于情节的过渡功能包括承接前文的故事脉络与引出后文的发展结局。例如,《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西门庆和王婆知晓武松将要归来,便设下毒计,既承接前文潘金莲见武松英俊高大,顿生邪念,做出许多“奸伪张致”,被武松怒骂一番后,反诬陷武松调戏她,暗含对武松的畏惧、不满与怨愤。“自是老娘晦气了,鸟撞着许多事!”潘金莲的风流也就不言自明。下文写她与西门庆勾搭,心生歹念要除掉丈夫当在情理之中。至郓哥与武大齐力捉奸的情节时,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这些铺垫也终于在“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的叙事中爆发。同时,矛盾尚未解决,故事也并未结束,用砒霜毒死武大,使关键人物武松回归,正义的惩治让恶人的结局大快人心,砒霜引出的一场悲剧终于在“供人头武二郎设祭”的高潮中落下帷幕。全览砒霜下毒武大的叙事情节,前有承合,后接起伏,不仅完整地构成了武松的身世背景,也为后文武松落草为寇、逼上梁山埋下伏笔。砒霜的出现标志着矛盾的爆发与故事的转折,作为关键要素服务情节、推动叙事,承前启后之间彰显矛盾,助推了故事高潮的到来。
对于情节的收束目的多是交代人物的结局,照应上文埋下的伏笔,体现故事暗线的发展。《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中,因为一文钱害死十三个人的情节扣人心弦,令人嗟叹。当案件侦破,高潮回落,罪人都得到应有的惩罚后,挑起事端害死无辜的赵家父子却仍然幸免,这不免引起读者的疑问与不满。为此,作者在书中过渡道:“说话的,我且问你:朱常生心害人,尚然得个丧身亡家之报;那赵完父子活活打死无辜二人,又诬陷了两条性命,他却漏网安享,可见天理原有报不到之处。”果不其然,胜过朱常后,赵家内部便起了分裂,砒霜下毒害人之计最终激化了矛盾,让恶人得以伏法。作为剧毒之物,砒霜背后掩藏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肆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性之恶,直面砒霜带来的死亡恐惧,人的意识会显露出强烈的生存防卫本能,由此暴露了潜藏的恶念与歹行,推动故事完成恶有恶报的结局,密切照应前文最初提及的“一文钱宜警醒”的训告,也对应杨氏妄死却被利用的暗线,交替连接故事脉络,逻辑清晰完整。
砒霜叙事也有贯穿全书,反复出现,作为线索推动情节发展,暗示后文结局,充当情节发展过程中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最典型的即《老残游记》中公堂审理“砒霜”谋杀的奇案一事。故事的起因源于中秋佳节之际,贾氏一家十三口暴毙,只有贾魏氏因为回家省亲而幸免于难,官府派人查看,发现贾氏一家都吃了贾魏氏娘家送来的月饼,而月饼馅里掺有“砒霜”,“砒霜”作为物证引出了案件的开端,也预示着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谋杀。“清官”刚弼枉顾案件中的疑点,将贾魏氏和她的父亲魏谦严刑拷打,主观臆想,胡乱定罪,故而引出了老残写信请得庄宫保派来真正的明吏白子寿侦查此案,白子寿对于掺入“砒霜”的月饼仔细调查,于是有了下段描述:
白公在堂上把那半个破碎月饼,仔细看了,对刚弼道:“圣慕兄,请仔细看看。这月饼馅子是冰糖芝麻核桃仁做的,都是含油性的物件,若是砒霜做在馅子里的,自然同别物粘合一气。你看这砒霜显然是后加入的,与别物绝不粘合。况四美斋供明,只有一种馅子,今日将此两种馅子细看,除加砒外,确系表里皆同。既是一样馅子,别人吃了不死,则贾家之死,不由月饼可知。若是有汤水之物,还可将毒药后加入内;月饼之为物,面皮干硬,断无加入之理。二公以为何如?”俱欠身道:“是。”
明察秋毫的白子寿,发现了真相所在,一场抓捕真凶的追查便在下毒方式明晰后展开,故事的最终结局也以元凶吴二被抓收尾。奇案之所以奇,在于文末揭露毒物并非毒药“砒霜”,而是一种药草“千日醉”,老残等人也在青龙子道长的指点下,让被“毒死”的贾氏十三口起死回生。可以见得,虽然砒霜并非害人的罪魁祸首,但贯穿了整个案件的始终,围绕砒霜的判案过程和侦查事宜十分详尽,串联起了行文脉络,也将人物形象勾勒得真实丰满。
四、明清小说中砒霜叙事彰显的主题功能
仅凭人物塑造与情节概要,无法区分优秀作品和平庸作品。为摆脱为事件本身而叙述的桎梏,需通过所刻画的人物形象、行为动机,描写及议论所构筑的语言,向读者传达深层蕴含的感知力和理解性。正是借助这种品性,基于生活真实所创的虚构事件才得以与感官世界发生联系,它可以是小说家在描绘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时所展现出的洞察力,也可以是作家虚构世界中所寄寓的美好愿景与理想主义。明清小说中的砒霜叙事,既一脉相承传统叙事的情节特征,又立足文本的故事特色,反映了深刻的社会意蕴。透过情节的外在躯壳,通过以人物和事件为主体的血脉,创造出富有生命力和永恒性的主旨,方才彰显了深层的主题功能。
通过叙事情节的逐步发展,我们可以明晰作者的意图逻辑。如上文所述,砒霜叙事多发生在故事的高潮前夕,或是尘埃落定的尾声部分,前者类似《水浒传》中的“淫妇药鸩武大郎”与《警世通言》中的“害人番害自家儿”,后者如《醒世恒言》中的“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与《红楼梦》中的“施毒计金桂自焚身”。作者往往将自己的写作旨趣、叙述思路与承起逻辑隐含其中。读者在阅读至砒霜出现的段落时,会明晰其创作缘由及故事走向,对人物结局也能给出大致猜想,产生与作者共鸣的情感体验。例如,当潘金莲等人借砒霜毒杀武大后,既能扩大读者对反面人物的怨愤与厌恶情绪,也能明了后文将围绕这一矛盾产生激烈的正邪斗争,荡妇淫贼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最终的结局也证实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猜想,悲剧完成了情感净化,情节完成了逻辑闭环。
通过叙事情节的逐渐成熟,我们可以清楚凸显邪善的对立价值。随着知识的演进,砒霜至明清时期成为大众熟知且超脱文化与社会阶层限制的“毒物”,“砒霜知识已经‘转译’成能够被轻易解读的术语,以老鼠药的名义在药铺购买更为一种普遍书写模式,这种互动式的知识传播形塑着毒药的阴暗世界。”砒霜在融入叙事作品后,已然成为邪恶的代名词,这一代表反儒学、反传统、反道德的叙事元素,倘若利用不当,其本身就是剥夺生命之物。心怀不轨的人使用了这种物质,便将其无限妖魔化,展现人物内心深处对欲望极端的毒恶,增强叙事内容的艺术感染力。心地良善的人使用了这种物质,便打破了尊重生命的传统价值观,将打碎一地的良善与残忍冷酷的邪恶进行了深刻对比,凸显了善与恶背后深层的道德内涵。幸得这样的结局往往是以邪恶势力的失败告终,或是善良之人成功得救而收尾,契合明清小说家所秉持的“惩劝教化”的儒家思想。正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为善去恶,化砒霜的毒恶为人性最终的善意,这才是小说家利用其叙事特征对主题的升华功能和价值指向。
五、结束语
明清小说中的砒霜叙事利用砒霜的剧毒品性,对传统叙事中的细节描摹、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都有着重要作用,凸显了善恶对立的价值观念和主旨意图的伦理思想。但值得深思的是,作为道教炼丹文化和中医药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家又是否能够挖掘砒霜治病救人的良善一面,着重刻画砒霜的价值,一改其妖魔化的“凶兽”面貌,树立以砒霜叙事为代表,具有中国特色,集宗教、医学、文学等特征为一体的综合知识谱系,从而传承更为自信的文化脉络与历史根基,这是砒霜叙事现代转型的重要文化意义,也是利用文学特色所能传递的更广阔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