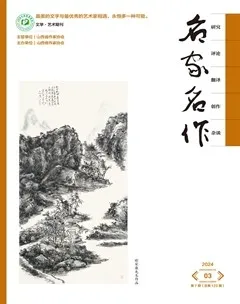倚天万里须长剑:唐诗宋词中剑意象之嬗变
王志颖
“物皆着我之色彩”,当圹埌的刀光剑影与葳蕤繁祉的唐宋文明邂逅时,意象本身便坐拥了多元灵动的涵蕴。剑常被文人用于表达繁复矛盾的精神追求,或“倚天万里须长剑”的豪情侠气,或“醉里挑灯看剑”的惆怅失意,或“弓背霞明剑照霜”的家国情思。整体看来,剑作为唐诗宋词中的常见意象,既有礼仪表达的形式,又兼具了托物言志的功能,蕴含作者内在精神底色与外在理想追求的统一、交错和挣扎。剑在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宋词中的意象嬗变有着举足轻重的研究意义。经由探析这一意象,可进一步体悟唐宋诗词大家行云流水般的艺术技巧,探寻文人墨客经由笔墨的刀光剑影抵达的幽微澎湃之境界。
一、文学意象与剑意象的概念界定
“意象”这一元素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丰盈情思的具象灵魂,它是“意”与“象”两个概念的融合。所谓“意”是指人的内心情感与意念,而“象”则是指这些情感与意念借以表达的外在物象。在文学中,“意象”是指那些具有斑驳情感色彩和象征意义的种种形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及“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象的雕琢与构筑可谓是行文笔酣墨饱的中流砥柱。
剑在文学作品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首先,剑作为一种武器,有着锋利的刃和坚硬的外壳。这些特点使剑逐渐成为一种象征,它可以代表勇气、力量和战斗精神。在唐诗宋词中,剑常被用来展现英雄豪杰的气概,如李白《行路难》中写道:“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这里的“拔剑四顾”是李白原有的豪情壮志和如今内心苦闷情绪的矛盾冲突。其次,剑也是一种高雅的饰品。在古代社会,剑被视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唐诗宋词中,文人雅士就常佩带宝剑,以此来展现自己的身份地位。在与友人惜别时,一些文人会将宝剑作为礼物赠送友人,如“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就是“寄情于剑”的写照。最后,剑在古代文化中也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在传统观念中,剑常被视为一种可以辟邪驱鬼的神秘武器。例如,苏东坡曾写道:“我家铜剑如赤蛇,君家石砚苍璧椭而洼。”这种“以铜剑换石砚”的仪式不仅是诗人“尔雅笺虫虾”高洁理想的真挚抒写,也显露了剑在民俗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十六峰长剑在,星斗气,郁峥嵘。刀光剑影下兴发的少年意气、家国情怀或惆怅失意等浩渺情思是江月年年望相似的古来共谈,但当它们坐落在华夏古典文明的盛夏和深秋时节,便独具匠心地显露着肝肠寸断的张扬或悲壮。
二、唐诗宋词中剑意象的类别
(一)剑
女皇武则天完善科举、确立武举制度,盛世之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喜悦蔚然成风。“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的多元取士制度让天下能者各美其美。由此,刀光剑影与诗词歌赋璀璨碰撞,觥筹交错间剑与诗词更至佳境。唐诗宋词中的剑常被用来象征战斗和勇武,通过描绘剑的锋利、寒光等特征,抒写剑的凛然威力和金鼓齐鸣的战斗氛围。李贺的《雁门太守行》中写道:“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里的剑是战斗的象征,表达了将士们护国佑民的决心和勇气;又如,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经由剑也显露了词人的壮志豪情。
(二)佩剑
佩剑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可用来表达佩剑者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追求高洁品性的凛然正气。如晚唐诗人温庭筠在《苏武庙》中曾提及苏武于丁年冠剑:“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古人对于男子佩剑的年龄有着严格的规定,佩剑即是代表着社会身份的成立。
(三)舞剑与剑术
舞剑与剑术均是修养身性的技艺,在唐诗宋词中,不乏描绘舞剑者或剑术高手的英勇气概、高超技艺、高洁品性。例如,杜甫曾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写道:“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勾勒出一个灵动飘逸的舞剑者的形象,大诗人的倾慕之情于字句间曲尽其妙。
三、唐诗宋词中剑意象的发展嬗变
(一)礼仪与道德之剑
剑,在古代中国既是武器也是礼器。在忠信礼义方面,剑始终扮演着虎虎生风的铿锵角色。唐诗宋词中,剑的意象仍一以贯之地被赋予忠肝义胆、大气凛然之底色。
1.仁义之剑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核心思想之一,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关爱和尊重。在唐诗宋词中,剑被赋予仁义的含义,代表对他人的尊重和关爱。如李白曾写道:“少年解长剑,投赠即分离。”这里的剑承载着李白与友人深厚且真挚的友爱与仁义之情。人生相知相识,恍惚如杏花遇雨、浊酒遇歌。
2.忠贞之剑
忠诚是古典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气节品性。唐诗宋词中,剑也常被赋予忠贞的含义,代表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的忠诚和矢志不渝的信仰,展现为“士为知己者死”的一片丹心。在“仗剑行千里,微躯敢一言。曾为大梁客,不负信陵恩”中,作者以侠客自喻,抒发自己对信陵君知遇之恩的感激,以及随时可为此赴死的一片赤诚。白居易诗云:“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这里也鞭辟入里地阐明了剑的使用应是基于赤胆忠心的远大抱负,而非汲汲营营的私人恩怨。文天祥曾写道:“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这里的剑寄托了词人以身许国的碧血丹心,象征着对风雨飘摇的国度和民族的深沉关切。
(二)身份与权力之剑
1.身份辨识之剑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生活中,剑常被视作一种礼仪的象征。不同阶层的人使用剑的材质、形状和装饰有所不同,以此来彰显其身份和地位。这不仅烙印在金玉其外的物质层面,也镌刻着钟灵毓秀的品性和底色。早在春秋时期,剑就被视为高雅、尊贵的象征。剑的形态大都修长正直,昭示着浩然正气、端庄正直。入鞘时方朴无华,出鞘后锋芒展露,此与君子无事时平和谦逊、遇事时勇敢有为的品性相得益彰。持剑者通常被认为具有高洁的品质和修养。这种观念在古典文化中蔚然成风,使剑成为一种身份认同的标志。“冠剑朝凤阙,楼船侍龙池”“高冠配雄剑,长揖韩荆州”,这些诗句都能有力地佐证。
2.荣耀权势之剑
在古代中国,剑也被视为权威和荣耀的象征。如皇帝的剑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统治地位,不仅是绝对权力的显现,更是国家葳蕤繁祉的象征。在唐诗宋词中,有关皇帝的剑的描写,典型的例子如李白的《塞下曲》:“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君主的剑鞘亦是绝对皇权下翻云覆雨、生杀予夺的臣服。
除了皇帝的剑,一些官员和贵族也有自己的剑。这些剑通常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代表着持有者的权力和地位。例如,官员的剑通常是由贵重的金属制成,配有华丽的装饰,以彰显其地位和权力、荣耀和尊严。“长剑既照耀,高冠何赩赫”,佩剑已经成为达官贵人阶层认同的文化产物。
(三)托物言志之剑
1.凌云豪情之剑(从侠义情怀、英雄风范到武士壮志)
凌云豪情之剑,充满豪迈壮志和英雄侠气的浩然风韵。这种剑不仅代表着诗人的豪情壮志和侠义情怀,也是他们少年意气与凌云壮志的理想抒发。这种“仗剑行千里”的意脉往往兴发于朝气蓬勃的青春年岁或欣欣向荣、如日中升的时代。唐宋政局稳定、海晏河清,是古典文明中最葳蕤的史诗。以剑来书写自己的壮志豪情和少年意气的诗词自然不胜枚举。
正如鸿雁这一意象之于宿命般的旅程者苏东坡,剑这一意象与太白和稼轩也产生了一生的羁绊。先是梦想仗剑天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之剑,少年意气是“秋霜切玉剑”“跨海斩长鲸”的梦想之剑、“直为斩楼兰”的丹心报国之剑;“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则是不平则鸣之剑。而《将进酒》一诗,剑这一意象精妙地被诗仙雕琢出新意。“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由剑这一意象着手,太白描绘了自己面临人生困境的苦闷心情。人生的马拉松道阻且长,但若有机遇的青睐,他仍坚信自己能够建功立业、名垂青史。他以剑为伴,追求着一种超脱世俗的自由豪迈的仙侠气韵。这种昂扬的精神追求,不仅是自我被放逐于悬崖边时荡气回肠的低吟浅唱,也与多元灵动的中华文明中的凛然风骨和铮铮气韵不期而遇。
在李峤《剑》一诗中,剑的意象也成为他书写赤诚豪情的灵魂支点。“我有昆吾剑,求趋夫子庭。白虹时切玉,紫气夜干星。锷上芙蓉动,匣中霜雪明。倚天持报国,画地取雄名。”他将自己的剑喻为昆吾剑,直抒英雄主义的人生理想。手持利剑,赤胆忠心、尽忠报国,意欲在如椽巨笔的史册中留下英名。这首诗取自李峤的《宝剑篇》,全诗共一百五十二字,较长的篇幅显现出唐代诗人对于剑这一文学意象的热爱。“一剑曾当百万师”“一剑霜寒十四州”“一舞剑器动四方”“万里只携孤剑去”等诗影中都能窥见大唐对剑意象的偏爱。
2.失意悲愤之剑(从怀才不遇到国恨家仇)
青山依旧在,夕阳几度红。盛极必衰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朝代更替、风雨飘摇等诗人之不幸往往酿造出诗家之大幸的盛宴。剑意象剑昭示着少年意气、凌云壮志的同时必然承载着失意悲愤,常被用来表达诗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郁郁和悲愤。挥不出的刀剑,经由纸笔化为无形利器,抒发出诗人内心的怅惘和愤懑。
如唐代诗人贾岛的《剑客》一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诗中的剑经过十年磨砺,却仍未有机会一试锋芒,这正是诗人自身遭遇的写照。经由剑的锋利和冷峻,诗人对身处境地和悲凉际遇的愤慨呼之欲出。
又如,稼轩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词:“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词人与剑一生羁绊,此生谁料“倚天万里须长剑”的碧血丹心最后沦落至“醉里挑灯看剑”“无人会、登临意”的深沉苦痛。他对风雨飘摇的民族深沉的忧虑关切,他无法消解的愁苦寂寥,尘暗旧貂裘,似乎只有这把旧剑懂他的收复故土之梦。
3.虚实相生,悲喜交集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纵然有开元盛世一朝繁华,仍难敌“历史”这如椽巨笔瞬息万状。剑作为一种承载家国天下的实指之物,在词中承载独特的人物记忆和宏阔的文学叙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醉梦里挑亮油灯,稼轩恍惚又回到当年势如破竹、气吞万里如虎的沙场。剑这一意象在他的诗词中是真实的情思,生命体验和实指之物。《济南府志》记载,辛弃疾在弥留之际仍大呼:“杀贼!杀贼!”他仍渴望光复故土,畅想“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 (《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 。
同时,剑亦为虚指之剑,即为心中意气之剑:有感而发,不平则鸣。剑意象中蕴藉的风雨飘摇、山河沦落之实激荡起国破与复国之间的情感落差。“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英雄未老,剑气已横秋。他心中有剑,手中有剑,遥想“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却离战场越来越远。与山水草木对饮,踽踽独行、独自舞剑,这是稼轩南渡之后的现实境况。“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剑意象经由稼轩词中实指与虚指的流动与嬗变将他一生的意气辽阔和郁郁不得道尽了。无人会,登临意。
总之,这些诗词中的剑意象酣畅地书写了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他们以剑喻志,不平则鸣,用悲愤的笔触描绘出自己的人生境遇和情感体验,通过发泄深沉的郁郁不得和报国无门,书写了时代与自我的放逐。通过体悟这些托物言志之剑,我们能更好抵达古代文人墨客匍匐在时代的洪流和个人命运之下的心绪和情思。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人的情思色彩经由托物言志之剑呈现出斑斓的意脉,诗词笔墨与刀光剑影相会,必然是酣畅淋漓。或为民请命、凌云意气,或浩然正气、肝肠豪情,都痛得高兴、落得尽兴。徜徉在唐诗宋词这片璀错的银河中,仍能显露出儒雅的倔强英气,不平则鸣,动人心魄。
综上所述,经由唐诗宋词中仁义之剑、忠贞之剑、身份辨识之剑、荣耀权势之剑、斗争角逐之剑、失意悲愤之剑、凌云豪情之剑等多种意蕴载体,再由礼仪文化到寄情惜别,由凌云侠气到怅然失意,或“一剑霜寒十四州”的动人心魄,或“剑气已横秋”的失意忧愁,或“秋霜切玉剑”的少年意气,或“弓背霞明照剑霜”的缱绻,剑的意蕴披上文人的情思摇曳在古典文明的盛夏和金秋时节,承前启后,生生不息。比起意脉如何流淌,更扣人心弦的其实是,挥出的剑指向风雨飘摇的国度,挥不出的剑仿若无形利器,刺向失意者深沉的未酬之志。于刀剑凛冽的寒光中,华夏民族昂首阔步地走向更加光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