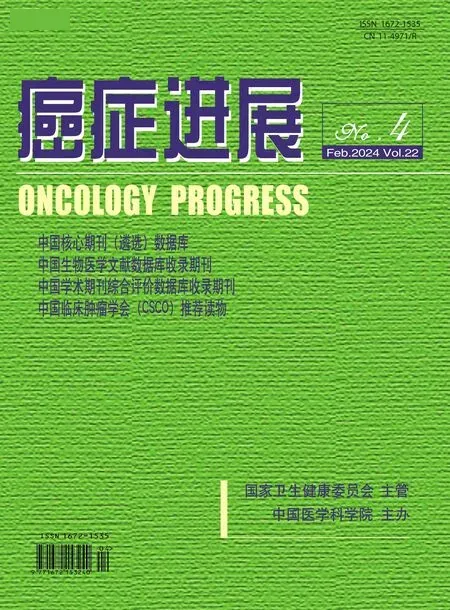口腔鳞状细胞癌耐药的表观遗传学调控研究进展△
严心悦,王雅梅
首都医科大学12022 级口腔医学“5+3”一体化专业,2 基础医学院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系,北京 100069
口腔鳞状细胞癌(or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OSCC)是发生于口腔中舌、口底、颊、唇以及牙龈等部位黏膜层,以鳞状上皮细胞为主的恶性肿瘤,发生例数占口腔癌的90%以上。依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6 年全国统计数据,中国OSCC 新增患者约21.1 万,是中国第二十大肿瘤[1]。虽然口腔肿瘤临床诊断较容易,由于患者就诊时大多已处于晚期且治疗效果受获得性耐药的严重制约,OSCC 患者的5 年生存率仅为50%~60%,其疗效的提升一直是临床难点之一。目前,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是临床OSCC 的主要治疗方式。分子靶向药物的出现使得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得到明显提高,药物治疗在肿瘤治疗策略中占比随之增大,耐药对药物治疗效果的影响也更为关键[2]。化疗药物通过DNA 损伤、促进细胞凋亡等方式杀灭肿瘤细胞,而表观遗传修饰可通过影响靶向通路中相关基因的表达削弱或增强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即影响肿瘤对药物的敏感性。由于表观遗传学的易受干扰性与可逆性,人为干预可改变表观遗传学修饰从而实现肿瘤耐药的逆转。因此,了解OSCC 耐药的表观遗传学调控分子机制,可以为寻找潜在的诊断标志物和有效的治疗靶点提供新策略,对提高OSCC 患者临床治愈率和总生存率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综述DNA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ncRNA)、染色质重塑对OSCC 耐药的表观遗传学调控机制研究进展,以期为OSCC 耐药抵抗研究提供参考。
1 DNA 甲基化异常与OSCC 耐药
DNA 甲基化是在DNA 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DNMT)的催化下,甲基共价加成到CpG 岛的胞嘧啶环,阻止转录从而抑制基因的表达,而DNA 去甲基化则可恢复基因表达。OSCC 耐药是由于药物作用通路中关键基因的异常甲基化导致表达异常,从而减弱通路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较为常见的有DNA 损伤修复基因与促凋亡基因的高度甲基化,可使凋亡通路难以激活,药物转运基因与肿瘤干细胞标志基因的低甲基化可降低细胞内药物浓度和敏感性。全基因组甲基化水平改变也能影响肿瘤细胞的耐药性,但机制至今尚未清楚[3]。
DNA 甲基化引起的OSCC 耐药中,细胞凋亡通路是抗耐药治疗的一大靶点,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并促进其凋亡的脆性组氨酸三联体二腺苷三磷酸酶(fragile histidine triad diadenosine triphosphatase,FHIT)高甲基化后,OSCC 细胞对化疗失去敏感性[4]。促细胞凋亡调控因子B 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 相关X 蛋白(B cell lymphoma/leukemia-2-associated X protein,BAX)也在OSCC 的发展及耐药过程中表达下调,其基因的改变、超甲基化及通过对p53/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PKB,又称AKT)通路的调控,均对疾病进展和耐药过程起重要作用[5]。Yes 相关蛋白(Yes-associated protein,YAP)同样也能够通过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肿瘤细胞耐药,耐顺铂的OSCC 细胞系在YAP基因敲除后重新显示对顺铂的敏感性[6],可以推测YAP基因的转录与表观遗传调控因子表达可能作为逆转耐药的靶点[7]。靶向药物转运体的耐药调控基因,如ATP 结合盒亚家族A 成员2(ATP binding cassette subfamily A member 2,ABCA2)及其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tide polymorphism,SNP),与将药物隔离于溶酶体从而降低细胞内药物浓度过程相关,但具体机制尚不清楚[8]。脂载蛋白2(lipocalin 2,LCN2)过表达同样在耐药机制中产生促进作用,而维生素D可以通过增强LCN2甲基化从而抑制其表达,增强肿瘤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9]。不仅是核DNA,作为顺铂主要靶点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 DNA,mtDNA)甲基化改变也可能影响OSCC对顺铂的反应性。细胞色素c 氧化酶亚基Ⅰ(cytochrome c oxidaseⅠ,COX1)和细胞色素b(cytochrome b,CYTB)基因已经在顺铂耐药细胞系mtDNA 中被检测到高甲基化,但甲基化改变致使耐药的机制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10]。
2 ncRNA 与OSCC 耐药
在ncRNA 对OSCC 耐药性的影响中,微小RNA(microRNA,miRNA)最为主要,其通过两个途径调节肿瘤耐药:直接参与生物蛋白与大分子的代谢和通过与目标信使RNA(messenger RNA,mRNA)的3'-非翻译区(3'-untranslated region,3'-UTR)互补结合来下调基因表达[11-12],从而干涉跨膜转运蛋白、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DNA 损伤修复、自噬等药物治疗中的关键步骤。而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大多通过海绵化或直接调控miRNA 的表达及作用参与OSCC 的耐药,此外还能通过直接识别药物转运蛋白和调控自噬基因表达途径调节肿瘤耐药[13]。环状RNA(circular RNA,circRNA)在OSCC 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其对耐药的调控机制还需要深入研究[14]。
miRNA 可以通过影响信号通路来影响OSCC耐药性,如miRNA-365-3p 通过抑制ETS 同源因子(ETS homologous factor,EHF)/角蛋白16(keratin 16,KRT16)/β5-整合素/细胞间充质-上皮转换因子(cellular-mesenchymal to epithelial transition factor,c-MET)信号转导调节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耐药性[15];miRNA-654-5p 通过生长因子受体结合蛋白2 相关衔接蛋白(growth factor receptor bound protein 2 related adaptor protein,GRAP)介导的RAS/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通路促进OSCC 对顺铂和5-FU 的耐药性[16]。miRNA 还可以通过直接干预基因的表达影响OSCC 耐药性:OSCC 细胞外泌体中的miRNA-21通过调节磷酸酶张力蛋白同源物(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PTEN)基因和程序性死亡受体4(programmed cell death 4,PDCD4)基因的表达诱导顺铂耐药[17];miRNA-22直接通过下调赖氨酸乙酰转移酶6B(lysine acetyltransferase 6B,KAT6B)基因的mRNA抑制其表达进而增加舌癌细胞对平阳霉素的敏感性;miRNA-24、miRNA-23a、miRNA-181a、miRNA-15b、miRNA-21 等miRNA 也都与舌癌顺铂耐药机制相关[18-22]。在细胞凋亡受阻引起的耐药中,piwi-交互RNA(piwi-interacting RNA,piR)-1037 可通过抑制OSCC 细胞凋亡而增强其对顺铂的耐药性;相反,piR-39980 诱导细胞内多柔比星积累、DNA 损伤和细胞凋亡,从而增加纤维肉瘤对多柔比星的敏感性[23]。而在内质网应激引起的耐药中,miRNA-340-5p 靶向内质网应激转录因子6(activat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6,ATF6)和PRKR 样内质网激酶(PRKR-like endoplasmic reticulum kinase,PERK)影响OSCC 细胞的增殖和耐药[24]。肿瘤干细胞(cancer stem cell,CSC)在化疗耐药、复发、转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CSC 的存在是OSCC 转移、复发和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lncRNA 同形盒A10 反义RNA(homeobox A10 antisense RNA,HOXA10-AS)可以通过miRNA-29a/髓细胞白血病序列1(myeloid cell leukemia-1,MCL-1)/磷脂酰肌醇3 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AKT 轴增强OSCC 中CSC 的干细胞特性[25]。EMT 导致耐药的机制已有报道,lncRNA 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改变EMT 程序来促进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耐药[26]。针对lncRNA 对OSCC 耐药的影响,CRISPR-Cas9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可靶向lncRNA 进行精准编辑的基因编辑技术,在OSCC 耐药中的作用正在被研究[27]。
3 组蛋白修饰与OSCC 耐药
参与OSCC 耐药的组蛋白修饰主要包括由组蛋白乙酰转移酶(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HAT)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HDAC)介导的乙酰化,组蛋白甲基转移酶(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HMT)、组蛋白去甲基化酶(lysine-specific demethylase,LSD)和包含jumonji 结构域(jumonji domain containing,JMJD)家族介导的甲基化。乙酰化与甲基化通过调控相关基因表达、自噬、EMT 和分子代谢等过程调节耐药。值得注意的是,HAT 大多促进肿瘤耐药,但其作为靶点的抑制剂还没有应用到临床治疗中[28]。
HDAC 的积累被证明与肿瘤相关,其抑制剂对耐药抵抗有很大的开发潜能,临床上也已经有较多研究应用。Tavares 等[29]对HDAC6 在口腔癌CSC 介导的化疗耐药研究中发现,在顺铂耐药细胞系和CSC 细胞系中都出现了HDAC6 的积累、DNA 损伤和过氧化物还原酶2(peroxiredoxin 2,PRDX2)表达升高,而HDAC6 抑制剂tubastatin A可增加氧化效应、修复DNA 损伤并下调PRDX2 的表达,诱导细胞凋亡。Liang 等[30]研究发现,4SC-202(一种新的选择性Ⅰ类HDAC 抑制剂)通过干涉miRNA-429/miRNA-1181 介导的mRNA 降解来抑制转录因子性别决定区Y-盒转录因子2(sex determining region Y-box transcription factor 2,SOX2)的表达,从而降低OSCC 的耐药性,且联合治疗效果显著。抑制肿瘤DNA 修复过程的药物如多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ADP-ribose)polymerase,PARP]家族抑制剂也是研究焦点,然而OSCC 对PARP 抑制剂耐药性的机制至今未被完全解释清楚。现有的耐药机制提出,可能是组蛋白乙酰转移酶p300/CBP 相关因子(p300/CBP-associated factor,PCAF)缺失导致复制叉稳定阻碍了细胞死亡,组蛋白的多聚ADP-核糖基化修饰等也通过染色质重塑对肿瘤耐药产生了影响[31]。针对PARP抑制剂的耐药情况,联合使用对染色质修饰蛋白有影响的强效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如溴化结构域蛋白抑制剂JQ1、PARP 抑制剂奥拉帕尼,能够增强细胞对PARP抑制剂的敏感性,提高治疗效果[32]。除单独作用影响外,组蛋白修饰还可以通过与DNA甲基化共同影响染色质状态来干预人乳头瘤病毒相关口咽鳞状细胞癌转录后剪接,同时HAT 如Spt-Ada-Gcn5 乙酰转移酶(Spt-Ada-Gcn5 acetyltransferase,SAGA)可招募并与剪接机制相互作用,影响了耐药的产生[33]。对于影响组蛋白修饰的病理因素,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的酸中毒和缺氧可能影响组蛋白的甲基化和乙酰化,间接促进OSCC 耐药的发生[34]。
4 染色质重塑与OSCC 耐药
染色质重塑是指酵母交配型转换(mating type switching,SWI)/蔗糖不发酵(sucrose non-fermenting,SNF)、模仿开关复合物(imitation switch,ISWI)、染色体结构域解旋酶DNA 结合蛋白(chromodomain helicase DNA binding protein,CHD)和肌醇营养缺陷型80 复合体等染色质重塑复合物调控染色质结构发生变化。重塑复合物各亚基、重塑因子的相关编码基因的异常通过影响染色质结构而使转录、DNA 复制、DNA 损伤修复等基础细胞生理过程混乱,从而影响肿瘤的发展与耐药[35]。除直接干涉DNA 的信息传递外,染色质重塑还能够通过影响DNA 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间接调控耐药的发生与抵抗过程。
染色质重塑物编码基因的状态与表达可以作为肿瘤治疗以及耐药的靶点。有研究发现,编码SWI/SNF 染色质重塑物BRG-/BRM 相关因子(BRG-/BRM-associated factor,BAF)亚基的肌动蛋白样6A 基因(actin like 6A,ACTL6A)在许多鳞状细胞癌的发展中被扩增,ACTL6A的过度扩增增加了其在BAF 复合物中的正常不饱和占用,增加了多梳对抗,激活鳞状细胞癌基因。这说明改变染色质调节复合体内的亚基化学剂量可以致癌,提示可以适当减少ACTL6A 的表达作为治疗手段。而ACTL6A中编码两个相邻疏水氨基酸序列的突变使得TEA 结构域转录因子(TEA domain transcription factor,TEAD)/YAP 复合物之间结合增强,使得多梳再分配,促进了鳞状细胞癌的生长,这为OSCC 的治疗发现了一个新靶点[36]。相比于正常组织,染色质重塑因子1(remodeling and spacing factor 1,RSF1)蛋白在OSCC 中表达升高,且其表达与组织病理学分级、临床分期与淋巴结转移有关,提示RSF1 的表达与OSCC 的发展与转归可能有密切联系[37]。其他染色质重塑物编码基因如赖氨酸甲基转移酶(lysine methyltransferase 2D,KMT2D)和核受体结合SET 结构域蛋白1(nuclear receptor binding SET domain protein 1,NSD1)表达的改变也分别与头颈部鳞状细胞癌对极光激酶抑制剂的敏感性和广泛的基因组低甲基化密切相关[38-39]。除重塑物编码基因外,核心调控因子如ΔNp63α也能够通过与酶或其他调节因子的相互作用间接改变染色质状态,从而影响耐药发展过程。ΔNp63α因子协调染色质重塑酶、组织特异性增强子景观和染色质的三维高阶结构,并通过与表观遗传调节剂的相互作用来影响染色质可及性[40],增强或抑制转录;还能与Snf2 相关CREBBP激活蛋白(Snf2 related CREBBP activator protein,SRCAP)、DNA 甲基转移酶1 相关蛋白1(DNA methyltransferase 1 associated protein 1,DMAP1)、RuvB 样蛋白1(RuvB like AAA ATPase 1,RUVBL1)、RuvB 样蛋白2(RuvB like AAA ATPase 2,RUVBL2)和ACTL6A 发生物理性相互作用并募集[41],成为SCC 治疗的一个潜在靶点。
5 小结与展望
比较而言,DNA 甲基化对OSCC 耐药的影响大多是通过凋亡通路与药物转运途径来实现,在CSC 标志表达上也有影响;ncRNA 影响范围则更广,涉及凋亡、内质网应激、CSC、EMT 等;组蛋白修饰中HDAC 靶点在临床应用较多,凋亡及DNA损伤修复过程为主要调控对象;染色质重塑在OSCC 耐药方面的机制尚未完全清晰,主要通过重塑复合物及调控因子的表达状态影响染色质可及性来促进耐药。此外,RNA 修饰在OSCC 耐药中作用的研究近年来不断深入,其中针对m6A RNA 在耐药相关信号通路中的作用以及对其甲基化与去甲基化的调控也是研究热点[42-43]。
表观遗传学机制对肿瘤耐药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各个机制间相互影响,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由于机制的复杂性,联合治疗效果更为显著,例如研究较多的JQ1 与PI3K 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Pembrolizumab)和HDAC 抑制剂伏立诺他(Vorinostat)等[44]。相对传统以手术为主,放疗、化疗为辅的OSCC 治疗方式,联合治疗可能达到协同效应并延长耐药反应时间,大大提高疗效。除此之外,绘制患者基因组和表观基因组图谱并给予针对性的表观遗传治疗也更能满足肿瘤治疗量身订制的需求,但对表观遗传因子研究的缺少和外源性药物的脱靶使表观遗传药物的应用仍具挑战性[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