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论争的起因
谢地坤 高继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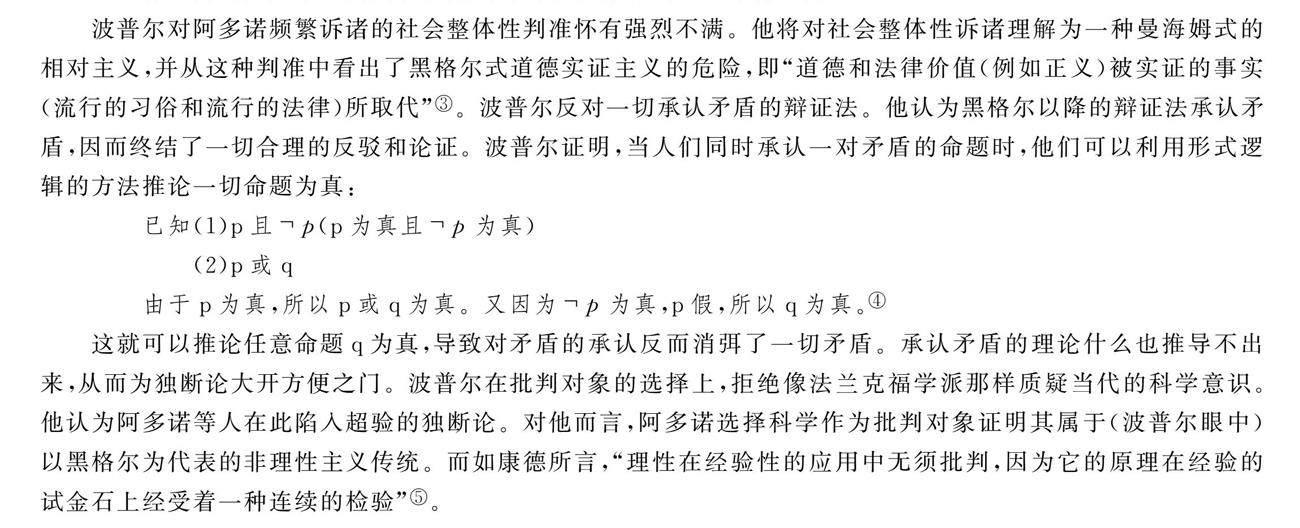
摘要:学界关于“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论争”的起因长期以来都存在误解。批判理性主义者认为实证主义论争的起因是哈贝马斯对波普尔的理论攻击,但波普尔与阿多诺之间本无实质分歧。达伦道夫意识到了波普尔和阿多诺之间的分歧,但将其理解为一种康德式立场和黑格尔式立场之间的冲突。根据对论争文本的考察可知,上述两种观点都是成问题的,图宾根会议上波普尔和阿多诺之间的分歧就是实证主义论争的起因,这从本质上表现了批判理论和批判理性主义对康德批判哲学的不同理解。
关键词:批判哲学;实证主义论争;波普尔;阿多诺;图宾根会议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4.0207
收稿日期:2023-06-09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地坤,男,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欧洲大陆哲学,E-mail: 13001265298@163.com;
高继鑫,男,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实证主义论争(Der Positivismusstreit)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其发端于波普尔(Karl Popper)与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1961年德国社会学会的图宾根会议上进行的关于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的会谈。这场论争一方面促使阿尔伯特(Hans Albert)发展了一种对先验诠释学的系统批判;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转向一种交往行动理论,深刻改变了当代德国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思想格局。然而关于这场论争的起因却存在一些流行的误解。这些误解要么否认图宾根会议上分歧的存在,要么误解了分歧的实质。本文试图揭示“波普尔-阿多诺之争”的实质,并驳斥研究文献中存在的种种误解。波普尔和阿多诺在会上确实存在关于批判概念的实质分歧。这代表着康德批判哲学传统的内部分裂。这种分裂虽然意味着康德一劳永逸解决哲学分歧的努力归于失败,但这并不意味着批判哲学传统的失败。相反,正是由于分歧,才使批判成为可能。
一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依据对“波普尔-阿多诺之争”的界定的不同,相关文献可大致区分为四类。第一类文献体现了批判理性主义者的立场,以波普尔、阿尔伯特、科伊特、内克【Hans Albert, “Karl Popper, Critical Rationalism, and the Positivist Dispute,”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5, no. 2 (May 2015): 214; Herbert Keuth,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A Scientific or a Political Controversy?,”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5, no.2 (May 2015): 157; Reinhard Neck, “The Positivist Dispute after 50 Years - An Unrepentant‘Positivist View,”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5, no.2 (May 2015): 186-187.其中,科伊特确实简要讨论了阿多诺的文本,但他只看到了所谓的政治计划(political program),完全无视其中有关批判哲学的认识论争议。】等人为代表。该误解主张阿多诺和波普尔当时并未产生实质分歧,因为他们并未就波普尔的27个论题展开真正的讨论,只是由于哈贝马斯1963年的《科学的分析理论与辩证法》一文攻击波普尔是实证主义者【Jürgen Habermas, “Analyt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Dialektik,”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Neuwied: Sammlung Luchterhand, 1972), 155.】才引發了后续论争。这导致他们在回顾实证主义论争时往往忽视阿多诺。其研究由于对双方分歧认识不足,往往流于一种基于政治立场的谩骂。后三类文献都承认分歧的存在,但对其界定不同。第二类文献的立场以达伦道夫为代表,他认为波普尔和阿多诺之间的一致是一种假象【Ralf Darendorf, “Anmerkungen zur Diskussio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46.】。他将分歧理解为康德批判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分歧【Ralf Darendorf, “Anmerkungen zur Diskussio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47.】。第三类文献以哈贝马斯、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Seabury Press,1974), 18-21,52-53.】等批判理论的拥趸和同盟为代表。他们将“波普尔-阿多诺之争”理解为一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的斗争。其界定大体准确,但并未点出论争同康德批判哲学的内在联系。第四类文献代表一种历史分析立场。其代表人物有弗里斯比【David Frisby,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trans. Galen Adey, David Frisby (London: Heinemann, 1976), xv-xxvii.】、达姆斯【Hans-Joachim Dahms, “Die Vorgeschichte des Positivismus-Streits:von der Kooperation zur Konfrontation.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Frankfurter Schule und Wiener Kreis 1936-1942,” in Jahrbuch für Soziologiegeschichte 1990, eds. Heinz-Jürgen Dahme et al. (Opladen: Leske+Budrich, 1990), 9-65.】、施特鲁本霍夫【Marius Strubenhoff, “The Positivism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1954-1970,”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44, no.2 (2018): 260-276.】。他们将此论争放在德国社会理论的论争史中加以考察。他们指出了实证主义论争同先前论争的密切联系,但对其特殊性研究得不够。施特鲁本霍夫用20世纪50年代德国社会学会内部实证社会学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斗争来说明波普尔和阿多诺之间的奇特友好氛围,但其解释更适合说明达伦道夫邀请波普尔作报告的动机,而难以解释波普尔与阿多诺之间的表面一致。因为按他的意见,达伦道夫邀请波普尔来做实证社会学的奥援,但实际情况是波普尔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实证社会学【Marius Strubenhoff, “The Positivism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1954-1970,” 261,265.】。他们未能发现这场论争的关键在于批判概念。
二 波普尔与阿多诺的相互误解
波普尔与阿多诺之争长期以来被误解所遮蔽。双方都误解了对方的主要论点。波普尔甚至完全未意识到阿多诺在图宾根会议上对其论题提出了当面批评。波普尔后来回忆道,“阿多诺的回应读起来很有力量,但他几乎没有接过我的挑战——亦即我的27个论题”【Karl R. Popper, “Reason or Revolu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no.2 (2015): 289.】。而在其1984年为《社会科学的逻辑》补充的注释中,波普尔又说:“我应使我的报告向一场争论开放。阿多诺教授受邀在其补充报告中继续这场争论,而他在补充报告中基本与我的观点一致。”【Karl R. Popp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besseren Welt: Vortrge und Autstze aus dreiβig Jahren (München: Piper,1999), 115.】这一点也有似是而非的旁证。如阿多诺在会后致波普尔的信中也谈到两人在本质环节上的意见一致【Hans Joachim Dahms, “Karl Popper und der Positivismusstreit.Neue Ansichten einer alten Kontroverse,”in Handbuch Karl Popper, hrsg.Giuseppe Franco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9), 708.】。达姆斯据此所做的分析说服了论争的另一位参与者阿尔伯特【Hans Albert,“Karl Popper, Critical Rationalism, and the Positivist Dispute,”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5, no. 2 (May 2015): 214.】。事实上,波普尔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阿多诺在其题为《论社会科学的逻辑》的补充报告中几乎攻击了波普尔文章中的所有核心论题。其中包括主张知识源于问题,具有总论性质的论题4;阐明诚实(Ehrlichkeit)、直接性(Gradlinigkeit)和简洁性(Einfachheit)的认识规范的论题5;点明证伪主义方法并将证伪主义方法与康德的批判哲学联系起来的论题6-7;以及波普尔处理价值中立问题的论题12-14。阿多诺也同样对波普尔有误解。他把波普尔对一种科学主义的批判理解为对所有科学主义的批判。接下来,我们首先驳斥波普尔的错误印象,再讨论阿多诺误解的根源,最后解释两人的表面一致。
首先是波普尔受到阿多诺批判的证据。波普尔在论题4中提出,知识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主张的那样起源于感觉经验或观察陈述,而是起源于问题。知识是从人们假设的知识和假设的事实之间的张力中产生的【Karl R. Popper, “Die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04.】。阿多诺反对这一点,他主张这种矛盾完全不是假设性质的,而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Theodor W. Adorno,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29.】。社会整体是人类知识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人类知识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约束。波普尔在论题5中把诚实、直接性和简洁性标举为人类认识应予遵循的规范,并提出当时的实证社会学研究在这几个方面还不够令人满意。阿多诺对这三者的规范性地位表达了质疑。他虽然承认在发表观点前应当深思熟虑的意义上,诚实是必需的,但诚实规范在实际研究中常被误用。他早已担心“那种科学诚实的姿态,拒绝利用不清楚明白的概念从事工作,变成了把自满的研究事业放在研究之上的借口”【Theodor W. Adorno, “Soziologie und empirische Forschung ,”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86.】。阿多诺更是就直接性和简洁性给出了一个康德式的答复,“当事实是复杂的时候,直接性和简洁性并非无可置疑的理想”【Theodor W. Adorno,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31.】。波普尔在论题6中主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适用于试错法,一个解答的科学性标志就在于它向中肯的批判保持开放;以及“所谓科学的客观性在于批判方法的客觀性。这主要意味着,没有理论可以超越于批判的攻击之上;而进一步讲,逻辑批判的主要工具——逻辑矛盾——是客观的”【Karl R. Popper, “Die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05-106.】。阿多诺并没有注意到波普尔在论题6中提出的自然主义主张(这是其误解的根源),他主要质疑的是解答必须向中肯的批判(经验的反驳)开放以确立自身科学性的观点。阿多诺认为,社会整体及其原则作为人类知识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是不能通过经验得到反驳的。这种整体及其原则作为理念,与资本主义社会令人不满的经验现实相对立。人们不能根据作为表象的经验现状去反驳作为这些表象的尺度和根据的理念自身。因此他说:“社会学定理作为对在假象背后运作的社会机制的洞见,在原则上,甚至出于社会理性的原因,与表象在如此程度上相矛盾,它们不能通过后者得到充分的批判”【Theodor W. Adorno,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32.】。阿多诺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对波普尔在论题6中提出的方法论说明。他认为论题6中关于形式逻辑方法独立性的主张实际上和胡塞尔的逻辑绝对主义主张如出一辙。逻辑绝对主义为了反对心理学主义,将逻辑方法独立化为绝对物。人们不但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为逻辑学奠基,而且逻辑学本身甚至独立于一切存在者。波普尔也出于类似的动机,不加批判地赋予形式逻辑方法以这种独立地位,而未能思考逻辑自身的可能性条件。在阿多诺看来,这实际上是无意识地屈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学科分工现状,“将科学学科之间的差异转变为存在基础的差异”【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5, hrsg. Rolf Tiedemann Dritte Auflage (Frankfurt: Suhrkamp, 1990), 71.】,因而是资产阶级物化意识。波普尔在论题7中将论题6阐述的证伪主义方法视作是批判的【关于波普尔的这句话,英译本较德文本多出一段括号中的说明:“‘批判暗示了这样的事实,这里存在一种同康德哲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尚不能确认这是英译本译者自己的理解性评论,还是根据会议本有的被遗漏内容所做的补充,或是按照波普尔本人的意愿所做的增补说明,因为其他德文的原文也有类似使用括号的体例。参见:Karl R. Popper,“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90。值得注意的是,波普尔1984年的德文文集收录此文时同样没有括号里的这段话,参见:Karl R. Popp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besseren Welt: Vortrge und Aufstze aus dreiβig Jahren, 120。】。阿多诺提出波普尔是“在一种非常非康德化的意义上把自己的立场称作‘批判的”【Theodor W. Adorno,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34.】。但阿多诺没有对此加以说明,而是试图缓和自己的批评,声称波普尔的方法在应用中已经逾越了波普尔为其规定的限制,因而还是符合康德的批判精神的。波普尔在论题12到14中把价值中立本身当作一个可以通过证伪主义和科学家间的相互批判来逼近的理想【Karl R. Popper, “Die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12-115.】。但阿多诺则强调价值中立的要求是物化意识,追求真理本身并不以价值中立作为前提。波普尔一方面尝试实现价值中立,另一方面也把价值中立视为一种价值。这体现了一种自相矛盾【Theodor W. Adorno,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38.】。由此可见,波普尔有关未发生实质分歧的印象是错误的。
其次是阿多诺对波普尔的误解。波普尔谴责那种错误的、误解性的方法论自然主义或科学主义【Karl R. Popper, “Die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07.】,其用意在于批判所谓归纳的神话。阿多诺则将其误解为对所有自然主义的批判。这里有两个要点。首先,波普尔不反对所有的自然主义,只反对采用归纳方法、遵循意义的证实原则的错误自然主义。其次,他认为其谬误在于相信人们可以通过保证认识来源的客观性来为知识的客观性做担保。也就是说,实证主义必然追求一个中立客观的第三人称观察者。然而这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为解决科学知识客观性的保证问题,波普尔才提出研究者应当通过试错法和科学家之间的相互批判来保证客观性。价值中立的科学客观性目标是一个可以逼近但不能达到的范导性理想。阿多诺赞成波普尔对自然科学方法的错误移置的批评,进而认为波普尔无意中与黑格尔的辩证法达成了一致。阿多诺在两个层面上误解了波普尔。第一,由于阿多诺将波普尔的观点理解为是对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总体批判,所以他将波普尔的话与黑格尔的主张混淆起来。黑格尔谈到:“如果说,当意识把客观事物理解为与它自己对立,并把自己理解为与客观事物对立的时候,意识所处的立足点是科学的对立:在这个科学的对立中意识只知道自己在其自身,这勿宁是完全丧失了精神。”【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版,第16页。】黑格尔将主客对立的状况看作是科学的知性思维的产物,并要求用思辨哲学的方法在自在自为存在的精神中克服这种对立。但波普尔实际上并不认为科学知性中主客对立的情况是一种缺陷,他强调的是人们不能用认识来源的客观性来保障知识的客观性。因此,这不能被理解成波普尔本人在反对科学的知性思维。第二,波普尔虽然批评中立的第三人称观察者的现实性,但也无意放弃客观性要求。价值中立虽然不能彻底实现,但可以起一种范导性作用。阿多诺本想通过揭示波普尔与黑格尔的一致性来揶揄波普尔,从而反驳波普尔的黑格尔批判,但既然这里波普尔并不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批判科学客观性,阿多诺的这种反驳也就无法成立。
由此可見,波普尔与阿多诺之所以未如达伦道夫所愿展开有效的争论【Ralf Darendorf, “Anmerkungen zur Diskussio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45.】,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彼此的观点。波普尔对思辨哲学文风的反感严重妨碍了他对阿多诺的批评的理解。而阿多诺也将波普尔对归纳主义的批判误解为略嫌不彻底的科学主义批判。也正因为阿多诺误解了波普尔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所以他才会在信中主张两人在本质环节上的一致。而由于阿多诺在评论中表现出的友善态度【在会上的评论中,阿多诺公开表态赞同了波普尔四次,分别是赞同批判自然科学方法的错误移置、批判科学主义、批判知识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的心理学主义,而公开承认分歧只有一次,即在结尾部分表达对当时社会的悲观态度。参见:Theodor W. Adorno,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28,137,140,141。】和其文风的晦涩,才使得波普尔没有注意到阿多诺对其主要论点的严厉批评。所以尽管如达姆斯所言,波普尔和阿多诺之间存在诸多共识【Hans Joachim Dahms, “Karl Popper und der Positivismusstreit.Neue Ansichten einer alten Kontroverse,”in Handbuch Karl Popper, 704.】,但他们对这些批评对象的理解乃至于采用的批判方法都大相径庭。共识实则建立在误解之上。有鉴于此,批判理性主义者忽视阿多诺,只将哈贝马斯当作主要论敌的做法便是不妥当的。波普尔和阿多诺的确存在实质分歧。
三 分歧的核心:批判概念
以达伦道夫为代表的第二种误解承认波普尔与阿多诺之间存在实质分歧,但错误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康德-黑格尔之争”。但阿多诺并不认同波普尔使用的是康德式的批判方法,他利用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资源来抵制波普尔的经验主义主张。两人对批判概念的理解本身就是有争议的,围绕着批判概念产生的分歧涉及三方面,即批判的判准、方法和对象。
(一)波普尔和阿多诺关于批判概念的立论
波普尔提出的是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批判主张。就判准而言,波普尔将假设的事实(基础陈述)视为检验理论的判准。他要求待检验的理论向中肯的批判开放,就是要求假设的理论命题受到那些相应的基础陈述的批判。就方法而言,波普尔关于检验理论的证伪主义学说是按照形式逻辑的否定后件式展开的。他在论题6f中强调逻辑工具具有客观性,又在论题18中对此作出解释:“演绎逻辑通过这种方式变成了理性批判的理论。因为所有的理性批判都采取这样一种形式,一种表明不可接受的结论能够从我们试图批判的前提中得出的尝试。如果我们成功地在逻辑上从一个断言得出了不可接受的结论,那么这个断言将会被驳斥。”【Karl R. Popper, “Die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16.】其方法的实质,就是根据否定后件式去不断检验假设的理论命题,从而获得经得住批判的理论命题。就批判的对象而言,波普尔认为应当受到批判的是逾越经验界限的认识,是超验的形而上学玄想。他这样评述康德:“康德选择《批判》作为标题,正是宣布对一切思辨性推理的批判抨击。”【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页。】他因此将康德的批判哲学解释成一种不幸掺杂了唯心主义要素的批判实在论。他试图通过“我们的理智并不从自然界引出规律,但试图(成功程度不等地)把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第274页。】,来抹除康德哲学中关于经验批判的先验唯心论要素。
阿多诺所提出的则是经由辩证法中介的先验批判立场。在判准上,阿多诺将社会整体视为批判本身的判准。阿多诺曾对整体(Ganze)做过区分。一种是自然科学所寻觅的整体,这种整体是通过人们对部分的认识获得的。另一种则是经过概念中介的整体,它适用于社会。阿多诺的判准实际上取自后一种整体【Theodor W. Adorno, “Soziologie und empirische Forschung,”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95.】。在方法上,阿多诺则诉诸一种社会历史分析基础上的辩证法。人们可以通过分析作为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的社会矛盾来对人类知性作出限制。辩证法所使用的矛盾推理方式事实上是社会矛盾的反映,这种社会矛盾的存在为人们对实证知识持一种批判态度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他说:“如果批判的结构满足了其潜藏的可能性,它反而能够蕴涵一种解决方案;不满足这一点后者几乎不会出现。这被归于规定的否定这一哲学概念。”【Theodor W. Adorno,“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34.】批判不仅能起到限制实证知识的滥用的否定性作用,还能够为实践方案的提出创造条件。在批判的对象上,阿多诺认为应当受到批判的是经验科学(人类知性),是僭妄的主体性哲学和工具理性。阿多诺强调:“知识生存在同非知识的东西的关系中,生存在同他者的关系中。只要它还仅仅间接地流行于批判的自我反思之中,这种关系就不会使自身满足;它必须成为一种对社会学对象的批判。”【Theodor W. Adorno,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35.】科学知识在阿多诺看来是值得怀疑的,他们是主体通过同一化过程征服自然的产物。人们应该通过辩证法揭露这些同一化过程的内在矛盾,暴露不能同化的外部性的存在,从而揭示其界限。
(二)波普尔和阿多诺对彼此立场的批评
双方都认为对方关于批判判准、对象和方法的界定是缺乏批判性的。
波普尔对阿多诺频繁诉诸的社会整体性判准怀有强烈不满。他将对社会整体性诉诸理解为一种曼海姆式的相对主义,并从这种判准中看出了黑格尔式道德实证主义的危险,即“道德和法律价值(例如正义)被实证的事实(流行的习俗和流行的法律)所取代”【Karl R. Popp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besseren Welt: Vortge und Aufstze aus dreiβig Jahren, 155.】。波普尔反对一切承认矛盾的辩证法。他认为黑格尔以降的辩证法承认矛盾,因而终结了一切合理的反驳和论证。波普尔证明,当人们同时承认一对矛盾的命题时,他们可以利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推论一切命题为真:
这就可以推论任意命题q为真,导致对矛盾的承认反而消弭了一切矛盾。承认矛盾的理论什么也推导不出来,从而为独断论大开方便之门。波普尔在批判对象的选择上,拒绝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质疑当代的科学意识。他认为阿多诺等人在此陷入超验的独断论。对他而言,阿多诺选择科学作为批判对象证明其属于(波普尔眼中)以黑格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传统。而如康德所言,“理性在经验性的应用中无须批判,因为它的原理在经验的试金石上经受着一种连续的检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康德著作全集》第3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页。】。
阿多诺则质疑波普尔对经验判准的信赖。他将经验事实首先按照康德的先验唯心论理解为是主体知性的产物,又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将这种主体知性理解为社会整体性的产物。因此,他谈到波普尔论题6a的模棱两可:“按波普尔的说法,如果一种尝试性解决方案无法获得事实的批判,那么出于这个理由它将作为非科学的东西被排除,即使可能仅仅是暂时的。这至少是模棱两可的。如果这些批判意味着向所谓事实的还原,通过被观察到的东西对思想的完全救赎,那么这一亟需之物将会把思想还原为假设并从社会学那里剥夺本质上归属于它的预测的环节。”【Theodor W. Adorno,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32.】雖然经验事实在波普尔这里不起证实的作用,但它作为既存社会状况的表现压抑了被预测到的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旧制度的事实与新社会的理念是彼此不相容的。在方法上,阿多诺则认为波普尔对形式逻辑方法的盲目信任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体制所塑造的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把形式逻辑方法当作一种独立的客观方法,没有反思其先验可能性条件。他试图举出一个无法通过证伪来检验却依然有效的理论命题:“很可能没有任何实验会令人信服地证明每种社会现象之于整体的依赖性,因为使可感现象成形的整体从不能使它自己被还原到特殊的实验安排之上。然而,能够在整体结构的基础上被社会地观察的这种依赖性实际上比任何能够通过殊相被无法反驳地确证的东西更为有效。”【Theodor W. Adorno,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34.】他认为,具体社会现象对社会整体的依赖性很可能不适用于证伪标准,但这丝毫无损其有效性。在批判对象上,阿多诺则认为波普尔盲目信从现代自然科学的有效性。他也承认在康德那里有一种对自然科学的信任:“康德的成就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可理解的,即科学提供了单纯抽象思辨所未能提供的绝对知识。”【Theodor W. Adorn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eds. Rolf Tiedemann,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Stanford, Calit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但他把此视作其批判不彻底的表现。康德对自然科学的信任符合渴望发现超时间的真理的资产阶级启蒙哲学的意识形态追求。
(三)对核心分歧的总结
波普尔和阿多诺之间关于批判的判准、方法和对象之间的分歧,充分暴露出二者对时代问题诊断的差异。波普尔将20世纪的社会危机视作是反对科学和误解科学的产物【波普尔在一篇1967年发表的演说中引证哈耶克,以证明他成功地说服哈耶克收回了一部分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他坚持认为问题出在对科学的误解上,而不是科学自身有问题。所以说波普尔依然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参见: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206页。】。他认为任何试图追问人类知识来源的问题,如“经验主义者的问题‘你如何知道?你的断定的源泉是什么?提法上就是错误的……它们是些企求独裁主义回答的问题”【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第35页。】。危机源于误解科学的本质。真正的科学所采用的是证伪主义方法。阿多诺对危机的诊断则是从对科学的批判入手的。他和霍克海默认为:“我们始终相信这种现代科学研究还是应当遵循的……但我们汇集在这里的断片表明,我们必须放弃对当代意识的这种信任。”【Max Horkheimer ,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Amsterdam: Querido, 1947), 5.】也就是说,20世纪的社会危机是由支配科学的工具理性导致的,它在征服外部自然的同时也支配人的内部自然。不论是精神性事物还是他人的生活都受到其摧残。而工具理性本身遵循着康德哲学中关于知性认识活动的模式,即理性“强迫自然回答自己的问题”【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康德全集》第3卷,第9页。】。
因此,双方均认为当时的社会面临危机,但他们就危机的本质与解决手段产生了分歧。波普尔将社会危机视作是独断的理性主义的产物,要求借助经验的批判予以克服。阿多诺将社会危机视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产物,要求借助社会整体性和辩证法的先验批判将其克服。波普尔继承了康德哲学中经验批判的要素,而阿多诺继承了康德哲学中先验批判的要素。波普尔与阿多诺之间的分歧既不仅仅是对既存社会持有乐观还是悲观态度的问题,又不像达伦道夫所言仅仅是康德式立场与黑格尔式立场之间的分歧。
四 “波普尔-阿多诺之争”的实质及意义
至此,我们批评了关于实证主义论争之起因的两种经典误解。波普尔和阿多诺一开始就存在实质分歧,而且是关于批判概念的分歧。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重估。
首先是论争的实质问题。波普尔和阿多诺对康德的批判概念的理解和应用迥然不同。波普尔采用经验观察的基础陈述作为判准,使用形式逻辑的否定后件式作为方法,批判超验的形而上学玄想。阿多诺则采用理论把握的社会整体作为判准,使用否定的辩证法作为方法,批判实证科学无反思的保守立场。这两种立场都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做了巨大改进。波普尔同意现代科学哲学所谓“观察渗透理论”的一般结论,但并未由此倒向康德的先验唯心论。相反,他调和了经验主义与批判哲学。渗透在基础陈述中的理论是假设的产物,人们用经验不断对其加以证伪。只存在相对可靠的理论命题,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理论命题。他一方面为经验观察保留了真理判准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批判哲学关于物自体的不可知论主张,因而可被称为一种批判的经验主义。而阿多诺在批判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了先验哲学的独断论风险。他首先承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用社会整体取代了康德的统觉作为自然科学的先验条件,又为了避免将社会整体绝对化、神秘化而引入了否定辩证法。社会整体不是给定的事实,而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矛盾综合体。这样可规避理性主义的独断论风险。由此,称阿多诺的立场为一种批判的理性主义立场也未为不可。“波普尔-阿多诺之争”实则无异于近代哲学“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之争”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重演。
其次是关于“波普尔-阿多诺之争”的意义问题。这场论争为我们审查康德以降的批判哲学传统提供了契机。康德考虑到哲学传统内部的争论长期以来缺乏成效,试图通过理性批判来终结“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的经典对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版)》,《康德全集》第3卷,第545-546页。】。但批判哲学并没有终结这种对立,而是要求它们反思自己的哲学前提。这促发了两种传统的全面更新。波普尔的经验主义观点将理论前见对科学认识的影响纳入考量,回应了无批判性的指控。阿多诺的理性主义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消解了先验主体的绝对性,规避了独断论指控。双方分别在经验和先验两个维度上发展了批判哲学内部潜在的理论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借助批判使哲学走出了纯粹学术的象牙塔,同实践的社会理論相结合。波普尔在非理性主义的政治狂热面前捍卫审慎的经验科学认识,阿多诺则敏锐地揭示出潜藏在技术治理和大众传媒背后的科学主义僭妄。二者的理论回应了时代问题的重大关切,提出了富于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
但双方的立场也各自存在缺陷。波普尔对经验知识本身的局限性认识不够。他仅在批判归纳主义的意义上承认经验知识的局限性,却预设经验(基础陈述)本身作为终极判准的资格。他声称:“一个理论的每一次检验,不论它的结果可靠还是被证伪,都必须中止于某一个得到公认的基础陈述。”【Karl R. 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Zur Erkemtnistheorie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 (Vienna: Springer-Verlag, 1935), 60.】不存在单纯的观察,观察总是受到兴趣、理论框架等前提因素的引导,所以论题4称之为“假设的事实”。所谓基础陈述的有效性与其背后预设的理论的有效性紧密相关,而这种理论本身又需要新的判准对其加以检验。但波普尔在用基础陈述作判准时对这种限制避而不谈,反而声称:“从逻辑的观点看来,理论的检验依靠基础陈述,而基础陈述的接受或拒绝则依靠公认的约定。”【Karl R. Popper, Logik der Forschung: Zur Erkemtnistheorie der modernen Naturwissenschaft, 64.】这就无怪乎哈贝马斯在波普尔的学说里看到了一种无批判的决断主义(Dezisionismus)的风险【Jürgen Habermas, “Analyt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Dialektik,”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73.】。
阿多诺则过度偏袒理论。他谈到:“但倘若社会学把自身投入对事实和人物的理解以服务于现存的事物,那么这种在不自由条件下的进步将会以社会学自以为胜过理论并谴责理论完全的不相关性的方式来损害彻底的洞見。” 【Theodor W. Adorno,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142-143.】经验是对现存事物及相应秩序的表现。而只有理论本身才能设想作为整体的社会,使批判成为可能。但这并不能让理论脱离经验的批判的尝试合法化。首先,关于社会事实的经验认识不仅反映该社会的支配意识形态,还反映其中存在的矛盾。理论和经验共同构成了人认识社会的必要环节,没有它们,社会整体的矛盾就无法得到充分澄清。不承认这一点对经验而言是不公允的。其次,阿多诺让一部分理论及其对应的社会整体脱离经验的批判,实际上危险地向他自己一贯严厉批判的资产阶级哲学靠拢了。因为这种做法让理论脱离了具体时间、地点等等经验限制,从而趋于一种无时间的、超时间的真理。而是否对人类认识作社会历史的限制,曾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区别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关键标准【马克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 李小兵等译, 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第213-214、221-222页。】。由此看来,阿尔伯特用列宁来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唯心主义倾向也不是无的放矢【Hans Albert, “Kleines verwundertes Nachwort zu einer groβen Einleitung,”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337.】。
上述分析表明波普尔和阿多诺各自无批判性的偏好。黑格尔曾说:“当意识在它的对象上发现它的知识不符合于这个对象时,对象自身就保持不下去,换句话说,当尺度所考查的东西在考查中站立不住时,考查所使用的尺度自身也就改变;而考查不仅是对于知识的一种考查,而且也是对考查的尺度的一种考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 第60页。】科学认识的深化并不是用一个固定不变的尺度去修正另一个永远待检验的对象的过程。我们关于世界整体的理论与我们生活中的感觉经验都在发生变化。经验事实和整体理论都在认识活动中检验彼此以获得对世界的更好说明。我们要想真正继承活跃在波普尔和阿多诺著述中的批判精神,就得努力克服他们的偏倚性,向可能的批判保持开放,无论这种批判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属于经验观察还是属于理论思维。没有分歧和论争的存在,就难以暴露出不同立场在价值上的偏倚性和在论证上的局限性。分歧和论争是理论保持活力,不断进步的重要前提。如果我们希望充分利用实证主义论争的思想遗产,就不能将其掩盖在“观点一致”的虚假共识之下,也不应汲汲于一劳永逸地消除分歧。哈贝马斯和阿尔伯特在“波普尔-阿多诺之争”的基础上展开的论战,已然为当代德国哲学和社会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这种现象富于启示意义。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应当大力发扬批判精神,勇于暴露理论分歧,投身于关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争论之中。这样有助于避免固步自封和崇洋媚外的弊端,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责任编辑:何 毅]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