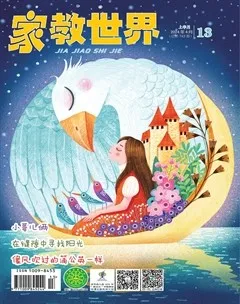像风吹过的蒲公英一样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就是搬家。搬家次数多了,总感觉一直在路上,就像蒲公英一样,风一吹,就去了远方。
搬家是因为我爸,他是一名水电建设工作者,四海为家。单位的房子,都不是自己的,人员流动性大,哪儿空了就可以往哪儿搬。好端端的房子怎么会空呢?那是因为全国的水电站很多,一个电站的人经常会被调到另一个电站去,这样一来,房子就空了。
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字就是“调”,说谁又要调到哪里去了。我那时小,误以为是“吊”,想着那种大吊车和绳子,觉得怪吓人的,好好的人为什么要被“吊”来“吊”去?并且希望我爸不要被“吊”走。
仅在凤滩水电站,我们就搬了十来次家。因为总是有房子空出来,有时候是因为单位安排,有时候是我爸想换个地方,打一个报告,卡车就“轰隆隆”地被派来了。几个年轻力壮的男青年跳下车,扛的扛,抬的抬,三下两下就把大大小小的家具搬上车,运到了另一个住所。
一个电站内的搬家,是小范围的流动,三五里路的距离。这样的搬家是没有离愁的,只有新奇和欢喜。搬到一个新地方,总会遇到同学,不到一天就和邻居小伙伴们熟络了,互相追赶打闹,还各自端了饭碗出来换菜吃。房子是大是小、是好是坏,孩子们并不关心,只关心哪里好玩。每次搬了新家,我就到附近的角角落落去探险,寻找一些秘密的藏身之所,包括废弃的空房子、幽静的通道,或者地下室、实验室,有时还能找到一些实验器材什么的,好奇地捣鼓一番。我一般会指认某棵树是自己的树,某块石头是自己的宝座,还要给它们取名字,我就是那个地方的主人了。
电站建设接近尾声时,营地和营地之间的大搬迁开始了,就是从一个水电站迁到另一个水电站。这种举家的迁徙,不是仅带几件行李的旅行,而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经常有一些院子里堆放着硕大的箱子和家具,都用木板钉着,方方正正,小山一样。这样的搬迁近则几百里,远则数千里。好在水电建设工作者都有一种随遇而安的个性,在哪里都能很快开始全新的生活。
因为搬家,我经常转学。小学一年级快结束时,我第一次转学,要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去读书。那天,妈妈到教室接我,老师送我到门外,和我说再见,我的泪水掉下来了。不过,一年后,我又转了回来。而在老家结识的小伙伴和同学,又要伤心地互道再见,互赠小礼物,依依惜别。
我记忆中有很多片段和画面,都是母亲带着我们一路辗转,在拥挤的汽车上、火车站、码头、旅馆,还有陌生的街头。那些片段像珍珠一样串联,组成了我漂泊的童年。
也许正因为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我也习惯了行走,说走就走,无论长途还是短途,都是一闪念的决定。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远足,经常翻山越岭。十四岁那年,班里十几个同学想做点惊天动地的事——从沅陵步行回我们生活的电站。一百多里路,清早出发,回到家时,已是电影散场的时候了,而那一起出发的十几个同学当中,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走完了全程,其余的都陆陆续续半路搭了车。那一刻,虽然精疲力竭,双脚磨出了泡,我却感觉自己像一个归来的王者。那一刻我就想,一条路,如果认定了,就要走到头,只有这样彻底地坚持过,才会成为一个胜利者。
后来路越走越远,东西越来越多,我不能一一带走的,就用文字去记录。走过的路,遇到的人,做过的事,所有的恩泽、温暖、光辉,都要诉诸文字。于是,便有了我最初的文章。有什么会比文字更让人心安、更让人信任呢?慢慢地,文字就成了我心灵的家。
摘自《儿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