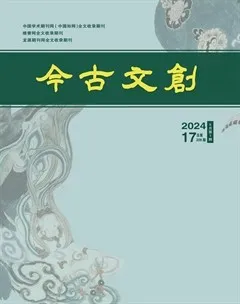东汉邓太后执政研究综述
段昌园
【摘要】女主执政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并非个别现象,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时代约有六百年的历史,仅在东汉短短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中就有六位太后临朝。其中邓太后是非常突出、与众不同的一位执政者。女性作为与男性相对而存在的一个群体,在主流文化领域和官方话语体系中实际所处的次要地位所在。因此,探讨女主政治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为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迁开拓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东汉;女主执政;邓太后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7-007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7.023
女主执政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并非个别现象。女主现象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相始终的。探讨女主执政可以为深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变迁提供一个有益的新视角。东汉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先后有六位太后临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其中邓太后临朝称制15年之久,面对东汉中期的内忧外患,其在位期间,凭借个人政治才能与邓氏家族的支持,努力改变累积的社会矛盾,发展社会生产,革除弊政。由于学术界对邓太后的专门研究比较少,多数都是在东汉豪族研究、东汉外戚研究、东汉后妃研究等几方面涉及的,故在此分述如下。
一、东汉豪族研究
(一)东汉皇室与豪族的联姻研究
东汉政权是在各地豪族地主势力的支持下建立的,皇室通过联姻以拉拢豪族巩固其政权。豪族通过与皇室联姻输送女子入主后宫,获得更多政治权力,进而发展为外戚集团。高颖飞《浅议汉代皇室等级婚姻的嬗变及其原因》认为,在汉代,随着大地主庄园经济的不断勃兴以及儒家学说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渐深刻,皇室在婚姻问题上讲究门当户对,从而使婚姻关系具有鲜明的等级色彩。[1]唐会霞《两汉关中豪族与皇室联姻考论》指出关中豪族与皇室联姻本质是政治与经济利益的交换,是双方相互选择的结果,等级性与政治性是这种婚姻关系的突出特点,对二者来说都有积极与消极影响。[2]王伟华《汉代豪族婚姻研究》指出:外戚豪族与皇室之联姻,豪族依附皇权统治,又有分享政治权力的利己功能;对皇权而言,豪族是需要拉拢以稳固政权的对象,但其势力的恶性膨胀也会威胁皇权。[3]
总体而言,学界目前较为认同东汉政权是刘氏皇族与豪族结合的产物,豪族凭借姻亲关系发展成为外戚集团,双方既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是一种共生和竞争的关系。
(二)邓氏家族研究
刘德杰《东汉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与文学成就》肯定了邓氏家族的子弟教育对其执政的影响,称其家族的文学精神彰显了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气度,是东汉世家大族的文化典范。[4]盛永芝《东汉南阳外戚家族研究》论述了邓氏家族从邓禹奠基起到桓帝的邓猛皇后被废,基本延续了整个东汉王朝,其中邓太后的临朝称制起到了重要作用。[5]刘太祥《论东汉南阳官僚集团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肯定了以邓氏家族为代表的南阳官吏为东汉政权的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邓骘作为其妹邓太后支撑的外戚,谨慎守法,为政有方,协助太后治理朝政使得“天下复平,岁还丰穰”。而邓太后也促进了更多南阳人进入官僚系统,维系了南阳官僚集团的长盛不衰。[6]邓氏家族在东汉政治中占有极高地位的同时,也有东汉豪族共有的弊病。雷福平的《邓氏家族与东汉政治》在肯定邓氏家族的政绩时,也指出其卖官鬻爵、任人唯亲、重用宦官势力等不仅为其家族埋下了隐患,更是对东汉社会后期产生了深远影响。[7]彭天仪《东汉安顺之际政局的演变与特点——以杨震为中心的考察》认为邓太后在内有政治斗争外有天灾人祸的局势下,拉拢士大夫并与其合作,缓和了当时内外的矛盾,保证了其在位期间处于斗争的上风,且在邓太后去世后士大夫群体仍发挥影响力。[8]徐振《东汉前期功臣政治势力探析》以邓氏家族为例,论述了东汉个别功臣家族通过与皇室、豪族之间的政治联姻、派系结党和家族文武双线并重发展等途径以谋求家族势力长久不衰。[9]
二、东汉外戚研究
陈苏镇在《论东汉外戚政治》中认为,东汉刘姓皇室不得不依靠外戚家族,并与之结成豪族婚姻集团,一起构成东汉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自章帝开了坐视窦氏操纵皇储废立的先例,“外立”的皇帝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外戚,使得外戚逐渐成为东汉政治舞台的主角。外戚政治是豪族社会的产物,是豪族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外戚政治又衍生出了宦官专权。[10]顾凯《东汉外戚政治研究》指出外戚政治是东汉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和帝依靠宦官等击垮了窦氏集团,之后又重用宦官,形成了东汉外戚与宦官平分政治格局的雏形。[11]徐芬、翁频《试论邓氏外戚对顺帝初期中枢政局的影响》指出在邓太后去世、邓氏一族遭到安帝打击后,邓氏一族对当时中枢政治格局仍有很大的影响力。邓太后临朝称制时利用宦官势力致使其坐大,邓氏一族征辟很多儒学人才进入中枢政权,重构了外朝政治格局。[12]薛海波《论皇权与东漢外戚豪族》认为皇后或嫔妃凭借其与皇权的关系,行使家长的宗法权,家庭的伦理关系让位于维护家族政治地位的政治关系,皇太后临朝称制后从维护皇权权威和自身家族执政的合法性出发,大多主动限制家庭成员的官爵和权益,外戚豪族属于在皇权作用下发生异化的特殊豪族,皇权既是加速外戚豪族权势扩张的根源,也是加速其家族衰落的决定性因素。[13]
三、东汉后妃研究
两汉特别是东汉时期是儒学发展繁荣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后妃研究多是从后妃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及政治参与度等方面展开。
(一)后妃的教育背景
蔡锋《对古代皇宫贵族女性文化教育的考察》认为,尽管中国古代专制政府剥夺了广大妇女的受教育权,但却对上层女性及贵族宫廷妇女接受文化教育有着默许、鼓励的倾向。东汉时期邓太后既提倡对宫人的教育培训,又专门设立了男女同校的贵族外戚小学。[14]高荣茹《两汉后妃选拔、教育及后妃与政治关系问题考述》从后妃群体的教育状况及其干政情况两方面对两汉后妃进行综合考察。东汉后妃出身豪族且文化素养较高,在幼主时艰或皇统屡绝的情况下,后妃们多以母后临朝称制,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但是对于当时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文化教育的推进都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15]陈苹《论汉代女性的教育》指出汉代统治者鼓励宫廷女子接受文化教育,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对有才学的宫廷女子持赞扬的态度,后妃参与朝政是宫廷女子教育的成就之一。[16]
王渭清《东汉皇后考论》认为东汉皇后大多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因而参政意识强烈,其中很多人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干,尤其是邓皇后,不仅参政意识强烈且具有非凡的政治才干,是东汉杰出的政治家。[17]解济红《〈后汉书〉所载知识女性研究》以《后汉书》中知识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东汉知识女性群体的家世背景、所受的文化教育内容、婚姻特点以及对东汉知识女性的参政途径和政治作用进行分析,着重分析太后临朝的原因和影响,从多方面深入了解东汉知识女性的生活。[18]
谭友坤的《试论东汉的宫邸学及其历史意义》肯定邓太后临朝称制后,为约束宗室子弟设立宫邸学,向他们传授儒家大一统忠君思想,使得宗室子弟能都“忠君”。[19]王爱华《〈后汉书〉女性研究》从政治环境、思想环境以及当时对女性的性別态度三个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东汉时代对女性个性成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范晔对东汉女性所持有的态度。[20]
(二)东汉女主施政研究
王鑫义《女政治家:东汉和帝皇后邓绥》中肯定了邓太后在位期间戒奢从简、检束宗族、重视教育、置师讲经、审慎断案、裁减淫祠、赈恤灾民、重视吏治等历史功绩,并对其用人唯亲和久不归政问题进行了辨析。[21]
沈宏《东汉“干政”皇后作用初探》通过横向对比,肯定了在东汉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和熹邓皇后为代表的皇后们的干政推动了东汉历史的发展。[22]方芳、俞凌欣《东汉皇后形象浅析》将东汉皇后分成三类,一是深明大义、克己奉公型,邓皇后就是典例;二是出身高贵、下场凄凉型,只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三是放权外戚、野心勃勃型,但又不得不依靠外戚与宦官,留下政治弊端。[23]
(三)女主政治产生的历史因素分析
东汉和帝以来,六位太后先后临朝称制,形成东汉中期百年外戚的政治格局。许多学者认为由于女主执政及其裙带关系而起的外戚势力导致王朝覆灭,然而女主政治不是简单的历史现象,它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
刘筱红在《后妃与政治》中提到了后妃政治的存在可在传统纲常伦理中找到理论依据。首先是传统伦理道德具有明显的对立统一特征,既强调主从关系,又赋予双方互相牵制的义务。另外则是“孝”观念,妇女虽夫死从子,但子也必须对母亲尽孝,皇帝为臣民表率,更应如此。[24]陈恩虎《简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后妃参政》认为包括邓太后在内的一些后妃,在宗法关系的角度看,其母后的身份是皇权可靠的监护人,在主幼国艰的时刻与朝臣在维护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保证了统治机器在君权幼弱的情况下正常运转。[25]张星久《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认为,“后”作为皇帝正式配偶的专称,也包含“君”的一层含义;传统孝道观念为母权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家天下”的政治属性这些都是后妃干政的条件。[26]米莉《帝制中国女主政治的合法性研究》论述了女主政治的几大合法性基础:“家事”与“国事”在政治概念上的模糊性、女主作为“天下小君”的地位设定、皇位继承制度的内在缺陷、意识形态对于“孝道”的推崇以及“官僚君主制”的特殊政治体制既对女主政治有制度支持,又有一定的文化制约。[27]
可见,学者对于后妃干政的原因有一些共同的认识:皇帝年幼的客观原因、母后干政的历来传统、两汉对于“孝道”“母权”的推崇、后妃个人的能力与母族的势力支持、皇权继承制度的缺陷等,同时也指出后妃干政的女主政治并不是常态,只是皇权交接的一种过渡。
(四)女主政治的实质
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即女主政治实质还是男权政治。杜芳琴《中国古代女主政治略论》认为“女主”不等于“女权”,女主政治是男权政治系统操作运转遇到障碍时的缓冲器和调节器,评价女主政治只需要用社会实际效果来衡量其是非得失功过。[28]蔡一平《汉宋女主的比较》通过对汉和熹邓太后与宋刘太后进行比较,分析了二位女主政治的不同内容与特色,认为在男性中心社会的封建时代,女主政治只能是男性政治、皇权政治的附庸。[29]韩林《性别视野下的女性干政现象》认为女子干政,用了一个“干”字,表明这是僭越之举,明显带有贬义。在古代男权社会中,女性执政永远没有合法地位,她们只是在男性统治出现危机时的替代品。[30]
(五)女主政治的评价
学界在对女主政治进行评价时既肯定了其积极作用,也沿袭了传统史家对其负面影响进行了批评,对于后者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
米莉《帝制中国的女主政治》认为皇太后的政治权力从本质上来源于无法有效行使统治职责的皇帝,在客观上具有了一种鲜明的“过渡性”特征,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态的变化,其在政治领域的继续存在就将转而变成为一种“不合法”与“不正当”的状态,也不得不接受官僚集团与主流文化传统对她的政治作为更为挑剔与严格的审查。[31]张星久《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认为由于缺乏安全感与政治合法性,女后临朝一般都会采用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但某些情况下后妃干政作为一种“幕后替补力量”而起作用,使得国家机器可以继续运转。在这一问题上,要跳出旧史家的眼光,避免不加分析地夸大女后干政的祸患。[26]陈丽平在《汉王朝的政治危机与女祸观念》中进一步指出,“红颜祸水”观念是两汉特定政治危机中的产物,是在两汉多“女祸”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两汉精英为了遏制女性对皇权的破坏而做的舆论宣传中衍生的观念,使得女祸观念在汉代得以形成。[32]
综上所述,学界对邓太后执政的综合评价是正面的,对其深厚的儒学教育背景、出众的个人能力以及施政措施予以肯定,但也对其执政期间放弃和帝长子刘胜而选立幼子刘隆、殇帝夭亡后选择外藩入继大统、安帝成年后久不归政、任人唯亲、重用宦官等方面多有争议。
参考文献:
[1]高颖飞.浅议汉代皇室等级婚姻的嬗变及其原因[J]. 兰台世界,2009,(14).
[2]唐会霞.两汉关中豪族与皇室联姻考论[J].文史纵横,2018,(12).
[3]王伟华.汉代豪族婚姻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21.
[4]刘德杰.东汉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与文学成就[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2,(03).
[5]盛永芝.东汉南阳外戚家族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017.
[6]刘太祥.论东汉南阳官僚集团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J].南都学坛,2022,(03).
[7]雷福平.鄧氏家族与东汉政治[D].湖南师范大学,2012.
[8]彭天仪.东汉安顺之际政局的演变与特点——以杨震为中心的考察[D].华中师范大学,2012.
[9]徐振.东汉前期功臣政治势力探析[D].南京师范大学,2014.
[10]陈苏镇.论东汉外戚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顾凯.东汉外戚政治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09.
[12]徐芬,翁频.试论邓氏外戚对顺帝初期中枢政局的影响[J].史学集刊,2010,(04).
[13]薛海波.论皇权与东汉外戚豪族[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1,(03).
[14]蔡锋.对古代皇宫贵族女性文化教育的考察[J].妇女研究论丛,2004,(03).
[15]高荣茹.两汉后妃选拔、教育及后妃与政治关系问题考述[D].吉林大学,2006.
[16]陈苹.论汉代女性的教育[D].郑州大学,2009.
[17]王渭清.东汉皇后考论[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
[18]解济红.《后汉书》所载知识女性研究[D].鲁东大学,2014.
[19]谭友坤.试论东汉的宫邸学及其历史意义[J].兰台世界,2014,(12).
[20]王爱华.《后汉书》女性研究[D].牡丹江师范学院, 2021.
[21]王鑫义.女政治家:东汉和帝皇后邓绥[J].安徽史学,1995,(02).
[22]沈宏.东汉“干政”皇后作用初探[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1996,(01).
[23]方芳,俞凌欣.东汉皇后形象浅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0).
[24]刘筱红.后妃与政治[J].江汉论坛,1995,(06).
[25]陈恩虎.简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后妃参政[J].淮南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报),2001,(04).
[26]张星久.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1).
[27]米莉.帝制中国女主政治的合法性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06).
[28]杜芳琴.中国古代女主政治略论[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报),1993,(02).
[29]蔡一平.汉宋女主的比较[J].中国古代妇女专辑, 1994,(03).
[30]韩林.性别视野下的女性干政现象[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4).
[31]米莉.帝制中国的女主与政治[D].中国政法大学, 2008.
[32]陈丽平.汉王朝的政治危机与女祸观念[J].云南社会科学,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