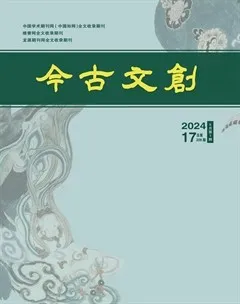论妥清德诗歌的文学治疗
【摘要】文学人类学认为文学的功能并非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娱乐等,还具有精神治疗的意义。因此,文学成为众多作家精神避难的手段,广泛表现在文学创作之中。诗人妥清德以诗歌的形式书写乡土——传统的黄泥堡草原,驾驭想象的翅膀挖掘故乡逐渐被淡忘的传统文化,疗愈故土巨变引发的精神创伤。同时,黄泥堡的传统文化在诗人自我疗愈的过程中得以保存,表达作者并试图引发更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流失的反思。
【关键词】妥清德;诗歌;创伤;文学治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7-006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7.019
文学的功能长期以来被简单归纳为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以及娱乐功能,忽略了文学产生之初最原始的治疗功能。国内对“文学治疗”的发现是在20世纪现代性危机中得到的启发,从而推动了“文学治疗”的再发现,即文学抚慰心灵痛楚、疗愈精神创伤的价值。就像严巍娥所言:“文学除了拥有外在的、实用的、功利的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还拥有内在的看似无用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即精神性价值。”[1]
纵观古今中外文学经典,能够被称作经典的文学作品往往都含有给人慰藉的因子。文学经典“是给人们带来幸福,使人们脱离苦难,予人们以安慰的东西”[2]。基于这样的文学素养,妥清德驾驭想象的翅膀在诗歌中塑造传统的故乡,让自己以及那些失去传统文化的黄泥堡人民回归精神家园,脱离现实的精神创伤。因此,妥清德的诗歌是一系列疗愈创伤的梦幻世界。
一、故土巨变引发的精神创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日新月异的现代化生活也不断侵蚀着几千年来的传统文明。聚居在我国西北部甘肃省境内黄泥堡草原上的人们,同样在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故土巨变。
妥清德是甘肃当代较有成就的一位诗人,其诗歌意境优美,风格质朴而浪漫,处处充盈着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般的景致,书写出一系列的草原牧歌。其中“黄泥堡草原”是妥清德诗歌中重复出现的主题。究其原因,妥清德出生于酒泉市黄泥堡自治州,这里有着他扯不断的血缘关系。费孝通谈道:“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3]因此,无论身处何地,妥清德始终无法忘却黄泥堡草原这片故土带给他的记忆,而在历史进程中故土的巨变引发了他巨大的心理缺憾与精神创伤,从而试图以诗歌的方式寻觅逐渐消失的草原,书写曾经的故乡。
据考证,黄泥堡聚居区的人们最早主要来源于古代北方的游牧人民——回鹘,后经过不断的迁徙和融合最终形成了复杂、多元的传统文化。他们一方面延续了祖先以游牧为主的生存模式,这漫长的游牧过程构成了他们最显著的传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在长久的社会生活中受到当地原生农业活动的启发而渐知农耕技术。社会发展到今日,现代化文明更是取代了黄泥堡传统的游牧文化。曾经马背上的人们丢掉了羊鞭,拿起了犁耙,走进黄泥堡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而是典型的汉区农庄,甚至也丢下了属于自己的语言。那些曾经属于他们的传统文明在工业文明的侵蚀下日渐衰弱,生于斯且长于斯的人们无法阻止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也无法适应传统生活节奏变得混乱,从而日积月累形成群体性文化创伤。“文化创伤”是指“当集体成员感到他们遭遇了可怕事件,这个事件在他们的集体意识和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而且不可挽回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就会产生文化创伤。”[4]对于黄泥堡人们来说,“可怕的事件”即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挽回的传统文化,“文化创伤”即是面对传统文化的失落而产生的精神创伤。
黄泥堡草原土生土长的人们面对传统与现实,感到迷茫和焦虑,精神创伤成为他们难以超越的最大难题。对于诗人来说诗歌是他们避难的港湾,用诗歌书写故去的黄泥堡便是妥清德用以疗愈精神创伤,超越精神困境的最佳手段。
二、诗歌疗愈精神创伤:想象中的黄泥堡
钟进文在《寻根的人》中写到妥清德:“他的诗歌语言质朴、意境优美,处处流露出一种扯不断抹不去的浓浓情思。这种情意仿佛告诉人们,作者正在寻觅一种失去的东西。”[5]这种失去的东西正是妥清德故土情结,是他心灵的缺憾,精神的创伤。因此,妥清德在诗歌中通过想象构建起黄泥堡草原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桥梁,营造出一座座传统牧歌式的草原风情,疗愈故土巨变引发的精神创伤。
正如作者所说:“在创作中,在黄泥堡草原出现的裕固族场景和情景都是我通过想象复制和构造出来的。”[6]所谓复制,即为了探寻黄泥堡曾经的风土人情,妥清德多次前往甘南草原体验传统的生活境况和风俗景致,并翻阅大量的史诗和民歌,再通过复制构造出曾经的家乡。总览妥清德的诗集《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在诗人笔下,黄泥堡的现实面孔并未被客观描摹,诗人摒弃了眼前被现代化裹挟的草原,发挥想象力构造出传统草原的模样。诗中的黄泥堡是一片一尘不染的净土,祥和、美丽且纯真,能够把读者带回千年以前的敕勒川、阴山下,呈现的是“风吹草低见牛羊”般的草原生活。如“露水分娩的早晨/运输星辰的马车自黄泥堡出发/一路要经过羊圈和青稞地”[7](《我家的羊群在风中吃草》),在诗人的想象中,黄泥堡的交通工具應是传统的“马车”,而清晨出行的路上会遇到无数的“羊圈”和“青稞地”。“一座草原/在大风中动荡/青青牧歌的源头/马蹄驾着白雪/进入雪山草绳像一条绿色的蛇/牧犬和草尖上的帐篷/都竖起耳朵”[7](《草原的风》),其中出现了“牧歌”“马蹄”“雪山”“帐篷”“草绳”等紧紧围绕着牧人传统生活的物象。草原的风裹挟着牧歌吹遍草原的角角落落,骏马踏着还未融化的白雪奔腾……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对传统草原的纯情与向往。“草原上的候鸟/潮水一样涌来或者退去/牧歌不会寂寞/绿风重现飞翔的感觉/从有花无花的植物里/取出我们的乐器/演奏给羊群听。”[7](《裕固民歌:蓝天上白云》)诗人笔下的黄泥堡草原是安静祥和的,蓝天白云之下是飞旋的候鸟,是悠扬的牧歌,是成群的牛羊,是没有工业化痕迹的青青草原,在这里生命不分贵贱,人依自然而生存,大自然因人而更有生机。此外,《雨中》《云是没有故乡的》《牧野》等诗歌中都出现了众多的草原景观。这些景观散布在每一首诗歌中构建出了一幅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传统景致,又共同指向诗人的审美理想——传统牧歌式的黄泥堡。
诗人不仅在物象上还原传统草原的特色,还在风格上重构大西北自然、闲适、朴素、浪漫的特征,每一处落笔都仿佛来自真实可信的生活,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幅幅触手可及的画面,但实际上都是诗人丰富的想象。显然,诗人在对祖先游牧生活构建的同时流露出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向往,字里行间的浪漫是妥清德对现实的无奈与逃避,诗人企图用诗律与文字恒久的守护故乡的传统文化,获得精神创伤的疗愈。正如村上春树所说:“我为什么开始写起小说呢?原因我不太清楚,只是在某一天,突然产生了写的欲望,现在想起来,那还是因为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手段。”[8]作家往往不自觉地走入创作,最后自觉地进行自我治疗。
可以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蕴含着文学治疗的因子。毛姆在文学中弥补情感的需要与身体的缺憾;川端康成从《伊豆的舞女》到《睡美人》无一不是自疗的尝试;阿库乌雾在诗歌中寻求文学的疗愈……作家在现实中溃烂的精神创伤,在文学中得以疗愈。固然很多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都有自我疗救的目的,但妥清德运用想象这种特殊的手法构建精神的故乡,则表现出更明显的文学疗救意义。通过想象让自我与故乡沉浸在传统的风情之中,实现精神缺失的疗救。同时,人类的情感和经历具有共通性,不仅诗人在书写中能够实现自我创伤的疗愈,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够通过幻想唤起对抗精神创伤的力量,达到更多人精神生态的平衡和健全。
文学是人类独有的用符号创造的世界,是精神生存的特殊家园,现实中无法消解的内心障碍在文学的世界中往往可以得到平衡。妥清德试图让诗歌成为自己避难的港湾,用想象的方式构建黄泥堡草原曾经的面孔。因此,妥清德的诗歌具有治疗功能,创作者与欣赏者走进诗歌都会受到诗意的熏染,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创伤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疗愈。
三、妥清德诗歌中文学治疗的现实价值
通过想象书写原生态的黄泥堡草原是妥清德独特的文学治疗形式。从精神角度出发,这种文学治疗的意义在于疗愈书写者的精神创伤。从现实角度出发,则在于对黄泥堡草原传统文化形态的记录与保存,并表达了自己并激发了读者对传统与现实的思考。这是诗人妥清德作为黄泥堡草原土生土长的一员为真正的故乡所做出的努力。
(一)黄泥堡草原传统形态的文学性记录
如果把妥清德的诗歌放置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衡量,会发现其在治愈创伤的同时把流失在历史浪潮中黄泥堡的传统面貌保存了下来。即使在现实中黄泥堡早已失去原有的模样,但妥清德仍然不遗余力地对黄泥堡草原传统形态进行了文学性的记录。
妥清德时常书写黄泥堡草原的风,随着风的痕迹把整片草原原生态的风光记录下来。“风从山坡上吹过/把古老的羊群甩向天边/岩石吐着花香/卷心菜般的裕固族村庄/在风中/抱紧孤独的露水。”[7](《风从山坡上吹过》)“一座草原/在大风中动荡/青青牧歌的源头/马蹄驾着白云/进入雪山。”[7](《草原的风》)“风,吹过山顶/风飘起来,安静的雪/高过草尖,顺从了幸福/风摸到我的羊群/露水与青草/爱成一团。”[7](《山坡下的草原》)此外,还有《在露水中》《我家的羊群在风中吃草》《高山》等诗中草原的风在无形中怀抱草原,吹过雪山、古老的羊群、马鞍、牧笛、牧童……妥清德笔下反复出现的是属于草原的独特物象,虽然已被农庄淹没,但却永远存在于诗人的心中,而且赋予了它们优美的意境。一方面,这种书写形式恰恰是诗人弥补内心缺失的手段。另一方面,将牧歌式的草原生活、代表传统文化的各类物象书写在诗歌中,用文学的形式将传统文化记录下来。
“文化记忆以诸如符号、物体、媒介、程序及其制度等可传输、可流传的客体为载体,替代了寿命有限的人并通过其可传递性保证了长久效力。”[9]虽然妥清德的文学治疗是通过想象对黄泥堡草原文学性的文化观照,但仍然不可否认其对后续黄泥堡草原地区历史、文化等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材料。
(二)引发对传统文化流失的反思
妥清德的创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期,也是众多知识分子逐渐产生文化危机感的初期。妥清德从创作初期便敏锐地捕捉到传统文化危机感,因此其诗歌中精神的创伤在隐隐作痛,而在疗愈创伤的过程中,自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流失的反思,试图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与思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根,是魂,是当代书写者在现代化进程中关注的重要命题。妥清德始终钟情于这一命题,他在诗歌中不断询问的是“黄泥堡的路”,如《雨后》:“牧歌已把我们带到/更广阔的草场/在这里,我向一朵花询问/黄泥堡的路”[7],那是通往黄泥堡人民传统生活风情的路,是被现代化吞没的草原传统文化。《祁连山腹地》中,前半部分勾勒出“羊圈”“牧场”“草原小学”等传统物象,是诗人构建的精神世界。就当诗人遨游在浪漫的精神世界中时,后几句便骤然打破梦境,回归现实:“我从工业城市穿来的鞋/温度很低,噪音很大/我怀念自己民族的寺庙”[7],现实生活中“工业城市”带来的“低温”与“噪音”是对传统黄泥堡的侵蚀,原本生机勃勃的草原在不断地侵蚀下却成了记忆中的物象,诗歌前后反差正是诗人面对文化流失的现实焦虑,同时引发读者的思考,呼吁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再如《迁徙的鸟群》:“迁徙的鸟群/从故乡再到故乡/不是被迫的,它们带着沉重的回忆”[7],鸟群是故土人民的影射,它们无论如何迁徙,仍然带着最初的回憶——传统文化,不过这回忆早已消失在了现代化的浪潮中,变得无比沉重。《路过建筑工地》:“吃土的猛兽。撕下一块土地/又撕下一块土地/我听见大地在疼/另一些村庄发慌/一连几夜睡不着觉”[7]现代化机械在草原上轰鸣,草原土地的疼痛、传统村庄的慌乱正是身为黄泥堡一员的妥清德面对传统文化流失的疼痛。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的传承已然出现了严重的断裂,随之,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也在不断流失,人们也因对社会前沿风貌的追逐而逐渐忘却了中华文化之“根”。文学疗愈只能成为一种消解与安抚,始终无法弥合创伤的轮廓,面对现实,更多的传统文化又该何去何从?因此,妥清德表现出极度的悲痛,在疗愈精神创伤的书写中试图呼唤更多人对传统文化流失的反思。
综上,妥清德的诗歌情感细腻、真挚、深情且疗愈精神创伤。他在诗歌中书写的黄泥堡草原是想象中的故乡,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从空间性的存在变成了时间性的存在的故土,是疗愈精神创伤的需要,通过想象让自我与故乡沉醉在黄泥堡传统文化之中,用文字、诗歌弥补现实已经逝去了的草原,实现精神缺失的疗愈。同时,实现了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并保存了黄泥堡草原传统文化,引发更多人对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流失的关注于思考。从文学治疗的角度解读妥清德的诗歌,我们看到了诗人高超的写作技巧与高尚的文化关怀。
参考文献:
[1]严巍娥.论文学的精神治疗作用[J].新课程学习(中),2012,(12).
[2]段宝林主编.谈作家的责任·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
[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
[4]陈全黎.文化创伤与记忆伦理[J].文化研究,2013,(05).
[5]钟进文.寻根的人——裕固族诗人妥清德诗歌中的民族情结[J].民族文学研究,1999,(03).
[6]华静.诗歌是我的精神家园——访诗人妥清德[N].兰州日报,2020-7-16.
[7]妥清德.风中捡拾的草叶与月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8]严巍娥.论文学的精神治疗作用[J].新课程学习(中),2012,(12).
[9]阿斯特莉特·艾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冯亚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2.
作者简介:
姚烨彤,女,陕西西安人,北方民族大学202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作家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