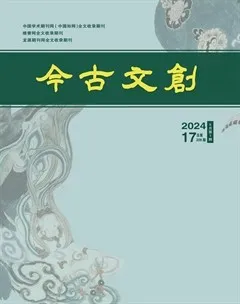王尔德《莎乐美》中两希文化的对立与统一
【摘要】唯美主义的理论渊源与两希文化密不可分。王尔德的《莎乐美》取材自圣经故事,但主角莎乐美对肉欲的狂热却体现出鲜明的古希腊“原欲”精神。两希文化的同步登场,使《莎乐美》对探究唯美主义的深邃内涵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在此基础上,王尔德又将唯美主义寄寓于莎乐美,让莎乐美兼备双重文化身份,使其世俗肉欲跃升至一个唯美主义者对纯粹美的渴求的美学高度,从而在价值观层面统一了具有内在对抗性的两希文化所分别代表的世俗价值与神圣价值,展现了作家独特的创作观、宗教观、道德观与美学观。
【关键词】《莎乐美》;王尔德;两希文化;唯美主义
【中图分类号】I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7-0036-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7.011
基金项目:2023年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王尔德《莎乐美》中两希文化的对立与统一”研究(项目编号:JGY2023038)。
19世纪的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身兼多重文化背景,他出生于一个新教家庭,在作为一名基督徒的同时,又深受古希腊文化这一异教文化影响,并对基督教产生了怀疑。《莎乐美》虽以圣经故事为基底,但王尔德以一种纨绔子弟式的玩世不恭、放诞轻狂对原本的宗教故事进行了亵渎性改编,将古希腊文化中立足感性经验的世俗色彩和自由开放的审美性特征融汇其中,使作为欧洲文明之源的两希文化在剧中同时现身。本文拟在考证《莎乐美》故事与各角色的希伯来文化原型基础上,立足故事发生的时代、王尔德自身文化背景、剧中人物形象,分离剧本中糅合的古希腊文化元素,指出角色的矛盾之中所体现的两希文化的对立,细较王尔德对两希文化的不同态度,进而探讨唯美主义与两希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最终解读王尔德独特的创作观、宗教观、道德观与美学观。
一、《莎乐美》的希伯来文化原型
王尔德的《莎乐美》虽取材自圣经故事,但故事本身与剧中各角色都有其真实的希伯来历史原型。通过结合《圣经》与相关史料的记述,我们可以完整还原《莎乐美》故事与角色的希伯来文化原型。
作为悲剧中的主角,莎乐美在《圣经·新约》中其实默默无名,仅以“希罗底的女儿”为代称。直至同时代的希伯来作家约瑟夫所著的《犹太古史》中,“Salome”(译为“莎乐美”或“撒罗米”)一名才得以出现。“‘Salome一词的希腊文原文是‘korasion,意思是‘乳房尚未发育、还没有来月经的小女孩。至于她跳的舞蹈,希腊原文是‘orxeomai,既是‘舞蹈,又是‘小孩子的嬉戏、做出愚蠢可笑的把戏的意思。可见,莎乐美实际上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孩子。”[1]
莎乐美出身高贵,其亲生父亲腓力一世为希律王朝的开创者希律大帝之子,剧本中对腓力一世着墨不多,仅在配角们的闲聊中略提一二:
卡帕多西亚人:可再怎么说,绞死国王终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士兵甲:有什么好可怕的?国王不也只有一个脖子,跟别人都一样。[2]10
尽管历史对腓力一世的记载同样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莎乐美的父亲其实并不当政,更非分封王。那位分封王腓力其实是其同父异母的兄弟,即希律大帝第五妻次子腓力二世。在剧中,也许是为进一步凸显莎乐美的尊贵,王尔德将两位腓力合二为一,使莎乐美成了国王的独女,而其亲生父亲则被其兄弟希律王囚禁于水牢十二年,最后被希律王下令绞死。
莎乐美之母希羅底则为希律大帝的孙女,先为希律·腓力一世之妻,后又嫁给腓力的异母兄弟希律·安提帕(即剧中的希律王)。在亲缘关系上,希罗底是腓力一世与安提帕的侄女。值得一提的是,施洗约翰的乱伦指责并非是针对叔叔娶了自己的侄女,而是因为犹太教基本戒律的“十诫”之一为“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及财物。”[3]703同样,据约瑟夫记载,按犹太律法,“娶自己兄弟的妻子(除非他没有孩子)乃是令人憎恶的。”[4]272而无论历史上还是在《莎乐美》中,希罗底在与希律王结合之前都已与腓力一世诞下了莎乐美这一后代。故而,希罗底与希律王的婚姻被视为乱伦。此外,史料显示,安提帕原娶了佩特拉王亚哩达四世之女为妻,为迎娶希罗底,安提帕决心废除自己与亚哩达之女的婚姻,从而引发了其与亚哩达四世之间的战争,结果在此战中全军覆没。至公元38年,“希律受希罗底的蛊惑,与其侄亚基帕在罗马皇帝加力果拉前争夺犹太王位,被亚基帕控告私藏武器,结果流放高卢,最后死于西班牙。其领地由亚基帕一世接管。”[3]875-876随后,加力果拉允许希罗底返回故乡,但希罗底却坚定选择了与丈夫安提帕一起被流放。在很大程度上,王尔德是将希罗底的性格抽空,转而填充了莎乐美这一形象,使莎乐美从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自我意识,被母亲操纵的复仇工具转变为了一个敢爱敢恨的蛇蝎美人,而其母希罗底则在剧中成了一个单一而空洞的纸片化人物形象。
此外,《圣经·新约》仅在道德层面提及了施洗约翰被囚禁的原因,即施洗约翰的谴责招致了希律王的愤怒。《圣经》将希律王描绘为一个奸雄与暴君:他杀死了圣徒施洗约翰。耶稣称他为“狐狸”,并要门徒防备“希律的酵”。但历史上的希律王曾“任加利利、比利亚的分封王,在位长达40多年。善于维持加利利地区的和平秩序。”[3]875事实上,希律王与施洗约翰之争其实更类似于政治博弈。根据约瑟夫的记载:
当其他人因听到施洗约翰的话语深受震撼,同样也加入到约翰的追随者行列中时,希律·安提帕便产生了警觉:对民众这样巨大的影响力,可能会导致一场起义,因为这些人似乎随时准备做约翰吩咐他们的任何事情。因此,希律·安提帕便决定更为妥当的处理方法就是:在可能出现任何暴乱之前,先下手主动攻击除掉约翰,而不是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为一旦爆发起义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抱憾。[4]282
总之,历史上的莎乐美与《圣经》中所颂扬的那位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靠吃蝗虫野蜜为生,在犹太旷野约旦河一带给人施洗、宣传悔改的福音的犹太先知施洗约翰之间并无情感纠葛,而是最终同自己的母亲一样,嫁给了自己的叔叔,也即上文所提到的分封王腓力二世为妻。
综上所述,通过结合《圣经》与相关史料,可以完整还原《莎乐美》故事与角色的历史文化原型。王尔德身为一名基督徒,其所创作的《莎乐美》中的角色原型虽都源自圣经故事,但内容却显而易见的带有对基督教的亵渎之意,而王尔德“借以批判基督教的精神资源,主要来自古希腊文化以及与其血脉相通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5]64在下一部分,将着重从戏剧角色中分离其中融合的古希腊文化因素,指出两希文化之间内在的对立性。
二、《莎乐美》中两希文化的对立
《莎乐美》具有其希伯来历史文化原型,但从故事发生的时代、王尔德自身文化背景、剧中人物形象三方面来看,都能发现剧本中糅合了明显与希伯来文化精神相对立古希腊文化元素。
从故事发生时代背景来看,当时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希律一族并非犹太人,而是隶属于以土买的安提帕支裔,属以东后代。希律王朝的开创者希律大帝曾任犹太总督,并因协助罗马人作战获得罗马公民称号,并将此称号为其子孙世代传承。作为古罗马帝国设置的代理统治者,希律一族大力响应古罗马帝国的文化政策,在巴勒斯坦地区推行古希腊文化,借以控制该地区的政治与文化。随着基督教的崛起,作为本土文化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统治地位形成了直接的挑战。可以说,这一历史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本身就受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双重影响。
在作者层面,古希腊文化对王尔德可谓影响深远。古希腊审美中的男同性恋文化在使他产生同性恋倾向的同时,“由于古希腊人崇拜美,崇尚思辨,向往身心和谐向美的生活,因此被古希腊文化深深影响的他在内心深处产生出异教徒对刻板、朴实、缺乏美感的基督教的对抗心理,在言行中透露出亵渎基督教的矛盾思想。”[6]95“从哲学基础来看,唯美主义文艺思潮继承了柏拉图以来的唯心主义艺术信条,倾向于‘灵感说这一艺术起源观。”[7]6作为悲剧的主角,“莎乐美专注于约翰的色相之美,在这一意义上,她象征着希腊、罗马的宗教与文化的美学精神。”[8]她对约翰之美的迷狂显然与诗人在灵感状态下的迷狂如出一辙。而身为神之代言人的约翰则与之相对,其秉持着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所推崇的禁欲主义,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事实上,施洗约翰同样体现出一定的古希腊文化元素。例如,针对《莎乐美》中的“约翰”一名并非法语中的“Jean”抑或英文中的“John”,而是写为“Iokanaan”一事,高卫泉与周敏先生指出,“Iokanaan”一名实为希腊神祇伊娥之名“Io”与迦南地名“Kanaan”的复合体。[9]理查德·艾尔曼则认为,“在《莎乐美》的晦暗事件中,也有阿特柔斯王室中的遗迹。一种厄运感弥漫着整个剧本。乔卡南就像是卡珊德拉,而莎乐美具有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某些特征。王尔德心中常想起的不但有圣经,还有埃斯库罗斯。”[10]468
以此推论,莎乐美与施洗约翰之间的冲突不仅构成了剧情的主线,同时也象征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之间在价值观上的斗争:与强调世界的道德秩序、原罪和最终审判、人对神的服从和人在神面前的卑微渺小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相比,希腊文化“蕴含的是一种张扬个性、放纵原欲、肯定人的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世俗人本意识。”[11]21可以说,古希腊文化所肯定的“原欲”恰恰是基督教文化极力赎还的“原罪”,而这也构成了两种文明在文化内质上的对抗性。对莎乐美而言,杀死约翰不仅是出于爱而不得的病态占有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报复。莎乐美控诉道:“我是个公主,可你鄙视我。我是个处女,可你却用言辞玷污我。我冰清玉洁,可你却让我的血液都燃烧起了欲望……”[2]66约翰为了维持信仰的坚定,从未真正直视过自己的内心,正如莎乐美所言:“你把自己的脸藏在了你的双手和你满口的诅咒后面。你满心想着见你的上帝,这使你的双眼犹如蒙上了绑带。”[2]63约翰的抗拒、侮辱与高高在上的姿态激发了莎乐美爱欲本能中隐藏的黑暗的、充满破坏性的野蛮兽性,被激怒的莎乐美为报复而献舞于希律王,最终通过希律王将施洗约翰斩首。如果说“莎乐美追求情欲的满足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显示出自己作为人的一种主体性与独立精神,体现出希腊式的自由意志与精神”[12],那么施洗約翰身上体现出的“只有对上帝的顺从与依附,缺乏莎乐美的那种独立与抗争意识。尽管他的形象不失神圣与崇高,却因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与独立精神而缺少了几分艺术魅力”[12]。
综上,在《莎乐美》的希伯来文化原型基础上,王尔德将古希腊的人本主义精神与世俗审美性特征融入其中。而王尔德所理解的希腊精神“是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人本的、感觉的、审美的精神,此种精神构成了其唯美主义思想的根基与内核。”[5]67下文将着重分析王尔德是如何在《莎乐美》中借由唯美主义对纯粹美的追寻这一命题,将两希文化所代表的世俗与神圣调和在一起,共同展现自己的唯美主义美学观的。
三、《莎乐美》中两希文化的统一
唯美主义与两希文化密不可分。“唯美主义的纯粹形式和强烈感觉大致代表着世俗与神圣,代表着希腊原则和犹太原则。”[13]42王尔德坚持艺术的独立和自律,其美学教义主张:“艺术只表达自己,除自身外别无表达。它有一个独立的生命,就像思想一样,完全按照自己的路线发展。”[14]208在王尔德看来,艺术具有自律性,能够自我规约、立法与支持。他“以自律性原则消解了艺术的认知、教化的功能,以审美的愉悦代替宗教的救赎,这一切反映在他的创作与生活中,结果就是精美的形式代替内容成为关注的重心。”[5]18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不是从感情到形式,而是从形式到思想和感情。在《莎乐美》中,王尔德对形式美感的追求首先表现为对语言美的追求,包括注重语言的韵律美与精美语象的塑造。他曾自赞《莎乐美》是一部“美的、鲜亮的、富于音乐性的作品。”[15]212除如诗般的语言韵律之外,为了给读者直接而强烈的感官刺激,剧本塑造了众多精美的语象,极力展现声、色、味、触之美,甚至连人的身体也成为一个被物化的存在——莎乐美将约翰的身体比作各种奇珍异宝、绝妙景观,本质上是一种完全着眼于施洗约翰形式美感的物化之爱。“《莎乐美》的一个特点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不复存在。人被肢解开来,人的部分变成一个个单独的客体,成为欲望的对象,进而成为审美的对象。在这里,人被彻底地物质化和客体化了。人的灵魂与主体性已经解构,只有物化的肢体和器官成为感觉的对象。”[16]187故而,王尔德的艺术自律性在造就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之时,对形式美感的过度追求也难免会使其作品丧失深度,并沾染上颓废主义气息。正如卡尔·贝克森将颓废主义视为唯美主义黑暗的一面,《莎乐美》也往往因其颓废主义色彩而被认为是“颓废主义的结晶,是病态性欲的描写,全剧的空气是污浊的,不健康的,男女主角都是害着极其反常的性病。如果不是形式之美将内容伪装起来,掩饰起来,使这污秽不堪入目的内容,放在远远的梦幻的虚浮的意境内,则《莎乐美》只是无数废纸堆里的几页废文而已。”[17]273
“具体而言,唯美主义的世俗价值意向与文艺复兴所发掘的希腊文化有关,而唯美主义的神圣价值意向则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有染。”[13]63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美学对形式美感的极端追求无疑受到了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希伯来文化精神与希腊文化精神之间,英国唯美主义者本来就更加青睐后者。”[5]64在《莎乐美》中,王尔德也显然更倾向于莎乐美这一古希腊精神的化身。“约翰的坚拒是忘我而非自大,但他铿锵激愤的语言与莎乐美喷发着原始生命力的语言相比仍显得空洞惨白——神圣的苍白与世俗的浓郁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8]尽管王尔德对基督教抱有怀疑,想要以艺术代替宗教,以审美救赎来取代上帝救赎,基督教思想却从未在王尔德的创作中退场。在《莎乐美》中,基督教文化也并非仅是作为一个被嘲弄、抨击的对象出现的,它在为王尔德提供具有历史底蕴的题材同时,也使得这出戏剧在欲望与情色中透出神圣。在塑造施洗约翰这一善与美的化身时,王尔德虽“绝非无意地渲染了善在恶行发生过程中所起的催化作用。”[5]130但他对约翰道德的刻意“抹黑”绝非仅是为了表达对基督教的亵渎。他在贬低施洗约翰所固守的刻板的宗教道德时,又极力凸显其带有神性的形式(肉体)美感,使约翰所具备的善与美相区隔,成了带有宗教圣性的纯粹美的化身。“莎乐美充满肉欲的性爱其对象是乔卡南,一个深具圣性气质的基督徒,而不是拥有世俗之美的年轻叙利亚人。这也许只是一个复杂的巧合,也许王尔德还是想说明世俗美深处的圣性美,虽然世俗美也那么诱人地展示着。”[13]93正如王尔德将《莎乐美》视为一部“寻找自我表现的作品。”[15]116莎乐美在象征古希腊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同样是唯美主义的化身,为了追求美不惜付出一切。她对施洗约翰的爱慕是一种无功利的、超越了性别的纯粹审美行为。“作为蛇蝎美人的莎乐美,抛却理性原则,不涉及功利目的,只关注自身的生理欲求,追求带来恐怖感受的激烈情感,显示出她追求新奇、刺激的年轻生命力,也使她同时成为童真式崇高的审美主体和客体。”[19]施洗约翰的崇高神圣之美唤起了莎乐美的爱慕,通过对施洗约翰这一带有宗教神性的审美客体的纯粹审美行为,作为古希腊精神象征的莎乐美也在追随美的过程中获得了崇高与圣性,超越了单纯的世俗肉欲美感。“借助艺术对无限精神的触探,感官感觉就能够接近神圣了。唯美主义也在此与滞留于感官的纯粹堕落分道扬镳。”[13]42以此,基于唯美主义对纯粹之美的追寻这一命题,《莎乐美》将古希腊文化所代表的世俗性、形式美与希伯来文化的宗教神性调和一体,使两希文化在作品中有机结合,展现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
四、结语
对基督徒而言,通奸和乱伦的题材是可厌的。但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异教精神重新崛起,基督教逐渐失去了控制人们思想的力量。“仅以近代悲剧而言,我们可以说,近代悲剧唯一有点独创性成就的地方,就是它表明了异教精神对于基督教的胜利。”[20]198但事实上,“正是两希文化的冲突、融合、相互作用的张力构成了文艺复兴艺术与唯美主义价值意向之双重性的文化根由,这种双重性就是:神圣与世俗。”[13]13《莎乐美》中各角色的原型皆源自基督教《圣经》,王尔德又将鲜明的古希腊文化因素,特别是其对世俗欲望的肯定与对形式美感的强调糅合其中,使原本歌颂基督徒坚定信仰的宗教故事充满欲望与情色的同时,却并没有停滞于单纯的感官满足,而是借由基督教文化的宗教圣性使其超出了世俗欲望,上升到美学的高度。王尔德为莎乐美这一形象注入唯美主义的精神内核,使莎乐美之死也象征了自己对美的殉道,在践行自己唯美主义美学信念,即“生活中没有什么是艺术所不能神圣化的”[14]130的同时,也在价值观层面将具有内在对立性的两希文化精神调和至统一。
参考文献:
[1]高黎.《圣经》中的莎乐美[J].传播力研究,2019, 3(30):33.
[2]王尔德.莎乐美[M].吴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3]梁工.圣经百科辞典[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5.
[4]约瑟夫.约瑟夫著作精选[M].保罗·梅尔编译,王志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陈瑞红.奥斯卡·王尔德:现代性语境中的审美追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6]杨霓.王尔德“面具艺术”研究:王尔德的审美性自我塑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7]薛家宝.唯美主义研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8]谈灜洲.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对莎乐美故事的改写[J].中国比较文学,2003,(02):55-64.
[9]高卫泉,周敏.比较神话与历史书写视域中重读《莎乐美》[J].中国比较文学,2019,(04):126-140.
[10]理查德·艾尔曼.奥斯卡·王尔德传[M].萧易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1]蒋承勇.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从古希腊到18世纪[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曹万忠.《莎乐美》:“两希”传统的冲撞与交融[J].四川戏剧,2012,(05):56-58.
[13]刘琼.神圣与世俗:唯美主义的价值意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14]王尔德.王尔德文选:镜子、谎言与瞬间[M].耿宏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15]王尔德.美之陨落:王尔德书信集[M].孙宜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16]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7]袁昌英.袁昌英作品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 1985.
[18]李小驹.王尔德的《莎乐美》及其圣经原型[J].襄樊学院学报,2003,(06):39-43.
[19]宫昀.王尔德《莎乐美》:恐怖原则下的童真式崇高[J].四川戏剧,2020,(06):146-149.
[20]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1.
作者簡介:
李泽华,男,汉族,山东青岛人,吉首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