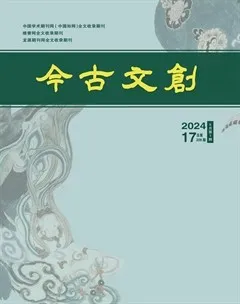多元的理想
【摘要】泰居·科尔是当代美国文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作为一位定居在纽约的尼日利亚裔作家,他的代表作《不设防的城市》(Open City,2011)以其独特的哲思散文式笔触开启了当下大众对于城市“情感”历史和自我存在的探索。科尔在小说中运用的象征手法不仅使主人公形象鲜活饱满,充分体现了人类矛盾的本质,同时,也巧妙地升华了小说的主题思想,传达出科尔身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关怀。
【关键词】泰居·科尔;《不设防的城市》;象征;世界主义;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7-003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7.010
一、前言
泰居·科尔(Teju Cole,1975—)生于美国,长于尼日利亚的首都拉各斯(Lagos),双重的身份或许也是他崇尚世界主义的根源之一。作为一名新人小说家,科尔至今公开发表的小说只得两部,但每一本作品的出版都引起了当代美国文学界的热议。科尔于美国文学界出道的处女座《不设防的城市》(Open City)[1]一经发布,就登上了当年的十大畅销书单,且广受读者和各大媒体的青睐。《不设防的城市》一再荣获海明威奖、国际文学奖、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罗森塔尔奖和纽约市小说奖等多项文学大赏,这些荣耀也正式宣告了科尔作为美国主流非裔作家的出道。科尔笔耕不辍,他的第二部小说《每日为盗贼》(Every Day Is for the Thief)[2]诞生于2007年的尼日利亚,2014年在英美再版,同时译有其他6种语言,这本小说也在同年被《纽约时报》等多家主流媒体称为“年度最佳书籍”。
《不设防的城市》带有科尔本人的身份印记及他对纽约这座城市所代表的美国社会、布鲁塞尔所代表的欧洲社会和拉各斯所代表的黑人国度的有关政治、历史和身份错位的思考。《经济学人》曾经称《不设防的城市》是“对爱情、种族、身份、友谊、记忆和错位的精确而富有诗意的沉思”[4]。为了更清晰地阐释他对于这一系列有关身份、种族、错位和记忆的思考,科尔在小说里尽量使人物间的对话贴近于真实,就像“我们常在生活中可以听见的那样”。这一点无疑是使小说受众广泛的關键之一,但同时,小说中也成功地运用了象征手法,包括连贯小说始末的飞鸟和自由女神像、隐秘在生活角落里的床虱(bedbugs)以及音乐。这些象征意象不仅映射了当代社会对于所谓移民或外来者、种族和身份错位的思索,使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真实丰满,最重要的是,它们对升华小说的主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孤勇的鸟群——主题与人物象征
科尔在《黑纸》中谈道:“翻译是一个情感与理智并存的文本分析兼具共鸣的过程。”[3]他以一次与自己的德国译者就小说开篇的标题“死亡看似如此完美”(“Death is a perfection of the eye”)如何尽美转换为例,蜻蜓点水般向读者透露出些许写作《城市》的意图。科尔言之再三,所谓的“眼”并非是世俗普遍意义上的生理器官,而是“看见”这个功能本身。因此,死亡可以被视为是通向一种视觉圆满的路径。(“death was being proposed as the route to a kind of visionary fullness”)[3]
“死亡看似如此完美”,初见使人疑窦丛生,再品便意蕴含蓄深远,耐人寻味。主人公朱利叶斯热爱观察鸟儿迁徙,将之作为下班之余缓解身心的一种寄托。雁群迁徙的景观在为朱利叶斯带来心灵上疏解的同时,也引起了他对自身记忆的质疑。他忧心忡忡,怀疑这些鸟儿是否真实存在,也不时扪心自问:“我很讶异,如果没有见到这些鸟儿,我竟然连自己的记忆都无法信任。”[1]主人公的有感而发正是对纽约“开放的”移民政策的质疑。
某日夜游,主人公途径自由女神像,被神像背后坐落的“传奇”的埃利斯岛吸引了目光。它曾经是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在1954年以后关闭。无论是对于早期的非洲人(“而且他们的身份也不是移民者”[1])来说,还是诸如当代的非裔移民,埃利斯岛毫无意义,因为,它“象征的几乎就只是流亡美国的欧洲人”[5]。
自由女神像在黑夜里闪烁着的荧荧绿光掩盖了过去港口浴血的罪恶,带来的是新的希望与新的死亡。聪慧的鸟儿往往可以避开城市中的摩天大楼,却屡次坠落于自由女神像手中,就人类而言,这不过是“单一的火把”。朱利叶斯为此讲述了一个有趣的轶事:1888年,自由岛上的官员将经历了某一暴风雨之夜后,于自由女神像上断送了性命的一千四百只鸟儿贱卖给当地的商户,充作时尚的装饰用品。可惜这一商机被当地的军事指挥官打断了,塔森上校义正词严:“鸟儿的实体只能用作科学研究,禁止商业贩售。”[5]而这恰恰又是美国历史上多年来贩卖奴隶的真实历史,当地的印第安人遭到屠杀与驱赶,外来的非裔与亚裔是随意买卖的货品,更有甚者被置于打着为科学献身为旗子的实验室里饱受折磨。
自由女神像“从一开始就有着指引旅人的象征性意义”,她是美国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宣誓,也是来美移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地标。于是,科尔借助纽约城里形形色色的人物,阐述着一只只离群索居的鸟儿的故事。这些人都代表着美国社会各阶层典型的外来移民的一员:高知的亚裔,带着过去旧影的老黑人,非白人的同性恋,生活在底层终日奔波的非裔,以及像主人公这样出身的黑白混血儿。无论是已经在社会上取得较高地位还是边缘地带的移民,作为“卑鄙的异乡人”,他们总是面对着无形的壁垒。一方面,科尔利用移民们的遭遇,迫使读者去怀疑所谓的公平、平等和自由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这却又恰恰说明了大熔炉里需要的真正平等的重要性。
科尔用鸟群来象征移民,用自由女神像撕裂美好的面具,但又对生活留有希望。所有移民都是孤独的行者,又是勇敢的奋斗者,身陷囹圄仍然拼尽全力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科尔将视线对准国际大都市中游离于边缘的各少数族裔,尤其是非白人的移民群体,呼吁社会关注新时代下多民族混合产生的困境,体现了高尚的人道主义关怀。
三、“隐形”的床虱——虚伪的社会本质
科尔曾在《黑书》里写道:“虚伪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特征。”(“Hypocrisy is common to all societies.”[3])他是在戏谑挪威,“早上交易军火,晚上便转眼颁发诺贝尔和平奖。”(“War machines in the morning, and in the evening the Nobel Prize.”)《城市》中基本所有非白人的移民都经历着一条大同小异的命运线:移民寻求新的希望——努力奋斗——遭受挫折——失望——继续挣扎寻找。他们遭受的歧视与冷遇,在这个大谈“政治正确”的时代里必然不是光天化日的,却如无孔不入的床虱一般,藏形匿影,灼烧着“自由”与“平等”,唾弃了“开放”与“文明”。
从利比亚历经千辛万难而来的非法移民赛都,怀抱着美国自由之都的信念,却最终只能龟缩在棺材似的监管楼里,唯一的交流是与探监的陌生人不交心的寥寥数语,最大的愿望是“外面”看一看他心心念念的美国,但他的结局是静默着等待归国的港湾。地铁里的海地擦鞋匠,年轻时作为奴隶来到纽约,备受白人主家的优待因而充满热忱,即使已有资本为自己赎身也坚持等到所有主人离世,等来的是沧桑年迈后苦于生计的奔波与孤苦无依。颇受朱利叶斯敬重的日裔斋藤教授,在失去年轻时的同性爱人及从大学退休后,逐渐形单影只,只好日益沉浸于内心的文学与回忆,直至病重离世前只剩下主人公的偶尔拜访。无独有偶,城市里渴望受到认同的黑人司机与博物馆门卫,移民大楼外衣衫褴褛的亚裔与非裔,夜晚后只余黑人的哈莱姆社区,地铁站里泾渭分明的黑白工人,他们都是自由的奴隶,他们到了应许之地,却被迫戴上了镣铐。
如果说纽约是代表了美国帝国主义的城市,那么布鲁塞尔就代表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布鲁塞尔声称自己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open city”,但是一路来朱利叶斯听见的是本土人对外来移民的极大恶意,舆论与政治不择手段地煽动民族仇恨情绪,这些赤裸裸的恶意使人胆战心寒。也是在这座城市,朱利叶斯遇见了弗朗科,一个同他一样不信宗教,心中谋求着“求同存异”梦想的“同位体”。
弗朗科的命運,不出其外,也重复着移民们共同的命运。他为寻求新的梦想来到所谓的“自由之都”布鲁塞尔,可惜处处碰壁,饱含心血的论文被斥为作弊,最后沦落到一个电话厅当前台。弗朗科还在为自己的理想拼搏,他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当作一个试验,即无论国籍与肤色,大家都相安无事地坐在自己的电话卡座上,各谋其事。科尔或许也在通过角色之口诉说自己的心愿:“在保证自己信仰与价值完整的同时,人们是可以和平共处的。”[5]这当然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的诉求。
奇异的是,最先大范围实现这一理念的是泛滥成灾的床虱,尽管它们作为昆虫来说并未共享任何人类的道德观念:床虱对社会上的所有群体都一视同仁。在面临着许多重大疾病和病毒的现代社会,床虱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是在征服了如天花病毒的医学技术面前,床虱仍然无所不在,春风吹又生。科尔把“不设防的城市”中无形的枷锁——傲慢与偏见,化为有形的存在,即床虱。床虱还负有一个极似人类的特质:同类相残。床虱的存在不仅是人们心中藩篱的具现化,同样也是人类文明出现以来自相残杀历史的缩影。《不设防的城市》通过“床虱”象征揭示了现代社会虚伪的本质,以及纽约矛盾的“开放”政策,科尔再一次表现了对种族、宗教和身份错位的深度思考,如果人类社会仍然以虚假和偏见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开放”的大都市将会是促使人类毁灭自己的坟墓,正如科尔借主人公之眼向读者言明:“底下的这座城市是座巨大坟场,充满了大小高低不同的白色大理石及石砖。”[5]
四、“无国界”的音乐
音乐的意象也是科尔笔下揭示文章核心的重要一环。科尔在《黑纸》中的“萨义德四重奏”一章里提到,小说“以马勒的《大地之歌》开始,又以叙述者在最后一章听到柏林爱乐乐队演奏的马勒后期名作《第九交响曲》结束”[3]。因此,尽管小说的大部分地点都发生在纽约,但是带来主人公心灵安逸的却在德国,柏林。正如,朱利叶斯为寻找德国祖母的消息远赴布鲁塞尔,他更多的是在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寻求自己的完整,“柏林,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座教诲了我许多文化记忆的城市。”[3]
与此相反,描写主人公对于古典音乐的喜爱是为了解构非裔对爵士乐狂热的刻板印象,以及多数白人潜藏在诚挚脸皮下的虚伪自大。朱利叶斯在前往布鲁塞尔的飞机上结识了一位定居于美国的欧洲白人,他们相谈甚欢,尽管一开始这位女士言辞中带有对黑人轻蔑的影射,但她马上就迫不及待地炫耀自己对爵士的喜爱,宣称自己与多为黑人音乐家私交甚佳,还热情邀请朱利叶斯离开布鲁塞尔前共同用餐。被这样的表象所迷惑,朱利叶斯坐上了这位女士的餐桌。两人之间的相处同样如沐春风,可在朱利叶斯尝试提起摩洛哥友人的“在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同时,大家可以和睦共处”的梦想时,却遭到这位女士的冷眼相对。她不经意间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言明在一个群体里生活可千万不要遐想什么不同,既然要追求不同,又何必融入。女士的言辞咄咄逼人,嘲笑年轻人阅历太少,痴心妄想,轻飘飘的话语满是白人的虚伪与傲慢,再不见之前谈起爵士乐以展示自身支持文化多元的诚恳伪装。
爵士作为“世界音乐”的权威地位在科尔的笔下沦为揭穿社会虚伪的一把利器。小说主人公对爵士的冷漠和他对古典乐的热情,不仅是主人公身上的多重身份导致的(纽约,拉各斯,柏林),而这恰恰是为了脱去黑人与爵士之间牢不可破的外衣。诚然,爵士作为黑人文化的集大成者,为提升黑人的社会地位功不可没,但是如此这般的刻板印象却反而固化了非裔的阶层。
即使是在黑人群体内部,一元化的音乐也必然受到攻讦。多元文化杂交的时代,民族文化的记忆问题势必受到重视。科尔以音乐为茅,直指帝国主义的核心:如果多元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交融,那么多元就成了一元,“杂交最后就成了单亲繁殖”[6],更遑论民族内部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的前途。“多元化应当是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前提下的统一”[6],反之,“开放的”“不设防的”城市就是帝国主义最可笑的谎言。
五、结语
三种主要的象征意象都汇交于小说的标题,即不设防的城市,抑或是开放的城市,这是作者的诉求,是身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理想国:所有民族,无论肤色,无论文化,无论信仰,都可以在同一个世界上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地和平共处。作者不仅仅满足于重新描绘新时代下黑白种族之间的关系,他把自己的目光跳脱出肤色的界限,聚焦到宗教间的针锋相对,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刀光剑影,外来人口与本地人之间对资源的明争暗夺,而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社会沉疴。科尔以“不设防的城市”畅想真正的“开放”,以小说角色的“自由”书写社会的不自由,引发读者对社会虚伪性的思考;他以笔下对城市新旧记忆的交织,抒发自己世界主义的多元理想,寻求现实世界里志同道合的力量。
参考文献:
[1]Cole,Teju.Open City.New York:Random House, 2011.
[2]Cole,Teju.Every Day Is for the Thief:Fiction.New York:Random House,2014.
[3]Cole,Teju.Black Paper:Writing in a Dark Time.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21.
[4]The Economist staff.“Bird's Eye View.”The Economist,30 July 2011,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24803.Accessed 15 November 2022.
[5]泰居·科爾.不设防的城市[M].杨馨慧译.台北:远流出版社,2013.
[6]张德明.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J]. 外国文学评论,2001,(3):11-16.
作者简介:
何嘉丽,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非裔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