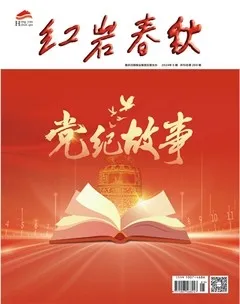江竹筠,“姐”是如何炼成的
杨新



学霸复习两个月考上川大
江竹筠人生最初的打开方式,是寒门子弟外加“学霸”。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在四川富顺县一普通农家。其父江上林长期在城市漂泊,一年两载才回家一趟。出身城市平民、不会种地的母亲只身带着她和弟弟,在农村勉强度日。
江竹筠八岁那年夏季,四川发生了一场大旱。眼看三人走投无路,陷入绝境之际,在重庆的三舅李义铭来信,让她们到重庆共克旱灾。
出身贫寒的李义铭,靠受教会资助考上华西大学,毕业后从医,以此起家。当时已是重庆精益中学校长、红十字医院院长、蜀通轮船公司董事,还有独自开办的义林医院,是重庆颇有分量的人物。
到重庆的决定显然对江竹筠的人生大有好处,因为她有了读书的机会。十岁时,她的母亲想方设法省下钱,把她和弟弟送到了重庆道门口一所教会小学。
江竹筠对第一次上学刻骨铭心,她多年后总是对人说,她和弟弟跨入校门时,回头一望,母亲正在后面笑着抹泪。然而,这次令母亲流泪的上学生涯只持续了一个学期。父亲供职的蜀通轮船公司破产,他竟撇下妻子儿女三人,回老家去了。为减轻家庭负担,江竹筠辍学进袜厂当童工。小人儿还没有机器高,只好站在特制的高脚凳上操作。
好在这样的日子不算太长。在三舅的帮助下,12岁时她重新走进小学校园。但父亲的无能与不负责任,母亲的刚强与辛苦,以及逃过荒、当过童工的苦难经历,都给江竹筠年幼的心灵划下了深刻的痕迹,养成了她踏实、独立、倔强、敏感的性格。她决心努力读书,早日工作养活母亲。
从12岁到21岁的九年里,她先后到重庆私立孤儿院小学、重庆南岸中学、中国公学附中读书,最后考入黄炎培开办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直至1941年夏天毕业。这几年的学校生活,她过得有声有色。小学一年级一学期连跳三级,直接进入四年级,成绩仍是全年级第一。在南岸中学学习期间,她每学期都拿奖学金。李义铭以她为荣,把她获得的、代表学校最高奖励的盾牌置于书房,哪怕她身陷囹圄,时人谈之色变,依然不换。
1944年9月,江竹筠工作三年后考入四川大学。这次入学并非有意为之。这时她已是党员,也有了社会职业,本来没有再学习的计划,仅仅因为这年5月,党组织安排她撤到成都隐蔽,她难以找到适当的职业,才在6月初决心报考四川大学。短短两个多月,江竹筠复习、补习高中的全部功课,竟然顺利在9月考入川大,许多人对此觉得匪夷所思。
事实上,作为天资不太聪颖的“学霸”,江竹筠亮眼的成绩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自律和比常人更加努力的勤奋。平时她不言不语,文静到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若有学习上的问题没有弄明白,她就会问个不停,完全没有那个年代女学生惯常的羞涩和好面子。小学同学卜毅对此印象深刻。
一次,卜毅被问烦了,说她:“你有完没完?”她反倒理直气壮地搬出在孤儿院小学里学到的粗浅教义,滔滔不绝地说:“同学之间应该仁慈博爱互相帮助,你这样不耐烦,是不是忘了做同学的根本?”她一反常态的泼辣模样实在呛人,让同学们目瞪口呆,由是获赠“地胡椒”(巴渝一带一种很辣的辣椒)的绰号。
十九岁加入党组织
正如所有的英雄都有其成长的轨迹,江姐不是一开始就是“姐”的。
抗战爆发的时候,江竹筠正在上中学。“要做斗士,不做装饰!”是那个年代知识女性中流行的一句话,江竹筠非常喜欢,奉为圭臬。在“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大环境和身边党员老师们的启发下,江竹筠骨子里属于“地胡椒”的辣性被彻底激发。她和同学们一起,成群结队地走出教室,涌向田间、街头,组成歌咏队、演讲队、壁报队、募捐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之中。
她很快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受到学校党组织的注意。其时,重庆已经不同于几年前一个党员皆无的荒芜状况。早在1938年3月,中共中央就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要求各地党组织把“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当作“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川东地下党因此迎来了大发展。各大学、中学是发展党员的重点地方。于是,在中国公学附中读高中的江竹筠成为大发展中的一名党员。
江竹筠的同学兼好友戴克宇是学校党支部委员,她介绍江竹筠入党,支部书记李培根则是江竹筠入党的批准人和宣誓见证人。多年后这对夫妻还能够清晰回忆起江竹筠入党宣誓的情景:那是1939年的一个夏日,学校附近幽静的竹林里,她庄重地举起右手,小声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优秀的地下工作者
江竹筠踏实、稳重,遇事冷静、沉着,善于联系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引人注目,很快在地下环境中崭露头角。1940年秋,她有了生平第一个党内职务——中华职业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那时环境恶化,她所在的江北县党组织,几次发生组织被破坏、党员被捕的事件,连续三任县委书记被川东特委、重庆市委紧急疏散。但是,她领导的组织不仅没有暴露,而且有所发展,显露了她作为优秀地下工作者的素质。
之后,江竹筠先后成为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助手,负责过重庆育才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西南学院等学校党的工作。其間,她换过多种社会身份,先是在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当会计,后又转移到綦江铁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合作社、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等处工作,并于1944年转移到成都考上四川大学植物病虫害系。
人们常常津津乐道她在校读书时为澄清皖南事变真相巧撒传单的故事。那时,新四军被诬蔑为“叛军”,所有报纸、媒体都不得发表为之辩白的报道,普通人根本不知事变真相。重庆地下党员都被动员起来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等传单,江竹筠所领导的党组织也接到这个任务。
那时到处都在抓人捕人,江竹筠不能暴露自己,就和何理立商议深夜将传单放到教师办公室和教室。可她们的宿舍在二楼,二十多人睡两排地铺,一个挨一个,两人又睡在中间,半夜起来惊动众人怎么办?
恰好当时流行跳交谊舞,两人便商定睡觉前教大家跳舞。一干女生劲头十足,最后累得腰酸腿胀,熄灯后很快睡着了。夜半时分,二人轻手轻脚地下楼。教室的门锁着,她们就用石块把传单压在门口和走道上。第二天早晨,中华职业学校师生们看到传单,全校哗然,纷纷同情新四军,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发动内战的不义之举。
而江竹筠的秘密活动还在继续。《挺进报》本是重庆市委的机关报,却因小说《红岩》而扬名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江竹筠就承揽了大部分的分发投递工作。
在国统区秘密办报,供稿、刻印、投递都是大问题,其中最危险的就是投递。白色恐怖中一份报纸要经过重重关卡,安全送达收件人手中可不容易,每个环节都要确保安全,不能出错。江竹筠为此智计百出,费尽心血。邮检严格,她就想方设法找来国民党财政局等单位的信封;街头邮箱被盯,她就通过邮局人员内部投寄;有的地方不通邮,她就建立秘密转发站专门分发。在她手中,《挺进报》的发行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地下党员王珍如曾参加过一次投递工作,她清楚地记得,当时江竹筠和她好像一对出门逛街的好姐妹,提着一个绿色的帆布袋就出发了。第一站是民生路邮局,江竹筠一边和她说笑,一边四下望了望,没等她意识到,江竹筠就已经从帆布袋中取出一叠早装好的信封扔进了邮筒,然后说笑着离开。上半城的投完了,两个人又转向下半城……为了让敌人摸不到邮路的规律,她们将整个城区的邮筒都投了个遍。
她被叛徒带特务抓走
1948年,江竹筠通过四川大学的同学在万县地方法院谋得一个雇员职位。她日常与法官为伍,掩护下来,参加万县县委的工作,与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保持着密切联系。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的特务以《挺进报》为突破口,先后逮捕了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二人相继叛变。
6月中旬,江竹筠收到一张卢光特从重庆带给她的纸条,上面写道:“渝地瘟疫流行,友人住院,谨防传染。”江竹筠明白重庆党组织一定出了大问题,立即做好应变准备。她设法通知在大佛寺小学教书的周毅尽快离开万县,并亲自置备行装,送其上船。
6月11日上午,冉益智引着一批从重庆专程来到万县的特务,在杨家街口码头看端午节龙舟竞渡的人群中,抓捕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涂很快叛变。
6月12日,雷震没回家。6月13日,雷震仍没回家。江竹筠心中断定雷震是被捕了。她做好了离开万县的准备。
6月14日午饭后,江竹筠趁同事们在睡午觉,从万县地方法院出来,准备去找个可靠的交通员,给长江南岸百里外龙驹坝的地工委委员唐虚谷带信,告知他这几天万县的气氛不大对,要特别注意提高警惕。
刚跨上马路,没走几步,突然听到有人叫她“江姐”,听声音很熟。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冉益智。冉益智急步上前,过分亲热地对江竹筠说:“你好啊!”
江竹筠心里一怔,问:“你怎么到万县来了?”“哎呀,我专门找你来了!”“找我?”“是呀!三哥他叫我……”江竹筠心中浮起阵阵疑团,这个冉益智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因工作关系,在重庆曾与彭咏梧有过交往。但下川东地工委直属川东临委领导,重庆市委与下川东地工委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没有任何联系。现在这个人突然来万县找自己做什么?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
“哪个三哥?”江竹筠边说边往前走。姓冉的挡住江竹筠:“你问哪个三哥?嘿嘿,老王呀!”江竹筠大吃一惊。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纪律,在大街闹市绝对不许交谈党的任何事情,更何况把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直接提出来。江竹筠突然想到卢光特从重庆带来的纸条,她觉得姓冉的肯定有问题。
“啥子老王、老张,我不认得!”江竹筠回答得斩钉截铁。
冉益智原形毕露,将江竹筠拦住:“你等等,我找你有话说……”江竹筠掀开他,愤恨地说:“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啥?”
这时,周围突然涌上来几个穿美制米黄色咔叽军装的武装特务。江竹筠完全明白了,她挣脱特务的手,走向冉益智,伸出手使劲打了他一记耳光,满脸的鄙夷化作一声痛骂:“狗!”
狱中组织难友总结教训
江竹筠被特务押解到重庆后,先在重庆行辕二处受过刑讯,后又被关进歌乐山下的重庆渣滓洞监狱,更是刑讯不断。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弄清了江竹筠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后,妄图从她口中打开缺口,以掌握下川东游击队暴动的种种情况,便亲自对江竹筠进行审讯。
徐远举先是对江竹筠劝降:“今天是叫你来交组织的,你不要怕,我们知道,你一个妇女起不了多大作用。只要把组织交了,就给你自新。取保释放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也可以。”接着他提了一大堆问题:“你在下川东干什么?你的丈夫是谁?你是哪一个领导的?你又领导哪些人?有多少武器弹药?”
江竹筠回答:“我在万县地方法院当小职员,只身一人,不懂什么组织不组织,领导不领导,根本谈不到这些事。你们应该马上释放我。”
徐远举威胁:“这是什么地方,你应该明白。到这里来不交组织是出不去的。冉益智、涂孝文你知道么?彭咏梧是你什么人?”他一连又提了10多個问题,江竹筠一概回答“不知道”“不认识”。后来对这类重复的审问,她干脆不予回答。
徐远举凶相毕露,指着各种刑具大叫道:“你看这是些什么东西?今天你不交待组织就不行,一定要强迫你交。”江竹筠回答说:“什么行不行,不行又怎么样?我没有组织,马上砍我的头也砍不出组织来!”
徐远举下令用刑,用竹筷子夹手指,江竹筠几次痛得昏死过去,特务又用凉水一次次把她浇醒。她依然吐字清晰地回答:“你们可以弄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没有!”
狱中,江竹筠起草了一份有关总结教训的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为此,难友们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时,白公馆的党组织也在就同一问题多次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