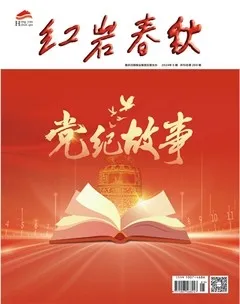重庆党史上三个重要阶段的政治生态
简奕



早期重庆党团组织的政治生态
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党组织的政治生态,开端并不算好。
四川是先建团、后建党,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四川就有党团员活动。1922年,重庆、成都等地最早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以后陆续发展到泸州、内江、宜宾、涪陵、綦江、南充、万县等地。以此为基础,各地团组织在四川开展工作,代替党组织发展党员。
但是,四川产生统一党组织的时间却很晚,迟至1926年2月,中共中央才同意在重庆建立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统一领导四川工作。这个时间显然晚于全国很多地方。之所以这样晚,根本原因就是四川团组织的政治生态不太好,导致中央对四川产生疑虑和不信任,迟迟不同意建立党组织。
四川团组织政治生态不太好的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成都、重庆两地团地委之间争吵不断;二是重庆团地委主要领导人素质极差,广受诟病。
关于成都、重庆两地团地委之间的争吵,实质上是成都团地委领导人王右木和重庆团地委领导人童庸生把个人矛盾上升为组织矛盾。其实,从两人关系而言,王右木是四川最早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成都出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就包括童庸生,两人可谓师生关系。但在成都团地委成立后,两人发生严重冲突,仅仅一个多月,童庸生等人以退出成都团地委、转而参加重庆团地委的方式与王右木公开决裂。童庸生的行为,影响了一批人相继退出成都团地委。
在童庸生加入重庆团地委并成为重要领导人后,两地团组织屡屡致信团中央指责对方,用词之尖锐,远超批评的范围。例如王右木称,童庸生“受安派(即无政府主义派)利用”,而童庸生指责王右木“投机于社会主义”“耻与为伍”。两地的矛盾长期存在,直到1924年王右木在贵州牺牲后才有所缓和。
关于重庆团地委主要领导人影响团的声誉问题,指的是唐伯焜。唐伯焜虽是重庆最早的党员之一,并受党指派,承担在重庆建立团组织的重任。但從各类史料分析看,其人素质堪忧。他经常为了私事不参加团的工作和会议,甚至“沉溺妓者家中”。共产党员恽代英致信团中央反映,唐伯焜“近荒唐而多虚荣心”,居然把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身份印在名片上招摇。萧楚女也说他把重庆团地委视为私有,企图一直把持,颇有“我必终身任事之势”。他作为重庆团地委实际负责人期间,重庆团地委活动乏力、组织涣散,团中央因此对重庆团地委的工作很不满意,委派萧楚女为驻川特派员,整顿重庆团地委。
直到杨闇公的出现,重庆团组织的问题才得以根本改变。
杨闇公是四川党组织的创建人和卓越领导人。在中共革命史上,杨闇公不仅以能力卓绝著称,更以坚决的革命性闻名,连当时远在广州的毛泽东对他也印象深刻,知道“四川有一位杨闇公”。1924年9月,杨闇公加入重庆团地委,迅速成为灵魂人物。
杨闇公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当他发现重庆团组织的主要问题在唐伯焜身上后,立即团结全体同志,积极配合萧楚女整顿重庆团组织,力主调整领导人选,最终由年轻的罗世文担任书记。1925年1月,重庆团地委进一步改选,杨闇公以公认的才干当选为代理书记。
重庆团地委领导人选的成功调整,极大地修复了团组织的政治生态。此后,杨闇公领导重庆团地委焕发出巨大的工作热情。他通过成立劳工互助社等合法组织,团结工人群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通过创办《曙光》等机关刊物,积极传播革命理论,开展反帝反封建舆论宣传;他领导发起了反对“德阳丸案”“五卅惨案”等反帝浪潮,扩大了党团员在群众中的号召力;他协助吴玉章在重庆开办中法学校,团结培养了大批骨干……从而使重庆团地委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影响力远超其他地方团组织,逐渐成为领导四川革命的坚强核心。
杨闇公修复政治生态的过程非常艰辛,但最终得到中央高度认可,中央同意成立中共重庆地委,并授以领导四川全省工作的重任。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委在重庆二府衙杨闇公的家里正式成立,杨闇公成为四川党组织的首位书记。
最能体现这一时期重庆党团良好政治生态的,莫过于杨闇公以批评会妥善处理杨洵向团中央反映重庆团组织的事件。
1925年12月24日,重庆一名叫杨洵的共产党员写信给党、团中央,反映重庆团地委存在“指导非人”“团体个人化”“同志无理论上的训练”等问题,甚至指责重庆团地委成员“许多是不学无术,骄满嫉妒遗传思想根深蒂固,渝地的同志散沙一盘,各不闻问”。其实,杨洵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基于他和团地委领导人童庸生之间的诸多不愉快和误会。但是,党、团中央高度重视,当杨闇公等人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严肃批评“重庆显然有两派的现象”,责成重庆党、团地委专题召开批评会。
杨闇公诚恳接受中央批评,严格遵照执行。1926年4月15日,经过充分的准备和酝酿,重庆党、团地委领导干部共10人,在杨闇公的家里召开了批评会。从保存完好的批评会纪录中可以看到,会议程序严明,陈述客观公正,参会同志的批评字字句句触及实处,杨闇公最后的总结一针见血。杨洵、童庸生两人深受教育,从刚开始的互相指责,到最后诚恳接受批评,达到了消除误会和矛盾的目的。会后,当事人未受任何影响,一身轻松地投入紧张的工作。童庸生始终战斗在四川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后于1930年牺牲;杨洵发挥理论功底深厚的特长,一边搞宣传,一边做统战工作,不幸在1949年12月7日牺牲于黎明之前。
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不仅解决了杨洵、童庸生之间的矛盾,更检验了杨闇公领导下的四川党团组织政治生态的成色。在这样一个正气充盈、是非分明、团结奋斗的党团组织领导下,四川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成为全国工作开展得最好的地区之一。
南方局重庆8年的政治生态
1939年1月,在党中央领导下,周恩来在重庆组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此后8年多的时间,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吴玉章等一批富有经验的革命家领导下,尽管斗争环境异常恶劣,南方局的政治生态却非常好。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领导班子党性原则强,带头从严治党;二是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三是南方局工作效果好。他们坚决贯彻中央要求,严格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作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周恩来初到重庆,就指示南方局举办“干训班”,从整顿国统区党组织,健全领导机关,加强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等入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南方局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以帮助他们在特殊环境下,进一步增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经受住险恶斗争的考验。
1942年春至1945年春,南方局开展了整风和审干工作,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既是领导,又是整风学习中的普通一员,他们处处以身作则,严格剖析自己,从不以领导自居,不以改造别人的面孔出现。周恩来曾教育廖承志,“对一个领导者来说,领导作风就要民主”,“一个好的领导者,要能主动造成下边同志敢同你争论问题的风气”。他总是尊重他人观点,重视反面和批评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决策。
在党内生活中,南方局領导层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严格批评,深挖根源,但绝不上纲上线,不让人背上包袱,真正做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致电董必武,批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反击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却刊登了几篇宣传宋子文、苏州反省院院长等国民党官员以及宪政方面的文章。指出平时对蒋介石国民党用头条大标题,这样的安排太不妥当。事实上,早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董必武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先后召开两次座谈会,几位当事人章汉夫、陈家康、乔冠华和夏衍等都受到批评。接到指示后,又进一步深入批评。
11月26日,董必武主持召开第三次座谈会,传达中央宣传部指示,再次检查和反省工作中的错误。12月7日又召集《新华日报》编辑部负责人与红岩、曾家岩负责对外宣传的有关人员继续学习讨论中宣部指示,进一步检查宣传上存在的问题。指出《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犯错误的原因是:一、政治警觉性不高;二、整风运动未能深入,未深刻研究毛泽东著作和思想;三、编辑上组织不周密,阅稿与检查皆有漏洞。同时,又召开报社全体大会进行广泛动员,还拟于次年报纸创刊6周年纪念时要作总结。
当事人和报社负责人都表示完全接受,并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夏衍后来回忆说,《新华日报》“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我们这些人在大后方工作久了,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几乎已经成了习惯,所以在国内外斗争严峻的时刻,这次整风对我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这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包袱,所以我们还是继续不断写文章”。
张黎群在审干中的经历,也折射出南方局良好的政治生态。1945年9月,南方局突然收到情报,称一个叫张黎群的人可能已叛变,引起领导层高度重视。张黎群当时在南方局青年组,掌握着数十个“据点”的情况,他如果有问题,将会对大后方青年工作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南方局对张黎群进行了政治审查,并让他放心:“我们在红岩和国民党斗争,积累了如此丰富的经验,还会弄不清这个问题吗?”组织上让张黎群在红岩独居一室,配警卫一名,闭门过了两个月的审查生活。其间,张黎群除回答了上百个问题,并写成书面材料外,还写了题为《我参加青年组工作10个月的叙述及其检讨》的报告,共计91页,原原本本记述了他在青年组的工作。详尽细致的审查没有白费,事实证明,张黎群“工作积极,群众工作有成绩”,“没有问题”,于是审查工作结束。刚满26岁的张黎群,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日后也没有因这件事受过影响。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正因为有南方局领导层率先垂范,南方局的党内政治生活坚持实事求是,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党员,不仅使人心情舒畅,而且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作风上有了很大改进,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风雨如磐的斗争岁月里,南方局坚守重庆8年,谱写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
川东党组织大破坏前后的政治生态
川东党组织是个特定概念,特指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区的党组织。川东地区党的领导机关,有时叫川东特委,有时叫川东临委,在组织序列中属于省一级机构,范围大致包括直辖后的重庆市以及四川东南部、东北部和贵州部分地区。
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川东党组织长期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在国民党统治最严酷的地区坚持开展工作,经受住了残酷斗争的检验,工作作风和工作效果都比较好。但是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时,国民党对重庆的统治更加严密,对中共组织的破坏变本加厉,川东地区党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化。加之1947年3月公开的四川省委被迫撤走,一大批优秀党员陆续东迁,川东党组织的上级领导远在上海,信息沟通不便,开展工作困难重重。川东党组织在上下川东先后发动的“奉大巫”和“梁大达”武装起义,因对形势判断失误、低估敌人力量以及组织准备仓促等原因,均以失败告终。在城市斗争中,又因对上级党组织开展对敌攻心策略的指示理解片面,因而采取了将秘密机关报《挺进报》直接投送给国民党当局大小头目的冒险行动,导致特务从《挺进报》发行的线索入手,开始破坏川东党组织。
最糟糕的是,外部环境急剧恶化的同时,内部生态还雪上加霜。具体表现为:川东党组织领导层的一些人理想信念滑坡,甚至道德沦丧;普遍存在纪律、规矩意识涣散的现象。
关于理想信念问题,譬如叛徒刘国定,被捕前既是重庆市工委书记,也是川东临委第三号负责人。当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工作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很受上级领导的器重和同志们的好评。但这时却信仰沦丧,道德败坏。据狱中同志揭发,他想包养情妇,就以做生意为由向川东临委管经济的干部何忠发借钱。何对刘国定说:“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私人没有钱可借。”刘国定对此怀恨在心,反向川东临委书记王璞诬陷何有经济问题。又如叛徒冉益智,他身居市工委副书记高位,一向与人高谈“气节、人格、革命精神”,以道德家面目示人。但他在被捕之后就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不仅迅速叛变,交待大量关系,而且向特务卑躬屈膝,讨好卖乖,暴露出“一直隐藏着自私、卑污的弱点”。像刘、冉这样理想信念彻底沦丧的人,他们背叛党的事业是迟早的事情,只看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形式出现罢了。
关于纪律问题,当时川东党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党员干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大破坏发生后,川东党组织马上行动,要求暴露的党员迅速撤离,保存力量。
但如此重要明确的指令,相当多的党员没有坚决执行。《挺进报》负责人陈然收到上级发来的暗语信件“近日江水暴涨”,本应立即撤退,但他仍想坚持,结果付出本人被捕、《挺进报》机关遭破坏的惨重代价。党组织通知交通员罗志德撤退,他为收回一億元(旧币)的钱款不愿撤退,声称“炮还没有打响,人哪能就跑了”,最终被捕。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得知与其熟悉的冉益智叛变、川东临委要求撤退的警示后,掉以轻心,时隔8个月后被捕,酿成了大破坏向川康党组织漫延的恶果。
还有一些党员缺乏秘密工作纪律意识。著名烈士、重庆市工委委员许建业被捕后,在酷刑下拒绝承认身份、交出组织。本已在事实上堵住了破坏的缺口,但他平时思想麻痹,将18份党员自传等党的机密资料放在志诚公司宿舍里,他担心这些机密材料落入敌手,轻率地相信了看守特务的假话,暴露了党在志诚公司的据点,刘国定因此被捕叛变,缺口进一步扩大。
除了许建业的教训,秘密工作纪律意识缺失还集中体现在《挺进报》的传阅上。《挺进报》是重庆市工委机关报,主要在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中传看。然而,一些党员干部阅读《挺进报》时,却无视保密要求,随意扩散。上川东一工委书记邓照明(后为川东特委副书记)反省道:“《挺进报》在有些地方,先是党员看,过后‘六一社社员看,进步群众看,都看过后无人看了,用来包花生米。花生吃完了,将《挺进报》一丢了事。”
种种问题交织,最终导致1948年春到1949年初的川东党组织大破坏惨剧,先后造成133名中共党员被捕,江竹筠、陈然、李青林等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入狱,其中川东108人(重庆市67人,上下川东41人),川康17人,宁沪8人。川东党组织因此元气大伤。
重庆解放后,从“11·27”大屠杀中幸存的共产党员罗广斌代表狱中同志,向党组织交出2万字《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第七部分共两页,约3000多字,是综合狱中讨论形成的“狱中意见”(“狱中八条”由此概括而来),总结了川东党组织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强调指出:“这些落后的,但资格很老的干部,抓住了领导机构,造成了领导机构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
大破坏后,川东党组织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一蹶不振,他们在上级领导钱瑛的带领下,积极反省问题,寻找原因,总结教训,顽强奋起。当时,钱瑛不顾工作繁忙,将川东、川康以及她领导下的其他省区党组织负责人和学运骨干分期分批地调到香港进行严格的整风学习和教育培训。她制定培训计划,亲自讲课,仔细摸清每个人的情况,倾听他们汇报工作,针对他们思想上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个谈话。
在钱瑛的帮助下,川东党组织的干部克服了大破坏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没有坐等解放,而是放下思想包袱,把上级新的指示贯彻到工作中,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重新投入战斗,最终在革命的高潮中迎来了重庆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