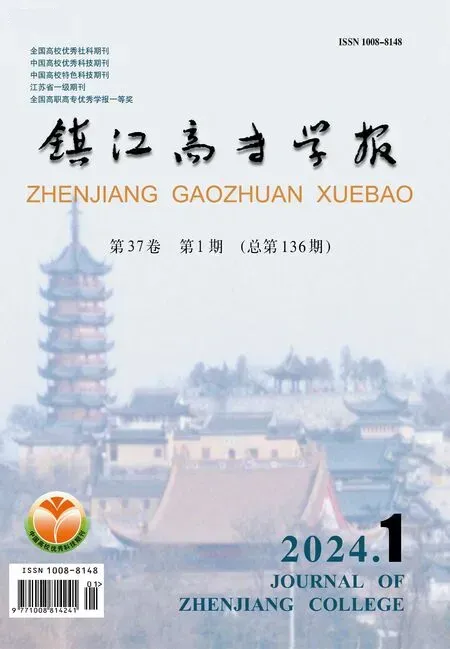柳诒徵早年伦理道德思想研究
——以《伦理口义》为研究中心
肖朝晖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与历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19)
柳诒徵(1880—1956年),字翼谋,晚号劬堂,江苏镇江人,为近代史学大家,其《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著作备受世人赞誉。1900年庚子之役后,清廷决意进行新政变法,兴学为重要内容。新式教育的推行促进了对教科书的需求激增,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在南京设立江楚编译局,主要编译教科书。1901年,在陈庆年的介绍下,柳诒徵进入江楚编译局工作,成为总纂缪荃孙的弟子。1903年,为借鉴日本兴学经验,缪荃孙、徐乃昌奉张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柳诒徵随同前往。此次考察对柳诒徵日后成功编写多部教科书、从事教育事业产生积极影响。1905年,柳诒徵应缪荃孙约请,担任江南高等学堂教习,教国文、历史、伦理三科。为专心教学,柳诒徵辞去了江楚编译局的相关工作[1]424。在任职江楚编译局和担任江南高等学堂等学校教习期间,柳诒徵编有《历代史略》《中国商业史》《商业道德》《伦理口义》等教科书。学术界对柳诒徵的研究主要侧重其史学成就,尤其聚焦于其《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等著作,而未有对其早年伦理道德思想的相关研究。笔者主要根据新近整理出版的《伦理口义》对柳诒徵早年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初步探究,揭示他在坚持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吸收与融会外来文化的重要意义。
1 《伦理口义》的成书背景
全国性伦理课程的设置要追溯至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章程规定:“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今无论京外大小学堂,于修身伦理一门视他学科更宜注意,为培植人才之始基。”[2]753《钦定学堂章程》将修身伦理作为一门正式学科予以确立。此章程虽正式颁布,但未及时实施。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也同样重视修身伦理,视之为各种学科的根本。其中的《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要求“讲授者尤当发明人伦道德为各种学科根本,须臾不可离之故”[2]579。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和正式实施,“新式伦理课程在清末学堂里普遍开设起来”[3],全国各级各类学堂大体都遵照《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设立了伦理课程。
柳诒徵于1905年担任江南高等学堂国文、历史、伦理三科教习。根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江南高等学堂一览表》,该校本科阶段开设有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日文学、历史、地理等主要课程,基本依照《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要求设置[2]639-640。柳诒徵编写了《伦理口义》。关于《伦理口义》,柳诒徵在自述中称:
高等学堂的功课,不要编讲义,历史是用的我在编译局编的《历代史略》,惟有伦理是每星期发一篇口义,要先做好稿子,送与缪先生看,缪先生许可,发与活字匠排好,方发给学生。我就参合《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内许多学说,以及当时译的书里有各国人物嘉言懿行,分类立题,编授学者[1]424。
缪荃孙的日记有阅改《伦理口义》的记载,“(1905年10月)三日甲子,……代翼谋上史学堂,到者十一人,又发《伦理口义》”[4]361。五日后又记曰:“八日己巳,……改翼谋《伦理口义》。”[4]362
由柳诒徵的自述和缪荃孙的日记可知,《伦理口义》为柳诒徵担任江南高等学堂伦理课教习时的课程讲义,柳诒徵拟好草稿,交缪荃孙改定,再印发给学生,每星期1篇。在自述中,柳诒徵明言《伦理口义》的编写主要参合了宋元明诸儒学案和各国人物的嘉言懿行两方面内容。这正符合“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对伦理学科教学内容的相关规定,前者要求“考求三代汉唐以来诸贤名理、宋元明国朝学案,暨外国名人言行,务以周知实践为归”[2]562,后者要求“摘讲宋元明国朝诸儒学案,择其切于身心日用而明显简要者”[2]572。
2 《伦理口义》的主要内容
按照“分类立题”的编写体例,《伦理口义》分为修己、家族、君国、群伦四部分内容。柳诒徵在《伦理口义》中集中阐发了对家庭(族)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的看法,体现了他早年的伦理道德思想。
2.1 家庭(族)伦理
家族篇主要介绍了家庭和家族伦理。关于“父母”“夫妇”的相关内容约占一半篇幅,为此篇重点之所在。“父母”部分阐述了善事父母的孝道思想、“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夫妇”部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强调男女有别;主张婚姻以父母作主为善;阐扬夫为妻纲之理,说明夫妇在平权的同时还有着治事上的主辅之分。
郑玄在《六艺论》中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5]3故而,《孝经》一般被视为六经义理之总会。柳诒徵进一步指出,《孝经》为六艺总会不仅是就学者治经而言,它还是治理天下的“要道”,“读六艺而不读《孝经》,则先王治天下之要道犹不明”[6]107。柳诒徵认为“人类日滋,纷无董理,相争相攘,政刑莫止。然人莫不亲父母,莫不畏父母。人人能体父母之心,畏父母之教,则天下自治。挈裘必振领,举网必振纲。故不曰以孝劝天下,而曰以孝治天下。”[6]107柳诒徵指出,“亲”“畏”即《孝经》中的“爱敬”,此爱敬父母之心乃出自人之天性,并非出自强迫,先王“以孝治天下”就是顺应人类自然的爱敬父母之心,从而使天下达到“民用和睦,上下无怨”的理想秩序。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自由、平等观念的传入和流布,传统善事父母的孝道伦理思想开始受到冲击,种种非孝言论与举动日渐增多。正如柳诒徵所言:“自欧俗东渐,视父母寖以淡薄疏逖,逆亲、抗亲之事,数有所闻。”[6]109柳诒徵推崇孝道,强调“吾国人当自保其粹”,不能因向西方学习,而并其短处也学之,从而“刊灭中国四千年以孝治天下之道,自趋于飞走之域”[6]110。他认为不重视家庭(族)伦理、以父母为路人是西人的短处。主要表现:婚后则与父母别居异财,甚至不相存问;子殴父与父殴子的行为在法律上受到的处罚没有区别。按照中国传统孝道伦理的要求,子不养父母是为大不孝,“子长成而弃其父母者,特飞走之属耳”[6]109,意为弃父母不养,直等于“飞走”的禽兽。子殴父与父殴子同罪则泯灭了父子间的尊卑、颠倒了父子名分,将导致“率天下而控亲殴亲也”[6]109。在柳诒徵看来,爱敬父母是人之天性,西人路人父母不是生而无此天性,而是受习俗所染,缺少“贤王”对孝道的阐扬,最终走向“自戕其天性,自贼其本原而不知”[6]110。
中国传统礼教重男女之别,有关男女远嫌疑、防暧昧、谨细微的礼俗规定颇为严格,但受近代西方风俗影响,相关规定受到质疑。柳诒徵认为男女之别出自先天,并非中国圣人的人为区分,“男女之别,非中国圣人之臆造而矫揉之也,亦本诸天而已矣。今夫天之生男女也,一阴一阳,形体判焉,天可违乎?”[6]117他认为,“男女之别”与礼制的产生密切相关,“盖天别以形,上古之圣人别以衣,中古之圣人别以礼,人伦之至也。因形体之别,而有男女之名,因男女之名,而严衣服之辨,因衣服之辨,而生礼制之防,精义之至也”[6]117-118。柳诒徵重视男女之别主要是为了防止男女因过度追求自由而导致“恣佚欲而堕廉耻”局面的出现[6]118。
传统的中国婚姻大体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7]2274。清末,婚姻自由、婚姻应以两性情意相合为基础的观念兴起,传统婚姻理念与模式受到冲击。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刊文指出中国传统婚姻“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强逼成婚”,认为这极不合理,贬之为“恶俗”[8]31。但柳诒徵认为婚姻由父母做主的中国模式优于欧洲的婚姻自主模式。他指出,欧洲崇尚自主婚姻,号称有“匹配当”“无怨悔”之利,而实际上会产生“毁礼义”“捐廉耻”的流弊;由父母作主的婚姻虽不都能完满,但天下爱护子女者无过父母,父母的阅历和见识更为丰富,婚配之事交由父母来决定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较为适宜。通过权衡婚姻自主与父母做主的利弊,他强调中国由父母做主的婚姻模式不可变革,“自主结婚利一而弊十,父母主婚弊一而利十,两弊相权取其轻,故吾国之父母主婚,未可革也”[6]119。
对当时备受攻击的“夫为妻纲”,柳诒徵提出自己的理解。“夫为妻纲”在当时的新学人士看来是极为不平等的道德规范,认为它强调男尊女卑,要求妻绝对服从于夫,损害了妻的独立、平等人格。柳诒徵引用《易·家人·彖传》“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9]158和井上哲次郎的“夫为一家之主权,妻则其辅佐”[6]119,说明“夫为妻纲”并非如新学人士所攻击的是要求妻绝对服从于夫,而指的是在任事上以夫为主、以妻为辅,任事上的主辅之分并不意味着夫妻权利的不平等。为此,柳诒徵进一步征引经史典籍的训释和史迹阐述其观点。《白虎通》《说文解字》释“妻”为“齐”,柳诒徵认为妻与夫齐,“其权力焉得而不平”[6]121。《大戴礼记》《白虎通》又训“妇”为“服”,服于人也,似乎又与前面的释义全然相反。刘师培在《伦理学教科书》中称:“《说文》训‘妇’为‘服’,足证三代之时,以服从为女子之义务,故重男轻女,自昔已然。”[10]5914柳诒徵认为“妻”训“齐”,说明夫妇“有敌体之义”,而“妇”训“服”,强调的是夫妇在治事时“有主辅之分”。他援引历代史书中张湛、仇览、樊英、吴顾恺等人的事迹和言论说明中国夫妇之道以敬爱为尚,“故知夫以平等礼其妇,妇自不以平权望其夫。征诸文字而通,绳之经史而合,固无俟夸欧化、张女权也”[6]122。
2.2 国家伦理
君国篇主要讲述尊君爱国以及守法、纳税、服兵役、接受教育、自治等内容,大致相当于时人所言的“国家伦理”。柳诒徵对当时“歧君、国为二,斥朕即国家”的说法表示不满。他从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阐释了“君”的含义:从史学角度而言,《说文解字》训“君”为“尊”,《鹖冠子》训“君”为“天”,这不是解字者的臆造,必然有历史经验的根据;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君,群也”[11]376,“君”是群体、社会得以成立和运转的关键要素;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君”是国民全体的代表,象征着国家主权。由此可见,柳诒徵并不将“君”视为某一具体的帝王,而是将其视为国家民族和社会群体的象征。他指出“忠”有三重含义:泛施于人者、专施于君者、下施于民者。显然柳诒徵没有把“忠”局限于君臣关系。柳诒徵对“忠”的论述主要着眼于君臣之义,即“专施于君者”,但其余两义实际上也贯穿其中。柳诒徵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能群则必于其所接之人,所荷之事,恪尽其心,知官体之能,谋其安而济其困,然后人群日进于乐利,而斯人亦得坐受其报偿。……故忠之为义,始于私人之相与,终于人臣之相勖。人臣所事者,君而大。君所谋谟而举错者,罔非利乐其群之举。则人之欲忠于民者,固莫便于忠于君矣。”[6]131由此可知,柳诒徵所阐述的“尊君”“效忠”的对象皆非指君主个人,他绝非宣扬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他指的是忠于君所代表的整个群体,实际彰显的是一种奉公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在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中多有受挫,时人在探究根源时发现国人国家思想的缺失是一大关键,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断言“吾中国人无国家思想也”[12]545。柳诒徵对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爱国心是一种天性,“民之必爱其国,天也,非人也”[6]133,他认为国人并非没有爱国之心,只是在长久的大一统局面下未得彰显,逮至近代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国人的国家思想被激发。柳诒徵称:
盖国与国接,则甲国与乙国之民,截然有间,有间而其爱护本国之心,自勃发而不可遏,……秦、汉以降,中国之疆域日广,为之邻者,文野悬殊,仅有族别而无国别。即内地之分为列国者,为时间亦暂而不久,又无画然之畛域,俾其民各致其爱情。故爱国之心,一变而为大一统之心。必待晚近欧亚交通,列强环伺,然后国家之主义,亦缘时会而复萌。而暗于事理者,猥曰吾国人无国家思想,几若凡民公共之德,独此由外烁而非本能,抑亦不思之甚矣[6]133。
末句的批评显系针对梁启超而发。柳诒徵和梁启超都重视国民的国家思想、国家观念的激发,只是柳诒徵更强调爱国心出于天性,不待外烁,“国民教育,亦只能因其本有者,发挥而广大之,无所用矫揉造作”[6]134。
2.3 社会伦理
群伦篇包括博爱、广师、合群、交际、爱物等五方面内容,相当于时人口中的“社会伦理”。针对当时流行的博爱观念,柳诒徵强调要注意儒、墨两家关于博爱的区别,应“熟审儒、墨之说,得博爱之法”[6]147。柳诒徵认为:墨子有鉴于天下大乱起于人之不相爱,故提倡无差等的“兼爱”,希望人们爱人之父若己之父;儒家亦言博爱,然儒家强调亲疏有别,博爱由爱近亲始,不同于墨家不别亲疏的兼爱。这与传统儒生区分儒、墨并无二致。“广师”部分不仅意在说明个人要“虚其心以受天下之善”[6]148,还强调在向西方学习时,要摒除门户党派意识,既不“动斥彼族之猥贱”[6]148,亦不得认为“惟欧美日本有学,而吾土之人之学,直土苴刍狗之不若”[6]148,体现了柳诒徵在清末新旧思想、中西思想冲突背景下强调既择善而从又自爱自重的稳健立场。“合群”部分揭示了“群之所以合”的三项要素:情、法、道德。在这三者中,柳诒徵尤为重视道德的作用,强调“合群之先励德,尚矣”[6]150,反映了柳诒徵对作为维系群体团结和维护社会秩序重要力量的道德的重视。柳诒徵反对当时“以新学说自文”而行猖狂恣肆之事,“奔竞夤缘,则美之曰运动。欺诈凶衅,则夸之曰手段。析锱铢、争升斗,则曰吾权利应尔也。背死友、卖石交,则曰吾目的有在也”[6]152。柳诒徵还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强调爱物的重要意义:“人生衣食之原,无往非物之所惠。苟或绝之,则人有不能一息尚存者。……民智开明之世,其必珍护爱养,不使一物失所者。”[6]154柳诒徵指出,这种强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于万物、主张珍护万物的爱物精神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近世各国思想中皆有体现。
3 柳诒徵早年伦理道德思想的特点
起自晚清,更确切地说,是起自戊戌时期,中国传统纲常伦理思想开始遭到批判。谭嗣同对以三纲五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予以了猛烈抨击,著名史家余英时称谭嗣同的纲常批判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破天荒之举,具有重要的意义。逮至进入20世纪后,“一种具革命性的反传统文化的革新思想才真正出现”[13]118。彼时,宣扬“三纲革命”“家庭革命”“打破礼教”的思想和言论大量出现,蔚为风潮。家庭制度的不平等,“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压制人性成为时人抨击中国家族伦理的要点,传统孝道也受到批评。与一味抨击、贬损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激进人士不同,柳诒徵在接受新式伦理思想的同时,依然肯定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
3.1 肯定传统伦理道德价值
在当时抨击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非孝、批判三纲的时代思潮下,柳诒徵仍坚守传统伦理道德。他特别推崇传统孝道(孝治)伦理,反对谬托自由、平等之说而行逆亲、抗亲之事,认为善事父母的孝道以及由之推扩而来的“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是中国的国粹,视以父母为路人的西方人士无异于“飞走之属”,强调不能因学习西方而丢失自家长处。在他看来,中国由父母作主的婚姻模式优于欧洲婚姻自主模式,前者利多弊少,后者利少弊多。柳诒徵对孝道的推崇、认为婚姻由父母作主优于西方自由婚姻的看法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柳诒徵的某些“坚守”(如仍主张严男女之别、反对西式女权等)在近代中国思想解放大潮中,显得过于保守,但他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坚守并非出于盲目,实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如他考察“妻”训“齐”、“妇”训“服”,认为夫妇在平权的同时有着治事上的主辅之分,辨明“夫为妻纲”绝非如新学人士所攻击的是要求妻绝对服从于夫。又如在说明“尽己之心为忠”时,指出“吾以为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子不待计父之慈而加孝,臣亦何至量君之仁而始忠?生人天职之常,所宜循分而自致”[6]132,强调“忠”是指尽一己之职分,后学者贺麟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3.2 吸纳新式伦理观念
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思想以“五伦”为核心,五伦指古代中国的五种人伦关系和言行准则,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时人多认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偏重家族伦理,而于国家和社会伦理有所欠缺。梁启超在《论公德》中称“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12]540,认为这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重私德、轻公德造成的结果,为培养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国民观念,梁启超特别提倡“一私人对一团体”的“公德”。柳诒徵在《伦理口义》中也大体接受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的提法,君国篇和群伦篇所述内容相当于国家伦理和社会伦理。“君国篇”将国家、主权观念融入“君”的范畴,并要求国民履行纳税、服兵役的义务,强调个人自治与地方自治、国家富强间的关系等。群伦篇除体现传统朋友一伦的“交际”外,还阐述了博爱、广师、合群、爱物等内容。这两篇在内容上突破了传统君臣、朋友之伦,体现了柳诒徵对新式伦理观念的吸纳。
柳诒徵对国家思想、国民观念的接纳和吸收尤其体现在对纳税的重视方面。在“小政府”的传统社会,“轻徭薄赋”是备受推崇的仁政,但此举已不能适应近代激烈的国家竞争。柳诒徵从国家兴办近代事业和养成民众国民意识的角度强调赋税的意义,他指出,纳税与接受教育、服兵役是国民的基本义务,特别是纳税,在柳诒徵看来,税款可供筹备海军、兴建学校以及地方自治等国家、社会事业之用,亦可使民众知晓与国家之关系,养成完全之国民。正是在近代国家思想、国民观念的熏染下,柳诒徵才得以说出“毋以得免丁税为乐”这样突破传统的看法。
《伦理口义》集中展现了柳诒徵早年的伦理道德观念,柳诒徵人伦道德观中的很多看法和主张皆可于此找到起源。《伦理口义》编写于中西新旧伦理思想冲突的清末时期,其时,由于西方自由、平等观念以及国家、国民思想的传入和流布,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开始遭受全方位批判,柳诒徵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下,一方面肯定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价值,一方面又对新式伦理思想有所吸纳,“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4]284-285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已然形成,无怪乎进入民国后,面对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柳诒徵起而成为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的灵魂人物。柳诒徵对中西伦理的看法及立场对促进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