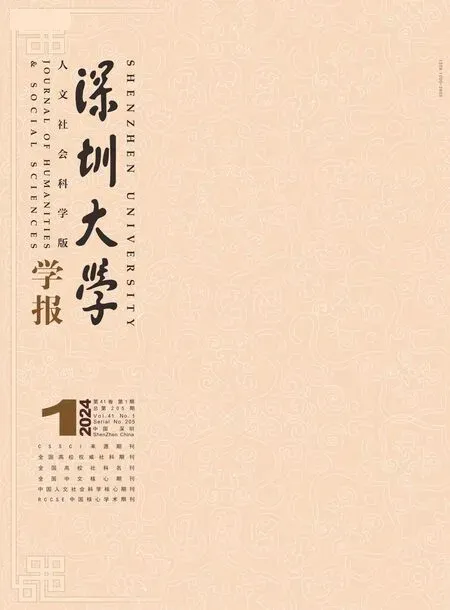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海外话语谱系及建构进程
杨 帆
(南昌大学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31)
话语认知已经成为海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开展学术探究的重要视角。大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海外话语认知是指海外学界藉由话语工具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时空认知而生成的话语图景,以及关于这一模式内在本质的话语表达集合。这也意味着,对海外学者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话语品质与极其可能实现的话语效果。沿着这一认知路径继续深入,可以发现,海外学者大多主张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现代性本质属于通过政治话语创造而生成的现代制度产物,更是用于统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遵循。由此,海外学者基于话语认知视角力图深刻判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借以生成的话语立场及其内容演进。进而可以看出,海外学界关于这一模式的话语认知力图转变以政治研究为重点并强调对这一模式进行权力关系分析与归纳的传统研究范式,开创性地将话语认知嵌入该研究命题。这极大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海外研究范畴,将外在的、显性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研究导向了内在的、隐性的、更为深入的规律探索。
迄今为止,尽管国内学界已经进行了一系列中国式现代化海外研究理论进展的评述,为相关海外话语认知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学者重视奠定了前提,但尚未关注到这一领域的最新海外研究动态。据此,本文拟基于海外话语认知视角,根据不同的历史分期,融汇全球有关学者的相关学术主张,探究这一研究范畴的海外学术话语谱系及观点演进历程,进而为国内学界探究相关海外研究的观点立场、话语内容以及理论缺陷等提供一定的学术镜鉴。
一、1980-1990 年:海外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话语认知起源
基于总体性视域考察,可以发现话语认知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海外研究的重要范畴,而关于这一模式相关概念的话语表达已经成为重中之重。特别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直接将研究重点设定于探究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并把这一模式视为话语认知对象,随之展开话语建构。美国政治学学者吴本立(Brantly Womack)、罗兹曼(Gilbert Rozman)以及加拿大中国学学者柯让(Ronald C.Keith)是这一学术趋势中的重要代表人物。1983 年,柯让发表了《中国的现代化与“自力更生”政策》(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of “Self-Reliance”)一文;1984 年,吴本立发表了《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改革》(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tic Reform in China)一文;1989 年,吉尔伯特·罗兹曼则主编了《中国的现代化》一书。
可见,早在20 世纪80 年代,紧随1978 年中国以改革开放谋求实现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上述学者就敏锐意识到一种新兴的现代化模式即将诞生,并尝试通过话语对这一模式展开认知。这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海外话语认知由此起源,并被海外学界视作值得重点考察的研究命题。
其一,中国积极谋求实现现代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效应,是中国以现代化口号引领建设实践、统合建设力量的重要举措,因此可以通过中国的现代化话语表达探究其内在的运行模式。其中,吴本立主张可以通过结构化话语建构现代化国家认知,以生成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可控的、有序的、渐次实现的大众化与民主化”[1]。这意味着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的“大众化与民主化”话语有利于为中国建构现代化国家形象。这也正如柯让所言,“‘自力更生’这一术语有助于准确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它表明中国要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寻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2]。
其二,现代化与国家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通过话语可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发展导向。首先,崇高的国际地位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核心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运行成效为全球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这决定了其之所以能得到正面的话语评价不仅在于发展效应的正当性,还取决于“其全面详实的计划,明确可行的目标以及实施计划的适当手段”[3]。其次,现代化与国家发展存在着话语趋同。尽管与纯粹政治话语有异,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话语仍然聚焦于表达特定发展目标、应对不同发展意见、解决不同发展问题,与起点于不同结构基础的国家发展终将实现话语趋同。最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逐渐成为海外学界重要的研究命题。这表征着一种学术转向,即集中于中国现代化成就的讨论正在向深度迈进,力图实现对其发展模式的深刻洞察。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外交政策之间存在一定的话语关联。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外交政策通常被海外学者视为传统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从另一方面来看,海外学者也一直在尝试通过剖析中国外交政策从而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特质。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集中于表达现代化模式所需和平国际环境的话语核心,进而准确判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自主性特质。诸如此类的隐晦性新制度主义政治话语并未遵循对这一主题展开认知的传统海外话语范式。对相关学者而言,由对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升级而来的自主性特质的观点集合本身就是一种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阐述,而这一模式阐述也可以被解读为关涉中国发展现代性的话语表述。对此,柯让予以重点关注,指出“法治理论所造就的政治稳定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4]。
可以看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代学术转向推动海外学界深化了对这一命题的话语认知。借由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话语阐释,这些学者意图围绕“现代性”这一核心概念系统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名词集合、理论意蕴以及相关话语要素。与此同时,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马里乌斯·迈因霍夫(Marius Meinhof)、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波莱(Richard W.Pollay)和谢大卫(David K.Tse)、香港中文大学的关兆安(Andy Kwan)、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俄勒冈大学的苏迈德(Richard P.Suttmeier)、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的亚瑟·摩尔(Arthur P.J.Mol)、乌克兰伊万弗兰科国立大学的尤里·梅尔尼克(Iurii Melnyk)、非洲博茨瓦纳大学的范莎娜(Sara Van Hoeymissen)等人的观点与罗兹曼等人的某些论述之间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学术关联。例如,范莎娜于2021 年发表的《非洲的中国学研究》(China Studies in Africa)一文就基于国家关系视角提出“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解的专业知识需求”[5](P201),这一主张和罗兹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例化”表达之间就隐含着相应的逻辑勾连。其实,罗兹曼早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已经呼吁海外学界要对中国的现代化给予重点关注,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因此“在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能够确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基本道路,又在哪些方面脱离常规走了自己的路”[6]。
紧随话语认知的起源,海外学者针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渐次建构并形成了基于不同哲学立场的话语认知模型。从其整体性进行观照,可以将其大致概括为“照搬论”与“本土论”。这两大认知模型由于哲学立场的不同与样态多维的表达冲突,造成了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差异。大致而言,其差异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照搬论”较为忽视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运行成效,认为其主要是套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经验,而“传统论”则将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哲学起源统归于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照搬论”未能深刻洞察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动能,而“本土论”则能观察到中国式现代化模式遵循马克思现代化理论所进行的实践创造及话语更新。
二、1990-2000 年:海外基于西方中心认知立场建构的“照搬论”
20 世纪90 年代,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影响,相较于80 年代海外学者看待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客观理性态度,这一时期的部分海外学者力图运用“西方中心论”解读中国正在大力实施的四个现代化战略。香港大学学者鲍勃(Bob Adamson)就认为,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追求之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吸收国外的教育思想以及专业知识”[7]。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话语认知立场,部分海外学者既不得不正视中国正在实现经济腾飞的现实,又着力从“西化模式”的视角出发探究这一腾飞背后隐含的模式秘诀。
其中,代表性人物当属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理查德·波莱(Richard W.Pollay)、谢大卫(David K.Tse)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关兆安(Andy Kwan)等。大致而言,海外学界基于西方中心认知立场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话语主要集中于功能主义的现代性探讨,即重点在于探究西方现代化模式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作用程度。更进一步来看,这些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展开话语表述的核心指向在于对这一模式进行西方化的政治溯源。其中,波莱主张,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工具化应用推动着其国家发展,“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心理以及文化影响刺激着中国的发展热情”[8]。而关兆安则指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是积极参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产业链分工体系,建构的是“出口导向型增长”[9]现代化模式。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发展平衡的实现需要得到西方国家的政治支持与经济帮助。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进行政治溯源,无非是想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纳入西方现代化学术体系与概念范畴。这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内延续至今。譬如,2018 年,德国学者迈因霍夫在《挑战中国现代性?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大学校园现代化话语》(Contesting Chinese Modernity? Postcoloniality and Discourses on Modernisation at A Chinese University Campus)一文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克服国家落后性是中国主动融入全球现代化秩序的紧迫性根源,并使得二者的现代化话语表达共处于双重权力结构之中,因为“一方面,中国国家话语应用于中国本身,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话语往往与中国保持一致”[10]。
上述学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话语解读推动了起源时期的认知模型转换,即逐渐生成一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话语范式。这一话语范式主要强调通过挖掘东西方现代化模式之间的逻辑关联以阐明西方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并主张全球国家都需主动拥抱与积极投入这一模式之中。这一观点的实质不言自明,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然而,西方模式多年来却依旧被视为寻求发展进步的唯一路径,现代化长久以来就等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11]。但是,对于持“照搬论”立场的海外学者而言,只有通过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模式的经验话语概括,才能够确证具备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得以通行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故而,在20 世纪90 年代的海外学者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具有明显的西方化特质,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特质可以清晰地表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世界趋向。
与此同时,对这些学者而言,深入阐释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以及什么是现代化话语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心,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优越性以及向其他国家传递的可复制性与可行性。其中,他们尤为注重基于话语认知视角考察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应用程度以及实现效度。正如波莱所言,“西方发明的传播工具——广告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得到极大应用,并引发了一场西方式的社会文化革命,即消费主义的极大盛行”[12]。据此可见,这些学者的主张仅停留于20世纪90 年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表现,而未深入至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现实语境,因而他们难以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做出中肯到位的话语评述。
与上述学者从现代化经济增长路径、社会结构调整等方面探究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西方化特质不同,这一时期极有影响力的学术人物之一——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Pye),则重点从价值观念以及普遍规范性视角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西式话语特质。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力图推进其相关论述。一方面,白鲁恂认为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存在着话语混淆现象。譬如,他提出,“随着国家发展的西方化,现代化概念被混淆很常见,因为人们越来越多地将现代化视为与国际标准、普世知识等相关的称呼以及适用于当代社会的先进名词”[13]。另一方面,白鲁恂过于强调西式民主、道德秩序等政治概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体现,提出“现代化的过程关涉到竞争性的社会经济利益与政治秩序。随着现代化的成功,社会政治权力以及新兴利益要向人民转移。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取决于经济现代化结果,而并非天然来源于正统的道德秩序”[14]。显而易见,与其他“照搬论”海外学者相比较而言,白鲁恂已经不满足从经济与文化要素中挖掘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西方之源,而是希冀中国式现代化模式遵循政治现代化结构运行,以在中国实现所谓的“政治民主化”。由此可见,“照搬论”海外话语认知的重点在于完全经由西方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进行话语评判、展开话语鉴赏。
总体来看,20 世纪90 年代海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话语认知较为激进,其观点极力鼓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西式话语特质,实质上是力图拼命维护以西方霸权为主导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这使得其话语认知尽管带有较为突出的学术性,却仍然掩盖不住其明显的学术不足。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这些学者始终秉承政治制度先于经济发展的模式考察视角,妄图将单一化、形式化的西方现代化模式适用于多样化、丰富化的全球现代化实践,尤其是想将其生搬硬套于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正如有学者错误地认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直接从西方社会‘移植’观念以及文化系统来解决新问题的情况比比皆是”[15]。其二,这些学者过去注重与强调西方民主、政治秩序与道德观念等话语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的体现与运行,而忽略与轻视了这些话语概念作为全人类文明成果的普遍性与共生性,更对它们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的“东方式表现与特征”进行选择性的忽视。更有甚者,有些学者仅是从西方现代化的话语概念出发,将其与中国的现代化实际进行简单粗暴的勾连与关涉,而对二者之间的融合性与排异性并未开展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
三、2000-2010 年:海外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建构的“本土论”
2000 年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而生的政治、社会以及生态等危机交织展开,形成了对西方世界造成重大冲击的系统性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作为危机中的“一枝独秀”,被一些海外有识之士所关注和重视,并愿意给予深刻洞察。值此背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本土论”海外认知话语被渐次建构并逐渐生成。这一类型的海外认知话语主要针对不切实际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万能论进行批判,并形成相关的话语集合。持这一立场的代表性海外学者包括杜赞奇、苏迈德以及亚瑟·摩尔等。
“本土论”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杜赞奇通过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致性,赋予这一模式显著的本土化话语特质。他发现,“中国反对将其定性为亚洲生产模式的一部分,因为这种定性将其设定为从属性的生产模式,使得当代中国甚至远不如古希腊和古罗马先进”[16](P62)。杜赞奇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关键价值在于为阐明“全球进程中的中国独特发展”[16](P5)提供了话语路径。据此我们发现,杜赞奇力图回归东方主义视角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这种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将东西方截然分开的思维方式最终必然帮助杜赞奇将其话语认知导向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其话语认知的实质隐含着对“照搬论”海外话语的批判,并通过重述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模式所展开的话语评论,对西方现代化模式优于、高于非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观点予以否定。
与杜赞奇同期,苏迈德也积极投入“本土论”立场的海外话语认知建构。他的论述重点在于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吸收与创新。他提出,“‘第六种现代化’,即制度与价值观的发展,可以有效管理现代化的风险,获取越来越重要的利益”[17]。其论述的实质在于通过对现代化制度与价值观的系统诠释以深刻阐明马克思现代化理论对现代物质生产的话语批判。与此同时,亚瑟·摩尔则进一步从马克思生态现代化理论着手探究“本土论”话语内容,以明晰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他指出,“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可以说是另一种模式,而不是已经被广泛研究的欧洲版本。……如果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体制进一步相结合,相关的理论安排有可能加强其环境改革的效用”[18]。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亚瑟·摩尔已经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有效承袭了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内蕴,又注重从生态现代化视角拓展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论述。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些海外学者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特质的追寻,其意图在于突破“照搬论”的狭隘理论视野,以回归东方而研究东方的方式探究这一模式的理论品质。他们主要遵循如下理论假设,即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生成与运行虽然仅是一个自然过程,却理所当然地接受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指导。这进一步表明,这些海外学者较为一致地承认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具有比较鲜明的本土化话语特质,而这种本土化话语特质主要是在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得以生成的。
由此,21 世纪初期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海外认知话语主要呈现以下特征: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具有突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正如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学者李怀印(Huaiyin LI)所观察到的,“在80-90 年代的中国,中国史学研究范式与西方史学出现了相类似的转变趋向,即从革命化叙事转变为现代化叙事”[19]。而这一叙事转变的指向在21 世纪初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上得以显著体现,也就是说,无论采用何种叙事方式对当代中国进行解读,都无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另一方面,能够以更为理性的“中国中心主义”态度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发展转向。通过从“照搬论”向“本土论”的转变,这些海外学者努力勾勒出中国语境下的现代化模式与马克思现代化理论之间的逻辑关联。恰如杜赞奇强调的,“紧随文化真实性话语对现代产品符号化的加剧,在当代中国,尽管面临全球资本主义狂潮的席卷,但是仍然滋生与蔓延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20]。由此可见,“本土论”海外话语具有显著的价值认知导向特征,其立足于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价值力或价值体特性。究其实质,这是一种阐释性的价值认知话语。上述学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话语在这种价值认知特性的导向下,生成了较强的话语表述力,并在客观上推动海外学界形成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积极认知。
还有部分海外学者根据其学术观点尽管可以将其划入“本土论”阵营,但是,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特点却与前述学者存在不少差异。以香港城市大学两位学者张宙桥(Chau-kiu Cheung)与梁君国(Kwan-kwok Leung)的主张为例,他们并未纠缠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究竟是依托何种哲学立场而生以及是否要对这种哲学立场进行理论溯源,而是基于务实性,更为看重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在中国情境中的效用发挥。他们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结构背景不同于其它国家,更与现代收敛性的说法毫无关联,因为中国现代化有其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运作方式。这决定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生活的满意度与西方不同”[21]。这种观点从理论本质上看仍然从属于“本土论”,但是却意图以一种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话语认知的本真化。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学者与杜赞奇等代表的“本土论”话语仅有表述差异,而无实质不同。
然而,这些话语表述差异却向我们表明,经过学术省察,“本土论”海外话语认知同样存在着理论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这些学者始终秉承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并由此生成一种机械的、静止的、相互割裂的话语认知。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运行实践之间如何实现逻辑关联,他们未能做出科学有效的回应。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为何不能突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新秩序以及数字新形态,但却能够科学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建构,他们也未能给予充分的理论关注。另一方面,这些学者同样未能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进行全面、系统的审视,他们过于片面地聚焦于探究这一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而对其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质则视而不见。具体而言,他们并未基于整体性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特色进行充分解读,也并未对中国特色的要素构成、运转机制等进行深入探究并展开理论诠释。
四、2010 年至今:海外基于新时代现代化成就建构的“超越论”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向全球展现了无与伦比的运行优势与独占魁首的成就魅力。一些海外学者对这一“人类发展史上真正的奇迹”给予了充分的学术关注,并建构了聚焦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人类社会发展新路径的“超越论”话语认知。其中,尤里·梅尔尼克以及范莎娜参与了这一话语认知建构进程,并提出了相关话语主张。尤里·梅尔尼克考察了非洲媒体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运行成效的正面宣传后指出,在非洲媒体人眼中,“中国被视为未来的世界超级大国以及一个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取得最快经济进步的先进国家”[22]。范莎娜则发现她的学生们被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巨大成就所吸引,“我注意到我的博茨瓦纳学生其实对中国的治理体系对其现代化发展的贡献更感兴趣”[5](P204)。他们的话语认知隐含着对“照搬论”以及“本土论”的批判,要求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以及全球适用性进行关注。
对这一任务完成得较好的学术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克里·布朗(Kerry Brown) 。在不完全认同前述“两论”话语认知的前提下,布朗主张中国的现代性正体现为其对西方发展道路的超越性,因为“社会主义通过信念驱动为中国带来了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体现为工业化与现代化。同时,这种现代性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特色之一就在于其是由坚持团结一致的政党所领导的”[23]。他的论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品质正在逐渐为海外学界所认可,并被给予了相应的话语关注。而其主张的潜台词在于承认与支持基于中国中心立场而建构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并呈现了这一模式异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新话语图景。正如布朗指出的,“通过发展出超越西方的现代化,以建设一个充满活力、更加美好的社会,是中国人普遍接受的愿望”[24]。由此可见,布朗的话语认知既与“本土论”的相关论述存在话语关联性,同时,又表现出他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现代性对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之重要性的话语表达惯习。
上述学者的话语认知侧重于表达非经济性与非文化性要素对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之超越性的重要作用。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以英国学者柯岚安(William A.Callahan)、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以及卢可欣(Kristen Looney)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则寻求依靠经验认识论的路径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展开话语认知。其中,柯岚安主张,基于源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双重性,西方很难再以优势心理看待中国的现代化,西方理论家也不再极端强调西方模式是唯一正确与可行的现代化模式,因为“中国的模式只能用中国标准进行评价,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不仅要在经济生产方面实现对西方的超越,还要从知识生产方面入手”[25]。柯岚安较为重视与坚持“超越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比较看重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运行逻辑进行超越性审视,而这种超越性审视却被“本土论”海外学者误认为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中的西方要素而予以排除。
不满足于仅与柯岚安的学术主张发生互动,德里克更为聚焦于从现代化经验论视角出发深入探究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并建构相关话语认知。他力主“中国现代化的模式既可以适应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又可以供其它国家模仿,因此,其具有超越中国社会界限的相关性”[26]。与此同时,卢可欣则将其关注点设定于中国城市化的经验历程,以力图更为深刻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逻辑。一方面,卢可欣认为城市化的成功经验是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具有超越性的核心要素之一,这是因为“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可以促进劳动力、土地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制度。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结合,则是中国的现代化”[27]。另一方面,她还主张城市化发展经验借由物性话语规训着现代化的物质性发展方向,这也确证了“中国数百个城市在没有经历政治动员的前提下实现了现代化,因为中国探索了一条排除过分政治动员的现代化道路”[28]。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来自非洲还是欧洲的秉持“超越论”立场的海外学者,都较为一致地力主基于中国发展成就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以及共同价值,并能够以融合性视角看待东西方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形成的重要价值。这也意味着,“超越论”是集合“照搬论”与“本土论”的理论优势所生成的最为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特质的话语认知,这决定了其突出表现在于和其他类型话语认知具有共性的“最大公约数”。但是也不能否认,“超越论”同样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理论不足。一方面,“超越论”的话语认知视角未能实现完全的“中国中心主义”。尽管持该立场的学者们力图转向以中国为中心对中国式现代化模式展开话语认知,但是,长久以来的研究惯习及范式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他们的学术尝试。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性究竟指向何处这一问题,这些海外学者还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认为这种超越至多是中国对自我历史的超越以及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超越,而不可能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超车”。
五、结 语
一言以蔽之,起源于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海外话语认知在诸多海外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卓越学术贡献下,已经生成比较完善的学术话语谱系,并成为海外学界关注全球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研究范畴。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21 世纪最现代化的国家可能是中国,它的现代化变革是如此独特与引人注目,使得西方现代化一词在全球经验中无效。中国的现代化经验值得让人探索,因为它的现代化经验肯定不是对西方现代化形式的简单复制”[29]。诚如其所言,中国现代化成就及其模式早已受到海外学界的重点关注,并生成了较为准确的话语认知。由此可见,“模式”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海外学界较为一致地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化身份标识。
但是,对“照搬论”“本土论”“超越论”等不同话语认知进行深度学术审视以后,我们也可以看出,不同立场的海外话语认知存在着一些共性的理论缺憾。譬如,话语表述之中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以及直接将西方传统政治学研究范式与手段套用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运行实践等。当然,瑕不掩瑜,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话语认知是基于最新的理论视角对这一命题做出的最大学术尝试。尽管这种海外话语认知囿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尚未达到预期的学术高峰,但其仍然可以被视为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培育做出了相应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