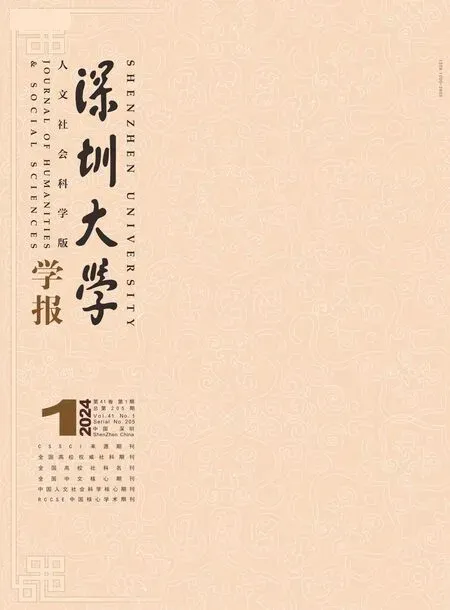国内法院解释条约的静态规则和动态协调
李大朋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88)
新时代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战略布局要求提高依据国际法参与国际治理的能力,作为我国的司法机关,我国法院正确适用条约的能力应得到进一步的重视。然而,我国法院在适用条约时,很少解释条约,或者直接按照国内法解释条约,存在对条约的解释不足问题,这直接影响到涉外审判工作的质量。
不同于解释国内法,国内法院(以下简称法院)在解释条约时首先面临的是采用何种解释规则的问题。只有在确定解释规则后,才会涉及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解释方法问题。就解释规则而言,这是对法院解释条约的静态规则分析,在于解决法院解释条约的规则依据问题。就解释方法而言,每一种解释方法背后均有不同的价值考量与适用依据,因此很难统一,甚至说根本无法统一。因此,研究视角应从对解释方法的“统一”问题转向动态协调问题,以实现条约解释因素、解释路径和解释结果的协调。基于此,本文先对法院解释条约问题进行静态规则研究,然后就国内法院解释条约的动态协调进行探索,以形成国内法院解释条约的完整理论框架。
一、国内法院解释条约的内涵
国内法院解释条约的规则问题发生在国内法院以条约为法律渊源进行审判的司法活动中,就其内涵,分析如下。
第一,条约解释可以区分为国内层面解释和国际层面解释。国内层面是指一国的国内机关包括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司法部门等对条约的解释。而国际层面主要是指国际司法机构、国际仲裁机构和国际组织对条约的解释[1](P14)。国际层面条约解释经过长期演变,已趋向于统一,特别是1994 年国际法院在其审理的领土争端案(Territorial Disputes)中明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编纂的条约规则具有习惯国际法地位之后。而国内层面条约解释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方式或规则,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理念和方法[2](P50)。
第二,在国内层面,如果解释的主体为国内法院,则为法院解释条约问题。法院解释条约与国内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解释条约不同。理论上,前者属于司法审判权范畴,而后者属于缔约权范畴,法院只能通过解释条约以适用条约,不能发展条约以赋予缔约国新的条约权利和义务,而立法和行政部门解释条约则可能不受此限。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一部分,法院在解释法律(包括条约在内的所有法律渊源)的过程中需要回答这一问题:法律的一般规范在适用于满足其构成要件的被推演出的个别规范(司法判决)时具有何种内容[3](P596)。通过解释,法官为了证成其法律决定或法律判断,在有关法律渊源的文本的诸多意义的可能性之中,选择一种最正当的意义[4]。
第三,法院解释条约问题包括两个子问题,一是法院解释条约的规则问题,二是法院解释条约的方法问题,就两者关系,进一步分析如下。
首先,条约解释的规则问题,即法院在解释条约时所应遵循的规则。作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解释的自由并不是无限的[5],而应遵循相应的规则。从司法审判角度看,不同于单纯的国内法解释,法官只有在确定条约解释的规则后,才会涉及自由裁量权范畴的条约解释方法问题,即法官根据条约解释规则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选择条约解释方法。由于解释者对条约的定性存在差异,即将条约视为缔约国之间的契约,还是缔约国的国内法,抑或单纯的国际法,这就导致条约解释规则存在以下3 种情形:契约解释规则、国内法解释规则和国际法解释规则。概言之,法院对包括条约在内的所有法律渊源解释的前提是假设法律规范总是只允许作一种“正确诠释”[3](P429),而不同法院寻找条约这种正确的诠释所遵循的规则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其次,解释方法用于处理不同解释因素之间的关系,法院需通过选择合适的解释因素或解释因素的组合以实现解释路径和结果的协调。就条约解释方法问题,理论界普遍认为存在3 种学派:客观解释学派、主观解释学派和目的解释学派。客观解释学派主张严格按照条约文本作文法解释或限制性解释,反对求助于准备资料,反对解释者主观性探讨缔约国的“意图”。主观解释学派则强调探明缔约国各自的真实意图,反对严格的文法解释和限制性解释。目的解释学派更为强调条约作为整体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宗旨,认为条约的解释应当遵循作为整体体现于条约中的目的和宗旨[6](P211)。这些解释方法共同作用于条约解释的实践,由法官根据具体的情形进行衡量和选择。
最后,条约解释规则影响甚至决定条约解释方法。首先,契约解释规则是指解释者将条约视为缔约国之间的契约,按照解释契约的规则解释条约,其核心在于确定缔约国的共同真实意图,因此它侧重于主观解释方法。其次,国内法解释规则是指解释者将条约视为国内法,按照解释国内法的规则解释条约,而各国有关国内法的解释方法存在差异。再次,国际法解释规则是指解释者以国际法特有的解释规则解释条约,特别是依据《公约》规定的解释因素解释条约。可见,法院对条约的定性不同,决定了可供其适用的解释规则的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对具体解释方法的选择。
例如,在世能诉老挝案中,一审新加坡最高法院高等法庭援引了2014 年1 月7 日老挝外交部致中国驻老挝首都万象大使馆的函件和2014 年1 月9 日中国驻老挝首都万象大使馆的回函,两封函件均认为中国-老挝双边投资条约(BIT)不适用于中国澳门,法院据此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与老挝的共同意图与立场,因此支持了老挝政府的主张。而二审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法庭认为应当依据《公约》第31条解释中国-老挝BIT,即基于条约的文本、目的和宗旨、当事国嗣后协议和实践解释条约。法院认为根据习惯国际法的移动条约边界规则,条约对缔约国的全部领土具有约束力,并自动延伸到缔约国新获得的领土。因此,中国-老挝BIT 应适用于中国澳门地区。暂且对新加坡法院条约解释的结果不做评价,仅从解释规则而言,一审新加坡最高法院高等法庭依据中国与老挝有关外交部门的函件,推断出中国与老挝均没有将中国-老挝BIT 适用于澳门的意图,采用的是契约解释规则,侧重于考察当事国的主观意图。而二审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予以纠正,阐明其依据《公约》第31 条解释中国-老挝BIT,采用的是国际法解释规则,综合考虑条约的文本、目的和宗旨、当事国嗣后协议和实践等解释因素。
二、法院解释条约的静态规则
上文所述,条约解释规则存在以下3 种情形:契约解释规则、国内法解释规则和国际法解释规则。那么,理论上法院究竟应采取何种解释规则解释条约呢?
(一)契约解释规则及其困境
一些学者认为,条约解释更近似于契约解释,其核心要义是明确当事国的合意[7]。作为缔约国合意的产物,条约必须信守正是源于古老谚语——约定必须信守(pacta sunt servanda)。国际法先驱们早已将古罗马法中的契约解释规则适用于条约的解释。例如,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在《战争与和平法》第2 卷第16 章中将条约的解释视为对缔约国承诺的解释,认为条约解释的最优规则是通过最合适的符号(包括词语本意与引申含义)推测当事国的真实意图[8]。可以看出,契约解释规则强调采用主观解释方法。
这种解释规则在早期条约解释实践中被广泛采用。例如,常设仲裁法院在1916 年审理的Timor岛屿案中明确,对条约的解释必须寻找缔约国在缔结条约时真实与和谐的意图,而不是根据文字的字面含义。进一步说,条约解释的原则就是解释私人契约的原则,应依据罗马法学家已经总结出的常识和经验进行解释①。早期大量法院案例都遵循这一理论,甚至当前很多案件仍能找到这一理论的痕迹。例如,1963 年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马克西莫夫诉美国案中认为,条约解释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定缔约国缔结条约时的意图,条约解释结果应与缔约国共同的真实期望相一致。直至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很多判例中也坚持认为解释条约的目的就是为了辨明缔约国的共同意图。
然而,契约解释规则存在以下困境:首先,缔约国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共同意图。缔约国的争议往往是他们在缔结条约时并未考虑到的,相反如果他们在缔约时能够考虑到这种争议,从而进行详细的规定,也就可能不会产生争议,因此在产生争议时,缔约国之间往往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共同意图。进一步说,当缔约国之间不存在共同意图时,法官在解释条约时声称寻找到的共同意图注定为法官个人的主观臆断。其次,法院解释条约属于司法活动,因此理论上缔约国法院在解释条约时只能受到本国缔结条约的意图和本国立法机关的意图的约束,而不是缔约国共同的意图,法院不仅无权单独决定其本国的意图,也无权决定其他缔约国的意图。因此,契约解释规则的困境在于,法院真正解释的是缔约国缔结的法律文件——条约,而不是法官主观臆断的当事国的意图[9],更不是缔约国法院无权解释的缔约国的共同意图。
(二)国内法解释规则及其困境
在这种规则下,法院在解释条约时,将条约视为一般国内法进行解释。例如,1799 年英国法院在马蒂亚特诉威尔逊案中明确,英国法院将按照解释国内法的规则去解释条约。英国法院之所以采用这种解释方式,是由英国国内法赋予条约的地位所决定的。英国缔结的任何条约都不被视为英国法的一部分,英国的法院也没有权限直接解释与适用条约。但议会可以颁布与条约条款完全一致的制定法,并从这个意义上将条约纳入英国法,可见,并不是条约,而是议会颁布的旨在纳入条约的制定法属于英国法[10]。因此,英国法院当然可以采用与解释国内法相同的规则解释条约。美国法院早期也有类似的司法实践。例如,1829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福斯特和埃兰诉尼尔森案中认为,尽管条约在性质上是两个国家的契约,并非立法,但在美国,由于宪法规定条约是美国的法律,这就要求法院应将条约等同于国内立法。
对于具体解释方法,国内法解释规则大致可以区分为主观解释方法与客观解释方法两种流派。主观解释方法认为法律是有约束力的宣示,以立法者的意图为基础,因此法律的解释应当与立法者的意图相一致。客观解释方法认为不应考察立法者的意图,而应考察法律本身的意图,法律本身的意图是指多数人共有的对法之宗旨的具有法律政策性的看法或正义观念[11]。两者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均有所体现,例如,在美国法院,主观解释方法(意图主义)相对客观解释方法(文本主义)一直占据优势,即立法者的意图优先于法律文本,直到1986 年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演讲后,新文本主义才开始兴起并提倡从立法者最初意图(Original Intent)转向文本的最初含义(Original Meaning)[12]。在新文本主义下,美国法院认为应先基于条约的文本与其使用语言的背景(context)来解释条约②。在一些案件中,法院还会考虑文本外的资料,包括缔约历史、其他缔约方的立场、其他国家嗣后实践等,但总体而言,法院对文本外的因素考察比较谨慎,如陈氏诉大韩航空公司案。又如,在英格兰法院,长期以来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不允许诉诸议会辩论记录,直到1994 年佩珀诉哈特案才有所转变,这种理念导致法院解释条约更倾向于客观解释方法。
从方法论角度看,条约解释与国内法解释在具体的方法上基本一致,大多数国内法解释方法能够适用在条约解释中[6](P211)。事实上,早期很多学者认为并未形成条约解释的特殊规则[13],只能将条约作为一般国内法进行解释。因此,这一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条约作为重要的国际法渊源,在性质上毕竟不能等同于国内法,这就导致国内法解释规则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条约为至少两个国际法主体意在原则上按照国际法产生、改变或废止相互间权利义务的意思表示的一致[14]。可见,条约毕竟具有契约性,是国际法主体之间确定其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意思表示,是缔约当事方之间的契约[15]。因此,理论上只有经全体缔约国一致同意或经全体缔约国授权同意的机构才有权进行解释[6](P210)。而法院解释条约作为一种单边的无权解释,如果径直采用国内法解释规则,只会加剧缔约国之间的矛盾甚至对抗,无助于提升条约适用结果的统一性和判决的可接受性。其次,国内法解释规则也将导致条约在各国横向适用的不一致。由于各国的国内法解释理论和实践差异较大,而国际社会并不存在类似于国内立法机关或者最高法院性质的权威解释主体,因此当条约在缔约国法院进行横向适用时,不同缔约国法院对条约的解释可能并不相同,进而导致条约适用的不一致,影响到条约在各国法院适用的可预测性。因此,坚持国内法解释规则的国家,例如英国,也在逐渐放弃原先立场,转向国际法解释规则。
(三)国际法解释规则的证成
基于解释规则的法律渊源,国际法解释规则包括依条约自身的解释规则和依习惯国际法的解释规则,法院在解释条约时均应适用。
首先,一些条约自身可能对其解释进行规定。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 条第1款规定:在解释本条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第23 条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当考虑其国际性质以及促进其统一适用的需要。本质上,条约自身规定的解释条款无一例外体现出条约起草者对于条约适用的特殊目的,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条第1 款的解释规则体现了统一性解释的原则[16]。如果条约自身存在此种规定,则根据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法院应适用此种规定解释条约。
其次,习惯国际法的解释规则是指《公约》第31、32 和33 条确定的解释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公约》的所有内容都被确立为习惯国际法,目前明确被承认具有习惯国际法地位的仅指《公约》的解释规则[17](P3)。
尽管《奥本海国际法》曾指出:习惯国际法并没有精确的解释规则[18](P362)。但在1946 年国际法院成立后,伴随着理论界与实务界在《公约》的制定、生效与实施中的充分讨论与实践,在众多国际司法机构的推波助澜下,《公约》解释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逐步形成,并为众多国际司法机构所遵守,特别是在1994 年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案中明确确定《公约》解释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之后[2](P54)。
就国际法院而言,其始终遵循着《公约》的解释规则。1994 年国际法院在领土争端案[19]中明确《公约》中的条约解释规则体现为习惯国际法。此后,基于《公约》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国际法院将《公约》适用于所有条约的解释,包括一个或多个当事国不是《公约》缔约国的条约,以及1980 年《公约》生效之前缔结的条约。就WTO 争端解决机构而言,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第3 条第2 款规定,WTO 争端解决应根据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至于国际公法解释惯例的内容,在大量的判例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援引了《公约》[20],可以说WTO 上诉机构的条约解释做法就是以《公约》第31 条和32 条为依据的。就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而言,在《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下设立的各法庭承认,必须把《公约》第31 条和第32 条作为条约法或习惯法予以适用[21]。除上述机构外,欧洲人权法院和人权事务委员会、美洲人权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刑事法院、欧洲法院等也均将《公约》作为条约解释的习惯国际法。可见,当前以国际法院为代表的众多国际司法机构已经明确认可了《公约》解释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事实上,国际司法机构之所以愿意援引《公约》,正是因为《公约》解释规则被确定具有习惯国际法地位,其可通过援引《公约》为其司法裁判行为提供一个抵挡批准之盾,以便在其判决缺乏国内法院判决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获得争议方的自觉尊重[22](P50)。
同样,若国内法院认同《公约》的习惯国际法地位,也应适用《公约》解释条约,从而提升其判决的认可度。以英国法院为例,早期英国司法实践直接将条约作为国内法进行解释,但在英国法院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条约解释的3 个规则:赋予用语与表达通常及自然的含义;寻找缔约方的共同意图;将条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释。这3 个规则正好契合《公约》第31 条,而这种契合使得英国法院更愿意适用《公约》解释条约[17](P48)。
那么,各国法院是否认可《公约》解释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呢? 答案是肯定的。对于《公约》的缔约国而言,有些缔约国法院认为应当适用《公约》解释条约,例如俄罗斯法院;有些尽管适用了《公约》的解释规则,但并不会提及《公约》,例如荷兰法院。而对于《公约》的非缔约国而言,有些非缔约国法院仍然会援引《公约》,例如印度、南非法院;而有些则内部不统一,例如美国的法院,包括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从表面看,有些法院不提及甚至拒绝适用《公约》,但本质上其解释规则正趋向于《公约》[23]。例如,墨西哥最高法院在其早先判决中认为应适用 《公约》解释条约,以便赋予墨西哥司法机关在适用条约时独立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地位,但当墨西哥司法机关逐步获得独立地位后,其认为需要重新考虑《公约》的约束力,甚至不再认为《公约》具有正式约束力,因此不应适用《公约》[24],但这并不妨碍其继续适用《公约》的规则解释条约。现代所有的法院,不论是明示还是默示,都将《公约》的解释规则作为解释条约的起点,适用于各类新旧条约[25]。可见,各国法院对《公约》解释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的认可是毋庸置疑的。
综上,在静态规则层面,法院在解释条约时,不应采用契约解释规则或国内法解释规则,而应采用国际法解释规则。
三、法院解释条约的动态协调
法院在国际法解释规则下,该如何使用正确的解释方法呢?换言之,法院在解释条约时,面对国际法解释规则提供的多样化解释因素时,该如何进行选择,以实现条约解释因素、解释路径和解释结果的协调,从而合理解释条约呢?
(一)条约解释因素
关于法律的解释因素,早期不同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萨维尼曾提出了“四要素”说,包括:文义、逻辑、历史与体系。萨维尼特别将目的排除在解释因素之外,认为规则的目的已然超越了解释的界限,而耶林泽却明确要求对每个规范的目的加以考察。经过恩吉施与拉伦茨的发展,逻辑和体系已被融合在一起,目的解释也因利益法学和价值法学而被普遍接受,因此,目前法律解释已形成新的四要素说,包括:文义、体系、目的和历史[26]。就条约的解释而言,这些因素已被纳入体现习惯国际法的《公约》解释规则中,然而条约的解释远比一般法律解释更为复杂。
体现条约解释习惯国际法的《公约》解释规则共包括3 条,分别为第31 条解释通则,第32 条解释的补充资料,第33 条经两种或两种文字认证的条约的解释。这3 条规则系统阐述了条约解释的具体方法。条约解释因素被规定在第31 条和第32条中,两者共同构成解释条约的整体框架。首先,第31 条共4 款,第1 款规定“条约应依其上下文并参考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含义,善意解释之”,第2 款就第1 款提及的“上下文”进行了界定,第3 款规定了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嗣后协定、嗣后实践和适用于当事国关系的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第4 款规定了通常含义的例外情况——当事国确定的特殊含义,上述4 款共同构成了条约解释的通则。其次,第32 条规定了条约解释的补充资料,用以辅助第31 条提及的各项解释因素。所谓辅助性资料,不是条约本身,一般包括缔约前的谈判记录、通过公约的全体大会或委员会的议事记录、条约的历次草案等[18](P366)。
综上,《公约》第31 条和第32 条提供了以下解释因素,包括:通常含义、目的和宗旨、上下文、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二)条约解释路径:对条约解释因素的选择
条约解释路径用于处理不同条约解释因素之间的优先性问题,以选择合适的解释因素或多种解释因素的组合来解释条约。如上文所述,国际法解释规则包括体现习惯国际法的《公约》解释规则和被解释条约自身的解释规则,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如下。
1.《公约》解释规则的内在逻辑
就《公约》规定的解释因素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这些解释因素表面上呈现的等级关系只是逻辑考虑的结果,并非法律层面的结果[6](P248)。因此,不能认为《公约》规定了不同解释因素之间的优先级,解释者应对《公约》解释规则进行整体理解。解释过程是一个整体,在这一行动中,解释者需要确定不同解释因素在具体案件中的相关性,并通过善意的适当强调,以确定不同解释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英国法院在金诉布里斯托直升机有限公司案中,就《华沙公约》规定的身体损害(bodily injury)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议题,在综合考虑《华沙公约》涉及的文本、通常含义、目的及宗旨等因素之后,认为《华沙公约》调整的身体损害并不包括精神损害。
而另一方面,文本、目的和宗旨、上下文、嗣后协定和实践等在逻辑上构成了权威解释方法的自然顺序。就文本而言,条约解释的起点是文本的通常含义。就目的和宗旨而言,任何条约在被解释时都应注意其目的和宗旨的真实含义,在可能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以尊重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方式解释条约。就上下文而言,条约应当在其上下文语境中被解释,应将条约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非孤立的章节条款[1](P89)。就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而言,根据《公约》第31 条第3 款,二者应于上下文中一并被考虑,辅助上下文进行解释。就补充资料而言,《公约》第32 条规定,为证实由第31 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者遇到意义仍属不明、难解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综上,在《公约》解释规则中,约文解释是基础,按照目的和宗旨以及上下文解释是正当性的保证,嗣后协定和实践在于验证上下文解释,而补充资料解释是辅助性手段[17](P164)。
因此,《公约》解释规则的内在逻辑要求:条约的条款被赋予的通常含义应是条约解释的首要要素;条约蕴含的目的和宗旨以及条约上下文应处于次级要素地位,用以保证通常含义解释的正当性;与条约解释有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应处于再次级要素地位,在于验证上下文解释[27];而补充资料则应最后考虑,用以补充或验证以上解释因素的解释结果。
2.被解释条约的解释规则对《公约》解释规则的调整
上文所述,除了体现习惯国际法的《公约》解释规则外,一些条约自身也可能规定了特殊的解释规则。在条约本身有此规定的情形下,若缔约国未在缔结条约时对此做出保留,则缔约国法院有义务适用该条款解释条约。
就条约自身规定的解释规则与《公约》解释规则之间的关系,根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作为特别法的条约自身解释规则,应优先于作为一般法的《公约》解释规则。这是对《公约》解释规则的特殊调整。条约自身规定的解释规则体现了条约的基本宗旨和目标,因此,条约自身就其解释问题进行特别规定是将条约的宗旨和目标因素提升到更为优先的地位。当然,对于被解释条约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公约》解释规则不再适用,而是在明确条约自身解释规则优先的前提下,其应与《公约》解释规则共同构成该条约的完整解释规则。例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 条第1 款规定,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可见该条约要求缔约国法院在解释条约时,应考虑到条约在各缔约国的统一适用问题。因此,法院在解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时,基于该公约第7 条第1 款规定的统一解释目的,对外国法院判决中形成的有关该公约的统一意见应予以特别考虑,换言之,法院应将统一解释的目的和宗旨提升到优先地位。相反,如果没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 条第1 款规定的解释规则,则这些外国法院的司法实践要么属于《公约》第31条第3 款(b)项规定的嗣后实践,要么属于《公约》第32 条规定的辅助资料,应劣后于《公约》第31 条解释通则中规定的条约通常含义、目的和宗旨以及上下文因素。
(三)条约解释结果:以条约解释结果优化解释路径
法官针对具体的待判案件进行法律解释工作,而法律倾向于促成符合正义的解答。通过解释,法官期待获得正当或至少“可接受”的决定,如果期望落空,则法官有足够的动机质疑原本解释路径是否妥当并重新选择解释路径[28]。条约解释也是如此,法官在解释条约时,应以解释结果为锚,优化不同解释因素之间的排列,以实现解释结果和路径的协调。在遵循国际法解释规则的基础上,法院通过对条约解释因素的选择而产生的解释结果应满足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同时解决被解释条约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并不得使其超越司法审判权的范围。
1.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对于任何条约解释规则而言,其背后最基础的原则为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是一项公认的习惯国际法,是条约法的核心,也是国际法最重要的原则[29]。根据《公约》第2 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当事国具有拘束力,必须由各国善意履行。条约必须信守源于古罗马法的约定必须遵守原则,根据该原则,契约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而类比私人契约理论,国家之间缔结的条约是缔约国之间的法律,对缔约国具有国际法效力。类比契约法中大陆法系的善意原则、诚实和信用原则,以及英美法系的正当履行和实质性履行原则,条约必须信守不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遵守,还意味着缔约国必须善意履行其缔结的条约[30]。缔约国应善意、诚实和正直地履行条约,不仅应按照条约的文字,也应按照条约精神、宗旨和目的,完整地履行条约。
条约必须信守在条约解释领域体现为善意解释原则。当法院提及条约解释中的善意解释原则时,其均倾向于强调该原则在条约解释中的基础性作用[17](P167),可以说大部分当前的解释规则,无论是解释条约还是解释合同,都是善意解释原则的具体化[31]。一般而言,善意解释拥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条约的精神优先于对条约文字的过度依赖;二是应寻找对条约文本的合理解释,这种合理解释应能为一个诚实和合理的当事方理解或应当被其理解。前者在于从消极意义上避免条约的恶意解释,后者在于从积极意义上确保条约的解释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32]。相反,一国不得以国内法为借口逃避国际责任。即便国内法和国际法相抵触时,受制于国内司法机关的权限,法院虽不能变更国内法以适应国际法的要求,但法院可以推定认为这种抵触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开明的国家不会故意制定与国际法相抵触的规则,因此,法院应尽可能加强解释,以避免抵触[18](P30-31)。
2.被解释条约与国内法的衔接
条约在国际法层面对国家的拘束力,并不意味着条约当然、立即具有国内法律的地位和效力,在此之前,条约还需要被国内化,即条约的转化和并入[33]。条约转化适用是指缔约国通过国内立法(包括立改废)方式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予以适用。但条约转化为国内法后,法院实际上适用的是承载条约内容的国内法律,因此不涉及条约的解释问题[34]。而条约并入适用是指缔约国将其缔结的条约并到国内法中予以适用的方式。本质上,处理好被纳入条约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在于实现由被纳入条约和国内法所构成的法秩序的内在统一协调性。
首先,法院应将条约置于国内法背景下解释。对于国际法层面的条约和被纳入国内法后的条约,尽管条约本身并无差别,但解释者看待条约的角度是不同的,前者从纯粹国际法背景看待条约,而后者是从国内法背景看待条约,被解释的对象除了被纳入的条约外,还涵盖了支撑被纳入条约的国内法体系。换句话说,法院解释的是以被纳入条约为核心的相关国内法体系。事实上,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法学建构理论,存在着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分野,前者主张国家法秩序优先,从主权国家出发理解法律体系;而后者主张国际法秩序优先,从国际社会层面去理解法律的存在。两种理论的对立对于法(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的内容没有任何影响,但前者认为国际法被包括在国家法之中,而后者认为国家法被包括在国际法之中[3](P593)。对于其他主体解释条约,该争议的理论分歧尚存合理性,但对于法院解释条约而言,受制于解释者的国内司法机关地位和条约产生国内法效力的方式,法院理应遵循国家主义理论,将条约放在国内法的背景下进行解释。
其次,对于条约未规定的事项,应依据国内法进行处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社会、法律背景的差异,各国在一些领域很难达成协议,即便缔结条约,缔约国也可能就某些事项声明保留[35]。这就导致对于一个法律事项而言,条约很难做出全面的规定。而对于条约未规定的事项,法院仍需依据国内实体法加强解释。
以1999 年《蒙特利尔公约》第35 条的解释为例,该条规定:一,自航空器到达目的地点之日、应当到达目的地点之日或者运输终止之日起两年期间内未提起诉讼的,丧失对损害赔偿的权利。二,上述期间的计算方法,依照案件受理法院所在地的法律确定。该条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该条规定的两年期间的性质是诉讼时效还是除斥期间? 二是如果该条规定的两年期间为诉讼时效,其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 就这两个问题,由于条约并未明确规定,因此,各国的判决并不一致。我国法院认为,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对航空运输合同规定相关的除斥期间,因此该两年期间在性质上只能属于诉讼时效。本质上,这是将条约置于我国法律背景下进行解释。就第二个问题,《蒙特利尔公约》第35条本身未对该期间的中止中断做出规定,而是将这一问题交给国内法处理,因此,法院认为该条规定的两年期间适用我国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本质上,这是对条约未规定的事项依据我国国内法进行处理。上述两个解释结果均是根据《公约》第31 条规定的解释规则得出的,它们可能与其他国家法院的解释结果并不一致,但就我国法院而言却是恰当的,这体现了《蒙特利尔公约》与我国国内法的良好衔接。
3.不得越权解释条约
不同于单纯国际法层面的条约解释,法院解释条约时也受到国内法的约束。然而,其应受到何种内容的国内法约束,则取决于各国司法权的范围和法律适用制度[22](P68),因此,各国之间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如下。
第一,不得为缔约国创设新的条约义务。缔约国政府解释条约是行使缔约权的范畴,而法院解释条约是行使司法权的范畴。作为缔约权的一种,缔约国政府可以非正式地同意某种解释,或者同意订立一个附于条约的解释性宣言或议定书,或者订立一个补充条约[18](P362),在缔约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这种解释可以为缔约国创设新的条约权利义务。但法院解释条约则不同,这是法院以条约作为解决案件争议的法律渊源,表现为法院以查明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以条约的规定为大前提,将条约适用到具体的案件事实并做出裁判的行为,这是法院依据法定职权与程序,具体应用条约处理案件争议的司法活动[36],法院在行使解释条约的司法权时,不得为本国创设新的权利或义务。换句话说,法院只能解释条约,不得发展条约。因此,若法院采用的解释路径为缔约国创设了新的条约义务,则应重新调整或优化解释路径。例如,在英国法院审理的琼斯诉沙特阿拉伯王国内政部案中,法院提出不得通过单边适用某一法律(条约)而发展国际法,无论法院多么渴望或此种解释多么有价值,都不会被其他国家所接受。
关于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条约的演化解释问题,法院在解释条约时应避免演化解释。条约的演化解释是指对条约的意旨和内涵作出随时间而变化的解释,本质上这是条约发展的一种途径,解释者通过对条约的演化解释推动条约与时俱进。这种解释方式在国际司法机构解释条约的实践中越来越频繁。例如,2009 年国际法院在审理的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关于航行和有关权利案中指出:“当事双方在条约缔结时应考虑到国际法的发展变化情况,愿意或假定愿意赋予所有术语或部分术语变化,而并非一成不变”[37]。然而法院在解释条约时,应尽量避免演化解释,因为条约的演化解释会造成语义变化与规则发展,直接引发缔约国条约权利和义务的变动,已经产生了类似造法的效果。例如,在美国联邦第四巡回法院审理的海猎公司和弗吉尼亚州邦联诉身份不明失事船只案中,法院拒绝按照当前的国际海洋法背景解释1763 年由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签署的《最终和平条约》(Definitive Treaty of Peace,以下称《1763 年条约》),而是回到1763 年该条约签署时的背景解释条约。法院认为由于1763 年尚未产生大陆架的法律概念,因此按照1763年缔约国的理解,大陆上的权利不可能包括大陆架上的权利,因此西班牙在《1763 年条约》中同意明确放弃所有位于北美大陆的财产不能被解释为其也同意放弃所有位于北美大陆架上的财产。
第二,对于缔约国政府做出的解释,法院在解释条约时应当尊重。换言之,法院解释条约应当受到缔约国政府解释条约的约束。例如,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行政部门做出的涉及政治性问题的条约解释,美国法院一般都予以尊重。对于政治性问题以外的条约解释,由于行政部门负责条约的谈判并更理解其他国家缔约后的实践,因此法院对行政部门的解释也应当尊重。若法院采用一种解释路径产生的解释结果不符合其政府所做的解释,则法院应重新调整或优化解释路径。
第三,法院解释条约的主体是国内法院,其对条约的解释属于国内司法活动,因此法院在解释条约时,应遵守国内法中的法律适用制度。例如,在英美法系国家,法院解释条约应当遵守国内法先例,而这优先于国际法上的条约解释规则。在英国法院审理的金诉布里斯托直升机有限公司案中,英国法院明确其解释《华沙公约》中身体损害(bodily injury)的概念必须遵循其先例,而不是跳过先例直接解释《华沙公约》。就我国法院而言,这些法律适用制度包括司法解释制度、指导性案例制度、类案检索制度等。我国法院在解释条约时,应恰当选择合适的解释路径,确保解释结果符合这些法律适用制度。以司法解释制度为例,对于一些重要的民商事条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指导下级法院正确适用条约,例如1987 年的《〈关于执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以及2011 年的《关于审理船舶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5 条,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中国法院在解释条约时应当适用,其对条约的解释不能违反司法解释。
四、结 语
我国法院正确解释条约能力的提高是我国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法院提升涉外审判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理论和实务界对此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以提升我国的司法公信力与影响力,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更好地维护我国国家、企业、个人的合法权益。
法院解释条约问题是条约法研究的新领域。至于我国法院如何解释条约,则更是一块理论研究的处女地。就法院解释条约问题,应同时进行两个维度的研究:一是静态规则研究,在于解决法院解释条约的规则依据;二是动态协调研究,在于实现条约解释路径和结果的协调。就法院解释条约的动态协调而言,法院应以解释结果为锚,调整和优化解释路径,选择合适的解释因素或解释因素的组合以合理解释条约。具体而言,首先,法院解释条约应予考虑的因素包括:通常含义、目的和宗旨、上下文、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其次,在解释路径上,法院应依据《公约》的内在逻辑选择合适的解释因素或解释因素的组合,如果被解释条约自身对其解释有特殊规定,则法院应适用此种规定。再次,在解释结果上,法院应遵守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同时处理好被解释条约与国内法的衔接问题,且不得越权解释条约。
注:
①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rbitral Award Rendered in Execution of the Compromise Singed at Hague, April 3, 1913, between the Netherlands and Portugal on the Subject of the Boundary of A Part of Their Possessions in the Island of Timor on 25 June 1914.
②例如:Water Splash, Inc.v.Menon, 137 S.Ct.1504, 1509(2017).Air France v.Saks, 470 U.S.392, 397(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