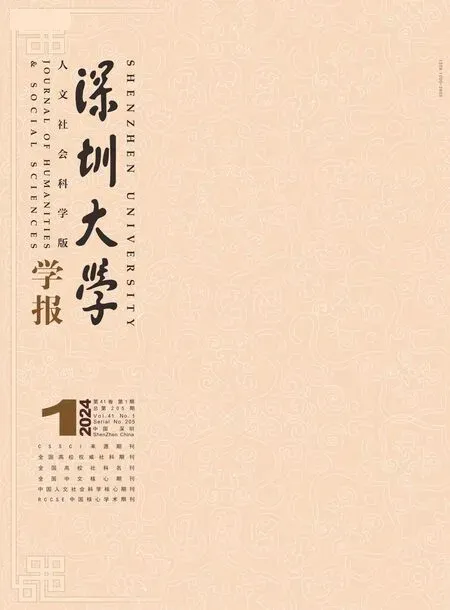空间位移下宋代女性文学的拓展与新变
刘双琴
(1.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2.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 南昌 330077)
空间和地方是表述日常经验时常见的词语。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中指出,人类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地方”是安全的,而“空间”是自由的,“人类的生活是在安稳与冒险之间和依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在开放的空间中,人们能够强烈地意识到地方。在一个容身之地的独处中,远处空间的广阔性能够带来一种萦绕心头的存在感。健康的人能够愉快地接受约束和自由,接受地方的有界性和空间的敞开性”[1](P44)。“空间”与“家”是人类经验的两极,二者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要素。前者表征着移动、行游,以及未知的将来,后者则暗示了沉静、停息,以及具体的当下。空间流动意味着对日常空间即“本地”与“家”的出离,同时,流动空间中产生的文学则是检视自我与景观、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空间的流动,往往可以使流动主体的眼前展开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化区域和文化视野,这种‘双世界视景’,在对撞、对比、对证中,开发了人们的智慧”[2]。那么,空间位移带来怎样的非日常空间经验,并如何影响文学表达?我们试以宋代女性作家的流动与文学创作为例予以论述。
一、从闺内到闺外:流动与宋代女性作家空间经验的非日常化
两宋时期,尽管传统主流价值观仍倡导以内外之别建构理想的性别秩序格局,强调“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等性别伦理规范,但在实际生活中,女性的活动空间并非如此狭窄,其主体地位与空间自由并未完全丧失。宋代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流动性增强,也为女性出游带来便利,宋代女性的日常游冶、节日出游等游览活动明显增多[3],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魏夫人《菩萨蛮·红楼斜倚连溪曲》、张玉娘《灯夕游紫姑神》等游冶诗词、节令诗词的涌现,都反映出传统性别秩序下宋代女性空间经验的非日常化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刺激作用。除了近距离的日常出游,两宋时期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女性作家的远行活动普遍增多。笔者爬梳《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以及宋人笔记、史志碑传等文献史料,整理出有作品传世的女性作家282 名。其中,有寓居异乡或在异乡活动经历的女性至少有122 人。
据初步统计与分析,在这122 例中,因战乱而颠沛流离、迁徙他地的就有56 例,占比几近一半。如鄱阳某妇人,据《景定建康志》卷五十载,该女子在建炎初年流落湖南,夫不幸溺死于洞庭湖,女子携幼子漂泊无依,无家可归,感时伤心,成小绝云:“故里萧条一望间,此身飘泊叹空还。感时有恨无人说,愁敛双蛾对暮山”[4]。孤独绝望之情跃然可感。又如某宫人,靖康之变后流落关中,在驿舍壁间题诗二首,其中一首云:“鼙鼓轰轰声彻天,中原庐井半萧然。莺花不管兴亡事,妆点春光似昔年”[5]。可见金兵入侵中原后,中原庐井萧然,人口大量流失,女性亦因战乱从中原流徙他处。在这些反映战乱流离的作品中,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最具典型性。这篇序文于绍兴四年(1134)作于临安,详细记录了靖康、建炎年间金兵犯京师时作者的南徙路线、途中经历,以及一些珍贵书籍、文物在战乱间流失殆尽的过程,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
除了因战争离乱而流徙他地,两宋时期女性作家随亲流动现象也极为常见。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身份属性往往以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性别伦理标准确定。与此种“三从”性别伦理相应,宋代女性随亲宦游的行旅活动主要表现为随父、随夫、随子流动。早在汉武帝时期,为防止地方势力的扩大,就有刺史不得用本州人等禁令。到唐宋时期,本籍回避制度进一步发展,禁令甚至拓展至邻县。两宋时期,随着科举取士的发展,漂泊、游宦更成为士人的人生常态。在前述122 例中,随亲流动者即有近40 例,包括随父流动、随夫流动、随子流动,以及随叔伯、兄弟等其他亲属流动等形式。随父流动者如太原王琼奴,曾随父游宦,行经淮山古驿,题壁云:“昨因侍父过此,时父业显宦,家富贵,凡所动作,悉皆如意。日夕宴乐,或歌或酒,或管弦,或吟咏,每日得之,安顾有贫贱饥寒之厄也!……平昔之心皎皎,虽今复过此馆,见物态景色如故,当时之人宛如在左右,痛惜嗟叹,其谁我知也? ”[6]随夫流动者如李清照,据其《金石录后序》记载,她与赵明诚结婚后,先随赵明诚居汴京,后赵明诚受元祐党争的影响,被追夺赠官,退居青州乡里,李清照亦随之居乡十余年。后明诚官莱州,守淄州,清照皆一路相随。此外,朱淑真婚后也长期随夫游宦淮、吴、湘、楚间,并留下众多反映其行旅经验的作品,如《春日抒怀》《寒食咏怀》《舟行即事》等,反映的都是“从宦东西不自由”的流徙生活。两宋时期,传统孝道伦理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加之入宋以来国家层面的倡导与鼓励,促使士大夫奉母宦游四方以行奉养之义,从而使随子嗣流动的女性作家数量有所增多。随子流动者如宋太祖之母昭宪杜太后,原居涿州涿郡,太祖即位后,随迁汴京。又如河南郡慕容氏,初随次子官随州,绍兴九年(1139)前后,随次子居江东,后移居长子处所。这些随子徙居的经验也或多或少体现于她们的作品中。
此外,引起两宋时期女性作家在不同地域间流动的原因还有很多。包括因日常生计而流动,如英州谭意哥、甘棠温琬、建宁真真;也有因家庭变故而流动者,如姑苏钱氏。据《醉翁谈录》乙集卷二载,钱氏尚未成年即适里人朱横,随夫经商于岭南。夫朱横客死岭南,钱氏携遗孤归姑苏,途经望湖亭(在今永修吴城),遇风驻留,题诗于亭壁。其序云:“予吴人也,世本良家子。顷因丧乱,父母以妻里人朱横,时年未笄耳。宋理宗即位之二十二年,横因商于岭右,妾两偕过此。不幸去岁秋,横竟殁于瘴乡。栖迟之踪,无以自处,因携其遗孤以归故乡。在道路,历艰虞,仅四十日矣。昨暮抵此,以风急未能济,舣舟城下。夜久不寐,有西风飒然而来,皓月皎然窥人。斯时也,况羁旅乎!晓登望湖亭,睹江山如故,不觉有所伤感然。因吐其胸中,书于壁间。好事君子,幸勿以妇人玩弄笔砚为诮。兹亦叙其略云”[7]。凄苦之情了了可见。
宋代女性的流动呈现出被动性、广泛性、时代性等诸多特征,这些流动为女性带来特殊的空间体验。一般而言,衡量空间位移与变换是否产生意义,主要在于移动主体是否获得了非日常的空间经验。与一般的短距离出游活动不同,自古以来,长距离的行旅活动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也是一件充满烦劳和风险的事。“英文的‘旅行’(travel)源自‘担心’(trouble)或‘辛劳’(toil),可见旅行自古以来即意味一连串的苦难”[8],路途中的林深叶茂、风高浪险、悬崖峭壁往往是引起人害怕、警觉和焦虑的“恐惧景观”(段义孚语)。古人极为重视出行,把出行看成非同寻常的事。无论出行目的为何,出行“总是离开自己较熟悉的地方而去之较不熟悉或完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地方……不但是必有危险,这些危险而且是更不知,更不可知,更难预料,更难解除的”[9]。对于宋代女性而言,形式各样的踏青、出游活动并不陌生,这些寻常的出游活动尚未完全超出她们的日常经验范围,而因生计、随宦、离乱等原因的流徙为她们带来特殊的非日常空间经验,尤其是社会动荡所带来的漂泊流离,无疑使她们的处境极为凄惨,并对其文学表达产生重要影响。流离是宋代女性最为艰辛的生命体验,女性自身对这一空间经验的文学表达,往往比男性笔下呈现的女性命运,以及史书所记载的女性遭际来得真实而深刻。可以说,长时间、远距离的空间流动不仅给宋代女性作家带来深刻丰富的异域经验,也为其文学创作增添了不少异质资源。空间行旅开掘了宋代女性思想情感的深度,拓展了她们知识视野的广度,提升了其文学作品的高度,从而促使古代女性文学由“中世”向“近世”转型。
二、从主体到客体:宋代女性身份意识的转换与文学思想的深化
日本汉学家内山精也在《宋诗能否表现近世? 》一文中指出,从北宋末开始,以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诗歌领域出现了新的作者阶层,即“出生于士大夫家庭,在正常情况下成长,经历了普通的婚姻生活”[10],且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闺阁诗人。在传统闺阁空间的制约下,宋代女性文学呈现出以闺情表达为主的特质。当女性因为各种原因被迫从熟悉的家室空间流入陌生空间,随之而来的就是其身份由主体向客体的变化,以及因身份转化而带来的焦虑感。身处异乡之时,身份的归属变得尤为重要。在“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天子以四海为家”(《史记》)、“丈夫四方志”(杜甫《前出塞》)等观念的召唤下,古代男子纷纷去异地他乡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知识与价值,对他们来说,空间位移往往是主动选择的产物。但对闺阁女子来说,“妇无公事,所知者蚕织;女无是非,所议者酒食。则窥观,乃女子之正道也”(来知德《周易集注》)。按照这种性别秩序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两宋时期,“女性”的身份就和“家-地方”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身份和空间来说,对女性空间流动性的限制在某些文化语境下是一种表示服从的重要方式。此外,对空间流动性的限制,即将女性局限在某地,与限制女性的身份紧密相关”[11]。因此,当空间位移被迫发生,女性更容易面临原有身份的遗失,更容易通过对家园的回望来确认自我身份。如朱淑真《春日书怀》:“从宦东西不自由,亲帏千里泪长流。已无鸿雁传家信,更被杜鹃追客愁。日暖鸟歌空美景,花光柳影漫盈眸。高楼惆怅凭栏久,心逐白云南向浮”[12](P17981),表达的就是随夫游宦、不由自主的身份失落之感、异地客居之愁。又如魏夫人,一生随曾布辗转各地,曾作《阮郎归》云:“夕阳楼外落花飞。晴空碧四垂。去帆回首已天涯。孤烟卷翠微。楼上客,鬓成丝。归来未有期。断魂不忍下危梯。桐阴月影移”[13](P268),把辗转流徙中的羁旅客愁书写得深沉婉转。再如李清照,靖康之难后,她随赵明诚至建康,也曾经历由“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14]的逸兴遄飞,到“春归秣陵树,人客远安城”“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13](P929)的枯寂无聊。晚年寓居临安后,李清照更是生发出“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永遇乐·落日熔金》)[13](P931)、“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声声慢·寻寻觅觅》)[13](P932)的今昔之感与故土之思,呈现出其客居身份与心态。
据笔者对《全唐诗》以及《全宋词》的统计,唐代女性文学作品中,“客”字出现了27 次[15],宋代女性文学作品中,“客”字出现了30 次。单看这两个数据似乎无法看出差异,但仔细考察唐、宋女性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即唐代女性以“客”指称自我仅4 处,占14.8%,而宋代女性以“客”指称自我则达23 处,占到了76.7%。可见,唐代女性多以“客”代指他人,而宋代女性笔下的“客”大都指向自我,并与“愁”这一情感联系。
在日常空间中,宋代闺阁女性的身份和地位一般都比较固定。一旦离开日常空间,进入陌生的非日常空间,她们原有的身份便逐渐弱化,“旅客”成为第一身份。“对旅行者来说,非日常空间是陌生的、危机四伏的,又是新奇的、诱惑重重的”[16],空间位移带给宋代女性由主体到客体的身份认知与焦虑,主要源于因未知而产生的无助与恐惧。按照段义孚的观点,地方意味着安全,空间意味着自由和威胁。地方是“价值中心、养育和支持的中心”[1](P22),地方感作为人地关系的文学反映,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方向起一定的指引作用[17]。当宋代女性走出深闺,获得非日常的空间体验,导致其身份由主体向客体转换,其文学书写的情感向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李清照《春残》:“春残何事苦思乡,病里梳头恨最长。梁燕语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12](P18007)。其诗收入《绣水诗钞》卷一,据考证,绣水乃章丘之别名,诗当为元符元年(1098)前后作于汴京,表达的是清照随父母由章丘客居汴京时对故乡章丘的思念[18]。再如苏氏《踏莎行·寄姊妹》:“孤馆深沈,晓寒天气。解鞍独自阑干倚。暗香浮动月黄昏,落梅风送沾衣袂。待写红笺,凭谁与寄。先教觅取嬉游地。到家正是早春时,小桃花下拼沉醉”[13](P200-201),极写客居旅馆时对家中姊妹的牵念。又如卢氏《凤栖梧·题泥溪驿》:“蜀道青天烟霭翳。帝里繁华、迢递何时至。回望锦川挥粉泪。凤钗斜亸乌云腻。钿带双垂金缕细。玉佩玎珰,露滴寒如水。从此鸾妆添远意。画眉学得遥山翠”[13](P194)。诗人辞别故里,取道泥溪驿向帝京而行,旅途中回望锦川,满眼是泪,客体身份一目了然。
对于宋代女性来说,最深刻而痛楚的空间移动体验莫过于因战乱而带来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两宋时期最杰出的才女,她们最优秀的作品,都并非出现在‘太平盛世’,而恰恰是在政局动荡、国难当头、社会巨变的时期”[19]。这一时期的民族灾难、社会动荡带给女性的冲击,往往伴随着地理空间上的长远移动。在空间的位移中,传统性别规范受到严重冲击,古代女性基于爱情、婚姻、家庭等日常生活的空间体验被迫中断,许多人流离失所,传统礼教下女性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社会身份彻底失落,她们被迫放弃闺阁空间中的“小我”,转而关注国家、社会、历史,并与国家、故土形成同构关系。乱世中,国家、江山不再是“他者”,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彼地空间,而成为“主体”的一部分,成为女性空间经验的一部分。她们的客愁,也不再仅只是传统的、直观的地理乡愁,而且还是国破家亡的政治乡愁。
三、从望远到怀乡:宋代女性地方意识的觉醒与文学主题的新变
“地方”是一个复杂的词,库克(Cook)指出地方是人类生活、活动和运动的背景,同时,人通过赋予地方人文意蕴来构建地方[20]。在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看来,当给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赋予意义和价值时,物理空间就变为地方,“地方有不同的规模。在一种极端情况下,一把受人喜爱的扶手椅是一个地方;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整个地球是一个地方”[1](P122)。地方的亲切经验埋在人内心深处,使人对地方产生深刻依恋。在宋代女性的空间位移过程中,地方依恋呈现出多样性。处于流离漂泊状态的女性更能感受到精神上的失落与失向,以及个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亲密的家庭能使其产生安全感,并因为有所爱的人在身边而感到宽慰。如北宋诗人王令之姊,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携幼子随弟王令辗转流徙于瓜洲、润州、江阴各地。尽管王令奉姊如母,教甥如子,然不求功名的人生信念和贫困潦倒的现实生活,使他不得不让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姐姐再嫁,以免大家因饥寒而死。姊作诗云:“无求子乐我何悲,且与儿曹并日饥。子道合人终不苟,有求虽欲可从谁”[12](P8192)。在王令姊看来,人生之乐并不在于物质的富足,而是能与亲人相依相从。
由地方依恋产生的地方感对作家创作的指引作用,主要体现为“文学作品能够在字里行间表达作者内心的地方情感,同时地方感会影响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17]。地方感主要包括地方依附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它暗示的是一种家园感,“其根子就是历代哲人所思考的‘还乡’之旅”。“人类的远行与还乡之旅,是文学家非常重要的表现主题”[21],远行与还乡二者中,还乡所牵萦的情感最为复杂,远行之旅则往往伴随着精神的还乡之愿。宋代女性由于常年居于深闺,她们的文学作品仍多局限于闺情的表达,然较之唐代及以前,她们获得了更多的非日常空间经验,其地方意识已然被唤醒,并直接体现于她们的文学作品。
地方意识引起女性文学主题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望远主题向思乡主题的转换,闺情主题向家国主题的发展。客愁、思乡作为地方感和地方意识的具象表达,并不是女性在其日常生活的家乡所生成的,而是经历了漂泊、流徙等空间移动之后,“通过‘追忆故乡’的方式激活了某种沉睡着的地方意识”[22]之后产生的。据初步统计,宋代女性表达怀土思亲主题的作品就有20 余首。如魏夫人《阮郎归·夕阳楼外落花飞》写暮春风光明媚,词人却流落天涯,不知归期,只能登楼远眺以寄乡情,全词所抒正是旅途漂泊中的思归情绪。此外,还有朱淑真的一系列作品,如《得家嫂书》《寒食咏怀》《秋日得书》《舟行即事》《寄大人》《和前韵见寄》《春色有怀》《春日书怀》,不仅仅抒发出随夫宦游时的怀乡之情,还表达出因嫁入夫家而产生的对父母、亲人的思念。可见,空间迁移带来的对故土的眷念与乡愁已成为宋代女性作家最深刻的情感记忆。
由地方意识带来的文学主题内容的拓展还反映在核心意象的选择上。以李清照南渡前以及南渡后的词作为例,一般认为,南渡之前,李清照的词主要写女性的闺阁生活,感情舒缓有致,词风清丽宛转;南渡以后,多写国破家亡后的体验,思想深沉复杂,词风沉哀凄苦。从空间位移与地方意识的视角解读李清照南渡前后的作品,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其核心意象的转换。南渡之前,李清照词的核心意象主要是“楼”“月”“琴”“花”[23],这些核心意象及其延展出的 “危栏”“帘幕”“沉水”“金猊”“玉簟”“纱橱”、“中秋”“星桥”“暗香”“花影”“玲珑地”、“瑶瑟”“羌管”“横笛”“玉箫”、“红藕”“海棠”“江梅”“白菊”“酴醾”等具体物象,构筑出一个典型的闺阁空间,同时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抒情系统,传达怀春少女的闺愁,包括百无聊赖的慵懒感、长恨莫名的迷惘感,以及芳华易谢的无奈感。但南渡以后,李清照词的核心意象却以“江”“雁”“雨”“梦”为主,这些核心意象及其派生出的“双溪”“江湖”“舴艋舟”“千帆”“春浪”“归鸿”“征鸿”“风雨”“三更雨”“黄梅雨”“细雨”等具体物象,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异域空间,抒发国破家亡、浪迹天涯的凄恨。这些新的核心意象,其功能由直观的感兴转为隐晦的暗示,部分意象甚至具有一定的原型象征功能。这标志着李清照词抒情艺术、思想境界的重要转变与走向成熟。例如核心意象“江”,因其流动不居,就具有原型象征意味。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江”与羁旅客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唐代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江”意味着流动,以及由流动义申发出的关于舟船漂泊、离乱人生的联想。又如意象“雁”“雨”“梦”,尽管在李清照前期作品中也曾出现,如“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点绛唇·闺思》)、“独抱浓愁无好梦”(《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但它们仅仅是缓解闲愁的陪衬,或个人睡眠状态的陈述。而到后期作品中,这些意象才真正具有核心意象功能,如“归鸿声断残云碧”(《菩萨蛮·归鸿声断残云碧》)、“次第岂无风雨”(《永遇乐·落日熔金》)、“熏透愁人千里梦”(《摊破浣溪沙·揉破黄金万点轻》),其感发功能增强,在文本结构中具有带动全局的作用。国破家亡后的“南渡”作为一种痛彻心扉的空间流动经验,极大地推动了李清照词核心意象功能的转换及文学主题的升华。
四、从单一到多元:宋代女性地理视野的拓展与艺术手法的开拓
空间位移带来的视野拓展为宋代女性文学艺术手法的演进提供了可能,主要表现为作品体式由短制向长篇的拓展。中国古代诗歌多为短制,这与儒家文化重言志、轻叙事的传统密不可分。“诗”与“史”的分野,诗言志、词缘情的理论主张以及诗歌自身声韵格律化的趋势、以含蓄为贵的审美取向等,对叙事诗的发展是一个极大挑战。一般说来,短制意味着以抒情为主的表达模式,长篇则为叙事提供足够从容的表达空间。地理空间的流动为宋代女性文学带来丰富的异质资源,从而为长篇形制与叙事表达提供了可能。通观宋代女性文学,短篇抒情作品常产生于静止的地理空间,而长篇叙事作品则多出现于流动的地理空间。宋代女性文学中,有代表性的长篇叙事作品如李清照南渡后所作的《金石录后序》,其最重要的叙述线索就是作者大半生的空间移动轨迹。又如曹希蕴,游历极广,曾遍访名山宫观,结交有道之士。她行游至罗浮山,因作长诗《赠邹葆光道士》,赠予居住于此的道士邹葆光。全诗以作者游踪为线,先说“罗浮自古神仙宅,万里来寻况是家”,写自己心念罗浮、寻访高士之行,末以“翩然孤鹤又南征,寄语石楼好风月”作结,写求神问道后离开罗浮[12](P45291-45292)。“来-去”的空间位移成为穿插全诗的重要叙事脉络。再如雁峰刘氏慢词《沁园春》、徐君宝妻慢词《满庭芳》、王清惠慢词《满江红》、金德淑慢词《望江南》、周仲美古体《书邮亭壁》、张玉娘古体《辞郎行》、韩希孟《练裙带中诗》,都是在因战争带来的空间位移中产生的叙事佳作。此外,王琼奴《题淮山驿壁》、韩玉父《题漠口铺》也是辗转流落之间对个人身世、经历、流徙路线等的长篇叙述。
在交通、通讯极为不发达的古代,远足可能意味着与朋友和爱人的分离。空间距离、离情别绪会带来表达方式的变化,“早期的中国文献中曾使用‘千里’(one thousand li)这一表达唤起对遥远距离的感觉。到汉朝时,‘万里’(ten thousand li)流行起来”[1](P44)。两宋时期,随着女性空间经验的增加与地理知识的拓展,女性文学的表达手法也更加丰富,“千里”“万里”“万迭”“千山”“万山”“万津”等表现宏大地理感知的词汇明显增多,女性试图以这一类词汇以及对比性的自然环境唤起距离感、分离感。如王安石长女出嫁后,随夫宦居汴京,作《寄父》诗曰:“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然和泪看黄花”[12](P10445)。苏氏《鹊桥仙·寄季顺妹》云:“星移斗转,玉蟾西下,渐觉东郊向晓。马嘶人语隔霜林,望千里、长安古道。珠宫姊妹,相逢方信,别后十分瘦了。上林归去正花时,争奈向、花前又老”[13](P200)。其均以“千里”唤醒距离感,传达分离之痛。朱淑真也极善于以空间距离的遥远表达乡情与亲情之切,如《舟行即事》其二称:“扁舟欲发意何如,回望乡关万里余。谁识此情肠断处,白云遥处有亲庐。”《寄大人》其一云:“去家千里外,飘泊若为心。诗诵南陔句,琴歌陟岵音。承颜故国远,举目白云深。欲识归宁意,三年数岁阴。”《寄大人》其二云:“极目思乡国,千山更万津。庭闱劳梦寐,道路厌埃尘。诗礼闻相远,琴樽谁是亲。愁看罗袖上,长揾泪痕新”[12](P17998)。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黄慧真《送水云归吴》:“万叠燕山冰雪劲,万里长城风雨横。君衣云锦勒花骢,此酒一杯何日更”[12](P44059)。章妙懿《送水云归吴》:“一从骑马逐铃銮,过了千山又万山。君已归装向南去,不堪肠断唱阳关”[12](P44062)。
空间经验的增加还带来宋代女性文学风格的变化。“能够超越已经习得了的、甚至内化为自觉模式的诗学,是由于来自文本中的诗学经验与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之间发生了根本冲突”[24]。如苏州歌妓盈盈最初写给王山的《伤春曲》:“芳菲时节,花压枝折。蜂蝶撩乱,栏槛光发。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来,空余栏槛对寒月。”作此诗时,盈盈正身居东海一带(今山东益都),然从诗中“芳菲”“蜂蝶”“栏槛”“花魂”“花骨”“寒月”等物象与意象,可见苏州文化在盈盈身上留下的地理印记。而居山东一年之后,盈盈至山东淄川,再写诗《寄王山》,则颇见豪侠之气、游侠之风:“枝上差差绿,林间簌簌红。已叹芳菲尽,安能樽俎空。君不见铜驼茂草长安东,金辘玉勒雪花骢。二十年前是侠少,累累昨日成衰翁。几时满引流霞钟,共君倒载夕阳中”[25]。齐鲁之地素尚豪侠,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着重记述朱家、剧孟、郭解三位游侠,名列首位的朱家就是鲁国人。盈盈此诗在以“芳菲”为主的温软意象群外,平添“铜驼”“金玉辘勒”“雪花骢”“流霞钟”等具有侠骨柔情的豪迈意象,齐鲁之地豪侠传统对盈盈文学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
空间位移还在某种程度上激发女性的时间意识,使其产生厚重的历史感兴。南宋末年,徐君宝妻被元人由岳州掳掠至杭州,居韩蕲王府,元人屡欲犯之,徐妻投池而亡。徐妻自尽前题《满庭芳》于壁云:“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台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梦魂千里,夜夜岳阳楼”[13](P3420)。词之上半阙以空间起头,以“汉上”“江南”“十里”等勾勒出江南地理空间的壮阔与人物风流;下半阙则以时间起头,写“清平三百载”的历史盛世,末以“梦魂千里,夜夜岳阳楼”这一地理空间意象作结,把由空间位移带来的历史感、宏大感,以及物是人非的沧桑感表现得极为贴切。
值得注意的是,空间位移对女性文学风格的流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当某一地文学风格形成后,会随着文人、歌伎的流动传播至其他地方,而处于权力中心的京城往往以其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影响及其他城市。据《夷坚志》乙志卷六记载,“江浙间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张安国守临川,王宣子解庐陵郡印归次抚,安国置酒郡斋,招郡士陈汉卿参会。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汉卿语之曰:‘太守呼为五马,今日两州使君对席,遂成十马,汝体此意做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同是天边侍从臣,江头相遇转情亲。莹如临汝无瑕玉,暖作庐陵有脚春。五马今朝成十马,两人前日压千人。便看飞诏催归去,共坐中书秉化钧。’安国为之叹赏”[26]。可见,歌伎应制诗词的创作以及阿谀应酬的风气最早盛行于京都,随着文人、歌伎的地理流动逐渐流播开来,最终遍及江浙等地各大城市的勾栏瓦舍。
结 论
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源远流长,女性作家可谓代不乏人。至宋代,女性文学发展更为繁盛,在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史上体现出独特的价值。宋代女性在文学史上的作用,时人已有察觉,阮阅《诗话总龟》单独列出“丽人门”,胡溪《苕溪渔隐丛话》也专设“丽人杂记”,可见女性文学的独立价值在宋代已经得到认同。宋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独立不仅体现于女性作家数量的骤增,更体现于宋代女性文学思想的深化、主题内容的拓展和艺术手法的新变。在严分内外的传统性别秩序与空间格局下,空间位移对宋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宋代以来,科举制度的发展不断加强士人的地域性流动,从而带动女性眷属的空间移动。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全社会流动性增强,也为女性出游带来便利。同时,宋金、宋元间频繁的战争也迫使宋代女性产生大规模的地域流动。空间位移是宋代女性获得非日常空间经验的重要途径,它带来女性身份意识从主体到客体的转换,地方意识从念远到怀乡的觉醒,以及文学视野由单一到多元的拓展。空间的流动提升了女性文学的思想深度,丰富了女性文学的主题内容,影响了女性文学的艺术风格,促使宋代女性文学走向独立,对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