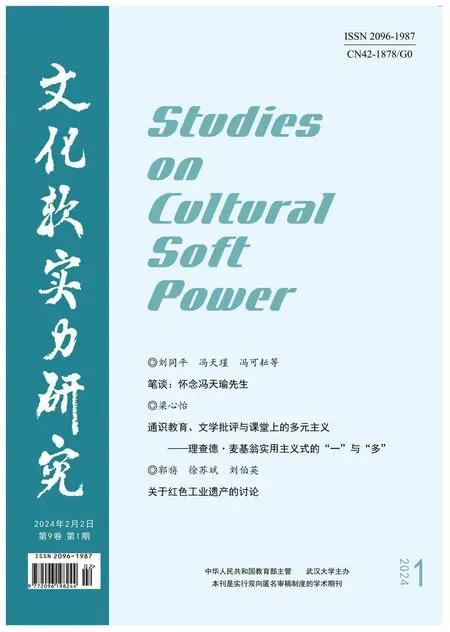探讨与红色工业遗产相关的遗产共识理念和原则
——从几个关键术语(基本理念)说起
郭 旃
* 郭旃, 国家文物局原巡视员、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副主席。
今天我主要探讨与红色工业遗产相关的遗产共识理念和原则, 并从几个关键术语说起。
众所周知, 现代科学的遗产体系与欧洲关系密切, 经过反复研究, 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网络架构。 西方遗产保护理念从古物的纪念观念开始。 例如著名的遗产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 建于公元315 年, 现存的三座凯旋门中年代最晚的一座, 正是为了纪念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12 年击败马克森提皇帝并统一罗马帝国而建的。
再如伊朗阿契美尼德帝国创始人居鲁士墓, 马其顿·亚历山大在参观居鲁士墓时, 命令他的一个战士进入遗迹, 战士在遗迹里发现了一段铭文, 根据《亚历山大传》的记载, 墓碑上铭刻着希腊文:“哦, 人们啊,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来自何方, 为我知你们将至, 我是成就了波斯人帝国的居鲁士,因此, 不要嫉恨覆盖着我躯体的这层薄土。”
遗产的问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人类的史学观念和以往对人群的关注, 大多从纪念引发回忆的实物开始, 这就是现在普遍使用的文化遗产最核心的要素“monument”, 这是我今天要阐释的第一个概念。 翻译成中文是纪念碑, 但是在实践中泛指大部分遗产, 所以我们常常因用纪念碑来描述遗产而感到费解, 但是又找不到一个简单可以替代的词语。 字典中的“monument”的意思首先就是纪念碑。一位加拿大同行曾经说起, 在他的语境里应该如何去理解“纪念碑”。 他说非常简单, 父亲去世了,立一个碑, 纪念他的事情, 就是纪念碑。 中国立碑的传统由来已久, 著名的如秦宰相李斯的小篆《封泰山碑》, 东汉远征匈奴的“燕然山铭”, 当代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等, 绝大部分的纪念碑都有相应的铭刻。
现在提及的“monument”一般都是不可移动的历史性建构, 更为综合的、 往往包含废墟和地下埋藏的遗产地被认定为“site”, 中文曰“遗址”。 字典标注“monument”为“纪念碑”, 从词源本意来说是正确的, 在科学的遗产保护理念中演进出“‘历史’的纪念碑”这一概念, “monument”从狭义到广义,可以是纪念碑, 也可以是一座桥, 一组古建筑群乃至一座历史名镇, 一项水利工程, 等等。
法国人在18 世纪末期的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历史’的纪念碑”概念。 这个纪念碑已经不仅仅是关于某一个人、 某一个事件的纪念物, 而往往是某一段、 或某一方面历史的实物见证。 从“monument”到“monumental”, 成了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专指。
这是法国奥班-路易·米林在《国家古物》中确立的概念, 换言之, 包括上述案例在内的很多历史建筑, 最初并不是为某一纪念目的而特意建造, 但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发展成为特定历史事件的实物见证, 从而成为了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建构, 以实物记载或者标志特定的历史。 这正如奥地利学者里格尔在多年前所阐述的“有意而为的纪念碑”和“无意而成的纪念碑”概念, 前者是人类为了特定的目的而树立的人工建造物, 后者则是一个现代的概念, 艺术和历史的纪念碑, 指代那些最初为满足当时实际的和理想的需求而建造, 并在后来才成为具有历史性价值的建筑, 因此它取决于现存客观的遗存, 以及人们的感知。
作为纪念碑意义的历史建构, 是以实物书写和铭刻的历史, 具有实物的历史文献的属性和特征,这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史上著名的意大利第一部保护宪章所采用的观点。 鉴于过去的建筑史迹不仅有益于建筑学的研究, 而且作为非常重要的文献有助于阐述和图示各个民族贯穿岁月历史的方方面面, 因此它们应该受到文献般严谨、 虔诚的尊重, 在其中的任何改动, 无论多么细微, 一旦它伪装成原件的部分组成, 将容易造成错误的推断,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由这一问题便合乎逻辑地引发了遗产范畴、 文献属性与真实性的关联探讨, 就是第二个概念“authenticity”, 在20 世纪90 年代, 国际、 国内都有一些同行认为这是一个完全西方的语言。 在使用中,日本同行偏重翻译为“原真性”, 韩国同行翻译为“本真性”, 后来一致同意将“authenticity””汉译为“真实性”。 我曾经不介意这3 种翻译的差异, 认为不那么敏感, 只要能准确理解就好。 后来的一次事件转变了这一看法。 当时, 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展开维修工作, 有人提出历史建筑的现状不足以彰显盛世, 有必要翻新、 换新, 大加修复。 这一事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一位主张应该“再现辉煌”的专家提出, “原真性”就是“原来的状况”, 是最辉煌时期的状态。 这使我意识到“authenticity”简单翻译为“原真性”所带来的问题, 因而后来我便特别注意使用“真实性”这个译法了。
文化遗产既然是历史纪念碑, 具有实物文献的属性, 那么认知和保存就必须保持历史全过程的真实, 一般不能改变, 即便不得已改变也应该有明确的记载和标识。 有这样几条阐述值得高度关注。里格尔赞成最少干预, 以及将修复限制在文物保存所确实必需的范畴内。 焦万诺尼同意博伊托, 认为最好的修复是不可见的。 “布兰迪陈述的三条原则: (1)任何整合都应是在近距离容易辨别的, 但同时, 应该不冒犯正在恢复的统一; (2)只要是构成形态而不是结构的, 直接形成形象的材料部分是不可替代的; (3)任何修复都不应阻碍而应便于未来可能需要的干预”。
我们不能设想使用篡改过的史迹来研究历史, 也不能用一份被篡改过的、 伪造的文献来辨证历史。 作为文物工作者, 我们必须要思考和反思, 在处理文物问题时我们是否篡改过这些珍贵的、 无可取代的实物文献, 是否不加标识的处理或者失误过, 是否在文物保护过程中, 为了利益以保护的名义进行过不当的变动?
有一个全世界公认的真实性保护的案例——罗马剧院, 在遗产保护领域提出了什么是“真实性”的确定。 它的下层是早期修建的, 中间两层是7—8 世纪修建的, 上面是13—14 世纪修建的, 建筑一角上留着的是墨索里尼时期“团结就是力量”的标志。 全过程保存。
遗产之所以为遗产, 有三个关键环节, 皆与历史的“真实性”相关。 《修复理论》的作者布兰迪提到成为遗产的三个阶段: 艺术家创作实现艺术作品所需的持续时间; 从艺术家完成艺术作品到当代的区间时段; 艺术作品在当代意识中被认可之时。 一个艺术家创作灵感的产生到实物的形成, 文物的形成与发展的历程, 研究历史的变迁, 会有历史的记载。 同时, 某一个时段的文献, 某一时代的实物见证, 需要界定遗产保护对象三个关键的时段, 这与文物的历史性密切相关。 这关系到中国文物保护观念的发展, 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一般情况下, 文物原状应当是一项文化遗产在科学体系和法律框架下, 被当代社会和国家认定为文物保护对象时的现状; 现状中如果存在威胁文物安全和可持续保存的因素, 应予以整治, 整治须遵循“ 最少干预”原则。 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对象之后又经维修变动者, 应以最近一次维修活动后形成的状态为原状。
那么这就顺理成章引出第三个概念“setting”。 遗产保护包括由法律划定的一个保护范围或保护区, 以及相关的环境关系。 “setting”可以翻译为设置环境, 即“设境”。 这一译法, 由上海的陆地老师率先提出; 我也据此和一位被称为当代世界最杰出的遗产理论家讨论过相关的解读, 完善对“setting”的理解, 包括三层含义, 无论一座城市, 还是一处工业遗产, 首先受制于先天的天然环境的选址,这是最主要的; 然后是在落地时, 在同时代认识水平和技术能力框架中对天然环境所进行的规划和适当的调整, 这也是历史形成的环境的一个方面; 再次, 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使环境发生的历史性改变, 直至被界定为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或保护区域, 设定相应的保护范围、 缓冲区、 协调区, 或建设控制地带。
作为monument 的遗产往往具有不可移动性, 不可移动起码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 不借助于机械的力量, 难以简单地被移动位置; 第二, 它的存在不应当是同整个环境分离或剥离的。
前面的内容我可能过度引用了西方遗产的概念, 但其实中国的遗产保护先驱在这一方面也提供了相似的智慧源泉与相应思考。 比如梁思成先生在实践工作中所形成的一些积淀, 尽管对这些积淀现在也有很多挑战。
第四个概念就是目前盛行的“遗产价值”这一概念。 以价值为基础, 创造更多的价值或者与此相关的评估, 非常高深。 从世界遗产评定的一条重要原则来看, 即意义, 是基于最简单的逻辑、 最符合客观事实和特征的描述。
价值核心首先源于世界遗产的核心品质——突出普遍性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但在操作上, 世界遗产的界定实际上是“突出普遍意义”(outstanding universal significance), 这里强调的是“意义”而非商业概念可以计量的价值(value)。 我们讲评判准则(criteria)也应是对是否具有杰出普遍意义提出一个判断标准, 而不是为之标价。 世界文化遗产的六条评判标准, 实际上是在陈述和论证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被公认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特定的方面, 无论是杰作, 抑或是典范。 那么意义等于什么? 我认为等于客观的物质存在加上特征, 就是historic existence(s)加上attribute(s)。
上述遗产的关键原则体现在所有和遗产相关的体系中, 自然也包括工业遗产。 《下塔吉尔宪章》和《都柏林原则》是工业遗产领域两个著名的文献, 相应也体现了文化遗产的阐释, 比如我们的遗产怎么向公众阐释和展示, 这实际上也源于一些最基本的认知观念。
如作为中国特定范畴的红色遗产, 如何在国际舆论中, 在共同价值观中阐释中国故事? 如何能够被世界客观的了解和理解, 而不是拒斥? 中办、 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 革命文物属于中国特色, 国外没有这个概念。 既然我国把革命文物的保护视为顶层设计, 那么我们还需要认真的思考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 红色遗产的意义作为近现代重要的遗产, 未必就不能在世界遗产的框架中得到提炼和升华。
西湖文化景观已经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们的名言是“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三面云山一面城”“天人合一”的这种人居模式, 历经千年保存到现在, 这为构建人类美好的生活环境提供了借鉴, 所以西湖被认为具有共通的文明史意义。 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那么在红色工业遗产中,是不是也可以有所借鉴?
再比如藏羌碉楼, 这是川西一种村寨, 我们可以看到景色宜人的崇山峻岭。 但国际同行并没有仅仅从它如何险、 如何美、 如何奇特等方面作出评价, 而是从其世世代代居住和繁衍的生存历史出发, 认为这代表着人类的一种韧性、 复原力和适应力(resilience), 即人类能够历经战乱与自然灾害等种种灾难直至现在, 所彰显出的复原能力。 因此, 这类遗产所体现出的正是对人类进步具有共同意义的精神和能力。
我们知道, 红旗渠正在考虑申遗, 那么它能不能达到类似于藏羌碉楼、 川西的村寨等具有的这种国际文化遗产的意义, 可不可以申遗? 还有很多红色工业遗产, 例如八路军的兵工厂, 可否在民族大义和反侵略反法西斯这种人类共同的认知中提升自身的意义? 诸如此类, 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和探索的项目。
另一方面, 即使是红色遗产, 也有真实性的需求, 以免伤害到直观的感受、 感染性和可信度。红色的历史更要实事求是, 有两个案例值得回顾和思考, 一个是“四八烈士纪念塔”。 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对这里进行了破坏。 “文革”时, 有烈士被一时冤为叛徒, 纪念塔再次被毁, 这些烈士遗骨被迁。 “文革”后, 再次重建烈士陵园。 另外我们还知道董希文先生的名画《开国大典》, 这是我国最重要的革命文物之一, 但这幅画完成之后曾因为政治运动被不断涂抹修改,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中国革命博物馆征得上级同意, 才决定将《开国大典》恢复原貌, 那时董先生已经去世了, 只好请阎振铎、 叶武林两位年轻画家代笔恢复, 那么当对待红色遗产问题时, 我们也应该反思, 如何去考虑这些遗产的真实性?
奥地利遗产学家阿洛伊斯·里格尔曾提出: “历史回顾价值……, 甚至连没有受到历史教育的人都会立刻感受得到。”这个观点的核心意思是, 遗产解读所产生的即刻情感效果“并不限于受过教育的人……, 而且也面对着大众, 对所有人有效, 并没有知识教育上的差异”。 遗产的真实性问题, 不会长期只被专业人士所垄断, 它们易于理解, 在文化文明发展过程中很快会被大众普遍关注, 并被大众所接受。
国内外都有人对我们文物维修后的真实性有不同程度的质疑。 我认为我们做遗产工作, 在真实性方面要特别注意, 不能留下不好的记录。
当然, 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物质总有一个从生成到消亡的过程, 于是会出现一个有形遗产无形化、 传统生活表演化、 建筑特征符号化、 历史体验模拟化的现象,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保存遗产的信息是遗产保存不可回避的终极手段之一, 所以数字技术会大有用途。 例如我们失去圆明园已成事实, 但在展示方面可以借助数据技术给公众进行非常生动的展示。
另外一个关键问题是, 目前全世界遗产保护存在一个共识的门径, 就是要整体统筹保护。 这对红色遗产也可能有借鉴意义, 例如说有形和无形遗产之间的互通, 不可移动的遗产和可移动的遗产互相之间密切的相互印证关系。 此外还有遗产本体与设境和社区的关系, 利益相关者的协调与城乡规划等等, 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