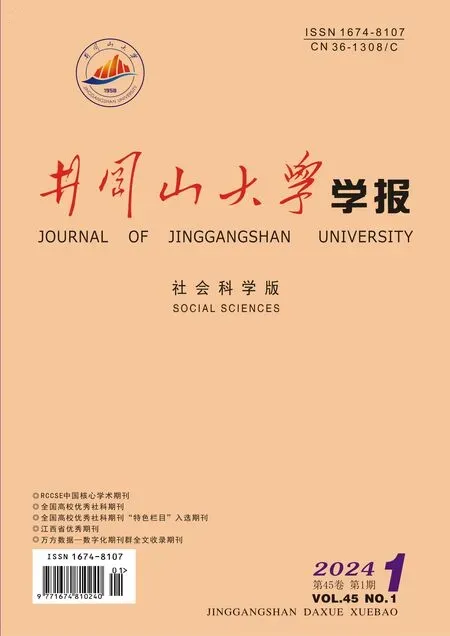论《红岩》改编作品的叙事类型与文化价值
赵可可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小说《红岩》自1961 年12 月正式出版之初,便被称作“共产主义的教科书”“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从而掀起了一股“红岩热”。 以《红岩》小说为蓝本的作品改编也层出不穷, 涉及各个地区的地方戏改编、连环画改编、话剧改编、曲艺改编、歌剧改编、电影改编、电视剧改编等多种媒介。据不完全统计, 改编作品多达五十余部。 通过对《红岩》改编作品的梳理以及与原著作品关系的比照,将《红岩》改编作品分为“紧密型”改编与“松散型”改编两种类型。对《红岩》改编类型与风格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深入掌握《红岩》与其改编作品之间的关系, 从而进一步把握改编作品的艺术特色。对《红岩》改编类型的分析,也能深化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研究, 推动研究者思考如何打造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实现其跨媒介传播的文化价值。
一、集中叙事:《红岩》的“紧密型”改编
“紧密型”改编是指将文学作品中的大部分故事元素都保留在改编作品中, 保持原著的主题内涵,放弃或者添加较少元素,在细节上与原著略有不同。这种改编方式与原著的关系最为密切,所采取的叙事方式是牢牢把握原著的主题、 情节、人物, 将这些主要的叙事元素集中到改编作品的开场、中间或者结尾处,将少量改动或者创作的元素加到其他地方。根据《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以及1984 年版电视剧《红岩》、1999 年版电视剧《红岩》都是这种“紧密型”改编的代表,这三部改编作品着力保持原著的主题内涵、 人物底蕴与艺术风格,在创作上追寻艺术的“真实性”。
《红岩》的写作背景源于重庆解放前夕真实的大屠杀事件,写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未署名) 是本次事件的亲历者和幸存者。 他们在解放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在政府组织下开始撰写相关事件的回忆文章和报告, 作者之一杨益言署名杨祖之写了回忆文章——《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罗广斌则肩负披露集中营真实情况的使命,做了《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报告》。这一时期的写作都是偏向纪实性的回忆,尤其是杨益言等人创作的回忆文章,还保有细节的生鲜、粗粝和真实。后又在集体创作下完成了《圣洁的雪花》和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几位作者也投入到各种“报告会”之中进行各种“言说”活动,在长期口头讲述的演练和反哺中形成双向互动对话, 他们酝酿出更深的小说创作基础。距离小说成型最近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这个版本相比于《圣洁的血花》的描写更为生动具体,更接近《红岩》小说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与事迹, 正如评论家阎纲所说:“《在烈火中永生》所根据的和所记述的原材料、原人物,正是《红岩》 再创作所根据的蓝图和模特儿。 ”[1]81循此路线,不难看出《红岩》的人物、事件、结构框架确实建构于比《在烈火中永生》更早的那些提供了“原材料”的文本基础之上,同时在“就地取材”的过程中,作者们从“实录”走向了“虚构”。
1956 年秋到1957 年初期间, 罗广斌、 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他们在整理大量材料的基础之上,创作出自认为是小说,其实是报告文学的《锢禁的世界》。 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后,历经三个修改版本,其后在党组织“最亲切的关怀和直接的帮助”下,完成了小说的定稿。 1961年底,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40 周年之际,中国青年出版社抓紧将《红岩》排出清样并装订出40 册样书送与各报刊和评论者。 经由出版社的布排与宣传,《红岩》 在1961 年打响了“第一炮”, 成为1961 年长篇创作的“压卷之作”,至此《红岩》成书。1962 年初,《红岩》开始大量印刷,各种评论的文章也接踵而至, 文艺界一夜之间形成“《红岩》热”,《红岩》更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创造出高达800 万的发行数量。 《红岩》小说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固然离不开中青社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源于时代的机遇。 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红岩》的出现,兼备“鼓舞人心”和“教育青年”的双重使命,像是一针振奋人心的强心剂, 其所展现的英雄主义的精神力量,一扫物质生活匮乏带来的低迷之风,使人们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对革命前途产生充分的信赖。可以说,《红岩》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为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形成同构与杂糅的张力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示范。
在当代文学史上,《红岩》的创作是一个特例。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论及《红岩》的写作方式时,认为:“《红岩》约十年的成书过程,是当代文学‘组织生产’获得成功的一次实践。这种‘组织生产’ 的方式在戏剧、 电影的制作中是经常使用的,在‘个人写作’的文学体裁中并不一定常见;但在后来的‘文革’期间,则几乎成为重要作品的主要生产方式。创作动机是充分政治化的。作者从权威论著、从更掌握意识形态含义的其他人那里,获取对原始材料的提炼、加工的依据,放弃‘个人’的不适宜的体验,而代之以新的理解。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岩》 的作者是一群为着同一意识形态目的而协作的书写者们的组合”[2]113。 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话语下创作的《红岩》,和最初生鲜粗粝的“实录”文章在艺术处理和现实功用上已经大不相同。 《红岩》的集体写作代表的是一种文学的“虚构”写作,其政治使命是“讲述革命故事”。正如李杨所言:“说《红岩》是一部以历史叙事为目标的‘小说’,反倒不如说《红岩》是一部关于人的信仰的启示录更为准确。 ”[3]178《红岩》小说的“真实”与“虚构”在“讲述革命故事”时通通被内化为表现伟大的革命思想与革命精神的有效工具,而这个“革命故事” 也为受众所相信且更具感染力,“读《红岩》时,首先给人的感觉是:这是真正的生活,这是真正的理想。……《红岩》感人的力量就是来自活生生的形象,表现了伟大的革命思想与革命精神”[1]83。 因为相信,许多虚构的描述也被大众作为历史真相接受,《红岩》 小说在 “真实”与“虚构”之间高举革命浪漫理想的旗帜,成为“教科书”。
纵观《红岩》小说的创作,它是一部脱胎于各种新闻报道、报告文学、会议录、纪实文学等多种文体的集体小说创作,经历过“口头讲述”的阶段,小说叙事较“本事”所披露的“赤裸的真实”,更具有号召力。 《红岩》小说的“真实性”是加工后的真实,这种真实源于其塑造的形象、描述的事件、表达的主题所代表的真实的革命理想及其起到的“教科书”的作用。 因此,小说的成型过程中,有意识地规避一些低沉压抑的调子,弘扬革命理想,小说创作从历史真实走向艺术真实。 作为和小说同频共振的电影文学,《红岩》的电影改编文本《烈火中永生》也遵循此路径,在电影文本《烈火中永生》的创作和修改中, 周扬就不止一次地提醒电影创作人员要注意规避作品中“低沉压抑”的基调,在电影中应该有高昂的调子[4]。 在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下,电影《烈火中永生》也参与到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大合唱中。 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将《红岩》 改编成电影的打算, 由来已久。 早在1959 年《在烈火中永生》单行本出版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就有意将之改编成电影。后来,在《红岩》正式出版前的“两三次征求意见的排印本,‘北影’编导人员都从‘青年出版社’要去看过,早就有了改编电影的打算”[5]。 1961 年《红岩》出版后,演员于蓝和导演水华等人都有意向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 据夏衍在1978 年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烈火中永生》附记中所写,他的创作是在小说原作者的第一稿以及水华、于蓝等人的第二稿之上完成的。与水华等人的“敌特片”创作出发侧重点不同,夏衍在创作《烈火中永生》时,将目光集中在“江姐”这一人物形象上。 在剧本改写阶段,他认为“江姐的经历多么感人,她有丈夫,有孩子,而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她的遭遇是感人的……老百姓会关心她的命运的”[6]。 于是,“江姐”得以与话剧舞台定型的“许云峰”双峰并置,在大荧幕上出现。
电影文本《烈火中永生》将原本小说中的三线叙事改为单线叙事,着重突出革命斗争这条主线,围绕这条主线浓缩了小说中部分经典情节, 集中突出许云峰与江姐二人的重要事迹。 在许云峰的塑造上,电影着重突出“茶园被捕”“饭店识破假宴请”“狱中斗争”“英勇就义”等几个情节,将这些情节有序安排在电影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从而串联起一条完整的叙事脉络, 再着重描写这些情节中人物的主要行动轨迹, 突显许云峰作为一个革命党人的英勇形象。如在“鸿门宴”这一幕中,导演将许云峰置身于特务反派阵营中, 在魑魅魍魉的包围之下,许云峰一眼识破徐鹏飞等人的阴谋诡计,干净利落地揭穿了他们的企图。 在徐鹏飞与许云峰的单独对手戏中,正与邪的交锋被拉到极致,看似是许云峰受制于徐鹏飞, 但在镜头表现和人物动作上,许云峰却一直处在上风,面对徐鹏飞的威逼利诱,许云峰临危不乱、反客为主,让敌人无计可施。这种极具戏剧张力的场景设置,受审判者变成审判者,二者身份的置换,配合着各种特写镜头的切换, 正面人物坚强刚毅的神色表现出革命党人坚定的形象,与神色慌张、奴颜婢膝的反面人物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二元对屹”的正邪人物设置范式在之后的歌剧《江姐》以及各种“红岩戏”的改编中也被广泛使用。
电影改编文本也“围绕江姐浓缩了小说中的部分经典情节:丈夫牺牲、会面老太婆、斡旋甫志高、受审受刑、新年联欢、狱中斗争、临终告别等,结合外部造型、蒙太奇、演员的场面调度等影视语言再现江姐多面的英雄气魄。 ”[7]28在电影中,“江姐” 的形象比之小说中作为群体英雄塑造之一的江姐更具真实性和感召力。这种“真实”源自导演、编剧和演员对于艺术真实的加工和创作。 在电影中,江姐被赋予凡俗英雄的特质,被定义为重庆街头无数普通女性中的一个, 其崇高的革命理想使她脱颖而出。 这样的塑造方式让江姐这一形象既有革命英雄的品格,也带有凡俗女性的细腻情感。电影《烈火中永生》在改编时,和原著的关系最为密切,但由于《红岩》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篇幅远远超过电影的容量,在改编时进行压缩和剪裁,抛弃一些叙事元素是必要的, 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 电影改编采取许云峰和江姐二者双峰并峙的叙事方式也并非难以理解, 相反这样的集中叙事, 正是电影改编所需要的, 更有助电影表达出小说中高扬的革命斗争主题,继续发挥其“教科书”的作用。
1964 年的电影改编文本《烈火中永生》与小说创作的年代相近, 在弘扬革命斗争精神和主题上是极为相似的,围绕着这一主题,电影改编虽然删去了大量的人物和事件, 将原著的五对革命夫妻也精简为两对,把“革命+恋爱”模式处理得更加隐蔽, 但富有人情味的集中叙事反而让电影改编与小说的联系更加紧密, 其艺术真实更具社会功用。与之不同的是时隔二十年改编的1984 年版电视剧《红岩》就十分忠实原著。 这一版电视剧将小说的艺术真实当作真正的历史真实, 其创作主旨虽说是在重温历史,其实是在重温小说。电视剧剧情基本上对小说按部就班, 细节上也与小说创作一般无二, 每一集的片头和片尾都以小说封面作为定格画面, 电视剧的一些镜头设计也参照了原著小说的木版画插图, 电视剧改编对原著小说亦步亦趋,成为小说“阅读”的另一个窗口,其改编创作的意义仍然是遵循小说的教育价值。1984 版电视剧《红岩》在整体创作上还未脱离遵循原著的创作主旨,是因为原著小说《红岩》的“教科书”地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被反复确认,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文化相关管理机关也相当重视改编这部“教科书”的意义。在《红岩》原著小说与电视剧改编之间,小说作为一个“强势媒体”,电视剧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不能完全摆脱原著小说的影响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形态,在改编时“弱势媒体”必然要服从于“强势媒体”,对原著的亦步亦趋也便容易理解了。
1999 年版电视剧《红岩》改编也遵循“紧密型”改编的方式,在尊重原著基础上做出了局部的改动, 但叙事上大致还是遵照原著的主题与故事情节。 作为一部献礼剧,1999 年版《红岩》仍然将《红岩》小说中的教育精神内化到电视剧中,虽然实现了媒介的跨越, 但在总体的思想表达上还是歌颂革命斗争精神、弘扬英雄主义。虽然相比较于原著小说,电视剧创作者增添了一些历史细节,但总体上还是为了使人物更加丰满、 更具有生活气息, 目的仍是为了让革命主体更容易走进当今社会受众的内心,从而实现其教育的目的。与电影改编相比,电视剧改编能够容纳更多的故事情节。因此,在改编时,与原著的关系更加密切,再加上大众文化还处于成型阶段,受众的审美还未受到“戏说”“解构”“颠覆”的影响。《红岩》小说的“教科书”地位相比较于其他媒介更加深入人心, 在“主旋律”文化潮流中,《红岩》的电视剧改编自然而然更加尊重原著, 以更好地实现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价值。
《红岩》作为一部“教科书”式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在改编时反而最不容易突破原著的限制。在新世纪之前, 改编的标准大都还是以是否忠实于原著作为优劣衡量,但《红岩》原著涉及的人物、事件繁多,又加上其带有一定的革命历史真实,在艺术改编时,如何把握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也是改编者要思索的难题。 集中叙事的“紧密型改编”能在最大程度上忠实原著的创作主旨, 还能适应各种媒介之间的转换,继续发挥《红岩》教科书的教育作用。虽然在创作上损失了一定的创新性,但对于打造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实现《红岩》的跨媒介传播是利大于弊的。
二、出发点叙事:《红岩》的“松散型”改编
“松散型”改编最具有创新性,与原著的关系最为游离。在改编时,选择削减掉小说中大部分叙事元素, 甚至模糊掉情节、 以人物名字作为出发点,重新拓展为一个新故事。《红岩》作为一部红色经典文学作品, 其改编最常用的方法便是“松散型”改编,将作品中具有戏剧性的人物挖掘、放大,围绕着这些人物重新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从而打造出更多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形成《红岩》跨媒介传播合力。
“松散型”改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歌剧《江姐》。 1964 年空政文工团编演的歌剧《江姐》以女性人物江姐为主人公, 围绕江姐这一人物形象主要展开华蓥山武装斗争和狱中斗争两个主线。 歌剧《江姐》节选原著中江姐的部分情节,致力于对江姐的塑造,故事情节都围绕着江姐展开,从码头告别前往华蓥山、华蓥山下见到老彭遇难、投身到华蓥山武装斗争、被捕在狱中斗争、最后到英勇就义, 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主线。 编剧阎肃谈到《江姐》的创作时,认为“长篇小说题材是有它的长处的,但看一遍需要花不少时间,同时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看的,作为一个歌剧创作人员,从本职的体会出发,就想若能利用戏剧的形式,就可以用两三小时使观众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受到艺术的感染,但又觉得全部改编嫌不精练,根据歌剧长于抒情的特点, 决定节选江姐可歌可泣的一生作为创作的主体,深刻展现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8]3。歌剧《江姐》出于普及的创作需求,兼顾歌剧的创作特点重新组织原著小说的故事情节, 围绕江姐重新展开叙事, 通过一系列智斗反派的故事情节与通俗优美的唱段来塑造江姐这一人物形象, 在艺术上的磨砺使得江姐这一人物形象越发深入人心。 歌剧《江姐》的主题歌《红梅赞》以傲寒怒放的红梅意象化地象征江姐的革命英雄形象, 从此在受众心目中奠定了江姐的艺术形象。
歌剧《江姐》的改编方式和成功示范,影响了《红岩》的地方戏改编。 地方戏改编也纷纷以江姐作为出发点,改编《红岩》。 截止到现在,据不完全统计,根据《红岩》原著小说改编的地方戏曲《江姐》涉及京剧、豫剧、昆曲、川剧、吉剧、沪剧、潮剧、庐剧、粤剧、吕剧、越剧、评剧、黄梅戏等多个地区的地方剧种。其中,现代豫剧《江姐》是陈涌泉根据歌剧《江姐》创作而成;重庆市川剧院创排的新版川剧《江姐》取材于小说《红岩》,剧本来源于阎肃创作的同名歌剧《江姐》剧本;吕剧《江姐》也移植自同名歌剧《江姐》等等。 多部地方戏曲改编参照了歌剧《江姐》,在剧作中形成了“一曲红梅传甲子,梅香四溢尽迎春”的创作状态。 有关《江姐》的地方戏改编大体上沿袭歌剧《江姐》的创作模式,以江姐作为叙事主体,主要展现华蓥山武装斗争、狱中斗争、绣红旗、英勇就义等多个情节,结合地方戏曲的特色,创作出属于地方的江姐形象,但这些江姐形象还是沿袭《红岩》小说中英勇的革命者形象。从艺术创作上来看,《江姐》的歌剧改编以及地方戏改编,脱胎于原著小说《红岩》,挖掘并放大江姐的形象, 从而使江姐这一人物形象既能借助《红岩》脱颖而出又能独立于《红岩》之外被大众广而得知。 《江姐》的改编也由此成为《红岩》跨媒介改编的又一红色经典文艺作品, 有助于推动《红岩》的跨媒介传播。
除《江姐》的改编外,话剧、连环画以及地方戏改编的《许云峰》《华子良》《小萝卜头》等也是“松散型”改编。 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小萝卜头等都是《红岩》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将这些人物从小说中单拎出来,作为一个独特的切入点,从人物自身的境遇去构建光辉的革命历程的各个维度, 既丰富了戏曲舞台上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 又从多角度解读了红色革命历史”[9]85。 对这些典型人物的深度挖掘, 也为其他红色经典文学的改编提供了一个可以创新的思路, 即在同一部红色经典文学中挖掘典型人物或者具有戏剧性的形象进行放大,并以其作为出发点,重新组织叙事,改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塑造深入人心的形象。这种改编方式, 既是对红色经典文学的解构也是对红色经典文学的重构, 对重新解读红色经典文学和融合新时代的审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北京京剧院对现代京剧《许云峰》的再度创排正是红色经典文学在新时代的新的生命力和可能性的有力表现。 现代京剧《许云峰》是脱胎于《红岩》的现代戏,其创排始于1984 年。2020 年,北京京剧院再次编排《许云峰》,并以“云首演”的方式在“东方大剧院”进行线上直播。2021 年,京剧《许云峰》 又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献礼剧目,在国家大剧院再度与观众见面。在《红岩》的改编作品中,许云峰是一个与江姐齐名的重要人物。京剧《许云峰》将叙事的重心集中在许云峰这一人物身上,通过塑造许云峰的革命情怀和优秀品质,表现红岩精神的精髓。2020 年重新创排的现代京剧《许云峰》在三十余年后,再次将许云峰这一革命英雄人物推至幕前,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重新审视许云峰这一人物,将他返归于真实的英雄人物。既展现他平凡的一面, 又凸显他超越常人的革命意志,以新的创作模式,挖掘革命经典,赋予红岩精神新的发展道路。
以某一个人物或者情节作为出发点的“松散型”改编,虽然在改编红色经典文学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但有时在审美上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评价。2009 年版电视剧《江姐》同样是以“江姐”切入点,但在改编时,为了迎合大众文化下塑造“平民英雄”的需求,将江姐定位为一个有情感有缺陷的能够引起普通人共鸣的平凡英雄, 因此在电视剧改编中, 着重塑造了江姐如何从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成长为独立的革命者的过程, 铺展江姐的革命成长历程。另外还在电视剧中增添了有关江姐、老彭以及幺姐之间的“三角恋”,以一些通俗的情感叙事吸引受众的目光。2009 年版《江姐》的电视剧改编对于推动红色经典文学的通俗化有一定的作用,但从其艺术审美上来看,远远不及原著《红岩》,且这种改编也有披露英雄人物的隐私从而满足受众窥私欲的嫌疑。稍有不慎,会将革命经典文学叙事滑向传奇叙事。 2006 年改编的《双枪老太婆》 就是完全以大众文化作为主导话语的世俗化改编,将双枪老太婆的故事改编为一个带有美女、枪战、多角恋爱的通俗传奇故事。
《红岩》的“松散型”改编也常在视觉影像上呈现“陌生化”,重视创新性改编。 1986 年上映的电影《魔窟中的幻想》借取小说《红岩》与电影《烈火中永生》中“小萝卜头”的人物原型,用新的事件和情节对“小萝卜头”的故事进行填充,集中而又细致地展现了小萝卜头在监狱中的生存状况及其丰富独特的精神世界。 影片以“小萝卜头”的故事作为出发点进行改编,但由于《红岩》原著中涉及“小萝卜头”的情节并不多,导演在改编时,将内部的故事转移到表达故事的形式上, 用形式上的探索代替故事情节的叙事, 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空间。 在影片中,导演刻意淡化小说的政治背景,将叙事的中心集中在“小萝卜头”身上,以儿童的视角贯通现实的监狱世界、梦境中的外部世界、幻想中的心灵世界, 用符号化的手法展现集中营的残酷生活。导演放弃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充分调动美工、摄影、灯光、音响各个艺术部门,以强烈的主观角度, 用高度浪漫和夸张的手法向受众铺展了一个高度主观化的世界。 电影《魔窟中的幻想》对“形式”的美学追求,将人们习以为常的“小萝卜头”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开拓,表现出一个全新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 《魔窟中的幻想》通过视觉审美上的“陌生化”实现了创新性的改编,虽然在审美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评价, 但这种形式上的探索, 对于经典红色文学的改编同样具有借鉴意义,这一点在徐克执导的《智取威虎山》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对于红色经典文学而言, 在新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松散型” 改编以某一人物或情节作为出发点,塑造可具代入感的“平民英雄”,贴近世俗化审美的创作,确实能够满足大众猎奇的心理。但对于传递革命精神、重塑革命英雄人物而言,这种过度迎合大众审美的创新改编, 既背离了原著的创作主旨,也不符合新时代发展革命经典文学的立场。围绕红色经典文学改编如何塑造符合时代审美特征的“平民英雄”,戏曲改编往往优于影视剧改编。从《红岩》的改编中可见,现代京剧《许云峰》虽然也将许云峰的人物形象进行“平民化”处理,表现他普通人的一面:看到来送水的小萝卜头,身陷囹圄的他也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妻儿而潸然泪下。 但这种普通人爱家的形象并无损于他坚定的共产党员形象, 相反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许云峰这一人物的真实性。 戏剧改编与影视改编, 由于媒介不同,其艺术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同。相比较于影视改编更加重视视觉化和娱乐化, 更加重视大众化而言,戏曲改编相对“小众”“封闭”一些。这样也更容易保持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受到的干扰小一些。因而,在改编红色经典文学文本上,戏曲改编虽然也有创新, 但其创新多是建立在以时代的精神重塑革命英雄人物,其创作仍不脱戏曲“高台教化”的目的。
三、打造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红岩》跨媒介传播的文化价值
红色经典文学有其特殊的创作时代背景,并且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精神面貌,不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作品中所蕴含的独特的英雄形象、革命认知、民族精神等引导和塑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 而且在今天的改编中也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满足着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红色经典文学创作和改编的出现,不是历史的偶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黄子平曾指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 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 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 ”[10]2创作红色经典文学肩负着记录历史、铭记历史的使命;而红色经典文学在不同时期的改编则担负着时代客观叙述历史的责任。 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审美机制, 其所表现的革命英雄的情感和建构的国人的主体意识, 在今天仍然能够通过其改编源源不断地与受众建立审美联系, 从而形成跨时空的传播效应。 新世纪以来由红色经典文学改编的作品层出不穷, 掀起一股红色经典文学的“改编热”。 虽然这些改编好坏参半、褒贬不一,与原著的关系也各不相同, 但对形成红色经典跨媒介传播合力, 打造红色经典文艺作品是一股有效的推动力。
透过不同类型的《红岩》改编,不难看出红色经典文学跨媒介改编的巨大潜力, 以及被改编传播后所产生的影响合力。 《红岩》通过“紧密型”改编与“松散型”改编,一方面联合不同的媒介充分挖掘同一原著的不同人物, 打造出更多红色经典文艺作品; 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原著中的“红岩精神”,实现其文化传播的价值。由《红岩》改编衍生而出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以及《红岩》本身的品牌价值,聚拢了一定数量的粉丝基础,通过粉丝之间的代际传承, 形成了红色经典的品牌形象,在下一次的改编中又转换为经济效益,推动红色经典的媒介转换。 这种跨媒介的改编又反哺到《红岩》本身的传播中,推动了红色经典文学在当下的繁荣。
不仅是《红岩》,其他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等,也通过改编,打造红色经典文艺作品,从而实现其文化价值。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红色经典文学的改编开始与消费主义挂钩。 红色经典文学想要通过改编打造红色经典文艺作品, 实现其文化价值的传播,势必要走向红色经典的大众化。在这一点上, 红色经典的影视化改编显然已经率先步入消费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红色经典文学所承载的革命话语和革命精神不断地被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挪用和改写。在电影上,其改编注重视觉化表现,满足受众审美心理。 读图时代的到来,助推了受众对视觉文化的追求。2014 年改编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便是将《林海雪原》中“智取威虎山”这一情节故事做了视觉的奇观化, 以游戏架构和三维逼真技术给受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 电视剧改编上,则利用电视传媒的特性,对红色经典文学进行普及和推广,从而实现大众化。这种大众化带有一体两面的性质。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影视化的消费主义推动了红色经典的大众化, 使其有效地实现了文化传播的价值。 但从文化传播的内容深度来看, 这种大众化的文化价值在承担起红色经典文学跨媒介传播的时代价值上还远远不够。
红色经典文学的跨媒介改编一直都是构成新中国主旋律文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文艺历史上不可抹去的记忆。“‘红色经典’改编与民众的怀旧情结相耦合, 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相贴合, 与激活文艺市场的发展需求相迎合, 早已熔铸于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之中。 ”[11]158在多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红色经典文学改编作为时代的刚需被留存下来, 并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历史精神, 承担着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的时代使命,在新的时代焕发着新的生命活力。除了1961 年出版的《红岩》之外,1959 年出版的《青春之歌》、1960 年出版的《红旗谱》,在其小说创作发行之初,相关改编也形成了热潮,并且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不同时代的主旋律话语不断地融入到这些红色经典的改编中, 形成一种跨媒介的传播合力。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红色经典文学的创作及其改编热潮不但将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来龙去脉呈现出来,所描绘的历史及形塑的英雄形象,也契合广大民众的心理期待, 有助于完成情感共同体建构。这种情感共同体凝聚着一代人的心血,承载着一代人的光荣梦想和成长记忆, 并在不同代际的传播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为民族精神的底色,发挥着文化价值意义。
红色经典改编的“兴衰演变及其再度流行既反映了艺术自身发展、自我继承创新的逻辑规律,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 经济巨大变革的时代诉求, 同时也暗合了转型期民众的特殊心理期待和感情投射, 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实的种种冲突与碰撞以及复杂多样的文化意义。 ”[12]5进入新世纪以来,商业文化高速发展,文化观念传播呈现多元化倾向,消费文化造成精神颓废、信仰缺失,当代人的物质生活虽然提高了,但精神困境越来越多,精神失落现象在年轻一代中尤为明显。基于此, 红色经典文学的跨媒介改编及其传播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消费主义时代下,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接踵而来。 红色经典文学的改编和回归无疑重申了革命理想的价值, 为当代年轻人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和怀恋的精神文化。 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 红色经典文学及其改编所传播的文化精神,积淀着中国传统的革命精神追求、审美理想价值等诸多因素。 既能唤起老一代的精神记忆,也能影响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红岩》中代表革命斗争的“红岩精神”,《林海雪原》中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红色娘子军》 中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情怀等等,通过影视、戏曲等改编的方式,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 用现代的审美方式重建红色经典文学的文化价值,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如徐克版《智取威虎山》采用最新的媒介传播技术,聚集了不同年龄的受众群体, 实现了受众群体的跳跃,将《林海雪原》的红色精神延伸到各个年龄层,不同年龄的受众在同一部影视改编作品中找到自己的时代记忆, 电影改编从而也实现了自己的经济价值,在取得票房收入的同时,也传播了红色经典作品的文化价值。
在大众传媒蓬勃发展的今天, 传媒的发展能够引发红色经典文学的价值重构, 虽然这种重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色经典原作的阅读动力,但于大众读者而言, 不可能强制性地让其阅读文本。从文学的整体发展态势来看,影视等大众传媒的日趋火热挤压着文学的发展, 文学的社会文化传播早已滑出核心的轨道, 文学不得不“改头换面”借助大众传播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因而重新思考审视“文学”的位置、限度和意义迫在眉睫。以红色经典文学为例,红色经典文学的创作时代虽然已经远离了当下的时代, 但其革命精神和文化价值凝聚着一代人的心血, 承载着一代人的光荣梦想和成长记忆, 在当代仍承担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因此,充分发挥新媒介的力量,对红色经典文学进行再次的跨媒介改编有助于传播经典文学原作及其精神价值。
充分发挥跨媒介传播的力量, 对红色经典文学进行再次的跨媒介改编有助于重塑红色经典文学,打造红色经典文艺作品,从而使红色经典文学以新的存在方式、新的话语平台、新的表达方式,通过自身新的增长点, 实现革命精神的传承与传播,促使红色经典文学从历史真实到艺术真实,最终实现红色经典文学跨媒介改编与传播的文化价值。此外,红色经典文学的跨媒介改编还能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 红色经典文学的改编包含着当代精神,“所谓的当代精神视野既包含着当代人对人性及其丰富性的理解, 更呈现出当代人超越历史、反思现实的精神思考及文化意识。拉开一定的历史距离,人们对历史的发现更为充分,理解更为深入,对英雄的诠释更为立体丰满;同时,任何对历史的讲述从来都隐含着与现实的对话关系,并勾连着当代人对时代社会现状的思考。”[13]红色经典文学的跨媒介改编之所以能够充满生机, 与其所反映的当代精神脱不开关系。 虽然表现的是过去的历史,但所承担的却是当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