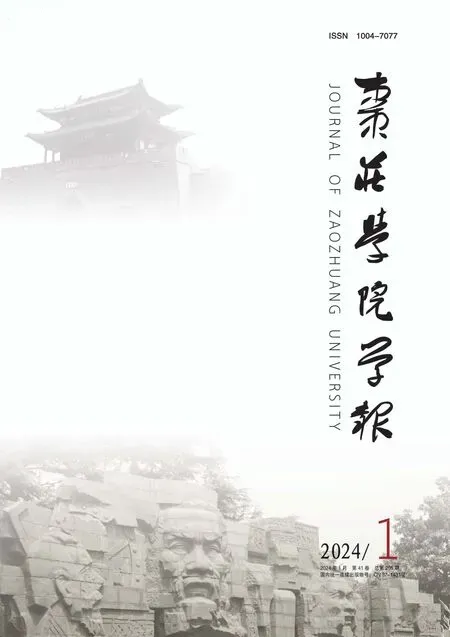《长恨歌》:自恋、主体性缺失及匮乏需求的关系
孙凡迪
(1.北京语言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3;2.中国气象局 华风气象,北京 100081)
自恋情结缘起于古希腊神话中那个相貌出众的少年喀索斯。在中国文学中,自恋情结的大规模亮相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小说中,这既是个人自恋的情结氤氲了文学中大片的自恋氛围,也是多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催生了个人和文学中相互傍依的自恋因子。自恋包含三个特征:一是夸大、积极的自我概念;二是为维持这种积极自我概念所采取的自我调节策略;三是低共情、低亲密度的人际关系。[1](P199~210)
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恋的含义。1914年,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856~1939)在《论自恋》(OnNarcissism)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自恋,并把其纳入精神分析领域。自恋是一个具有多维结构的概念,表现为浮夸、自爱和膨胀的自我,就其功能而言,自恋“既好又坏”。自恋者与人交往之初多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但这种人际关系的虚假性会在长期的互动中暴露出来;从决策的角度来看,自恋者的过度自信、高度冒险以及对回报的短视常常导致其决策偏差。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在1941年发表的《逃避自由》(EscapeFromFreedom)中认为,适当良性自恋可以对人的精神活动有积极意义,自恋是自我认同的主要机制,在建构主体过程中具有必要性。他同时还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应付孤独感的几种心理机制,称之为性格的动力倾向性。过于自恋的人往往具有接纳倾向性,这类人没有生产或提供爱的能力,他所需要的一切完全寻求别人帮助、依赖别人,是接受者而不是给予者。而具备创造性倾向性的人却可以主动创造可能、构建关系,让自体在关系的流动中逐渐强大,从内心主动觉知、思索、体察爱与被爱,继而创造出有价值意义的思想和行动。
西方自恋理论伴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漂洋过海,来到了渴望突破男权社会、重塑真实自我的中国女性作家面前。在自恋理论影响之初,有不少女性作家推崇追求自我、体认和肯定自我的价值论,把过分理想和膨胀的自我奉为一切成长的内在动力。自恋在90年代的文学中更多地体现在女性作家把对自我的欣赏和本土文化的偏执热爱,转嫁到小说女主人公的身上和故事里,表现为对她们不分对错的同情、明目张胆的偏爱和光明正大的抬高。本文以《长恨歌》为例,探讨自恋、主体性缺失及匮乏需求的关系问题。
一、自恋:海派文化的优越感和原生家庭自卑感的怪异产物
《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悲剧是过度自恋导致的,但首先是作者的自恋赋予了她这份自恋的权力,从而揭示了90年代女性作家的某种身份焦虑和精神危机。50~70年代的小说对女性人物的叙事是以祛除女性独特的性别特征、生命体验为指征的,对历史驱动和革命理想的书写湮没了对女性主体性和差异性命运的思考。但是,90年代以来女性书写呈现出日益繁杂的样态,女性的成长又被简单粗暴地扭曲为与男权意识的对抗、欲望化叙事,这种激进化态度似乎让90年代的女性文学走向了与建构自足、自立、自强的女性生命主体和生存空间的反面。女性的成长叙事、感性经验、世俗人性或者日常生活,与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往往有着一种对立、紧张和互峙的关系。[2](P164)
《长恨歌》对女性的书写,假借了新旧海派文化交织变迁的幌子,对小说中人物的同情与赞美很多时候影响了我们客观理性的判断。通篇看到的是对王琦瑶命运充满怜香惜玉般的同情,并唱起了因同情发酵出来的悲怆赞歌,而王琦瑶也顺遂地成了一个因过度自恋而步步丧失女性主体性的人。在一段段自我的纠结踟蹰,以及与男人的情爱纠葛和女性的明争暗斗中,王琦瑶钝化着觉知,撕裂着意识,加剧着匮乏,最终导致其彻底拒绝成长,更引发了她无休止的自恋,直到在自恋的幻影中死去。王琦瑶的40年人生,在自恋的视域下或许是跌宕起伏的一生,而客观审视之后,充其量只是始终走不出弄堂的深闺怨妇静滞沉沦的40年,同情用错了地方,也是自恋的体现。
她们漫长一生都只为了一个短促的花季,百年一次盛开。她们是美的使者,这美真是光荣,这光荣再是浮云,也是五彩的云霞,笼罩了天地。那天地不是她们的,她们宁愿做浮云,虽然一转眼,也是腾起在高处,有过一时的俯瞰。虚浮就虚浮,短暂就短暂,哪怕过后做他百年的爬墙虎。[3](P233~234)
无论是浮云还是爬墙虎,似乎都看得出作者内心是深知这些“王琦瑶们”的结局会是多么不幸,但她还是给与了“王琦瑶们”足够的同情和理解。小说对王琦瑶原生家庭描述不多,但可以看出她和母亲关系的冷淡,而且从不同角度的描述对比中,也能感觉到王琦瑶的家庭是很一般的小市民家庭。在上海这种物欲横流的城市氛围下,她内心希望依仗姿色成名成媛的强烈欲望,使她对现实生活越来越不满。后来,她有机会和家境优越的蒋丽莉成为朋友,并被邀请住进蒋丽莉家。那个夜晚,王琦瑶内心的自卑和自恋再一次不可遏制地交织在一起喷涌出来:
她听着静夜里的声音,这声音都是无名的,而不像她自己家的夜声,是有名有姓:谁家孩子哭,奶娘哄骂孩子的声;老鼠在地板下赛跑的声;抽水马桶的漏水声。这里只有一个声音有名目,像是万声之首的,那就是钟声。它凌驾于一切声息之上,那些都是它的余音,是声的最细小的笔触,是夜的出声的冥想。[3](P131)
不满却又无法改变的自卑,让自己的自恋像无根而又肆无忌惮的浮萍,随便抓住一点可以攀上的高枝,就可以倾注一切,所以遇到高官李主任的时候,王琦瑶骨子里那股媚劲儿和处理人情的老道世故就显现出来了。她其实很懂这类男人,用自己无条件的“乖”迎合他们的一切需求,从而让自己获得跃龙门的机会。为了实现这一人生理想,王琦瑶急得连婚纱也没来得及穿就 “献”了身。
在男权社会,女人要想活得锦衣玉食、高人一等,只有王琦瑶式的倒贴才是最快和最省力的捷径,但王琦瑶选择的这条路只能让自己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很难再有抬头之日。海派文化就算再包容,再进步,也无法脱离中华民族根上的美德标准,王琦瑶走到这一步既违背孝道,也毫无操守德行可言。还待字闺中的时候,家人就对她保持着一种不正常的疏离和生分,父母很多时候也要把她当客人款待,不敢得罪。在作者笔下,原生家庭带来的自卑,海派文化对“美”的盲目偏爱,导致很多女性的价值失衡,并助长了一大批“王琦瑶们”病态的自恋情结暗潮涌动。“情结”一词是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最早使用的,他认为“情结是个人潜意识中一组组心理内容的聚集,有似完整人格中彼此分离且独立自主的一个个小人格;它有自己的驱力,并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与支配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4](P9),情结大多是心灵分裂的产物。王琦瑶的自恋情结,就源自对名利世俗的贪婪和对现状生存的强烈不满,这两种情绪是在“无意识色彩的自发内容”冲击下,一点点吞噬主体意识而形成的,自恋情结变成了王琦瑶内生的基因。在病态生长的自恋中一次次败下阵来的王琦瑶,如果将自恋的劲头放在自我主体性的觉醒和成长上,也不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二、自恋导致女性主体性的缺失
女性主体性,是女性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而存在,通过不断地反思和行动,超越自身处境,在现实社会实践中追求自身在生活方式、知识技能、社会地位、人格塑造等方面不断提高的自觉能动性。在小说中,王琦瑶一直自以为主体意识明确,却始终活在对客体的依附中而不自知。爱的缺失导致爱的能力缺位,没有爱的能力,就只能用日益膨胀的自恋来获取缥缈的希望和虚假的安全感。一直假装冷漠地对待世界的王琦瑶,其实内心比谁都更强烈渴望被关注、被疼爱。自恋为何导致了其主体性的缺失,可以从与自己的关系、对男性的依附和对女性的态度这三个层面看出缘由。
(一)自恋:让美成为一切的免死金牌
在与自己的关系中,王琦瑶始终认为靠美可以拥有一切。小说开头先是用了四个章节描摹海派文化中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然后才是王琦瑶的登场。王琦瑶的自恋,就源自上海这座城市给予美人们的天生优越感,以及在优越感里夹带着的清冷和迷惘。小说对王琦瑶的描述用了两个“典型”:其一,“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其二,“王琦瑶是典型的待字闺中的女儿”。“她们夏天一律疰夏,冬天一律睡不暖被窝,她们需要吃些滋阴补气的草药,药香弥漫。这都是风流才子们在报端和文明戏里制造的时尚,最合王琦瑶的心境,要说,这时尚也是有些知寒知暖的。”[3](P53)小说中的价值观都是围绕美与丑进行的,长得美的人即便作态也是可爱的,而长得丑的人活该要比别人低一等。吴佩珍的出场和王琦瑶形成鲜明对比,只不过作者这样对“美”的一味纵容和对“丑”的惯性歧视,虽然给予王琦瑶一块免死金牌,却最终把她送上黄泉路。
《长恨歌》中人物间的直接对话很少,而作者的转述很容易带着立场和情绪。王琦瑶和吴佩珍都不再只是小说中的人物,更像是作者价值观附带下的女性符号。美就是王道,丑就是卑微。王琦瑶因自恋而夸大自己的美,又因为美而深深陷在狂妄可笑的自恋中,所以从未清醒的她一直没有真正的主体概念。从最初去片场,到后来坐在程先生的相机前,再到成为上海选美的“三小姐”,她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这份美给她带来所渴求的一切,虽然有时有些故作姿态。作者或许意识到了这份美的单薄,因此也想让这份美有更深的厚度,想赋予这种美一种内在的智慧。
王琦瑶却是个不犯错误的例外。她比较聪敏,天生有几分清醒,片厂的经历又增添了见识,这就使她比较含蓄和沉着。要说作态,她也有,是不作态的作态,以抑代扬,特别适合照片的表现。……她心情很明净,拍过的照片她不再去想,当它是桩没结果的事情。[3](P88)
可是她真的不在乎吗?她是太在乎自己的美貌了,所谓的不去想,只是怕自己对美貌的自恋赢不过世俗的评判和权钱的交易而已。因此,王琦瑶的这份美,毫无人生智慧可言,世俗的小聪明倒比比皆是。她的这种美是在女性价值观尚未成熟前极其危险的诱饵,她会把美当做攀上高枝的资本。单纯的美,让王琦瑶因自恋而走向危险,夹杂着世故的美和自恋,让王琦瑶步步沦陷,直至彻底丢失自我。跟着李主任住进“爱丽丝”公寓的日子,让她迅速飞上云端,又瞬间跌至地狱。而王琦瑶从未反省过当初错误的选择,只是逃离到外婆住的邬桥,一味自怜自艾。
因为丢失自我主体性,拒绝成长,所以王琦瑶对有限肉身和生命长度极为关注,她担心时光会带走美赋予她的一切权利。“她想,老这东西真可怕,逃也逃不掉,逼着你来的。走在九曲十八弯的水道中,她万念俱灰的只有‘老’这一个字刺激着她。”[3](P302)从爱丽丝公寓跌回人间的王琦瑶感到绝望,而更大的绝望还在等着她,没有了李主任这棵大树之后,最大的恐惧就是接下来找谁攀附,小说又借着外婆的话,再次把王琦瑶的美兜售一遍,但这里面竟然还是充满了深深得同情,丝毫没有怒其不争。
从作者对王琦瑶的塑造中,我们也逐渐认识到王琦瑶真实的自我认知。她一味回避自己失了德行和操守,觉得最初的选择并没有错,只是因为李主任的突然死去,自己从天上掉到地下,自己一直都是受害者。这就是王琦瑶搬进平安里之前,由美和无知而产生的过度自恋所导致的悲剧根源。她从来没有过“自我”的主体意识。笔者认为,《长恨歌》传递了一种错误且带有迷惑性的价值观所滋生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恰恰为那些因自恋而丧失主体性的女性拒绝自体的成长,提供了一个错误的精神向度。其实,除了沉溺于自己的美,自恋更可以也更应该是源于自体的成熟与强大。
(二)自恋:导致寄生
王琦瑶一生都在寻找可以令自己高枕无忧而寄托终生的男人。太过自恋的王琦瑶,不仅对自我的态度上从未清醒,而且她的梦还一直缠绕在所有和她有交集的男人身上。适度的自恋可以促使女性主体性的增强,但是过度的自恋就会抹杀主体意识。女性主义哲学的起点是波伏娃的《第二性》,波伏娃认为“男性是外在的、超越性的自我;女性则是自在的、内在性的自我”[5](P39~40)。女人的“他者”地位总是和她的总体“处境”息息相关的,是存在主义的。女人不是生来就是客体,而是被男权社会规训和压抑成客体的。
可怜可悲的王琦瑶,一直心甘情愿地成为毫无主体意识的客体。40年代末自愿被李主任金屋藏娇,避乱邬桥时与少年阿二不切实际的精神意淫,50年代与康明逊、萨沙不合时宜的情欲纠葛与互相欺骗,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和老克腊旧梦重温,都是在自以为寻找女性主体性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沦为了客体。似乎只有在60 年代初为人母,与程先生精打细算、隐忍妥协的那段生活中,王琦瑶才短暂地感受到了女性主体萌生的别样体验。很可惜,这短短的自我觉醒也随着程先生的自杀以及和女儿的争风吃醋而再度灰飞烟灭。
王琦瑶希望依附的主体,本身都是虚弱的客体。王琦瑶早年披金戴银的“繁华”和余生被弃的“落寞”,其实也观照出每一个走进她世界的男人也是落寞的,这些男人都是王琦瑶强大的自恋思想中幻生出来的一种对残缺的爱的镜像。李主任高处不胜寒的落寞,阿二追梦无踪的落寞,康明逊自私逃避的落寞,萨沙逃之夭夭的落寞,程先生纵身一跃的落寞,老克腊没赶上高潮只赶上结局的落寞。这些都是王琦瑶曾经以为深爱或者深爱着她的男人们,但所有的这些也恰恰是王琦瑶不同人生阶段自恋情结的实体投射。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来什么样的人。每一次和男人关系中的勇敢和担当,其实都是王琦瑶庞大而又脆弱的自恋个体在作祟。和李主任在一起时从未有过的乖,和康明逊在一起要独立生下孩子的孤勇,对程先生付出多年爱意的理所当然,以及最后对老克腊低三下四的强行挽回,这一系列的清晰主体性的缺位,都是王琦瑶骨子里病态的自恋所导致的。
适度的自恋,会让个体在关系中更加强大;而过度的不加反省的自恋,会让自体的觉醒和成长彻底瓦解。“内聚性”是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Heinz Kohut,1913~1981)提出的概念。内聚性是指自我有一种向心力,可以保证心灵各个组成部分向内聚合,从而构成一个整体。在情绪的惊涛骇浪中,内聚性自我稳稳地在那里。王琦瑶的内聚性自我从未形成,但是全能型自恋却从原生家庭中时就如影随形。因为家中没有所谓的温暖和想要的财富,所以她在一元索取型关系中畸形地生长起来。所谓的一元型关系,就是要么你们都要爱“我”,要么你们都是魔鬼。因此,王琦瑶在年龄增长、心智停滞的时光里,她有一个庞大的潜意识:你们必须承认“我”是美的,继而给“我”想要的一切,不然你们就是罪孽的。
如果内聚性自我足够稳定强大,适度的自恋会让王琦瑶们学会不断地突破重生,在认知迭代的过程中,会有更强大的意识层面以外的东西来摧毁小我,让一切认知、理念正向流动,最终在破碎后修复进化成一个更强大的全新自我。但是王琦瑶在自体价值观都未成熟的时候就急于让自己自恋包裹的欲望野蛮生长,因此她没有一个内核稳定的内聚性自我,以后也谈不上由内而外地成长,只是在原地重复地做一些简单的肢体动作来证明生命的原始意义。
(三)自恋:导致个体迷失
如果说王琦瑶对自己、对男人的态度,让她的自恋由内而外地涌现出来,淹没了自己的主体性,那么在她与女性的相处中,则是由作者赋予了其特权,可以自外向内地把自恋进行到底。
作者想把王琦瑶塑造成一个不被动地等待命运安排的人,赋予了她很多“自主”性以及改变命运的选择。比如,竞选“上海小姐”、做李主任偏房、隐居平安里,以及为康明逊生下没有名分的孩子,等等,都是出于她的自主选择。可这恰恰是因果倒置,她正是完全服从于命运的推波助澜,让自己凭借美貌获得了其他女孩得不到的一切,才被命运安排了和这些男人相遇。如果懂得自我成长、主体性选择,王琦瑶压根不会遇到他们,更不至于覆水难收。从这个角度看,自恋情节渗透到王琦瑶生命的各个环节,作者想要体现海派文化的包容,却恰恰把海派文化“做小”了。小说中提到和王琦瑶同时代的女性还有吴佩珍与蒋丽莉,在作者的笔下,这两个女性都是来衬托相信“美就是王道”的王琦瑶的,她的一生不仅值得被羡慕,而且又必须被同情。
吴佩珍的存在就是为了显示:美就可以肆无忌惮,丑就该退避三舍。面对王琦瑶的颐指气使与忽视冷淡,吴佩珍始终抛开自己的一切自尊,站在王琦瑶的角度替她考虑。在抛弃一切女德成为别人情妇的王琦瑶面前,吴佩珍一直那么卑微。吴佩珍对王琦瑶的崇拜和望尘莫及的内心定位从未摇摆过,反倒因为王琦瑶“靠自己”住进了爱丽丝公寓,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这是王琦瑶辐射出的强大自恋直接导致了身边女性的主体性缺失的典型说明。多年后,真正靠自己努力成为中产阶级的丑女吴佩珍,还是在做了小三的美女王琦瑶面前怯懦自卑。小说将价值观简单地锁定在对美丑的错误定位上,导致一个个出场的女性被王琦瑶强大的自恋情结席卷过去,丢掉了自我对真正价值的评判。“这时,娘姨送茶来,说声:小姐请用茶。王琦瑶厉声道:分明是太太,却叫人家小姐,耳朵听不见,眼睛也看不见吗?”[3](P278)骄纵病态的王琦瑶,虽然借高官上位,但内心深处依然无法欺骗基本良知,这又是面子上的自恋,进而加重了芯子里的自卑。因此,当听到吴佩珍结婚的消息时,王琦瑶更加深了对自己当下处境的哀叹和痛苦。一方面,王琦瑶希望借外在形象抵消曾经的自卑,希望展现一个独立、美丽、自强而又智慧的女性形象,可这只是她的外显人格;另一方面,她潜意识里也清楚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一切更加吞噬着残喘的灵魂,撕裂感会越来越强,直到瓦解掉她所有的主体性,在分裂中心甘情愿成为无意识的客体,与宿主的关系变成了单纯的索取与交换。
蒋丽莉算是陪王琦瑶时间最长的女性了,但是她和程先生也是失去主体性,并臣服于王琦瑶强大的自恋,喜怒哀愁都是为了王琦瑶而产生和消失。程先生是王琦瑶一生的备胎,蒋丽莉一生都对程先生无法放下。就这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两人,在王琦瑶自恋的光环笼罩下,成了两个毫无主体意识的客体。最后,一个病死,一个自杀。蒋丽莉一生都未得到爱情,虽然后来有了婚姻,但是她却一直嫌弃对方。在海派文化的冲击下,作者把其他一切文化历史都描写得有些低人一等,蒋丽莉的丈夫和他的家人虽然一直对她照顾有加,但是在蒋的眼中,口音以及本分的处事方式都让她心生厌烦。
王琦瑶周边的女人是如此,海派文化周边的文化亦是如此。没有主体性,没有自己的地位,一切都要仰望着那具有包容力和魅力的上海,以及无论做什么都值得保护和同情的“王琦瑶们”。这再次说明,自恋已经不单单是王琦瑶对自己偏执的认知,更是周围女性对她失焦的评价。
三、主体性的缺失导致匮乏需求增加,再次加重自恋
马斯洛(Abraham H.Maslow,1908~1970)将人的需求分为七个层次,最主要的是基本需求和成长需求。基本需求是由于心理和生理上有某些欠缺而产生的,所以又称为“匮乏性需求”。当人的基本需求出现匮乏时,心理能量就会一直集中在追求这些基本需求上。主体性缺失导致匮乏需求变本加厉地生长,进而碾压成长需求,使心智不再成长,退行到孤独的全能自恋中,并如“衔尾蛇”般再度加重自恋情结。
自恋一般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我”是对的,“我”说了事情会怎样,事情就会向那个方向发展;第二层是“我”比你强,“我”在关系中要高过你,“我”地位高、你地位低的格局才能让“我”舒服和自在。王琦瑶基本上处在自恋的第一层,她总是认为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得到上天眷顾、男人垂涎、女人羡慕,所以蒙蔽了对自我的真实认知。而她和周边人相处的过程中,体现了自恋的第二层,就是“我”一定要高过你,强过你。除了第一次在李主任面前装出的“乖”,其他的一切都是伏笔和铺垫。在自体和关系中的过度自恋,导致王琦瑶主体性缺失,使她一直都处在心理和生理上的低级匮乏层面,而匮乏需求又导致成长需求处在永远断裂的状态,所以她到死都无法完成自我的成长。
(一)主体性缺失到匮乏需求增强
王琦瑶的心理出现明显变化是在她竞选“上海小姐”之后,在此之前,她一直有意强行压制自己的潜意识,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要等待男人救赎才能拥有理想生活的低俗女人。从她第一次去片场的态度以及在程先生的相机前故作骄傲和清冷的姿态可以看出,自恋的膨胀最初激发的是她虚假的自尊。直到李主任出现后,王琦瑶潜意识里强烈渴望摆脱平庸生活的欲望爆发出来,欲望让她仅有的一点理智丧失了,甚至是急不可待地跳进了没有名分却享尽繁华的爱丽丝公寓,这就是命运。住进爱丽丝公寓的那一刻,王琦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顺从和依附可以让她暂时获得想要的一切,因此主体性在她的身上没有任何价值。但是主体性的消亡会直接导致自我构建的坍塌、内心匮乏,从而外化出更贪婪的索取,所以王琦瑶对李主任也由最初仅乖乖地止步于物质的满足,到慢慢迫切地想抓住李主任这个人,求得感情的认同和归属。在王琦瑶生命中有两个极端的男人:一个是李主任,另一个就是程先生。一个是一手遮天,可以为王琦瑶重造命运,让她从真匮乏到假清醒;一个是一元型好人形象,始终提醒着她在真匮乏中保持真清醒。
但是李主任突然死了,这种索取链条的突然断裂并没有让王琦瑶清醒过来,反倒使其一直沉浸在遇到第二个李主任并把自己拯救出来的幻象中。当然,这个人一定不能是程先生。王琦瑶太过自恋,对于程先生这份毫无攻击性的好与善,她躲在自恋的躯壳里驾轻就熟地免疫了一辈子,因为和程先生在一起就会提醒自己曾经不光彩的过去、那些跌落神坛的惨败。王琦瑶因为太过自恋,始终把自己架到一个高处不胜寒的地方,俯视着人间最该被珍视、却一直被忽视的爱情,而“匮乏”的程先生却只能给与王琦瑶“贫乏”的爱情。
(二)因匮乏而自恋升级,拒绝成长
在平安里的那段日子,是王琦瑶试图自我拯救,尝试寻求主体性,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拒绝成长的一段复杂时光。跌下神坛后,王琦瑶开始重新寻找人生方向,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得基本的生存需求,这是因匮乏而开始和过往的自己较劲,要寻得新的成长的开始。但是,当在炉边夜话的美好时光里再度遇到康明逊和萨沙这样对她有吸引力的男人时,之前那个自恋又不切实际的王琦瑶又卷土重来了。
王琦瑶之前始终停留在匮乏需求这个层面,无法进阶到成长需求,以至于她一直禁锢在匮乏认知层面,这样的人会根据自己的想象行动而不是根据现实行动。如果一个人有了正确的成长需求,那么她的认知也会进化为存在认知,就是说,以现实为基础来正确客观看待世界,而绝不自欺。这段时间里,王琦瑶就是拎不清现实,并和自己较劲,她觉得自己命不该如此。先是傍上李主任,李主任死了,又爱上康明逊,却依然无法获得名分和安全感。但此时经历过温柔乡的王琦瑶并不想再用“乖”来依附男人了,她决定生下和康明逊的这个孩子。这次的姿态是故作独立和坚强,这也是王琦瑶经历前期巨大匮乏后产生的自恋进阶版。不得不说,还有一部分是她在半觉醒边缘想寻找主体性的表现,但更多的还是强大的潜意识,就是过分自恋导致了极度不自信。不是由内而外地成长,而是试图从外向内在男人面前证明自己。她在和自己较劲的过程中,内聚性自我还是没有形成,否则就不会有一个李主任,又接二连三地有了康明逊和萨沙以及最后的老克腊。这些都是王琦瑶骨子里的自恋吸引来的爱情残次品,是王琦瑶奴性基因在真实生活中投射的实体。
意识层面越自恋,潜意识深处就越觉得自己不配被好好爱,这种较劲就会导致思想扭曲。越是得不到,越能激发她内心巨大的不安被触碰后的变态狂喜。她内心深处就是喜欢这种由不安引发的关注,被更多人疼爱、佩服的那种变态快感。所有表象的爱,都是因为对匮乏的恐惧,在不断索取中,又一点点增加自恋,丢掉主体性。
自恋到主体性缺失,再到匮乏,最后又回归到自恋加重的恶性闭环,在王琦瑶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她觉得平凡的生活配不上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掉落人间,但又没有能力回到天上,所以对着鸽群,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描述,它们是最洞若观火的生灵,自己就在人世间上空高不成低不就般存在。她就是不能从对爱的匮乏中走出来,走到成长的需求层面,去看看这个城市40年风卷残云后,剔除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迎来了什么。虽然王琦瑶有胆量做外室,名不正言不顺地生孩子,编造一个莫须有的父亲,但是她不敢学会成长,不敢学会去爱和付出。
(三)自体成长的停滞反过来加重自恋
王琦瑶的一生,从做女儿到当母亲,一直拒绝成长,在匮乏中投射出一个巨婴般的自己。到1976年,王琦瑶的女儿微微已经15岁了。成为母亲的王琦瑶,自恋的泛滥没有那么理直气壮和汹涌澎湃了。在女儿面前,她作为独立女性的自主意识在不断完善;但是,作为一个呵护女儿、疼爱女儿的母亲,她又总是在寻找那种能弥补年龄代际的心理安慰。很多默契和交流不是发生在母女之间,而是发生在微微的好朋友张永红和王琦瑶身上,因为张永红又是微微那个时代的美人,这在作者的价值观里,都是海派文化中的“优等人”。王琦瑶面对张永红有很分裂的两种情绪:一方面是对那么像自己且拥有大把青春的女孩的嫉妒和痛惜;另一方面是女儿姿色平庸,只有和张永红相处时才能找到自信和昔日光环,这让年事渐高的王琦瑶自欺欺人地认为没有被这个城市彻底抛弃。
日本女作家上野千鹤子《厌女》一书中曾提到母女之间微妙的关系:
母亲一方面期待着女儿,可当女儿真的实现了自己未能达成的欲求,却又不会是单纯的高兴,而会怀有更复杂的心情。但儿子无论实现了什么,母亲都无需与他竞争,性别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便利的缓冲作用。但女儿不同,因为同为女性,母亲无法为自己找到借口。[6](P126)
王琦瑶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要一辈子被疼爱的,包括女儿的出现也不能把她的这份特权夺走。王琦瑶也试图做一个好母亲,但在微微去美国以后就彻底放弃了这方面的想法。她每一次和自己抗争,都在强大自恋的控制下完败。女儿走后,王琦瑶再次“活回了”自己,寻找寄生的宿主,又和老克腊牵扯出了一段有些让人反胃的姐弟恋。男人对她的垂涎,是她得以生存在自恋幻觉里的氧气。看似一直要独立自尊的王琦瑶,从来不懂独立和尊严为何物。到最后,长脚夜半闯进她的房间时,她本来可以通过失去财产来保住性命,但是太过自恋的王琦瑶怎能让自己受尽这样的侮辱,那可是李主任当年对自己真爱的唯一见证了,然而她以为拼命保护的是对爱情的守护和残存的尊严,但是到最后呵护的却恰恰只是一个幻影和执念。
王琦瑶的40年,从来不会主动付出爱,投射到她身上的爱也都被一点点掐灭,更别说很多人对她根本谈不上爱,只是出于好奇感和征服欲。最虚妄的东西却被她攥得最紧,并视为证明自我价值的重要筹码。只有主体性的增强,才能让自己快速成长,才能真正懂爱、会爱。在一味被动等待的过程中,自恋会扭曲变形,唯有主动走到真实世界,真正为一份值得的爱献身的时候,身上那种变态的自恋才会土崩瓦解,才会由内而外成长出一种自信和智慧的力量,自体也会因成长而变得更丰盈。不需要自恋,而且能迎来更多人真正的爱恋,这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有明确主体意识,敢于宽恕并无畏付出,也依然可以嫉恶如仇的独立完整的生命。
王琦瑶的一生是可悲又堕落的,她自恋而不自爱,以至于看不见女性该有的广阔天空。她的一生都在寻找宿主,却自我欺骗在寻找真爱,其实她从来就没有爱的能力,也没有接受爱的资本。她只是试图通过外在的变量来寻找心灵安定的“锚点”,却从不懂如何由内而外地成长,找到内生力量的“聚点”。她因自恋而迷失自我,又因主体性缺失而始终滞留在生命的匮乏层面无法成长,反过来加重病态的自恋,困在这个因果倒置的畸形闭环中,一生都从未走出。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