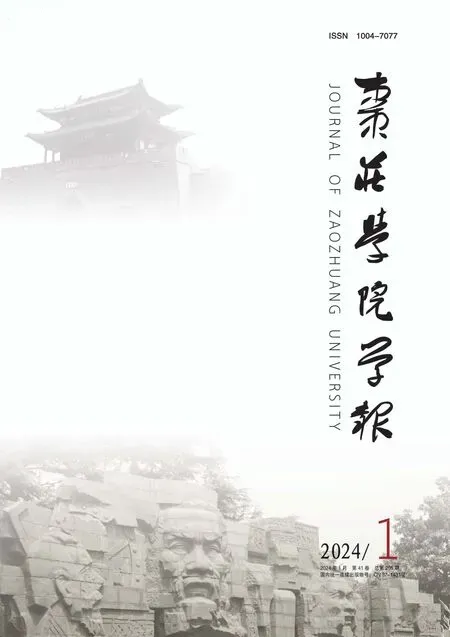孔子“仁者,人也”的逻辑理路、内涵义理及其当代价值
宗 超
(曲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日照 276800)
《中庸》所载孔子之语——“仁者,人也”,是“先秦儒学对‘仁’的唯一定义式表达”[1](P5),同时也是孔子人学的标志性话语,其重要性自不言而喻。现代学者对于这一命题的研究虽依据其结构与含义的理解差异大致呈现出偏重人论或仁论——此命题主要是对“仁”的回答”还是“人”的回答——的不同倾向①,但基本聚焦点皆一致指向命题的释义,而关于命题逻辑理路与当代价值方面的探讨则较为缺乏。本文借鉴诠释学的方法,旨在透过命题语式的表达结构和基本语义,在把握命题“何以生成”又“如何落实”的逻辑主线中呈现其内涵的丰富义理,进而以此为契机,深刻理解中华德性文明的基本特征与文化底蕴,并为当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必要的启示与借鉴。
一、“仁者,人也”之生成
既然“仁者,人也”这一命题是由“仁”与“人”这两个概念构成,那么这两者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就决定了命题之由来。从命题语式的表达结构来看,这一命题显然是孔子对“仁”的回答,而孔子何以用“人”来回答“仁”,对此问题的解答自然要从孔子之“仁”开始。
(一)孔子对“仁”的提升:由综合性道德到标识人之根本价值的完美道德
“仁”这一概念并非孔子首创,据学者考证,“仁”之起源与古代东夷文化密不可分,具体指东夷地区的一种礼俗。②到了周代,周人开始用“仁”来表示一种美德,《周礼·大司徒》中即直接将“仁”列为六德之一。③另外,《国语·周语中》在记载“郑人伐滑”事件时也明确提出“以怨报德,不仁……仁所以保民也”的观点,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开始以“仁”或“不仁”来进行道德评价,而且“仁所以保民也”的说法也将“仁”从众德中的地位突出出来,一跃成为关乎“安邦保民”的关键性德目。随着“仁”这一德目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突出,“仁”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综合性意义的概念,《左传·襄公七年》就有“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合为仁”的记载,“仁”成为“德”“正”“直”三德的综合。由此,“仁”不再只是一种关键性道德,而且成为一种具有涵盖统摄意义的综合性道德,“仁”的含义被再度丰富和扩大。
孔子正是沿着这种趋势,对“仁”做了进一步地提升,被提升后的“仁”成为孔学的核心范畴,有了全新的蕴意,这一蕴意被学者精准地概括为“全德”(冯友兰)[2](P48)、“最高的德”(张岱年)[3](P403)。两种释义看似不一,实质并无本质区别。所谓“全德”,是指仁可“统摄”诸德;所谓“最高的德”,则是指“仁”虽“自为一德”,却不是普通的德,而是所有德目中最重要、层级最高的德,而层级最高的德自然可以“统摄”其他诸德。
春秋时期被陈来先生喻为“德行的时代”[4](P300),因为这一时期德目数量众多、内涵丰富。而孔子拈出一个“仁”字,一举将所有德目“统摄”在内。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用‘仁’统摄了‘智’,又统摄了‘勇’,还统摄了‘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统摄了‘恭、宽、信、敏、惠’(《阳货》)等,凡是以前属于德的那些子目,都被孔子的‘仁’所统摄了”[5](P80)。
那么,如何理解仁可“统摄”诸德呢?具体而言,“统摄”二字蕴含着二层意义:其一,“仁”作为全德,可涵盖其他诸德的价值,而其他诸德皆从不同方面体现和丰富了它的内涵。譬如孔子指出:“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即明示仁必包含勇,而勇却包含不了仁,它只是仁之价值的某一方面的体现而已。其二,“仁”作为最高的德,是其他诸德的根本指导原则,对其他诸德起到一种调节和滋养作用,其他诸德必须符合“仁”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才有真实的意义。“仁”的这种统帅和灵魂作用在孔子的下面这句话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就算聪明才智再多,但是如果不能守住“仁”,那么他所追求的东西即使得到了,最终也一定会失去。这正说明,“智”想要发挥真正的作用离不开“仁”这个核心价值。总而言之,正是基于“仁”既可包容其他诸德,又是其他诸德最根本的指导原则,“仁”才称得上为“全德”“最高的德”。
那么,孔子为何要将仁提升为“全德”“最高的德”呢?事实上,顺应仁德的历史发展趋势或者说为诸德确立一个核心价值只是其表层原因,孔子如此做的真正目的是他需要一种完美道德以说明和匹配“人”。也就是说,在孔子“仁者,人也”的命题中,后者乃是前者的逻辑前提。孔子将仁提升为“全德”“最高的德”,其最终落脚点就在于“仁”之于“人”的重要意义。据《王阳明全集》记载:
太夫人郑娠十四月。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岑警寤,已闻啼声。祖竹轩公异之,即以云名。乡人传其梦,指所生楼曰“瑞云楼”。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岁。先生五岁不言。一日与群儿嬉,有神僧过之曰:“好个孩儿,可惜道破。”竹轩公悟,更今名,即能言。[6](P1071)
王守仁的祖父为其改名“守仁”,而“守仁”二字的选取就来自于孔子“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卫灵公》)的这段话。他的祖父相信,正如孔子所强调的那样,智而不仁,智无法长久,唯有以仁守智,智的作用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而纵然自己的孩子天生愚钝无智,但只要能够守住“仁”,也不失为一个好人。“仁”是一个人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品质,彰显着一个人的根本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仁”构成了界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或者说根本原则,而这正是孔子所谓“仁者,人也”的内涵,孔子正是以“仁”来看“人”的,而一个人若没有“仁”,那就称不上一个真正的“人”。孔子的这一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至深,钱穆先生于《人生十论》一书中提到过,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曾对他说:“中国人骂人说,你算个人吗?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钱穆先生对此感叹道:“他可算得明白了中国文化。”[7](P163)若我们要对这一文化追根溯源,则可以追溯到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此后,做一个有仁德的“人”的观念牢牢扎进了我们国人的生命里,绵延千年而不坠。
由此可见,孔子重“仁”归根结底源于孔子重“人”,孔子对“仁”的提升是由其对“人”的思考和认识所决定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知道,孔子的仁学是基于对“人”的了解而发生的,亦即基于对“人”的认识而产生对人之仁德的关切。
(二)孔子对“人”的反思:人性直承天之仁且可将天之仁发扬光大
在孔子以前,人们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自孔子开始,孔子以“仁”这种完美道德来界定“人”,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仁”。孔子何以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仁”?如同休谟所言:“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和特点的形成都受它所处的时代的影响和制约。”[8](P30)孔子的哲学思想亦是如此。“仁者,人也”思想的表达正是一种与时偕行,是孔子面对春秋时代社会的激变,对天人关系的反省深刻之后所发掘出的人性深处的需求。
春秋时期是政治腐败、礼崩乐坏、社会失序的动荡年代,政治危机与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使原来用以维护王权的天命观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天神的权威逐渐衰落,人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高。《左传·桓公六年》中“夫民,神之主也”的观点,是最能清晰表达这一转变的文献。人是神之主人的观念,使人彻底从天神信仰的樊篱中脱颖而出,把目光拉回到人身上,反求自身,自求多福。“聿修厥德”(《诗经·大雅·文王》)的观点更加受到人们的认可和信赖,人“修德”成为确立人之价值、地位的关键,鲁大夫叔孙豹所谓的“三不朽”之说,可谓最佳证明: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很明显,“立德”被视为居于“立功”“立言”之上的人之最高价值。自然地,德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正因为如此,德在春秋时期意义非比寻常,这也正可解释何以春秋时期“德”如此大势发展了。
“德为人之最高价值”的思想被孔子继承、创新,发展成为“仁者,人也”的思想。也就是说,孔子将标识人最高价值的“德”具体化为“仁”:只有完美道德“仁”才足以彰显人之最高价值或者说根本价值,“仁”意味着人之所以为人的充分体现。
那么,问题在于,人何以能具备这种完美道德?人之仁德从何而来?孔子说:“天生德于予。”(《述而》)就是说“仁”是人承天德而来。《中庸》把孔子的这一思想更直接明朗地表达为“天命之谓性”,即人性乃天所命,或者说天所命于人者谓之性。从表面上看,孔子“人承天德”的思想似乎又退回西周“以德配天”的老路,实则不然,因为在孔子那里,虽亦有对天的信仰,但信仰模式却与以往大相径庭。孔子信仰的不再是天之本身,而是天之所以为天之“仁”。从《论语·阳货》的如下论述中,我们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
在孔子看来,正因为天有纯然无私至善之德才能使四时行而百物生,此即天之“仁”,而“天之所以为天者”正因此“仁”。也就是说,孔子是“以仁发明天道”,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说:“孔子以前亦有天,人亦知信天,而敬天学天之仁等;然自觉天之所以为天道,即是此仁,而惟以仁道言天者,则自孔子始。”[9](P36)由此,仁成为天性和人性的贯通,这意味着天道的全部意义可以由人性体现出来,这样,人之主体地位才能得以完全挺立。
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看,人承天德并不是由于天的恩典,也不是出于利己的动机,而是由人之“生”自内引发出来,是伴随生命而来的生之本然与自然过程。人性可自“生”而言之,包含着人之为人的道德性的当然义理之善。在孔子看来,人天生就有此潜在的性体仁心,即孟子所说的人之皆有的仁义礼智之善端,乃“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而动物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秉承这种天命之性,因为动物根本不具备这种性体仁心。孔子坚信,作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的人之性是最高级且完备充足的,故宇宙间惟人能秉承天命天德以成性。对于人之性体的这种特殊性,牟宗三先生曾在诠释《中庸》“天命之谓性”一句时有过深入精细的分析:
其流行于人而命于人,而人能受之。即为人之“性”,是即为“天命之谓性”。其流行于物而命于物,而物不能受之而为性,则于此只好说“天命之谓在”。就人而言“天命之谓性”,则不但命人之生,亦命其性,是“天命”即“降衷”也,而人亦独得之矣。[10](P200~201)
“物不能受之而为性”,“人亦独得之矣”,所以“仁”是惟有人才拥有的天命本性。就此而论,人作为宇宙间独一无二的天德秉承者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责任与使命。因此,孔子认为,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修德成仁、弘扬天道成为人之终极价值,如同孔子所强调的那样:“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这一观念与其说是揭示了人的伟大,毋宁说是彰明了人的责任和使命,而恰是人的责任和使命成就了人的伟大。孔子“人能弘道”的思想在《中庸》的如下话题中被进一步解释: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人能够通过“尽性”以最终达至“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在此意义上,“仁”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亦是人无可逃遁的神圣使命,只有将人与生俱有的最真实的人性完全体现,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仁”会被定义为“人”了:仁是人性,同时也是人的实现,天所赋予我们的人性,构成了我们必须奋力追求的使命目标,而人性的实现也就等于达成了天赋使命。因此,在终极意义上,“仁者,人也”的深刻道理在于——人彻底挺立起人之为人的道德主体地位,担负起顶天立地立人道而见天道的神圣使命者。正是基于此,孟子说:“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
二、“仁者,人也”之落实
我们说,孔子“仁者,人也”的观点彻底挺立起人之为人的道德主体地位,赋予了人顶天立地立人道而见天道的神圣使命。但是,“仁”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经过努力就能自动尽性达道。正如孟子所说,我们天然拥有的本性只是一个“端”而已,还有待人去认真地培养、开发。④如此,人如何去达成这一使命?即“仁的实践”问题必然成为“仁者,人也”这一命题落实的关键之所在。而这一问题又内在地包含了两个问题:何以体现仁?如何实现仁?即:通过什么表现人性之仁?又如何能确保将人性之仁落到实处?这两个问题既关涉实践“仁”的载体,又强调落实“仁”的方法,构成了我们探究“仁的实践”问题的有效门径。
(一)人何以体现仁——“爱人”
我们发现,当孔子的学生纷纷向孔子兴致盎然地问仁之时,孔子的回答虽不尽相同,但皆是从当下具体生活中去指点学生践行仁,譬如: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颜渊》)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同上)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
从表面上看,孔子对不同学生或同一学生在不同境遇下的指导千差万别,但实际上,在这些具体的实践中贯通着一个统一的行事原则,那就是孔子回答学生樊迟问仁时所说的“爱人”二字。当我们认真分析孔子指导学生践行仁的相关说法,不难发现,“爱人”二字相较其他说法而言最具代表性,可谓高瞻综概,启发性丰富。⑤诚如韦政通先生所说:“孔子对仁左说右说,言之再三,但没有比‘仁者爱人’这一点更重要的。”[11](P59)
既然“仁者,人也”的达成依赖于“爱人”,那么如何理解与实践“爱人”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关切的问题。
“爱人”首先标示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人与人的关系是从感情开始建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基本出发点。”[12](P81)
当然,孔子并不认为这种“仁爱”是一种普通的感情,孔子强调“仁爱”是一种由内心而发的真情实感。易言之,真诚性是“仁爱”的显著特征。通过读《论语》,我们会发现,孔子根据人的道德境界的不同,将人分为若干种,诸如圣人、仁者、君子、贤人、小人等。而其中有一种人最令孔子不耻,就是“道德败坏的小人”。⑥《论语》中,孔子常常将君子与小人对举,譬如: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在这些对比中,不难发现,小人呈现出与君子截然相反的人格特征:心胸狭隘、成人之恶、心怀鬼胎等,而究其原因,根本则在于小人缺乏真诚的仁爱之心。的确,指望一个没有真情实感的人能够待人真诚或心胸坦荡,那是不可思议的。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孔子会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
毫无疑问,所谓“爱人”,正是说这种由内心而发的真诚感情是必须体现在人际关系中的,这完全符合儒家始终强调人之社会性的传统:“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仁爱需要表达,需要在不离凡俗世界的社会交往实践中通过“礼”投射出来,否则再炙热真诚的感情也会窒息。也就是说,“仁”作为一种真挚的内在道德”需要“礼”作为窗口与手段展现出来,“礼”是“仁”在社会关系中的外在化,且只有借着礼,那些呈现基本德性的人类真挚情感才能适当表达出来,此所谓:“克已复礼为仁。”(《颜渊》)
接下来的问题是,“爱人”从何种人际关系开始?对此,孔子有明确地回答,即“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显然,孔子所谓仁爱不似佛家所说的对普天众生平等的爱,也不似墨家所说的对所有人没有差别的兼爱,相反,孔子强调仁爱有差等与区别:人之亲亲之情最为重要。因此,孔子认为仁爱应当首先爱父母兄弟,从自己的家庭出发向外扩展,这正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及”二字不仅标识出仁之利己利人的原则,也同样清楚地表明了仁之推己及人的次序。孔子对这种感情的差等性作了深刻的解释,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孔子认为,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爱的基础。确实,以这种无可逃避的人人都有的亲亲之爱为仁爱的出发点是非常自然的,毕竟一个人想要绕过生命本初的关系纽带来表达对人类一视同仁的爱是非常困难的,况且,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如果连生养自己的父母、朝夕相处的兄弟都不爱的话,很难想象他对别人的爱是纯正的。
当然,孔子所谓“亲亲为大”并非表明我们该做一个心胸狭隘的裙带主义者。孔子真正想表达的是:人之常情的亲亲之爱是正当且难以被绕过的,因此,我们重视这种亲亲之爱并以此同理心去努力地爱他人,正是我们实践“仁”可供遵循的正确路径。《学而》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的表述正说明了这一点,在此,血缘亲情(孝悌)之爱构成了群体之爱(泛爱众)顺理成章的逻辑前提。而这也恰体现了孔子所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的深刻道理。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孔子之“仁爱”需在人际关系中实现,并不是说它仅仅适应于人与人之间。相反,仁爱具有普遍性,它是仁民爱物、两不偏废。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孔子人承天德的思路已然决定了仁爱的体现必不会拘泥于人伦,而定当回馈于更广泛的天(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之爱物与自然正是爱人的自然延伸。儒家奉行的仁爱原则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孔子所创设的仁爱哲学正是一种爱的无限扩展。正是基于此,儒家坚信人通过扩展仁爱的努力能够成为“天”似的存在,同天一起推动与成就万物,这种实践既是对天赋使命的回应,也是人性的充分体现。孔子的这一思想的对后世影响至深,《水浒传》里忠义堂的一百零八位好汉高举“替天行道的大旗”,正是孔子仁爱思想的典型体现。人能替天行道、弘扬天道,成为天地的合作者,正因为人对天地万物有责任且真的可以通过扩展仁爱帮助到天地万物。
(二)人何以实现仁——“学”的工夫
在孔子这里,仁爱是体现人性的必由路径,与我们可以合适合理地表达仁爱之间并不存在直通车,仁爱作为一种天赋能力,依然需要为之提供可行的实现方法。因为一个人天赋的仁爱情感和能力,并不能保证仁爱的自然完成。这就好比说我们天生具备学习语言的能力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经过努力就能自动掌握一门语言,正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仁爱能力的发展也是如此。
那么,如何发展仁爱的能力?孔子“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的话可谓真知灼见。即一个“学”字实际上构成“仁”与“人”的中间环节,先天的仁性作为一种道德本体,必须经由“学”才能达成后天现实的仁爱。我们无法自然做好仁爱这件事情,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探索、思考、分析、综合以及发展理论与求证方法,而这也正是孔子所谓“学”的工夫。正如成中英先生所说:“通向本体的路,必然需要一番做学问的工夫。事实上,学问之重要性也就在于从知识和经验中去认知问题和自我。换言之,通向本体的道路一定涉及知识辩证性的发展过程。”[13](P284-285)
达成后天的仁爱亦即达成了自我实现(实现了人之根本价值),这种向着自我本性奋进的学习之路被孔子寓意为一种“为己之学”,因为,正如前文所述,由爱人到爱天地万物的一切行为,其动机莫不源于自我对天赋责任的感知与理解,故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实现。在孔子看来,仁爱的实现绝非易事,它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学习过程,而我们正是由此来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也就是说,学习知识,不是我们发展仁爱的一个项目,而是其根本。孔子由“学”以发展仁爱的思想在《易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理”即“穷尽万物之理”,这离不开为学求知的工夫;“至于命”也就是完成天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亦即实现人性(仁爱)。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是意指穷理即所以尽性,能尽性则最终能达致天命、实现自我。此一语可谓将学习对于做人的重要意义透彻地明朗了:学习的贡献在于个人心性之自觉与最终实现,这其中亦内在地包含着构筑同类共同体(亲亲与仁民)和辅助成就天地万物(“赞天地之化育”)的广大福泽的目标。这正是孔子所谓“君子学以致其道”的基本理由,同时也是“仁者,人也”这一命题成立的基石。在此意义上,“学”可以被视为贯穿始终的成人之本,它昭明着人可以在学习的、实践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人之为人的终极意义,故孔子“仁者,人也”的命题在“仁-学-人”的结构中得以最终落实,这昭示着天然的仁性虽然标志着人之为人,但这种仁性必须经由学习的后天努力才能达成现实中正确而合理的仁爱(构筑同类共同体与辅助成就天地万物)。
三、“仁者、人也”的当代价值
孔子“仁者,人也”的思想是中华传统人伦文明的一次重大理论建构和精神奠基,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与中国人的心性品格。可以说,这一思想己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且应当继续为当今时代提供新的价值导向和智慧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14]在今天,我们重新回溯与思考孔子“仁者,人也”的思想,就是要把握其根本内涵义理,切入现实、回应时代、为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有效助力。根据上文所述,孔子“仁者,人也”思想所反映出的根本内涵义理可以集中概括为三点:一是确立了人之“仁爱”的价值追求;二是宣告了主体自我之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是指明了“学以成人(成仁)”的刚健进路。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华德性文明传统以及助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皆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一)对深刻理解“中华德性文明”之精神传统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人为理性动物”的认识,引导西方文明走向理性,孔子“仁者,人也”的思想,又何尝不为中华文化确定了其德性的价值追求?正如杨新铎所说:“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可称之为德性文明的传统,其主要根据在于作为文化主流的儒学确立了人的道德主体性。”[15](P19)而奠基于人之道德主体性的中华德性文明主要体现为三大精神传统:推崇道德共同体、强调道德责任与注重道德养成。
所谓道德共同体,就是基于天地创生万物的生生之仁德,追求人与天地万物的一体和谐、天人合一。这正是孔子“仁者,人也”思想的智慧结晶,人性秉承天之仁德,就要像天地一样护养万物,使天下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各安其职,实现真正的圆融与和谐。这种道德共同体思想塑造了中华民族追求“中国一人、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合和”的文化特质。在当今人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顺应时势提出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德性文明传统密切相关,孔子“仁爱”的价值追求所塑造的道德共同体意识不仅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撑,铸就了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中国风貌——这与西方文化“更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冲突”[16](P20)迥然有别,而且更具意义的是,它还可以为全人类福祸相依、休戚与共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权利不同,中华德性文明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注重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早在《尚书》的“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中即已种下根芽,而孔子“仁者、人也”的思想则由“仁爱”出发将这种道德责任的范围由家庭扩展到整个宇宙自然,从而确立了人之道德责任的集大成之典范——“人对天地万物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通过这一典范为中华民族注入了“勇担重任”的文化基因。这在我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诸多实践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由于中华德性文明的价值追求是通过“尽己之责”以求“一体同仁”,这就内在地规约了其处理问题的方式与态度绝对不会像西方一样退却甩锅,而是更易于从自我履职尽责出发走向寻求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也更有动力负重前行,积极面对困境与挑战。可以说,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仅向世人展示了其政治优势,也同样彰显了其文化优势——中华民族数千年所创造、积淀和传承的“仁以为己任”(《泰伯》)的仁者情怀。这一显著的文化特性不仅“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担当意识……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17],也决定了中国在谋求自我发展的同时亦一定会为全人类做出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贡献。
中华德性文明传统还尤其注重道德养成,在孔子这里,这一问题实际上即是指如何“成仁”或“成人”的问题。对此,孔子自身便是最好的现身说法者。正如成中英所说:“孔子正是通过学习在社会上立住了脚,达到了道德的成熟,能够远诱惑、不生疑、知天命、明人世,最终达到道德的自由,将先在与内在统一。”[13](P38-39)因此,孔子的道德养成思想,简而言之,即“学以成人”,寓意着人的存在过程就是不断通过学习塑造人性、完善人性而生成的过程。这一观念塑造了中国人注重品格修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放之当代而言,它无疑构成了新时代我国“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文化根基,显然,立德树人内含“德可修养”的道德养成思想,这正是对孔子“成仁”或者说“成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如此,孔子“学以成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有关“学”的深刻洞见与实践导向,对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可以期待的是,儒家“学以成人”的思想可以在回应新时代“立德树人”中形成新的思想系统,从而推动中华德性文明在未来继续发展壮大。
(二)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启示
2019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新纲要》),为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公民道德素养提供了根本遵循。《新纲要》明确指出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要充分利用中华民族丰厚的道德资源。毋庸置疑,孔子“仁者,人也”思想中所确立的人对“仁爱”美德的价值追求构成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之文化底蕴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所包含的丰富具体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自觉”思想,能为促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重要的价值启示。
孔子极其重视道德责任,在他看来,道德必须落实为人的责任,道德才能得以实现。正如上文所说,“仁爱”的价值追求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责任的宣言,孔子从责任出发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构筑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当中,每一个人在履责的道路上所付出的努力,不仅自己会受益,对于整个人类乃至天地自然来说都是一种贡献。这一强调,无疑意义重大,不仅彰明了责任对于人类生存在世的重要性——人是责任主体,人为能履责地存有,更进一步澄明了个人履行责任、自我发展对于外部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不仅具有道德的意义,同时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与生态意义,不仅能导向自我完善与家庭和睦,同时也能促成政治有序、自然和谐。正是基于此,孔子认为,“人”不仅是自然中的被创造物,同时也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的创造者,而不得不警惕的是,也正因为人具有如此创造力,因而人也极有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与自然极具危害性的破坏者。尽责和不尽责的效果天差地别,这更加凸显了人之道德责任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儒者才催生出高度的道德责任感——“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泰伯》)
孔子对道德责任的认识启示我们,强烈的道德责任感是实现道德的有效手段,陈根法也指出:“德性的社会价值,最现实、最普遍地体现在人们的责任感上。”[18](P9)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应当借鉴孔子所阐发的“己任”“弘道”“赞天地之化育”“任重而道远”等道德责任观念来对治当今社会责任意识缺失,甚至是无责任、无义务的现象。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重视提升公民的责任意识,引导公民不断扩充内在人性亲情的仁爱基础,以唤醒公民的道德责任心与自律心,培养公民的责任胸怀和责任情怀。另一方面,要注重培植公民的责任人格,引导公民将责任意识转化为履责行动,在不断积极地“履责”与认真地“负责”中自我内化而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敢于担当的责任人格。另外,还要使公民深切认识到“尽己之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且使之能够充分预判履责的重要效力以及弃责的严重后果,从而提高公民对责任的警惕心与忧患意识,促使公民不能失责也不敢失责,当然,这需要法律、制度等多向度地保障和推进。
然而,在法律、制度等措施的保障之外,孔子还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道德自觉。在孔子看来,人之责任的担负,不是出于一种社会的要求或者说外在的约束,而完全是由内心而生的对做一个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的自觉。儒家所谓“为仁由己”(《颜渊》)、“仁以为己任”(《泰伯》)正显示了其以内在道德力量涵养外在责任要求,在尽责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内在道德的儒家宝贵信条。这启示我们,想要责任主体获得高度的责任感并真正将这种责任感转化为实际的行动,主体对自我道德肯认与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不可缺席,这才是一切责任落到实处的终极保障。儒家的这一观念转换到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即是要注重培育公民的“个人道德”或者说“个人私德”⑦,只有将社会公德与国家大德转化为个人道德或个人私德,才能推己及人并对他人、社会乃至国家做出纯正而长远的贡献,明大德和守公德才能真正成为现实。正如梁启超所言:“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19](P26)肖群忠也指出:“只有加强每个人的个人品德或者私德建设,才能为全民族道德素质整体提升奠定坚实基础。”[20](P31)2019年我国发布的《新纲要》中首次明确将“个人道德”单独列出且对其内容进行了详细阐释,彰显了党和国家对公民个人道德的重视。但是,个人道德在公民道德建设中缓慢出场,也从侧面说明当前我们对公民个人道德或私德建设的关注和推进还远远不够,有学者就指出,当代中国存在“以国家道德替代公德,侵蚀私德”[21](P139)的紧张和冲突。在此情况下,积极汲取儒家有关“道德自觉”的有益思想,立足时代现实,加强公民个人道德的培育,促进公民个人道德与社会公德、国家大德的协调发展,便成为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突出任务。
综上所述,“仁者,人也”是奠基孔学大厦的核心命题,此命题的生成与落实基于孔子对“仁”的提升、对“人”的反思以及对“仁”的实践:孔子基于“仁”的历史发展而将“仁”提升为“全德”“最高的德”,赋予了“仁”以“人之本质规定”的蕴意。孔子对“仁”的这一提升归根到底源于他对“人”的反思——人性直承天之仁德,故担负着顶天立地立人道而见天道的神圣使命,且孔子认为,这一使命的达成依靠的是真诚之“仁爱”由亲亲之情向自然万物的无限扩展,而“学”作为培养与获得仁爱能力的现实手段,是仁爱能够合理而正确地表达与实践的根本保证,孔子“仁者,人也”的命题正是在“仁-学-人”的完整结构中得以最终落实。孔子“仁者,人也”的思想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在当今世界被重新认识与诠释,发挥其创造力与影响力。我们相信,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复活传统的东西,我们才有希望开拓崭新的天地。
注释
①现代学者对这一命题的专门性论述并不多,其中偏重人论的代表性学者是白奚,而偏重仁论的代表性学者主要是陈来、朱刚。
②关于“仁”具体指何种礼俗,目前学界主要有二说:一说认为“仁”指东夷地区的一种见面问候之礼,持此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刘文英;另一说认为“仁”指东夷地区的一种尸祭之礼,持此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许少敏。
③《周礼·大司徒》中记载:“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
④“端”意指“开端”“萌芽”,这一说法已然表明人之天然善性必须经过后天的扩展方能被真正体现。即孟子所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⑤仔细阅读《论语》会发现,孔子有关子“仁”的说法,皆围绕着“爱人”这一基本原则展开,表达的是对人尊重、关怀、了解、负责、体谅等“爱人”的方方面面。譬如:“如见大宾”“如承大祭”,表示对人的尊重和恭敬;“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体现的是对别人的体谅和同情;“克己复礼”则体现了一种“爱人”的规矩和规范。
⑥《论语》中所谓小人有两指:一指怀土之民,一指道德败坏之人,而最令孔子厌恶的是后者。
⑦个人品德与个人私德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个人品德主要是指无关他人的个体品德,而个人私德主要是相对于公共领域而言的私人领域内的道德。两者虽各有偏重,但皆指向的是一种主体自身自内在的、不依赖外力约束的道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