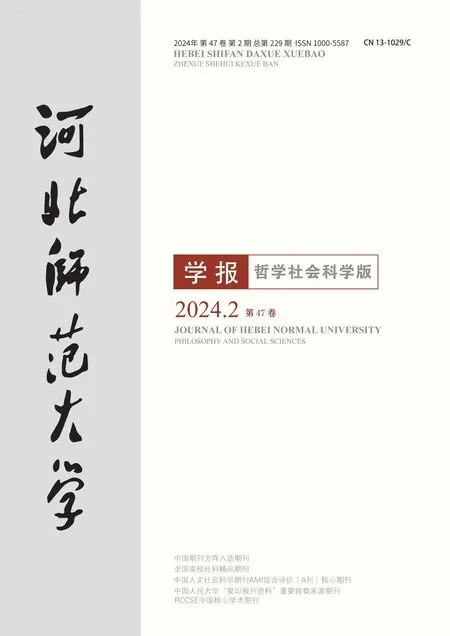20世纪以来西方舞蹈理论中的身体话语
王晓华,黄秋燕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一个反叛身体的大阴谋”就长期支配着西方舞蹈研究:“在我们的西方历史中,我们贬低、抹煞和污蔑我们的身体几乎两千多年了。我们的宗教是没有形体的灵魂的宗教,而我们的心理学则是没有形体的精神的心理学。”(1)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涂纪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由于认定“躯体之运动实有赖灵魂为之做主”(2)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8页。,舞蹈中的身体被众多理论家定位为“供灵魂表现的工具”(3)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谈艺录》,张本楠译,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譬如,柏拉图就曾如此谈论舞蹈中的身心关系:“在严肃的戏剧中,一种舞蹈用适宜的形体动作来表现战争,由勇敢、坚忍不拔的灵魂来承担;另一种舞蹈则表现繁荣昌盛的快乐,由有节制的灵魂来承担,后者的恰当名称是和平舞蹈。”(4)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3页。由于舞蹈是直接由身体完成的活动,因此,这种研究范式会遇到很多反诘:舞蹈中的身体难道不需要动用自己的感知觉功能吗?如果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活动,它又怎么能在舞蹈过程中进行自我调节?倘若承认舞蹈中的身体具有主动性,我们岂不应该修正对它的过低定位?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舞蹈研究者往往顾此失彼,无法做到“思想脉络的贯通”(5)彼得·基维主编:《美学指南》,彭锋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34页。。要走出这种困境,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否定贬抑身体的研究范式,重建舞蹈理论的基本框架。
20世纪以后,变化的机缘出现了。通过援引自然科学和生命哲学所提供的证据,众多阐释者不断清除残存的灵魂假说,强调不存在“非物质性的自我”,认为感觉、情绪、理性都是身体性过程。(6)Mark Johnson. The Meaning of the Body: Aesthetic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13.随着“反叛身体的大阴谋正在告终”(7)查尔斯·威廉·莫里斯:《莫里斯文选》,涂纪亮译,第261页。,西方舞蹈理论中出现了影响深远的身体话语。在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布洛克(Betty Block)、吉赛尔(Judith Kissell)等众多学者的推动下,身体开始同时被当作舞蹈活动的主体和客体。(8)让-雅克·库尔第纳:《身体的历史·目光的转变:20世纪》,孙圣英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页。在这个过程中,一种重视身体的研究范式逐步成型,舞蹈理论逐渐形成了连贯的话语谱系。由于上述变化的重要性还未被充分阐释和评估,本文将在身体美学视域中全面梳理相关的理论踪迹,力图说出西方学者的未尽之言。
一、揭示舞蹈与身体的关系:回到“身体-主体”
在《实用主义美学》(1992年)一书中,美国哲学家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称赞舞蹈是“最卓越的身体美学艺术”(9)Richard Shusterman.Prag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New York &London: Ro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278.。从学术史上看,这个命题的提出绝非偶然:它既是现当代西方舞蹈研究出现身体话语的表征,又是对相应学术建构的精确总结,因此,此类话语隶属于一个前后相继的理论谱系。
回顾20世纪以来的西方舞蹈研究,我们发现身体是一个占据核心地位的概念。在马丁·约翰逊、阿恩海姆、比厄斯利、布洛克和吉赛尔等人的言说中,下面的两个命题则获得反复阐释:(1)“在舞蹈中,舞蹈者的身体本身就是表演的艺术内容得以表达的媒介”(10)David Davies. Philosophy of the Performing Arts.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1:190.;(2) “舞蹈不是别的,只是人体的礼赞,生命的凯歌”(11)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随着类似言说实践的持续,身体与舞蹈的原初关系不断进入澄明之中。
1905年,邓肯(Isadora Duncun)撰写了论文《舞蹈家与自然》,认为人的身体“业已成为美的最高象征”,预言未来的舞蹈家将“用自己的身体去创造富有立体感的崇高形象”。(12)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论舞蹈》,张本楠译,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4页。1939年,约翰·马丁(Johan Martin)在其影响深远的专著《舞蹈概论》中指出:“尽管实际上,舞蹈或许通常是所有艺术中最难让人理解的,但它用作媒介的材料,即人体动作,对其周围环境的反应距离生活的经验,却比任何其它艺术都要近一些,人体动作的确正是生命的本质所在。”(13)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1954年,阿恩海姆出版了《艺术与视知觉》(ArtandVisualPerception),强调舞蹈不能由所谓的精神完成:“当舞蹈涉及整个躯体时,其主要的动作就只能由躯体最显要和最能动的中心部位去完成,而不能由神经中枢所在的部位完成。”(14)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到了1982年,比厄斯利(Monroe C. Beardsley)撰写了论文《舞蹈里发生了什么》,把舞蹈定义为“由身体活动分类生成的行动以及由身体静止分类生成的姿势”(15)大卫·戈德布拉特、李·B·布朗:《艺术哲学读本》,牛宏宝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0页。。1995年,弗朗西斯·斯帕肖特(Francis Sparshott)出版了研究舞蹈的专著《适度的步伐》(AMeasuredPace),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某一种艺术的主要媒介是在动静中沉默的身体,它就随之会被划归为舞蹈。关键的概念是‘身体’:要利用人的肉身化的重要性来克服黑格尔对此的轻视。”(16)转引自彼得·基维主编:《美学指南》,彭锋等译,第236页。接着,他又说:“舞蹈艺术是见诸运动的人体艺术。那么,人的身体是什么?舞者,无论其展现的是已编排的舞蹈片段,还是创作新的舞蹈,或是随着技法条件的发展去创新改进某一舞蹈片段,无论其是在表达他们自身,还是只是单纯地移动,这都是人在以人的方式所做的一切。”(17)转引自彼得·基维主编:《美学指南》,彭锋等译,第237页。在如此这般的表述中,身体已经成为人的同义词。
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身体话语获得了更为全面的总结。2001年,布洛克和吉赛尔发表了论文《舞蹈:具身化的本性》,开始总结上述各家之言:“我们——舞者和哲学家——将揭示作为一种在世方式的舞蹈。……它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洞见,有利于我们理解成为‘身体-主体’——身体认知者和身体表现者意味着什么。”(18)Betty Block and Judith Kissell. “The Dance: Essence of Embodiment.”Theoretical Medicine and Bioethics 22(1), 2001:5.在他们看来,人不能被强行分成身心两个部分:“如果追问我们哪个真正的自我撒了谎——在我们的身体中还是在我们的心灵中,我们或许会回答:在我们的心灵中——没有意识到以这种方式提问本身已经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假设。”(19)Betty Block and Judith Kissell. “The Dance: Essence of Embodiment.”Theoretical Medicine and Bioethics 22(1), 2001:6.在拒斥了二元论以后,选项实际上只剩下一个:我们就是能够感受、思想、行动的身体。对此大卫·戴维斯(David Davies)说得非常清楚:当舞蹈者谈论“内在自我”时,我们不一定非得把后者等同为某种非物质性的东西,相反,它完全可以用神经学术语来进行定义。(20)David Davies. Philosophy of the Performing Arts. 2011:190.由于神经系统是身体的一部分,因此,舞蹈不是某种内在自我的表现,而是“身体-主体”的在世方式。正因为“身体-主体”总在行动、感受、认识,舞蹈才会获得诞生的机缘。
如果以上论述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能否“从身体出发”重构舞蹈学呢?事实上,约翰·马丁已经演绎了建立舞蹈身体学的可能路径。在《舞蹈概论》中,他曾以调侃的口气谈到“灵魂”:“在解释布丁时,我们发现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它对‘灵魂’的作用。这就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恰当起点。把饮食当作满足‘灵魂’需要的说法已成为一种标准的笑话。”(21)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第31页。
接着,他又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实际上的灵魂,是用它的需求来统治人,是由那些有助于生命的延续并使之和谐地发挥作用的有机体来构成的。它们通常是由有时称为生命器官的东西,以及它们自己具有的、实际上独立的神经系统所组成的。”(22)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第32页。按照这种说法,“心”(生命器官)就是身体的内部构成。换言之,“身-心”问题就是“身-身”问题。在解释运动的机制时,马丁走上了从身体出发的道路:(1)“我们与外界接触的唯一可能是通过各种感觉”(23)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第40页。;(2)“当一种感觉印象停留在眼睛、耳朵和皮肤的器官中无数有意提供的接收器上时,它的迅速产生主要通过神经到达脊髓与大脑,这里就像一部精心设置的电话交换机一样,当即被送到输出脉冲之中,再通过其他神经传达到某些恰当的肌肉与腺体,以做好运作的准备”(24)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第40页。;(3)“身体是主动地运动,而无生命的物体是被动地运动”(25)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第62页。;(4)“舞蹈中的节奏,只不过是身体节奏一种演化了的变体”(26)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第69页。;(5)在舞蹈中,身体是“一个自发的表现性整体”(27)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第253页。。这种自我组织依赖复杂的身体运作:“当躯体运动神经接收到来自大脑的信号时,身体会立即做出反应,肌肉收缩。”(28)雅基·格林·哈斯:《舞蹈解剖学》,王会儒主译,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除了脊椎、心脏、骨盆、骨骼肌之外,身体还拥有大脑。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只能在身体中运作。在解释舞蹈时,他勾勒出一个明晰的身体学图式:
动作—感觉—神经—大脑—神经—肌肉—动作。
舞蹈中的人形成了一个开放而封闭的环路,这是自我组织的体系,神经中枢“接受信息和指挥一切”(29)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第555页。,就是精神所在地。它由脑和脊髓组成,可以支配整个身体。由于它是身体的一部分,因此,舞蹈中的身体是自我组织的主体:既是表现的媒介,又是表现的发起者、承担者、欣赏者。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完整的舞蹈身体学就会诞生。
作为推动西方舞蹈研究建构身体图式的关键人物,约翰·马丁的贡献在于演绎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回到身体,推动舞蹈研究踏上返乡之旅;强调身体的主体身份,从身体的主体性出发重新阐释舞蹈的建构机制。在他的论述中,“身体-主体”概念事实上已经获得了阐释:身体不是被灵魂控制的木偶、工具、机器,而是能够自我认识、自我控制、自我创造的主体。现在看来,这个思路影响了众多的西方学者,引导他们建构新的舞蹈研究范式。
二、从“身体-主体”概念出发:身体话语建构的具体路径
在引入“身体-主体”概念以后,西方的舞蹈研究开始回归现实。它的建构者不再想象精神如何创造世界,而是试图重构身体自我实现的基本方式。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种新的理论话语已经成形。
从根本上说,约翰·马丁的建构属于新的知识范式。1906年,神经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查谢灵顿(Sir Charles Sherrington)提出了“本体感受”概念,用其概括所有的感知行为,包括我们今天所称的“运动的感觉”或“运动觉”。(30)让-雅克·库尔第纳:《身体的历史·目光的转变:20世纪》,孙圣英等译,第307页。他所说的运动感非常复杂,几乎涉及身体的所有活动:“它同时涉及关节、肌肉、触觉和视觉等方面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通常被某种更加不明确的运动机能所改变,即调整深层生理节奏的(比如呼吸、血液流出等)神经植物系统的运动功能。”(31)让-雅克·库尔第纳:《身体的历史·目光的转变:20世纪》,孙圣英等译,第307页。这个发现再次肯定了身体的自我组织能力。身体不仅仅是诗意表现的对象,而且很有可能是诗意的源泉:“正是在人体这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变幻不定的土地上开启了20世纪初期的探险之旅。感觉与想象在此展开无尽的、优雅的交谈、激发出各种表演和诸多关于感觉的传奇故事,从而造就了一大批充满诗意的身体。”(32)让-雅克·库尔第纳:《身体的历史·目光的转变:20世纪》,孙圣英等译,第307页。诗意不是来自身体之外的主体,相反,身体本身就是诗意的身体。根据玛莎·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的观察,“收缩与释放”是身体运动的基本原理。以躯干为中心,收缩身体使腹部凹陷,背部隆起;释放时身体伸直,脊椎挺立。(33)茱莉娅·L.福克斯:《现代身体:舞蹈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张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23页。在她20世纪初期的实验中,身体和空间的关系获得了确定。譬如,1930年排演的《悲悼》(“Lamentation”)演绎了“困扰身体的悲剧”,展示了“在自己皮肤之内伸展的能力”,探究和见证“忧伤的周长和边界”。(34)Jonet Anderson. Modern Dance.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10:44.这是处于空间中的身体,是探测自己生存边界的有机物,本身就是具有灵性的主体。那么,身体应该如何回应世界呢?她写道:“舞者的艺术建立在倾听的态度上,用他的整个身体去听。”(35)Michele Root-Bernstein, Robert Root-Bernstein and Martha Graham. “Dance, and the Polymathic Imagination: A Case for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r Universal Thinking Tools?” Journal of Dance Education 3(1),2003:17-18.听的对象首先是自然,是风、花、树,是大地的话语。在她的戏剧中,大地不再是逃离的对象,而是身体回归的目标:“格雷厄姆之前的舞台舞蹈技术拉长身体,尽可能地使身体向上,芭蕾就是这样。她则钟情地板和大地——坐在上面,落向它,触及它。”(36)Jonet Anderson. Modern Dance. 2010:43.舞蹈中的身体不再向想象中的天堂飞升,而是表达对家园的依赖和爱。当身体舞蹈时,它展现了它与大地的原初关系。每当它试图向上飞升,下落运动都会随即产生,同样,随着身体不断落向地面,它又会不断反弹并站立起来。这就是多丽丝·汉弗莱(Doris Humphrey)所说的“下落与恢复”原理。在舞蹈的过程中,身体每个部位的运动都会带动下个部位的运动,而脊椎则是整个运动的轴线和传动带。至于哪个部位是轴线外的中心,舞蹈家的观点并不相同,邓肯等人重视上半身,认为“一切真实身体表达的发生位于心脏一带”;格雷厄姆则强调骨盆才是身体的重心,是原动力的来源。(37)让-雅克·库尔第纳:《身体的历史·目光的转变:20世纪》,孙圣英等译,第308页。不过,两种说法并无本质区别:无论是心脏,还是骨盆,它们都是身体的构成。有关二者的地位之争最终凸显的是身体。当人们说脊椎、心脏、骨盆是身体运动的轴线和中心时,他/她所强调的恰恰是:身体并不是可以随意操纵的傀儡,而是一个自我组织的有机体:“‘我并不是在使用我的身体,而就是我的身体’,我呈现在我的舞蹈之中。”(38)彼得·基维主编:《美学指南》,彭锋等译,第237页。身体不是心灵的对应物,而是拥有心灵的主体:“头部和颈部为精神区域,躯干为精神-情感区域,臀部和腹部为物质区域。此外,胳膊和腿是人体探测外部世界的接触器——附着于躯干的手臂具有一种精神-情感特征。身体的每一区域都可以进一步分成三个部分。”(39)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第556页。这种定位的细节或可商榷,但它的总体思路符合当代人学的基本走向:“思想的具身化和身体的具脑化(embrainment)。”(40)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86.精神并非隶属于神秘的独立实体,而是身体的活动功能。依靠感觉和意识,舞蹈中的“身体-主体”可以自我控制:“舞蹈演员主要是通过对肌肉的松紧程度的感觉,以及可以用来区别垂直方向的稳定性和前倾、后仰的危险性的平衡觉,而创造了自己的作品。”(4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第559页。一个钟爱舞蹈的人,其身体感觉是强烈而完全的,渗透于每一处随意肌,遍及指尖、喉咙和眼睑。“舞蹈欣赏的中心是具有体积和重量、柔顺和抵抗的身体,对它们的肯定和否定;舞蹈的荣耀与悲悯都建立在它是运动与被运动的人的身体之上。”(42)彼得·基维主编:《美学指南》,彭锋等译,第238-239页。符合这些特征的艺术活动构成一个体系:从原始巫仪到由此分离出来的戏剧和舞蹈,乃至现代行为艺术,呈现于观者面前的活动网络都直接与身体相关;身体出现于自己的作品中,构成自己作品的一部分。舞蹈中的人既是身体-认知者,又是身体-表现者。(43)B. Block and J. Kissell. “The Dance: Essence of Embodiment.” Theoretical Medicine and Bioethics 22(1),2001:5-15.在舞蹈时,所有的感受都会被整合到身体图式之中,因此,演员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动作。他/她可以聆听自己内在的生理节奏,谋划表演的总体过程。质言之,他/她是“身体-主体”,而舞蹈则是自我组织的一种方式。由于舞蹈中的“身体-主体”同时是艺术家、艺术媒介、艺术品,因此,上述形象-动作就成形为一个真正的视觉艺术品。推论至此,从“身体-主体”概念出发的舞蹈美学已经构造出完整的阐释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新型舞蹈美学已经落实到实践维度。在现当代舞蹈理论中,“身体-主体”概念早已经出现。它虽然首先属于学术空间,但并非纯粹思辨的产物:它是“身体-主体”自我认知、自我肯定、自我表达的产物。当邓肯呼吁超越传统舞蹈的程式时,“身体-主体”已经开始说话:“我们的儿童为什么要卑躬屈膝地去跳这种装模作样、奴性十足的小步舞呢?为什么要稀里糊涂地转来转去,跳那种自作多情的华尔兹舞呢?不如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大步行进,欢腾跳跃,昂首张臂……”(44)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论舞蹈》,张本楠译,第157页。这是现代舞的宣言,更是“身体-主体”的心声。觉醒后的“身体-主体”不希望自己继续被规训,不愿意总是被已有模式所限制,而是渴望设计、展示、演绎更加自由的动姿。20世纪初,大批舞蹈家脱下了紧身胸衣,穿上了灯笼裤,解放双腿和躯干,演绎“新女性”的精神面貌。她们开始“在舞蹈中采用区别于芭蕾舞和歌舞杂耍表演的方式”,“将身体动作从芭蕾舞僵化的技巧和歌舞杂耍浮夸的表演风格中解放出来”。(45)茱莉娅·L.福克斯:《现代身体——舞蹈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张寅译,第15页。在这个过程中,海伦·塔米里斯(Helen Tamiris)曾经尖锐地嘲讽足尖练习:“用趾尖跳舞……为什么不用手掌跳舞呢?”(46)茱莉娅·L.福克斯:《现代身体——舞蹈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张寅译,第21页。她不愿意在舞蹈中保持队形,在舞台上又异常活跃,因此又被称作“野贝克尔”(Wild Becker)。(47)塔米里斯原名海伦·贝克尔(Helen Becker),后来邂逅一名南美洲作家,开始使用现在的名字。这个名字源于一首讲述古代波斯女王的诗:“你便是塔米里斯,冷酷的女王,扫除一切障碍。”(茱莉娅·L.福布斯:《现代身体——舞蹈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张寅译,第20-21页)到了20年代中期,众多美国舞者放弃芭蕾舞而转向现代舞。据费思·雷耶·杰克逊(Faith Reyher Jackson)回忆,现代舞光着脚跳舞的方式吸引了那些买不起足尖鞋的贫困舞者。(48)茱莉娅·L.福克斯:《现代身体——舞蹈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张寅译,第21页。这只是表层原因,真正的动力来自于主体性的身体。身体总是处于规训-反规训的张力中。它既是规训的始作俑者,又是被规训的对象。此刻,身体的身体性就会绽露:每个身体都在宇宙中占据独一无二的位置,因而不可能完全被他者同化。身体是充满可能性的密室,是主体性诞生的地方,是希望的真正故乡。这正是大批舞蹈家所揭示的原初事实。
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个原初事实获得呈现的过程中,女性身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是解放的对象,更是解放的主体。由于性别的等级制,女性身体曾经备受压抑,但也因此成为“她者”:一方面,女性被视为男性的副本(49)自古典时代以来,身体就被理解为两种性别之一种(非男即女),但只能拥有单一的性。男性和女性被理解为有相同的性器官,尽管女性版本是男性的倒置。因此,阴道是阴茎的反转,卵巢是内部的睾丸,诸如此类。参见约翰·罗布:《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吴莉苇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87页。;另一方面,她们又被当作危险的源泉(与自然类似)。这是一种具有吊诡意味的定位。它意味着女性总是生存于悖论之中,被各种矛盾挤压。女性身体因此成为不同力量博弈的场所。当理想的光照降临时,后者会成为反抗力量的发源地。对于女性舞者来说,这是时刻会起作用的基本逻辑。在她们的推动下,“舞厅变成了公共舞台”,“为探索身体动作提供了场所”。(50)茱莉娅·L.福克斯:《现代身体——舞蹈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张寅译,第18页。譬如,随着“跳舞疯”(dance madness)的流行,一种新的精神诞生了:主动、参与、分享。它体现于现代舞之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表演风格:现代舞演员“绝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一台在空间维度被预先设计好的用于制造产品的机器”,“而是坚持将其永远看作身体自身”。(51)茱莉娅·L.福克斯:《现代身体——舞蹈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张寅译,第26页。“身体自身”这种说法意味深长。它是作为身体的身体而非对象化了的身体。它提供尺度,发出召唤,表达吁求。这岂不是暗示身体的主体身份吗?如果身体本来就是主动之物,那么,对它的规训、压抑、束缚就是反身体的实践。在格雷厄姆1930年表演的独舞《悲歌》(“Lamentation”)中,这个主题已经获得了充分阐释:
一名孤独的舞者坐在长椅上,身体被一套筒状的衣服所包裹,四肢被紧紧地束缚,头部也被遮盖着,只露出脚和脸。躯干的动作若隐若现,如胚胎般地蠕动。舞蹈透露出一种悲伤的情绪,并将这种情绪注入到被束缚的身体做出的紧张而充满渴望的动作中。
身体为何悲伤?它渴望什么?答案几乎不言而喻。对身体的遮蔽、规训产生了切己之痛,引发了延续至今的悲伤。没有反抗,就没有自由。自由是现代舞的基本法则,也是“身体-主体”至深的生存冲动。(52)茱莉娅·L.福克斯:《现代身体——舞蹈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张寅译,第26页。它引导舞蹈家演绎“真实的舞蹈”:“‘真实的舞蹈’重视最美的人类形体,而‘虚假的舞蹈’则与此相反,也就是说,它的动作表现的是畸形的人体。”(53)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论舞蹈》,张本楠译,第87页。真实的舞蹈属于“身体-主体”。它是“身体-主体”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每个“身体-主体”都在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都在编织以自己为中心的文本。身体的身体性体现为世界的世界性。世界有其边界,这边界就是个体生命的外围。后者不断延展、分叉、交织,成形为伸缩不定的动态网络。无论如何,最外部的疆界不能是皮肤,而是行为体系的末端。世界之溃散意味着身体之殇。身体总会看护自己世界的边界。这吁求源自身体的身体性。它并不会由于性别差异而被完全遮蔽。女性身体也是自己世界的看护者。1935年,格雷厄姆创作了独舞《边境》(“Frontier”),演绎了这个主题。舞蹈开始时,她单腿撑在一个围栏上,侧脸对着观众,眼睛注视着侧台。接着,宣示主权的动作依次显现:“她首先宣示对围栏的所有权,接着在围栏的前方描绘了一个空间,然后她以一种将一切据为己有的目光环顾四周,最后自信地坐回到围栏上。”(54)茱莉娅·L.福克斯:《现代身体——舞蹈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张寅译,第51-52页。这类动作虽然算不上十分新颖,但再次表现了身体的主体性。
从理论到实践,西方的舞蹈艺术已经演绎了回归“身体-主体”的基本逻辑。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意味着理想的光芒已经照进现实。沿着上述线索前行,对身体图式的建构将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推动艺术研究回到自己的本体和起源。
三、二元论的遗痕:未完成的身体话语建构
随着“身体-主体”形象的完整显现,舞蹈身体学也展示了其基本框架。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后者的建构并未形成破竹之势。由于西方文化总是把人分成身体和精神,因此,二元论已经深入到言说者的内心深处。在相关话语的影响下,试图引入“身体-主体”概念的美学家经常会陷入自我矛盾状态。
在约翰·马丁留给我们的文本中,这种矛盾依然留下了清晰的踪迹。虽然他已经展示了从身体出发的可能性,但却没有建构出连贯的话语。譬如,他曾经使用“身体执行内心命令的努力”(55)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第40页。之类表述,多少重蹈了二元论的覆辙:难道内心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吗?如果不是,岂不是必须援引精神主体概念?显然,马丁的论述潜藏着致命的悖论。由于这种不彻底性,他受到了后来者的批评。在《论约翰·马丁的舞蹈理论》一文中,朱迪思·B·奥尔特(Judith B. Alter)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尽管马丁的措辞表明,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必须纠正通常流行的那种身心分离的概念,但他在将心当作理性的或者理智的能力,而将身体当作舞蹈家的工具时,还是将两者的功能进行了区分。他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潜在的矛盾。”(56)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第357页。接着,更尖锐的追问出现了:所谓“身”,就是位于他或她的头脑之下的某个部位吗?或者说,“身”指的是整个人,及其整个肉体和个性吗?马丁三番五次地提到社会对“下贱”的身体之感受。尽管期望对“身”的欣赏有所改变,然而,他在多次将身体当作舞蹈家的工具时,曾宣称舞蹈家在运用自己的身体去跳舞,便将其身体对象化了,这就意味着心高于身这种带有等级制度的审美标准,以及“心对物”的垄断。(57)约翰·马丁:《舞蹈概论》,欧建平译,第357-358页。
这追问针对的不仅仅是马丁,而是西方曾经长期流行的二元论。当舞者活跃于大地之上时,牵引他/她的似乎是战胜重力的意志。后者可能来自于更轻盈的存在,一种与血肉之躯形成鲜明对照的事物。人们称之为灵魂、心、自我,想象它可以驱使身体。事实上,在进行具体论述时,马丁已经极力避免使用灵魂范畴。相比于马丁,邓肯的说法更容易招致批评:“不难设想,一个舞蹈家在经过长期训练、苦修和灵感启发之后也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他认识到自己的身体只不过是供灵魂表现的工具罢了,这时,他的身体便会按照一种内在的旋律舞动,而表现出另一个更为玄妙的世界。”(58)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谈艺录》,张本楠译,第8页。她眼中的灵魂“比X光更飘然”,可以“会使身体化作明亮的云雾般的东西。”(59)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谈艺录》,张本楠译,第8页。当灵魂完全掌控身体,后者就会变得轻盈,可以翩翩飞翔到神界。吊诡的是,邓肯本人后来几乎完全否认了灵魂概念:“我们每个人不过是熔炉里的一颗星火,它燃着,我们便有形有体;它熄灭了,我们便化为乌有。此外,我们还会有什么呢?”(60)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谈艺录》,张本楠译,第136页。当她习惯性地说出灵魂一词时,后者的所指不过是一种残留物或遗痕。它仅仅是习惯用法或者隐喻。这个残余物依然受到主流信仰和民间意识形态的支持,可以衍生出众多温和的解释模式。在很多时刻,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某种假想之物,而身体则被当作“一种和谐的、得心应手的工具”(61)伊莎多拉·邓肯:《邓肯谈艺录》,张本楠译,第46页。。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舞蹈理论就无法做到“思想脉络的贯通”(62)弗朗西斯·斯帕肖特:《舞蹈哲学:动静中的身体》,转引自彼得·基维主编:《美学指南》,彭锋等译,第277页。。事实上,这不是少数人的错误,而是一种至今仍在延续的思维模式。除了邓肯和马丁之外,格雷厄姆也没有完全超越二元论。谈论音乐的影响时,她曾经说:“我现在用身体去感受,正如我用心灵去倾听。”(63)Michele Root-Bernstein, Robert Root-Bernstein and Martha Graham. “Dance, and the Polymathic Imagination: A Case for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r Universal Thinking Tools?” Journal of Dance Education 3(1),2003:19.甚至,一些较为年轻的学者也经常重蹈覆辙。在《舞蹈中发生了什么》一文中,比厄斯利写道:“身体的活动即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基本的行动,是所有其他行动的基础,至少就我们所说而言如此,因为尽管有纯粹的精神行动,并不会劳烦肌肉,但这并不是舞蹈的素材或原材料。”(64)Monroe C. Beardsley.“What is Gonging on in a dance?” Dance Research Journal 15,1982:32.此处,“纯粹的精神行动”这种表述引人遐思,似乎暗示了非身体性自我的在场。类似的问题也出现于弗朗西斯·斯帕肖特的《适度的步伐》中:“跳舞一般来说是跳一个舞,至少总是跳一种舞,并且舞蹈一般被表述为或适合表述为步法、姿势、手势、连续动作或其他类似的片段,虽然如此,舞者终归是而且被看作一个在运动中的活跃的人。舞是人做的事情,舞者运动中的身体也必须被视为在各种可能状态中都被看作肉身化的人的身体。”(65)转引自彼得·基维主编:《美学指南》,彭锋等译,第242页。此处,“人的身体”这种表述显然会引发下面的联想:人多于身体。也就是说,论者可能不自觉地重蹈了二元论的覆辙。
到了21世纪,这种状态依旧延续下来。在2001年发表的《舞蹈:具身化的本性》一文中,布洛克和吉赛尔写道:“大多数人不允许他们的身体思想,事实上,我们从小就被训练去压抑具身性感知。我们被告知,释放身体记忆或允许整个身体做行动, 这在文化上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重视理智和惯例胜过一切,被训练去压抑身体想去体验的体验。”(66)Betty Block and Judith Kissell. “The Dance: Essence of Embodiment.” Theoretical Medicine and Bioethics 22(1),2001:10.这种言说显然具有悖谬意味:言说者不自觉地假定了某个高于身体的我;他们被自己思想中的残余物所捕获。那么,怎样才能清除这些残余之物?不能想象擦去或清除等物理学动作。因为,这些残存物并非顽固的精灵,而是一些功能性的存在。当人们遇到当下身体学无法解释的现象时,他就会求助于这些古老的范畴。就像古代的神祇,它们是一些功能(如理性思维)的象征。只有证明这些功能属于身体,陈旧的灵魂观念才能最终进入历史。
正是由于二元论模式未被克服,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流舞蹈研究尚未完成身体舞蹈学的建构,许多研究者依然满足于进行情绪化的鉴赏以及玄虚的解释。通过邓肯、马丁等人的话语实践,下面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如果不彻底超越身心分裂的图式,那么,舞蹈的身体话语建构就不可能自圆其说。
从根本上说,本文提到的西方舞蹈研究已经建立了前后相继的身体话语,演绎了艺术理论回归“身体-主体”的路径。虽然它还存在不彻底之处,但已经初步揭示了下面的命题:(1)能动的身体是舞蹈活动的承担者;(2)原初的舞蹈是身体的实践,是身体建立世界的一种方式;(3)通过舞蹈,“身体-主体”自我观照、自我表达、自我照料。由于残存的二元论观念尚在拖滞正在发生的转向,许多学者在言说上述命题时呈现出明显的犹豫之态,遮蔽-敞开的冲突形成了绵延至今的张力。为了克服这种欠缺,舞蹈研究必须更加彻底地回到“身体-主体”。作为“最卓越的身体美学艺术”,它理应率先完成这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