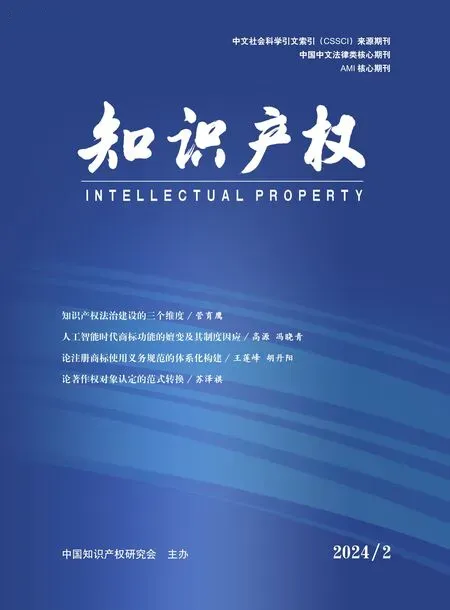人工智能时代商标功能的嬗变及其制度因应
高 源 冯晓青
内容提要: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商标制度的重要价值目标。人工智能通过精准营销、体验式消费、替代决策等形式介入消费活动,在引发消费行为转向的同时逐渐动摇了以识别来源功能和广告功能为支柱的商标制度。对商品来源的抽象与对背景信息的简化本是商标的独特优势,却在与具有强大信息整合能力的人工智能的比较中日渐显现出信息遗漏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商标具有财产属性,其使用能够刺激消费,但由于智能消费逐渐导致商标应用程度的降低,其广告效果也将有所削弱。因应人工智能时代商标功能的嬗变,商标制度应巩固其维护信息分配正义与竞争秩序的价值目标;强化对售后混淆的防范,全面保护识别来源功能;有限拓展反淡化规则的适用,在对广告功能的保障中实现对商誉的维护。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在丰富社会生活、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对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2023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促使人们将目光集中到其对著作权法①参见焦和平、梁龙坤:《人工智能合成音乐的著作权风险及其化解》,载《知识产权》2023年第11期,第103-125页;郑飞、夏晨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著作权困境与制度应对——以ChatGPT和文心一言为例》,载《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年第5期,第86-96页;冯晓青、李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著作权客体中的地位》,载《武陵学刊》2023年第6期,第46-55、66页;杨利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探究》,载《现代法学》2021年第4期,第102-114页。及专利法②参见刘友华、李扬帆:《ChatGPT生成技术方案的专利法保护探究》,载《知识产权》2023年第7期,第76-89页;杨利华:《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可专利性及其制度因应》,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2期,第346-364页;关儒、黄玉烨:《人工智能算法的专利适格性问题研究——基于算法特征的讨论》,载《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年第2期,第88-96页;冯晓青、郝明英:《人工智能生成发明专利保护制度研究》,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143-152页。的影响上,却鲜有研究关注到商标制度可能遭受的冲击。③自2019年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围绕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议题已开展多次对话会,内容涵盖生成式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版权保护、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认定与权利归属等热点话题。但是,相较于著作权与专利权,有关人工智能之于商标制度潜在影响的讨论不够充分。实际上,在商标产生、使用与保护的各个环节,人工智能的影响均已初见端倪:在商标设计与注册环节,商标申请人可以借助人工智能进行标记样式检索及设计④See Sonia K.Katyal & Aniket Kesari, Trademark Searc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Role of the Private Sector, 35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501 (2020).;在商标审查环节,商标行政管理部门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审查,能够提高行政效率⑤参见张惠彬、王怀宾:《人工智能驱动知识产权审查变革:技术逻辑、价值准则与决策问责》,载《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1年第4期,第100-103页。;在商标侵权认定中,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及时侦测侵权行为,并替代完成标志相同或近似的对比⑥参见冯晓青:《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法》,载《数字法治》2023年第3期,第37-38页。。作为延伸人类能力的有效工具,人工智能对商标制度运行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上述现象仅是人工智能影响商标制度的次要方面,尚未触及制度之根本。商标是市场的表征⑦刘春田:《商标概念新解——“商”是民法学上的又一发现》,载《中国知识产权》总第175期,http://www.chinaipmagazine.com/journal-show.asp?id=3770.,商标法规范的是市场主体的行为,调节的是市场利益,因人工智能介入市场而将要引发的制度变革,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主要方面。在商标所关涉的诸多市场主体中,经营者受到的影响最为直观。据统计,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最常见的应用场景就是营销和销售,⑧Michael Chui, The State of AI in 2023: Generative AI's Breakout Year, August 2023,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quantumblack/our-insights/the-state-of-ai-in-2023-generative-AIs-breakout-year.在市场策略制定、商品或服务⑨为简化论述,后文所使用的“商品”一词涵盖了“服务”。的推广方面均有突出表现。与此同时,智能营销所面向的主体——消费者行为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工智能辅助甚至替代消费者完成“标—品”⑩参见胡进功:《辨识商标“四体”及其意义》,载冯晓青主编:《法大知识产权评论(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7-218页。的对应,使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消费”决策愈加显现出高度的人机交互属性,而这也将成为人工智能可能颠覆商标制度的关键所在。
之所以将对消费者的影响程度作为人工智能时代商标制度动摇与否的判断标准,是因为消费者自始即参与商标保护正当性的建构,是商标制度得以稳定运行的根基所在。首先,消费者是赋予商标价值的主体。商标法保护的不是单纯的符号组合,而是对人类具有意义、能够为主体提供价值的财产。商标的价值需要得到人们的评价和接纳,服务于人们获取商品信息的需要,并在人们的使用中得到发展,这些都指向了商标所服务的主体——消费者。商标的识别商品来源价值只有在消费者接纳和承认商标的来源标识地位后才能确立,商标所具有的广告宣传价值依赖于消费者对其所承载的精神意义的认同。消费者虽然并非商标的创造者,却是商标价值的判断者和商标意义的缔造者,动态参与商标价值的建构。一旦消费者对标记的评价标准或认可程度发生改变,商标价值也将随之变化,通过法律制度对商标予以保护的必要性就需要重新认定。
进而,保护消费者利益是商标制度设计的基础原则。“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是商标权的起点,也是其终点。”⑪黄汇:《商标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保护——以“微信”商标案为对象的逻辑分析与法理展开》,载《法学》2015年第10期,第76页。商标制度所维护的消费者利益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第一,消费者的识别利益。“商标是意在向消费者快速传递信息的区分工具”,识别商品来源的能力则“是商标制度的根本意义所在”。⑫孔祥俊:《商标法:原理与判例》,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58页。因此,保障消费者能够从商标中获取准确的商品来源信息是商标制度的主要目标,以显著性为基础的商标权客体规则和以混淆理论为支柱的商标侵权规则,均旨在维护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保障消费者的识别利益。第二,消费者的信息公平利益。消费活动存在信息分配不公的现象,为践行公平原则,商标制度需要促进商标信息的分配正义。一方面,相较于消费者,经营者在初始信息总量上具有优势地位,商标作为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传递信息的媒介,有义务消除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平等,当商标成为经营者滥用信息优势地位的工具时,如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标识,商标法将不予保护;另一方面,因能力和资源禀赋、所处环境和信息获取渠道等方面的差异,消费者群体内部存在信息获取能力的不平等,商标虽然不能从根本上予以消除,但为所有消费者提供了平等、公开的获取商品信息的渠道,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信息公平。第三,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商标法中存在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只有充分保障消费者福利,才能实现在保护一般社会公众利益基础之上的更广泛的公共利益。⑬参见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8页。因而,减少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增进其收益成为商标法划定其边界的必要遵循。
综上,维护消费者利益是商标法的重要使命,消费者的观念和行为因此成为商标制度演进的“柴薪”,人工智能引发的智能消费能否点燃商标制度的“火焰”,还需要探寻商标功能这条“商标观念嬗变的暗线”⑭杜颖:《社会进步与商标观念:商标法律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商标制度的发展与商标功能的演进相伴相生。商标具有识别来源功能,是消费决策的工具,为消费者提供必要的交易信息;商标又具有广告宣传功能,是商誉的象征,对消费者产生持久的吸引力,两大功能相互融通,致力于实现商标法防止市场混淆与保护商誉的制度目标⑮同注释⑫,第39页。。对于人工智能给商标法带来的挑战,有论者认为“目前没有理由重新考虑商标的功能或重新定义法律概念”,⑯WIPO, WIPO Conversat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hird Session, 8 January 2021, p.12,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docs/en/wipo_ip_ai_3_ge_20/wipo_ip_ai_3_ge_20_inf_5.pdf.在这次对话会上,与会人员还就人工智能对非视觉商标的识别、元标识、人工智能推荐错误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也有观点指出未来作为“数字消费者”的人工智能将大幅度削弱商标的功能和作用,足以引发“商标之死”⑰See Michael Grynberg, AI and the "Death of Trademark", 108 Kentucky Law Journal 199 (2019).。可见,对人工智能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商标制度的分歧直指商标的本质功能,对该问题的回应也应当以此为起点。尽管技术发展尚需时日,但基于人工智能介入消费活动的现实进行必要预想,将有利于引导商标制度的发展方向。本文试从人工智能对消费决策的影响展开,分析智能消费决策对商标功能带来的挑战,并提出商标制度因应的建议。
二、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消费决策的表现与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对现有消费决策模式的冲击是商标功能转变的事实基础。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主要通过精准营销、体验式消费、替代决策三种方式参与消费活动,将以消费过滤器和替代决策者的角色引领未来的消费活动。
(一)人工智能介入消费决策的主要方式
1.精准营销
市场竞争带来了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同时促使消费活动向个性化、多样化的方向转型升级。消费者对商品与需求契合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给营销活动提出了精准服务的新命题。现代社会中消费观念的快速变化和影响因素的复杂化进一步强化了消费需求的个性化特点,给经营者的市场预测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此时,若固守“基于‘定义目标消费者群体’的粗放式市场营销行为”,将无法对个性化需求作出有效回应。⑱参见阿里云研究中心:《AI时代零售业的智能变革》,载《大数据时代》2018年第12期,第15页。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深度结合,有助于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建立起精准对应关系,⑲参见张昕蔚:《数字经济条件下的创新模式演化研究》,载《经济学家》2019年第7期,第35页。给供需双方都带来精准营销的福利。首先,人工智能增强了经营者的分析能力。依托于人工智能,经营者得以获取与消费者行为相关的海量数据,并结合人工智能的初步分析结果预判消费趋势和制定营销策略,从而提升营销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例如,全球知名的亚马逊公司已开始借助人工智能预测每天超过4亿件商品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进行供应链的优化,大幅提升了消费体验。⑳Amazon, 5 Ways Amazon is Using AI to Improve Your Holiday Shopping and Deliver Your Package Faster, 27 November 2023, https://www.aboutamazon.com/news/operations/amazon-uses-ai-to-improve-shopping.其次,人工智能加快了对消费者需求的响应速度。与传统营销依赖于历史数据处理,往往难以解决初次搜索的“冷启动”问题相比,人工智能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活动即时且高效,用于个性化推荐的信息将更具时效性和多维性,[21]参见李欣琪、张学新:《人工智能时代的个性化推荐》,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第91-94页。有利于提升用户黏性。最后,人工智能促进了生产端、销售端与消费端的充分对应。对生产端及销售端预测消费需求精准度的提高,将大大减少生产或营销资源的浪费;人工智能又助力消费端,帮助锁定最符合消费习惯和预设条件的目标商品。供需双方由此建立起紧密而又稳固的联系,在精准营销中实现有机协同。
2.体验式网络消费
集成于人工智能的视觉识别系统、语音识别系统、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赋能新零售,对传统商业模式带来了颠覆性冲击。[22]参见徐印州、林梨奎:《新零售的产生与演进》,载《商业经济研究》2017年第15期,第5-7页。经营者在线下零售中的服务能力及消费者获取销售服务的均衡性与消费需求扩张的速度不能完全匹配的局限性,[23]参见阿里研究院:《C时代 新零售——阿里研究院新零售研究报告》,2017年3月发布,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1703200421508129_1.pdf?1509036166000.pdf.使得电子商务得以飞速发展。据统计,2023年我国实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已达13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7.6%。[24]参见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2023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发展报告》,载全国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网2024年1月31日,https://dzswgf.mofcom.gov.cn/news/5/2024/1/1706682497854.html.不过,尽管势头猛烈,电子商务因不能提供对商品或服务的直观体验这一先天劣势,在与线下零售的竞争中存在难以突破的上限。新型智能视听技术的出现正当其时。在人工智能的助力下,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各类智能终端远程检验生产者所提供的商品信息的准确度。电子商务的时空便利性在提供亲历性消费体验的过程中被进一步放大。正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组织的第二届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会议上所指出的,“人工智能助理、搜索引擎、客户服务机器人和线上市场在塑造消费者决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和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正在改变商品和服务购买流程的本质”。[25]WIPO, WIPO Conversat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Second Session, 21 May 2020, p.12,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docs/en/wipo_ip_ai_2_ge_20/wipo_ip_ai_2_ge_20_1_rev.pdf.可以预见,由人工智能引领的体验式网络消费必将继续参与消费活动的塑造。
3.替代决策
智能消费时代,具有强大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的人工智能成为消费者的重要辅助工具,将显著提升消费者收集信息的效率。以此为基础,人工智能将结合对消费者的历史消费数据及个人偏好的科学分析,精准地确定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范围,进而完成“替代决策”,即人工智能将代替人类出现在消费活动中,完成商品挑选及购买的全过程。近年来,在需要定期更新的日用消耗品的消费场景中,一些大型电商平台陆续推出自动购买服务,虽然目前还依赖于用户对商品信息、购买周期等数据的预先输入,但已足以表明替代决策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而是即将到来的现实。在物流、仓储等供应链产业链的支撑下,人工智能有望将在消费者尚未决策或授权决策时就提前分析并做好响应消费需求的一切准备,推动现有的“先购物后发货”(shopping-then-shipping)消费活动向“先发货后购物”(shipping-then-shopping)转变,自动执行(automatic execution)将成为智能时代消费的主要形式之一,[26]See Lee Curtis & Rachel Platts, Trademark Law Playing Catch-up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PO Magazine (June 2020),https://www.wipo.int/wipo_magazine_digital/en/2020/article_0001.html.消费活动的效率将随之发生革命性的突破。
(二)人工智能对消费决策的影响
1.“消费过滤器”的有限冲击
面对大量源自不同生产者且质量与性能各异的商品,消费者在锁定目标时,通常要借助其他主体或工具,在此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市场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以各个时期影响消费的主导性因素为线索,可以将人工智能出现之前的消费决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被称为“维多利亚式消费”,其特征是“店员推荐”,表现为店员作为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过滤器”发挥作用,店员的推荐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消费者的决定。[27]Ibid.进而,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在“使用功能层面的可替代性范围不断扩张”,[28]马辉:《消费决策机制变迁视角下的直播营销法律规制》,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2期,第123页。消费者“越过”柜台进行自主挑选的动机日益提高,商标成为销售者与消费者直接对话的重要工具,“品牌推荐”取代“店员推荐”成为第二阶段消费活动的典型特征。互联网的出现则带来了第三阶段的消费革命:表达的自由化导致信息总量指数级增长,交流效率的提升使消费者群体内部的评价逐渐超越了销售主体及品牌的作用,此时消费决策呈现出“消费者自推荐”的特点。实际上,消费者内部的相互推荐以店员、品牌、广告、社交评价等多重因素为基础,过去与现在所有的消费决策影响因素均内化于消费者自推荐机制间接发挥作用。
人工智能最初也只是消费者自推荐模式中众多的辅助因素之一,但数据、算法和算力这“三驾马车”带来了消费活动效率的质变,并且在促进信息披露和传输过程中,推动消费者与商品之间建立起直接互动关系,消除供需之间的隔阂,显著拓宽了远程网络消费的空间。因此,人工智能相较于其他工具或手段的地位日渐突出,甚至大有直接超越消费者自推荐机制而占据消费影响因素中主导地位的趋势。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是否会对第三阶段的消费决策模式造成根本性冲击,将人们引入新的消费阶段?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工智能对消费活动的影响尚限于“消费者+人工智能”人机协同模式的框架之下,消费者在决策权重上享有绝对优势,人工智能则相当于站在网络柜台后的“店员”,即作为最先接触商品的角色代替消费者完成最初的搜寻和推荐工作;因在响应速度和准确度上的良好表现,人工智能也可以被视为经验丰富的消费者同盟。但无论如何,人机交互场景下的人工智能,本质上只是服务于消费者获取信息的辅助手段,不足以导致“消费者自推荐”的根本转向。
2.主体性危机中的消费革命
作为“消费过滤器”的人工智能固然尚难以催生一场消费革命,但替代决策的深入应用或许会带来转折。智能时代的消费决策将实现从“消费者自推荐”向“智能推荐”的转型,届时人工智能对消费决策的影响程度将超过消费者自身,而这将极大地冲击人的主体性。从历史上的“维多利亚式消费”到大型市场消费再到目前的网络消费阶段,尽管存在诸多干扰因素,但消费者的自主性从受制于店员推荐发展到现阶段的自主性高峰,整体上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预想中全面应用人工智能的消费时代,消费者却面临着丧失决策权的危机,以至于仅剩下“是否授权人工智能替代决策”的权利。如果认为“维多利亚式消费”阶段的自主性不足是受制于消费能力的被动结果,未来受智能推荐操控的消费者则不能以此为自己开脱,因为彼时其完全具有自主决策的能力,是自愿放弃决策并主动接受算法结果。最终,人工智能的全面“入侵”将使“决策权威从人类转为算法”,人工智能将成为重要的决策主体。[29]参见王锋、刘玮:《人工智能参与决策过程的挑战与图景》,载《求实》2023年第3期,第24页。
目前人工智能在被应用到消费、医疗、司法、社会管理等各类决策场景时都以“人”的决策权重的绝对优势为前提,纯粹人工智能决策的时代还遥不可及,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主体性危机并非危言耸听。例如,消费者之所以购买某件奢侈品,很可能只是因为人工智能经过对消费能力和消费可能性的精准计算后,在工资结算日进行了推荐,而对这一件非必需品的消费很可能导致消费者入不敷出。再如,消费者在“选择”人工智能推荐列表中的商品时,可供选择的范围实际上早已被预先压缩,站在人工智能的角度上看,实质决策已经完成,只需要人类在推荐列表内完成形式点选。[30]“亚马逊Alexa这类人工智能应用在消费者购物搜索时平均会推荐三种产品。消费者并不了解市场上所有产品,因此即使最终亲自作出购物决策,他们面对的产品选择相对有限。人工智能应用再度成为消费者认牌购物的过滤器。”同注释[26]。技术狂热者在鼓吹科技神力之时,往往容易忽视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工智能提线木偶的事实,当人工智能在消费中主要担任替代决策者角色之时,消费者将发生决策自主性的全面倒退,而这无疑将深刻影响市场行为与市场利益关系,足以预示着全新的消费时代。
三、人工智能时代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危机
通说认为,识别来源功能是商标“最初始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甚至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商标所具有的唯一功能”。[31]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第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52页。长期以来,商标都作为最主要的信息来源在营销活动中发挥作用。人工智能介入消费活动之后,人们出于惯性思维仍将其视为次于商标的信息搜集工具,却忽视了人工智能对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冲击甚至可能产生撼动商标制度正当性的后果。
(一)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原理与局限性
1.对商品来源的抽象
商标制度的演进历程表明,识别来源功能是在完成对商品来源的抽象之后才成为商标的本质特征的。在生产力尚未高度发展的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商标雏形的所有权标记、质量认证标记等向消费者提供的是生产者所属行会、地区等具体信息,只是行会或政府的监管手段,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商标。随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市场上商品总量的扩张,虽然消费者的可选范围因此扩大,但寻找预期商品的难度也随之增加。此时商品标识开始肩负起新的职责,即用于表彰经营者身份,传达其对维持质量一致性的承诺。[32]参见[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中译本第2版),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从具体的商品产地或管理主体到商品标记所有人,从对商品的具体属性的确证到对标记所有人的信赖,商标识别来源功能是在对来源的抽象过程中产生的,自始就带有一定的抽象意义。
在商标保护初期,行政机关或法院对商标使用人与商品具体来源的准确对应有严格的要求,商标与具体来源之间的关系依然十分紧密。商标许可与转让的实践,促使识别来源功能最终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蜕变。随着商品生产者与使用商标的主体出现分离,消费者所关注的重心也不得不“从相同的商标所表彰的商品应有相同来源向相同的商标所表彰的商品应具有相同的品质方面倾斜”。[33]同注释[31]。商标日渐转向对负有质量担保义务之主体的抽象来源的指示,这既可以被视为识别来源功能派生出品质保障功能[34]同注释⑭,第16页。并将其内化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商标制度完成了从“严格来源规则”向“来源不明确规则”的演化[35]参见张林:《标示来源功能与商标显著性——兼与彭学龙老师商榷》,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101-102页。。总体上看,商标所指示的“来源”与商品实际来源逐渐分离,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却愈加得到认可,说明人们普遍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商标给消费者提供的来源信息已经是一种确定可能性而非具体确定性的认识。继续以识别来源功能描述商标时,“必须让步于公众并不关心涉诉商品实际的特定来源和所有者的事实”。[36][美]佛兰克·I.谢克特:《商标法的历史基础》,朱冬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第159-160页。易言之,商标并不能指向实际的商品生产地或经营者所在地,而是指向单一的、可确定的质量控制主体。对来源的抽象稳固了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也为商标权在地域和主体上的扩张提供了可能。
2.搜寻成本理论的隐藏预设
在支撑商标正当性的众多依据中,搜寻成本理论的地位几乎不可撼动。为完成理想的消费决策,消费者需要尽可能全面地获取与商品有关的信息,但对商品总价值起到关键作用的商品性能、耐用程度等通常难以通过对商品的直接观察得出,必须耗费额外成本搜索与确认。[37]See Nicholas S.Economides, The Economics of Trademarks, 78 The Trademark Reporter 523, 526 (1988).经济学分析发现,商标作为提供信息的有效工具,能够使消费者快速从过去的消费经验中确认商品的有利特征,免去对产品信息的再次调查及与其他产品的比较,从而节约搜寻成本。[38]同注释[32],第205页。通过应用商标,一部分检索信息的成本被替换为维系商标制度的成本,且后者被认为远小于前者,由此商标获得了经济效率方面的认证。商标制度正是通过维护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来降低消费者的搜寻成本,进而促进市场资源的有序配置,最终服务于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目标。
搜寻成本理论的分析结果无疑对商标制度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如果将视角转向对其前提的探究,可能会有相反的发现。搜寻成本理论之所以成立,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预设之上:影响消费决策的实质性因素是有限的,只要商标能够基本替代实际获取预设范围内信息的作用,就是有效率的。换言之,商标只是对特定信息的简化,而简化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放弃与删除。搜寻成本理论所圈定的决策所需的必要信息实际上只是表明质量稳定性的抽象来源信息,除此之外的信息都会被舍弃。[39]同注释⑰,第206页。在大多数情况下,简化信息并不会产生问题,因为受制于有限理性的消费者必须进行成本—收益核算,[40]同注释[29],第20页。被舍弃的信息通常不会对消费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且由于能够将消费者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与商品本身相关的认知过程上,商标通常会提供提升决策效率的积极效用。
但从根本上看,简化信息有其潜在风险。历史表明,在尚能以较低成本实现对商品的亲自体验时,消费者对商标并不会产生依赖,但亲历性消费场景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消费者接受了商标的协助,即令只能从中获得质量一致性的保证。问题在于,商标对信息的拣选在很大程度上是“中立”的,不仅会剔除无用信息,也很可能造成有效信息的遗漏,因为商标自始就未将区分信息有效程度作为前提,其所联结或承载的信息只是在主体的认知和记忆中更容易被调动或激活的特定内容。受到商标强度或使用场景等的限制,这些信息的数量和种类显然十分有限,那些无法被商标所覆盖的信息,比如与竞品的比较优势与劣势、相关市场情况等,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影响商标功能的实现。对这些信息的认知不足,很可能导致商标在售后阶段遭受责难,因为从消费者选择借助商标完成决策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因商标所忽略的信息只有在商品实际到达消费者手中时才能重新得到关注。如果被遗漏的信息恰好能够影响个体的特定决策,消费者就可能会因误判而对商标产生消极评价。可见,简化信息既是商标的优势,也可能成为其最易遭到攻击的缺陷。
(二)人工智能在提供商品来源信息方面的比较优势
1.丰富信息总量
如上所述,与其认为商标是对商品信息的整合,毋宁将其看作是简化信息的工具,而具有潜在风险的商标之所以仍能在消费决策中居于难以撼动的地位,主要是人类受制于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而不得不接受来自商标的辅助。人脑存储和处理能力是有限的,即使人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个针对特定主题的单一的认知网络中,也会因为人脑的“信息过载”机制而自动遗漏信息。商标作为刺激消费者心理的最有力的“信息组块”,可以使消费者在售前的有限时间内有效地组织、存储以及从记忆中提取与商品有关的认知。[41]See Jacob Jacoby,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rademark Law: Secondary Meaning, Genericism, Fame, Confusion and Dilution, 91 The Trademark Reporter 1013, 1022-1025 (2001).
人工智能则突破了人类生理层面的限制,克服了“信息过载”的困境,帮助 人们摆脱对商标的依赖。区别于商标的作用机制是节略信息,人工智能则走向了反面,其在筛选商品、预测购买倾向之前必须尽可能充分地获取信息才能保证输出结果的准确性,原本将被商标所省略的信息从一开始就被人工智能所应用。从信息总量上看,消费者虽然通常不会查看人工智能存储的全部信息,但是可以随时随地以极低成本调取,这意味着其可获取的信息几乎是无限的。从信息获取方式上看,消费者无需追溯商品来源以及产销渠道。人工智能尽管也没有进行实物考察,但可以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并根据数据之间的相互印证情况提供与客观情况高度接近的商品信息。此外,从信息延伸上看,人工智能还能够在极短时间内收集其他用户对于同一商品的历史评价或者是同一用户在同类商品上的消费情况,整合所有间接与商品相关的信息。可见,人工智能代替消费者对与商品相关的背景信息进行全面的替代审查,大幅度提升用户获取商品信息的效率,从而使同样作为消费决策辅助工具的商标的比较优势下降。
2.减少信息不对称
消费者借助商标所获取的来源信息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商标在充当经营者与消费者对话媒介的同时,也构成了两者之间的阻隔。尽管立法者可以通过商标法、产品质量法等规范督促经营者采取措施维持商品与其商标所传达信息之间的一致性,但显然并非所有经营者都能一以贯之地履行义务。此外,规模消费进一步扩大了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距,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引发商品供应量猛增,确保“标—品”关系的稳定性的成本相应上升,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缺漏与错误的风险随之提高。
人工智能应用于消费活动,将能够有效减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提高来源信息的准确度。首先,虽然人工智能与商标一样也是作为经营者与消费者对话的中间角色参与信息传递,但对经营者一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在从经营者处获取商品信息时,预设了严格的信息甄别和拣选过程,且将在后续分析中通过相关数据加以印证,这意味着此前得以借助于抽象来源而隐身的经营者将难以回避其来源保证或质量控制义务,也难以任意操控信息。进而,人工智能提高了消费者获取信息的能力,改善了消费者在获取信息中的相对劣势地位。智能视听技术为消费者带来了直观的商品体验;智能检索使包括商标信息在内的任何与商品相关的信息都得以存储和分析;智能推荐以多维度的客观真实信息为支撑,很难受到经营者美化或不正当竞争者丑化的“欺骗”。可见,人工智能不仅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效率,更有助于消除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雾障”,维护了供需双方的信息公平。
(三)人工智能动摇搜寻成本理论的可能性
即使尚未进入强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的潜力也毋庸置疑:作为拥有无限收集和存储信息能力的工具,其完全替代了人为的信息搜集过程,并以海量的具体信息为商品背书。搜寻成本理论将对信息的简化视为效率的提升,但若人工智能无需通过简化信息就可以替代商标的功能,搜寻成本理论的适用将难以为继。
不过,虽然理论上人工智能具有动摇搜寻成本理论的可能性,但上述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理想化的“思维试验”[42]同注释⑰,第203页。,即假定作为分析对象的人工智能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理想化模型,它有能力甄别机器学习过程中所获取信息的重要程度,排除消费场景中无用信息的干扰,并基于中立原则将与消费决策直接相关的信息呈现在最后的分析结果中。然而,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还不能实现这一点。技术水平的限制只是一个方面,消费者与人工智能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信任关系,[43]参见朱国玮、高文丽、刘佳惠等:《人工智能营销:研究述评与展望》,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年第7期,第92页。也进一步减缓了人工智能对商标地位的冲击。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虚假信息风险为例,此前,决策式人工智能受限于算法和算力,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至多提供明显不可信的错误结果,因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之前,人工智能的信任危机尽管存在但并不突出。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以“运行目标的不可知化”为其主要运行特点之一,在“少样本”“单样本”和“零样本”情况下借助少量甚至不借助已有处理结果完成任务,效率与自主性得以提高的同时,虚假信息的风险也随之增大。[44]参见朱嘉珺:《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有害信息规制的挑战与应对——以ChatGPT的应用为引》,载《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5期,第35页。人工智能的信任危机涉及人对技术的态度和技术本身的可信任两个维度。欧盟在2019年就发布了《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45]See European Commission, 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 8 April 2019,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ethics-guidelines-trustworthy-ai.,尝试为建立可信人工智能提供方案,但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虚假信息的风险被暂时搁置。尽管借由商标获取信息亦面临风险,但基于路径依赖的心理作用,同样不完全可靠的人工智能建议对用户的吸引力并不明显高于商标,基于思维定式和行为习惯,消费者仍可能会以商标作为来源确认的主要工具。
总之,在技术达到理想状态之前,对人工智能的乐观预期不能走向技术狂热。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对商标的冲击力度仍相对可控。因此,更重要的是结合当下的技术发展水平认识商标及其作用机制,在商标法的框架下探讨人工智能引发的商标保护问题。
四、人工智能对商标广告功能的冲击
除了传递商品来源信息,发挥基础的识别来源功能之外,商标的品质保障功能具有表彰并建立商业信誉作用,从而衍生出广告宣传功能。充分利用商标广告功能,有利于刺激消费,特别是与商品符号价值相关的消费活动。但随着人工智能对商标出现频率和应用方式的改变,商标广告功能的实现程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一)商标广告功能的理论与实践
1.商标广告功能与商标财产属性的发现
商标广告功能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商标财产属性得到法律确认的过程。商标是否具有财产属性,商标权是否能够作为一项财产权得到同版权、专利类似的无体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在商标制度孕育时期一直争论不断。对标记的保护最初只通过禁止欺诈实现。但是,由于禁止欺诈的直接效果是维护公众利益,只是可能同时产生防止经营者利益受损的附带效果,对标记持有者的保护力度十分有限。此外,由于禁止欺诈之诉依赖于公众及司法机关的主观判断,导致标记持有人倾向于忽视“创造商誉的一般因素”,而更关注“司法上对公众主观状态的估计”,[46]同注释[36],第177页。大量资源被投入到攫取他人投资利益和对司法机关的游说上,无益于建立和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
改变上述情况的契机是大规模广告投资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市场上商品总量的扩张,经营者开始将资金投入到扩大标记影响之上以吸引消费者购买。广告行为的普遍化使人们认识到,商标所有人为扩大标记影响而进行的投资能够产生刺激消费和积累商业信誉的经济利益,其对此当然享有禁止他人攫取利益的权利,商标所有人所享有的“可能发生之期待”的利益由此具象化为商誉价值,[47]同注释[36],第177-179页。商标的财产属性随即得到法律确认。如今,对商标与商誉之间具有内在紧密联系这一点几乎已经达成共识,商标的广告功能也日益突出。通过在商业活动中强化商标的使用和宣传,经营者意在使“标识与商品进行强力对接,在消费者心目中营造通过商标而联想到特定商品的效果,形塑优良的商业信誉”。[48]凌洪斌:《社会经济发展视阈下的商标功能扩张进路》,载《知识产权》2016年第1期,第101页。具体而言,经营者为塑造商标形象付出的努力至少在两个方面培育了商誉:一是强化商标的独特性,使商标成为经营者的“名片”,对品牌的忠诚度部分甚至全部代替对商品本身的理性分析成为消费决策的依据;二是增强商标的精神意义,使情感和文化诉求超越对商品本身的需求成为作出购买决定的动因。
2.商标广告功能的实质意义
不同于对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普遍认同,对于商标的广告功能是否能够指向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一直存在争议。[49]例如,有学者认为:“广告与商标的联系并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联系,商标的广告功能其实是对商标‘识别功能’的一种商业利用,它不是一项独立的功能,也无独立存在的必要。”参见余俊:《商标功能辨析》,载《知识产权》2009年第6期,第78页。除了对广告功能独立性的质疑,对于保护商标广告功能可能造成的对表达自由的限制,以及其可能造成的无序竞争,都曾经挑战了广告功能的正当性。同注释⑭,第18页。尽管经营者为商标进行的广告性质的投资客观上产生了吸引消费者的积极效果,但有论者认为商标广告功能对消费的刺激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消费的活跃程度只取决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营者在商标广告上投入高额的设计和宣传成本并未增加供应端的商品总量,也未提高消费端的消费能力,消费规模并不会因为商标的介入而有显著改变。相反,过度关注商标的广告功能将带来盲目的“品牌拜物教”,使经营者错误地将资源投入到广告宣传而非商品质量的提高上,从而将消费活动引向虚无。[50]See Katya Assaf, Brand Fetishism, 43 Connecticut Law Review 83 (2010).
诚然,过分强调商标的广告功能并因此无限度地扩张商标的保护范围的确存在消费虚无化的风险,但因此否定商标广告功能的价值无疑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商标能够刺激消费”的判断应当建立在市场竞争的语境下,关注商标对特定竞争主体的效果。从经营者个体视角出发,具有独特性并得到充分宣传的商标更容易使商标所标识的商品在众多同类、同质商品间脱颖而出,从而将对替代商品的消费转移至该商标商品。如果不允许通过广告宣传强化商标间的差异,商标所有人虽然享有基于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垄断性质的权利,却不能形成实际的市场优势,就不得不通过无限接近于边际成本和零利润的价格出售商品,而这显然不是一个良性运转的市场所希望形成的局面。[51]同注释[37],第532页。认可与保护商标广告功能,能够激励经营者在保障商品质量稳定性的前提下,以培育商品在客观属性上的优势或针对不同层次的消费市场制定差异化营销战略来打造竞争优势,提高消费者对特定商标的信任程度,促进既有市场的重复消费和延伸市场的首次消费。因此,保护商标的广告功能符合商标权是对“商标信誉的保护”[52]同注释⑥,第36页。的要旨,具有实际意义,商标法需要为保障广告功能的顺利实现制定相应规范。
3.符号消费演进中的商标广告功能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观念发生了从单纯对“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的转变,即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不再将商品的性能、品质以及价格等作为其作出购买选择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更加关注商品或消费行为所象征的意义与理念。[53]参见孔明安:《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载《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第68-74页。符号消费趋势的出现既是生产力水平发展的结果,也是消费者满足个人更高层次的归属、尊重乃至自我实现需求的目标与要求。[54]参见徐聪颖:《论商标的符号表彰功能》,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2页。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使得符号消费的特点愈发突出,不仅商品因其“符号”属性而被赋予文化和社会意义,与交易对象相关的商标、广告、社交活动等也成了消费意义的载体,影响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商标丰富多样的表达形式恰好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自我表达、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的方式,因此逐渐深入到缔造消费意义的过程中。消费者可能基于“商品拜物教”心理将对商品的评价转移至商标,甚至会在“品牌拜物教”的观念下选择替换此前的消费选择或购买延伸市场的商品,这并非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产物,而是来自商标广告功能的劝说效果。通常认为,商标是由标志、对象、意义构成的三元结构,但在符号消费的发展中,商品在商标结构中的地位淡出,商标与其意义的结合愈加紧密从而趋向二元结构,[55]参见冯晓青主编:《知识产权法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612页。可见符号消费与商标广告功能之间形成了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商标广告功能为符号消费的深入发展创造了可能,符号消费也有益于强化商标广告功能的独立地位。随着商标结构呈现出新形式和新特点,商标法需要为了应对商标广告功能日渐突出的情势作出相应调整。
(二)人工智能对商标广告功能的影响
1.影响对商标的接触程度
人工智能广泛参与消费决策将影响商标广告功能发挥的前提。首先,人工智能导致消费者对商标的接触不足。在商品信息的初步收集阶段,人工智能将替代消费者进入市场,消费者将无需也无从建立与商标的联系,商标的广告效果因无法作用于消费者心理而无法实现;在需要由消费者完成最终选择的后期,消费者所能接触到的商标数量本就已经十分有限,且出于对人工智能的信赖,消费者对商标的关注度也会有所下降,从而削弱了劝说效果。实际上,并非广告功能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成为营销活动的对象,商标只能通过作用于人工智能的“心理”而实现宣传效果。
进而,人工智能在辅助消费者预先缩小待选商品范围时,尽管将增加某些商标出现的频率,但也可能阻碍部分商标广告功能的实现。这是由人工智能算法的复杂性导致的,且不论人为操纵算法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造成的歧视性后果,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人工智能算法公开透明只是一种“美好的技术理想”[56]参见侯东德、张丽萍:《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网络信息生态风险的法律规制》,载《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6期,第99页。,人工智能应用于信息检索、精准推荐乃至替代决策时依赖大量的随机和自主运行程序,在技术上也难以解释输出结果的确定性。物质属性完全相同但商标不同的商品被推送到消费者面前的概率几乎完全取决于随机算法,尽管消费者仍能获得价值相当的商品,但对经营者来说,人工智能实际上转移了本将因接受商标劝说而选择购买其商品的消费者。
2.减少背景信息的辅助
从认知过程上看,消费者即时获取信息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长期记忆的调用效果决定的,商标虽然是存储、调动与商品相关记忆的最有力刺激,却很难孤立发挥作用,经营者在突出显示商标、强调商标作用的同时,往往需要运用广告、包装装潢等辅助工具。一方面,这是为了将消费者的注意力尽快集中到商标所处的位置,以启动商标所关联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商标之外的宣传手段有助于丰富商标通常不能传达的背景信息,如潜在的市场条件、产品、购买频率、信息在消费者之间传播的容易程度以及召回能力等,[57]同注释[37],第526-527页。从而加强商标与商品、商标与所处市场之间的关联性,发挥商标在市场中的广告作用。
人工智能对包括商标在内的传统信息载体的冲击,将极大地影响商标广告功能的实际效果。人工智能不再用于启动以商标为结点的认知过程,在取代现有的辅助手段之后,其并未接替作为启动商标认知过程的工具地位,而是替代商标发挥作用,商标对消费决策的介入程度因消费者注意力的转移而有所下降。进而,在其他营销手段无从应用的同时,人工智能向消费者呈现的信息与分析结果又直指商品,导致背景信息总量减少,进一步阻碍了商标广告功能的实现,长此以往商标广告功能的效果将受到极大影响。
3.扩大符号消费中的商标价值
人工智能将促进符号消费的发展,有助于扩大以商标广告功能为基础的商标价值。人工智能对符号消费的推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工智能有利于为消费活动建构新的精神意义。人工智能作为交易对象或交易工具应用于商业活动,能够满足部分群体的情感需求,唤起人的情感共鸣,使消费者产生更多忠诚度和依赖感,[58]参见王先庆、雷韶辉:《新零售环境下人工智能对消费及购物体验的影响研究——基于商业零售变革和人货场体系重构视角》,载《商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17期,第8页。追求此种精神意义吸引的消费者将主动参与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符号消费中,而这将相应地为人工智能商品商标注入一种“智能消费”的意义。第二,人工智能在整合数据和传播信息方面的强大作用,有利于使消费者更快获取和更易接受新的消费文化,促进对特定消费活动中的精神意义形成共识,也会对消费者观念和意识进行引导与改造,塑造并强化消费者对特定商标的印象。[59]参见윤선희、陈芳鑫:《基于符号学理论的商标功能之重构——以本源功能与派生功能为中心》,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34页。在此意义上,商标的广告宣传效果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符号消费中有更好的表现。
(三)人工智能对商标广告功能冲击力度的有限性
从商标广告功能的转变路径考虑,人工智能在信息搜集乃至自动执行过程中对消费者角色的替代,产生的结果是代替人承担劝说作用,而未就此否定广告功能的有效性。这就导致尚未发展成熟的人工智能可能因为对商标所提供信息的依赖或“干扰”,成为商标广告功能的接收者;高度发展的人工智能若将以无限接近于人脑的思维模式运作,与商标对人类劝说的相同结果甚至更有可能出现。此时,如果经营者能够及时调整商标战略,使商标广告功能因应智能消费作出调整,将有助于削弱人工智能造成的冲击。具体而言:首先,经营者可以侧重于在工具层面使用人工智能,通过精准推送、智能生成广告等方式使人工智能用于提高商标曝光度,而不是替代商标的作用;其次,在智能时代,一个同时便于人和人工智能“识别”的商标或许更具竞争优势,经营者可以对商标形式作出必要调整,以“满足人工智能的需求”,例如,现阶段人工智能对非视觉商标(如声音商标、气味商标)的识别可能存在困难,经营者可以加强对视觉商标的使用。
此外,人工智能对广告功能的影响程度还受到来自其自身应用场景的限制。人工智能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基于数据分析准确判断商品的客观属性上,更关注商品本身与消费者需求的契合程度。在商品的质量、价格、特征等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人工智能将倾向于重复推荐或替代购买同一商品,其对同一品牌或延伸市场的商品预测也只是对历史消费的商品可量化指标的延伸,无法克服以销售总量、消费趋势等客观指标代替人的主观评价的弊端。这也意味着,人工智能辅助具有高度主观性、难以被客观数据测量的符号消费活动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就现阶段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而言,其主要冲击的是商标广告功能中以提供商品客观信息发挥作用的部分,难以取代基于文化意义的商标劝说作用。
五、智能消费时代商标制度的因应
商标法所划定的商标专用权范围,以及禁止他人未经许可的商标使用行为等各种具体制度,都服务于保障商标功能正常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在人工智能介入消费活动之后,商标识别来源功能以及广告功能遭到了巨大挑战,以此为基础的商标制度也将随之动摇。人工智能将以两种形式挑战商标制度的有效性:一是降低消费者对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依赖程度,防止混淆规则的侧重点应随之变化;二是放大消费转型升级中的商标广告功能,对由此扩大的反淡化需求有必要在立法上作出回应。因应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消费的挑战,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巩固商标法的独立价值
当人工智能足以在消费决策中大幅甚至完全替代商标所能实现的效果时,商标制度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回答是肯定的。从商标价值的来源出发,即使只是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消费者依旧提出了对商标的需求,法律就需要为商标功能的顺利实现保驾护航。且不论人工智能对商标的替代程度尚取决于技术的发展程度和社会消费观念的变革,即使未来智能消费高度发展,消费者也仍然享有对商标存续与否的控制权——既有能力在人工智能代替商标“干扰”决策前就加以限制,也可以随时决定是否允许人工智能介入及其介入程度。消费者的主体性将成为商标制度的坚实支撑。未来,商标法需要为有限场景中的商标功能发挥提供保障,确保商标在维护分配公平和规范市场竞争上持续发挥作用。
1.维护特定群体的信息分配正义
第一,商标将在传统的线下消费中继续得到使用,商标法有利于维护实体消费中消费者的信息获取权。人工智能虽然明显优化了网络消费体验,但在实体消费中尚无突出表现,线下消费在销售特定类型的商品上仍有独特优势。实际上,线下消费与智能消费两者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智能消费所不能及的空间将为商标留有一席之地,在遥不可及的全面智能消费时代真正到来之前,线下消费不会完全谢幕,商标仍需要在线下消费中得到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足以用于作出消费决策的信息。[60]同注释⑰,第210页。
第二,商标将服务于网络消费中的少数消费者,保障信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即使将关注点放在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领域中,商标也需要继续发挥作用。对于那些因为信任不足而拒绝使用人工智能,或者受制于有限的获取方式、使用成本等因素而未能应用人工智能的消费者群体,商标仍然是消费决策的首要辅助工具,如果忽视这些群体对商标的需求,将无法维系信息的分配公平。
总之,商标法为传统实体消费以及网络消费中特定消费者继续通过商标获取信息提供了保障,将有助于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信息分配的公平正义。在当前人工智能深刻影响消费者行为和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情况下,维护特定群体的信息分配正义,无疑具有特殊意义。
2.以良性市场竞争增进消费者福利
商标刺激重复消费的作用有利于激励生产者持续提高商品质量,良性参与市场竞争,这在智能消费时代也不例外。在智能消费时代,虽然部分消费者评价实质上可能是对人工智能或者人工智能技术提供者的反馈,但商标仍将辅助理性消费者的决策。在未来人工智能足以全面替代消费者决策时,若容许消费活动倒退到历史上无标可依的状态,对商品的识别和评价将只能依靠商品参数、价格等能够被数字量化的指标,导致在物理属性上相同或相邻市场上的商品几乎被同化,经营者将不得不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制造差异,这将偏离以积累商誉为核心的良性市场竞争的正确航道。虽然可以通过提升商品质量或者扩大生产规模稳定市场份额,但并非所有的经营者都具备相应的生产能力,且处于任一质量层次上的经营者都必然会面临无限接近边际成本的价格竞争,久之市场竞争主体数量减少,既有损于自由竞争,也因可获取的商品数量减少且质量下降而损害消费者福利。与之相比,维护商标制度有效性的成本显然是必要的。
(二)明确售后阶段的防止混淆规则
如前所述,无论是基于“消费过滤器”的属性还是替代决策者的属性,人工智能都会显著降低消费者与商标充分接触的程度,但是这一判断是将消费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而作出的,为了寻找商标法的存续空间,需要对人工智能的势力范围进行更细致的认定。准确地说,人工智能主要被应用于商品销售之前及消费决策作出之时,对商品售出之后的影响程度有限。例如,智能视听技术只是在商品出售之前预先提供接近于对真实商品的感知,通常不能替代消费者取得商标商品后的实际体验(虚拟商品或服务除外),后者才是生产者建立稳固的市场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此外,售后阶段的商标还有其独特作用,当人工智能出现错误或遭受算法操控时,已经处于售后阶段的消费者可以借助对商标的认知检验校正决策结果,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在智能消费时代,售后阶段商标使用和商标权保护的重要性将更加突出。
1.防止智能消费中售后混淆的必要性
从商标法以防止混淆为核心所构建的商标保护规则考虑,商标法应在防止售后混淆方面进一步优化。最早的商标法只禁止对正在购买商品的实际消费者造成混淆的行为,因为“商标在消费者购物时是向导,在消费者购物前则是劝说员,在消费者购物后则成为体现其身份和地位的名片”[61]邓宏光:《商标混淆理论的扩张》,载《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10期,第39页。,在售中、售前阶段的错误认知将直接影响购买决定,所以通常认为混淆主要削弱的是商标作为“向导”和“劝说员”的作用。随着商标权的扩张,商标的“名片”角色日益凸显,混淆可能性判断中的主体范围从实际消费者扩大到未购买商品的潜在消费者;时间维度上从消费行为发生的当时,扩展到了售前以及售后。“实际上,如果是否存在混淆可能性的认定不以购买者为限,混淆就完全可以发生在购买前或购买后”[62]参见彭学龙:《商标混淆类型分析与我国商标侵权制度的完善》,载《法学》2008年第5期,第108页。,而时间限制的淡化也用于佐证混淆主体拓展的必要性。上述混淆判定规则的扩张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消费活动之后将有更突出的体现。
对售后混淆予以规制的必要性,主要源于其对消费者乃至一般旁观者产生消极影响的高度可能性。一是防止消费者在售后阶段因假冒商标而产生对真实商标的混淆误认。售后阶段是消费者重新建立商标与商品之间关联性的关键环节,如果消费者因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消费决策而在没有充分接触商标信息的情况下购买了低质量的假冒商标商品,消极评价就可能被错误地累加到被假冒的商标上,对真实商标商品的购买意愿下降无疑会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二是防止潜在消费者乃至一般旁观者在售后阶段的混淆误认。人工智能在整合和扩散多来源信息方面的强大能力,使得某一消费者评价容易产生群体性影响,因售后混淆产生的负面评价将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分析判断的基础数据并作用于经营者目标营销群体的消费决策,加之参与塑造消费意义的主体日渐多元,混淆的消极影响在主体之间相互传导和扩大的可能性也将有所提高。因此,在智能消费时代,防止售后混淆是保护商标权人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应有之义。
2.准确界定售后混淆的相关公众
我国商标法固然未按照发生混淆的时间将售后混淆明确列举为商标侵权类型之一,但也没有排除有关商标权保护的各项具体规范在售后混淆中的适用。实际上,司法实践中早已出现了相关案例,法院也基本已经认可应当对售后混淆予以规制,只是在认定规则上存在一定分歧,其中最大的争议之一在于对售后混淆主体范围的确定,即相关公众的认定。[63]有的法院认为我国《商标法》第57条的“混淆”仅指“直接混淆”而不包括售后混淆,参见叶孟宗与香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73民终1530号。有的法院则支持售后混淆也属于我国《商标法》所规范的混淆的观点,参见上海维尔雅化妆品有限公司、上海维尔雅日用化工厂与爱茉莉太平洋株式会社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73民终17号;莆田市阿迪思克贸易有限公司与阿迪达斯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辽民终1138号。
相关公众是认定混淆时必须首先予以确定的部分,因为混淆可能性是以相关公众的认知和一般注意力为基准加以判断的,相关公众包括与商品相关的消费者和经营者,且以直接消费者为主。[6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9号)第8条规定:“商标法所称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和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对于经营者的范围,借助商品或者服务的相关情况、地域、主要营销市场等因素相对容易确定,因此,本部分将集中分析经营者之外的主体是否属于相关公众。在售后混淆中,界定相关公众的特殊性在于可能发生混淆的主体并不限于直接消费者,还会涉及在商品使用过程中可能接触到商品的一般公众,例如商品的潜在消费者甚至是对该商品没有消费兴趣的旁观者,后两类主体是否应当被纳入售后混淆中的相关公众,值得深入探讨。
潜在消费者应当被包含在内,因为其对商标以及商标商品的评价将成为后续消费决策的依据,保障其识别利益符合商标法的规范目标。商标商品“招徕未来消费者”,吸引商品潜在顾客的能力,能够激励商标权人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商标法对潜在消费者售后混淆的防范,可以为实现商标制度对生产者的激励目标提供“事实措施”[65]黄汇:《售前混淆之批判和售后混淆之证成——兼谈我国〈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载《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6期,第13页。。
关于直接消费者与潜在消费者之外的主体,情况则相对复杂,尤其是对“相关性”的界定,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消费者之外的旁观者与消费者的未来消费意愿相关,尽管其自身可能不会购买商标商品,但其对商品的评价很有可能间接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另一种情形是旁观者的可信赖利益与商标相关,例如在奢侈品领域,即使是不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群体,其与商标之间也存在因识别利益而建立的弱关联性,对此种基于信赖关系的相关性的肯定亦符合商标法的意旨。[66]参见周贺微:《商标法中“相关公众”的适用研究》,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11期,第45-46页。因此,本文认为,在商品的消费者之外,至少还存在上述两种情形下主体的“相关性”,需要被纳入售后混淆的考虑,不应将其直接排除。
综上,防范有损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售后混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商标法必须重视的问题。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最终体现在商标与消费者的互动中,即使是当下没有作出购买行为,或没有购买意愿与购买能力的主体,也享有相应的识别利益,在确定相关公众的范围时应予以全面考察。当然,不能因此过度扩张相关公众的范围和防止售后混淆规则的适用,应根据主体接触商标的可能性、相关群体的数量、主体所处地域与市场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基于消费可能性和与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关联性适当设定相关公众的边界。为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加强对售后混淆的规制和基于统一裁判标准的需要,我国在完善商标制度时,可以在商标法中明确将售后混淆列为侵权类型之一,并在司法解释或行政法规中列举可用于确定相关公众的考虑因素,以更准确、更全面地保护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
(三)拓展反淡化规则的适用空间
1.扩展适用以商标广告功能为基础的反淡化规则的必要性
通常认为,商标法是以识别来源功能为核心构筑商标权的藩篱。与之相比,商标广告功能则难以作为独立依据支撑起商标保护规则,原因之一是商标广告功能通常为享有知名度的商标所具备,之二是商标广告功能的保护范围相对不易确定。[67]参见吕炳斌:《商标侵权中“商标性使用”的地位与认定》,载《法学家》2020年第2期,第80页。因此,对商标广告功能的保护往往只能被视为维护识别来源功能的附带目标或结果,且现有为驰名商标提供反淡化保护的规则的适用空间十分有限,总体上,以商标广告功能为基础的反淡化规则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但是,广告功能是商标财产属性的重要体现,建立在商标广告功能基础之上的顾客吸引力,才是商誉的核心,也是商标法必须予以重视的方面。[68]参见董美根:《英国商誉保护对我国商标专用权保护之借鉴》,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5期,第88页。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信息过剩而注意力稀缺的特点将愈发突出,当消费者有限的注意力被从本应发挥作用的商标之上转移至另一商标时,消费者虽然没有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但可能就此放弃对真实商标商品的搜寻,造成商标权人市场份额的缩减。对商标的广告功能给予充分保护不仅是维护权利人财产利益的要求,也有利于提高经营者保障商品质量的积极性,服务于保障消费者利益的目标。尽管实践中在规制损害识别来源功能的行为时,往往同时起到了扫除商标广告功能障碍的效果,但这种保护不够充分。随着商标功能向广告投入功能的倾斜,重新界定商标的价值,重新确定商标反淡化保护的广告功能基础,才能真正维护商标背后的商誉。[69]同注释⑭,第169-170页。在智能消费冲击商标功能的背景下,适度扩张反淡化规则,有利于巩固商标广告功能的地位,维护智能消费时代商标制度的稳定性。
2.智能时代反淡化规则适用的有限扩张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智能消费时代,反淡化规则所保护的商标范围应当得到明确和拓展。目前,我国商标法体系中的反淡化规则主要体现于《商标法》第1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9号)第9条,可适用反淡化规则保护的商标被限定为“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驰名商标。一方面,应明确“熟知”的含义。从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规则沿革上看,“熟知”既包括了“广为知晓”所代表的通过主体地域、数量等体现的认知广度,也须具有由其自身决定的认知深度。同时,鉴于该要件将用以确定商标的知名度,而不涉及商标所指示的对象或意义,“熟知”可以被定义为“较广地域范围内一定数量的相关公众知悉该商标的存在”。另一方面,既然立法对参与划定驰名商标界限的主体与上文防止混淆规则中所涉及的主体采用了相同的表述,两者的扩张就应同步进行。因为智能消费时代中的直接消费者、潜在消费者以及与商品仅具有弱关联性的旁观者都可能参与商标知名度及声誉的建构,所以放宽驰名商标中的“相关公众”是应有之义。此外,为防止“相关公众”滑向“一般公众”,也有必要在商标法中设置专条规定用以确定主体“相关性”的因素,或列举通常应予以考察的主体类型。
同时,对反淡化规则的适用应当持审慎态度。虽然广告功能可以独立作为商标保护的基础,但相较于识别来源功能一旦受损将同时损害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广告功能则更侧重于保护经营者的利益,只是在最终结果上也有利于保障消费者利益。人工智能固然能凸显广告功能所带来的商标价值,但反淡化规则的适用范围仍相对有限。除了在立法时可以通过对商标知名度的要求来划定广告功能的边界,在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谨慎适用反淡化规则;若广告功能与识别来源功能同时受损,可将两者的损害结果合并评价,但主要以后者功能受损认定侵权性质。如果仅涉及对广告功能受损的认定,可以通过市场调查等方式确定消费者的注意力是否被不当转移,将对商誉的保护作为最终立足点。
结 语
在商标制度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对信息的简化或删除完成的从具体来源向抽象来源的演变,是商标识别来源功能的重要突破。然而,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商标因简化信息机制而面临危机,搜寻成本理论难以继续为商标的正当性提供足够支持。商标具有广告功能,经营者在广告宣传中对商品的物理属性和社会文化意义加以表彰,能够提升商誉并刺激消费。尽管人工智能对广告功能有所削弱,但随着智能时代符号消费趋势的增强,若经营者能够及时顺应技术和营销环境的变革调整商标战略,广告功能将有继续发挥作用的空间。面对智能消费浪潮,商标法应当坚守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基本价值追求,为维护信息公平以及规范市场竞争持续作出贡献。在商标制度运行的具体环节,有必要明确售后阶段防止混淆规则的适用条件,并适度扩张反淡化规则,使商标的识别来源功能和广告功能继续为商标制度的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未来,人工智能将发展到何种程度尚未可知,其在消费决策中的作用以及对消费者地位的取代程度还有待技术和时间的检验,亦取决于人类对人工智能的定位和利用方式。现有研究建立在“消费者+人工智能”的人机交互型的消费决策模式上,而全面人工智能决策时代的到来可能会带来更严峻的挑战。未来若消费者隐身于与经营者、商品、品牌的直接互动的消费模式成为常态,与此同步发生的人类主体性的削弱还会触及更深刻的科技哲学命题。不过在现阶段,更重要的是挖掘商标法在智能消费时代的作用,至少在人工智能完全取代商标之前,巩固基于商标功能的商标法律制度仍然具有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