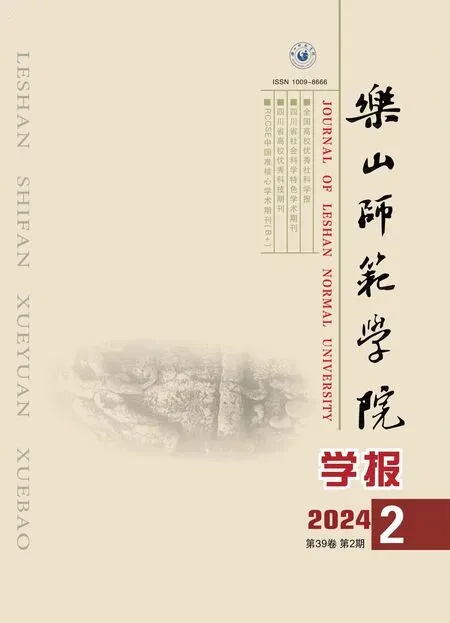移动短视频社区中的视觉人类学新特征
王玉坤
(贵州民族大学 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视觉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摄影术的发明,开启了现代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大门。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依托民族志纪录片(Ethnographic Film)这一媒介载体,能够让人们看到让·鲁什(Jean-Pierre)的《夏日记事》[1]。20 世纪7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徳(Margaret Mead)将电影与人类学相结合并延伸出“Visual Anthropology”的概念,国内大多将其译为“视觉人类学”或“影视人类学”[2]。学者朱靖江曾着重阐释了自己对于“Visual”的观点,他认为应建立以影视人类学、影像人类学与视觉人类学为分支学科三个层次[3];邓启耀则倾向于将群体性图像信息、视觉符号和视觉文化行为纳入视觉人类学研究的视野[4]。为了本文论述清晰,特别使用含义较为广泛的“视觉人类学”概念,不但有观察层面的“视”,还有心理层面的“觉”。将可视化的短视频纳入统一的视觉空间,认清影像不只是具有“文本人类学”的记录功能,还拥有“视觉人类学”的可视化和冲击性。
媒介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拍摄的平民化,拍摄工具的多元化带来了影像的极大繁荣,拍摄的主体不再是具有独特身份的摄影师、记者、人类学家。国内以抖音、快手、哔哩哔哩为代表的短视频社区让视觉的平民化表达变为可能,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也将改变传统视觉人类学的拍摄工具和手段、田野调查的方式以及研究模式的转变。学者余点认为,新媒体的发展有利于诠释和保护世界文化、解决跨文化交流的障碍和带来影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新媒体语境下,影视人类学发展机遇与困境共存。”[5]应该借势新媒体的发展,重新阐释学科的人文精神,丰富影视人类学的生产和传播。朱靖江也论述了以快手、抖音为主的短视频社区所产生的主位影像表达和由此带来的社区认同和商业变现模式[6]。这些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掷于视觉人类学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变迁,但总体而言不够深入和具体,本文继续聚焦不同于以往传统人类学视角的移动短视频社区所引发的新蝴蝶效应,在关注短期大环境引起学科变化的同时,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学科未来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利害关系。
一、当代媒介技术发展带来视觉影像转向
视觉人类学的基础理念是“文化是可视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使得视觉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展了。王海龙认为,大多数的人类学家荒唐地摒弃了在照相术发明以前对自史前人类开始绘画以及用图像记载文明时期所有视觉材料的研究及以此来探讨-传承文明的所有努力及其实践活动,这是错误的。他认为,视觉人类学是用图形、图像来阐释和研究人类文明、文化的学科,是一门全景性的学科,不仅涉及电子媒介时代的影像记录,还可以包含摄影术发明之前的图腾、符号、文字、绘画、雕塑、建筑等诸多能纳入人类视觉范围并与人的生产发展密切关联的人文艺术[7]。远古时期的结绳记事反映了先民们记录生活的美好愿景,结绳的繁琐性与材料的的易腐性使得就地取材的石刻与陶绘成为新的记录方式和视觉符号,而文字的诞生则开启了人类进入文明世界的大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及中国中原地带的甲骨文都是将原始符号与契刻结合起来,形成了早期图文并茂的原始文字。原始先民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编码”留存于可以永久保留的岩石、龟甲、兽骨上,清晰地记录了人类早期的生活方式与渔猎实践,现代人类将其“解码”并发现其中奥义,使得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更具完整性。正是由于文字的静态性和隐晦性,增添了其解码的难度和时长。同时,人类的文化认知是一个不断纠偏发展的过程。“司母戊鼎”因其“司”不符合青铜器铭文规范而更名为“后母戊鼎”,原因是“后”字在古时有“君王”“领袖”的含义,亦可延伸为“王后”“母后”之意[8]。如果说文字人类学的发展与研究需要进行编码与解码,而绘画、雕塑、建筑等具象化的图形则使得译码的难度大大降低或者说能够以更直观原始的视觉将思想展现在人类面前。一方面,绘画诞生的初期是为了记录客观对象和对同质物体加以区分,人们看到的内容就是画面本身的结果,不需要思维的二次运作和加工;随着时代的发展,绘画不仅仅是早期的“写实主义”,视觉作品依托时代大背景和艺术家的个人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己独立的主题、思想、风格和灵魂,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到现代、从现实到浪漫的演变过程,视觉语言的变化彰显着人类对于自身所处时代和环境的思考,是人类文化自觉和自省的重要体现。
19 世纪早期摄影术的发明,一般被当作是现代视觉人类学发展的原点。快门的按下大大缩短了绘画所需记录的时间,并且以高保真和高还原度再现社会场合和人文风貌。摄影术在19 世纪四十年代传入中国,那时的中国人将照相机视为异物唯恐避之不及。执掌照相机的人也仿佛有了权力与规训的话语,看与被看在这样一种场景中被建构,并且拥有多层次的复杂关系,“跨文化观察”成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一种常态。被誉为中国视觉人类学先驱的纪实摄影家庄学本早年在进行游历和社会考察时拍摄了大量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影像,兼具艺术和人文价值,为视觉人类学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如果说照片的拍摄是一个凝固时光的过程,而摄影机的发明将人类社会的动态性保存在电子存储介质中,人类文明影像以“比特”的形式活跃在各类电子媒介,完成了静态的照片到动态影像的视觉转换,更是成为人类学影像记录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表现方式。早期的人类学影片以罗伯特·弗拉哈迪德《北方的纳努克》和M·库珀和舍德沙克(Coper,Schaedsaek)拍摄的民族纪录片《草地》为主要代表[9],形塑了人类学影片的基本态势和民族志纪录片的风格,20 世纪30 年代,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把拍摄的影像素材用电影的制作手法和呈现方式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创作了具有电影风格的人类学影片[10]。20 世纪70年代,视觉人类学学科独立发展。近十年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媒介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传统的胶片摄影、DV、磁带、录音机等媒介设备已不足以支撑学科未来发展的需要。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和拍摄器材的廉价化让视频拍摄的门槛大大降低,而第四代、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更是让短视频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其中,拍摄者、被拍摄者、我看人、人看我、我看我、我看人看我都变得复杂而多元,社会中的“他者”身份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人类学家的田野分为“现实田野”和“虚拟田野”两个部分,新媒介环境下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中的视觉人类学新现象值得人类学者关注和反思。
二、视觉人类学视阈下影像创作新特征
移动短视频的发展消解了人类学影像纪录片的专业性,但不同时段不同地域多元生成的短视频大大丰富了人类的影像资源库,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视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难度和成本。数以万计的用户在平台分享自己与他人的点点滴滴,又数以万计的人们观看和聆听“他者”的观点、意见和想法,新的“虚拟田野”拓展了视觉人类学研究的场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
(一)自我与“他者”界限消弭
自然界中的生灵大都囿于环境的限制,偏居一方。人们受制于自然条件、社会水平和学识认知,将与自己秉性相同或相近的同类画进自己的圈子,形成族群或建立部落和国家,而将不同于自身的“异类”排斥在外,形成了“我们”与“他者”(异类,the other beings)的对立。如果说上古先民划分他者是出于自身的生存意识,那么现代社会对大众他者的区分则是基于客观意识,用一系列的评价指标和文化标签将“异类”加以区分,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圈层和民族性格。传统的视觉人类学者进行田野调查时,扛着摄影器材进入异域,仿佛自身就拥有着特权与话语。“我”已不再是原始意义上的我,而是赋予了背后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当“我”作为媒体人而存在时,其背后所倚靠的是国家力量和传媒话语,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大众的利益与诉求,社会效益与传播价值应该是记者在进行拍摄时放在首位考虑的;当“我”作为一名摄影师而拍摄时,其所考虑的更多的是影片所拍摄的艺术性或其所能产生的商业价值,光线、构图、色彩、影调都要得到合适的彰显,后期的剪辑、拼接都需要在中期拍摄时做好规划;而当“我”真正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民族学家来拍摄时,更多考量的是其背后的学术价值和民族情感,将拍摄对象置身于人类发展的历史的脉络中,来考量拍摄的内容与要义,反应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文化观念、族群历史、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等。作为自身的拍摄主体“我”也不是要置身于被拍摄的“他者”之外,而是要熔铸于他者的生活方式,将“我”看成“他者”,以进一步消弭二者之间的界限,形成角色转换和价值对位,在平等对话与合作互信中以一种“不打扰”的状态完成视觉的形塑。
移动短视频的拍摄就是以这样一种“不打扰”的情形拍摄完成的,拍摄主体可以在私密的空间中完成录像,不必再有采访时畏惧镜头的拘束感,拍摄内容可以是即兴的、表演的,也可以是精心策划安排的。视频录制完成后拍摄者可以依据自身喜好对影片进行剪辑和拼贴,使之符合自身特定审美与情感需要,最后经由高速互联网络上载至大众媒介完成发布,短视频社区平台会根据特定机制对内容进行二次分发与传播,实现流量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让·鲁什的“共享人类学”(Shared Anthropology)思想得到彰显并放大,拍摄主体不仅仅是拍摄对象同时还能主动录制和剪辑,既是视频的生产者又是视频的消费者,实现了移动短视频的“产销合一”(Pro-sumer model)。自身作为“产销合一者”(Prosumer),在利用视频媒介自拍时摄影机看我,完成了“我”向“他者”的转换,当把短视频上传至社区之后,拍摄者的“我”又即刻换回被拍摄的主体对象。而作为拍摄主体的“我”看待被拍摄的自身时,实际上是在观看被技术宰制后“异化”的自己[11]。拍摄者利用媒介技术完成了自我的“审美”或“审丑”式的形塑,在拍与被拍、看与被看中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荡然无存。此外,视频上载于社区之后,不计其数的网友或者人类学者可以对社区的内容进行虚拟的田野考察,观察其背后的拍摄地域、民族性格、语言服饰、观念情感等。在对拍摄视频点赞、留言、转发、分享时,实际上与实地的田野考察中的人际交往并无二致,都是一种互动与认可,并实现了人际间的交流。人类学者在社区观看视频是一种我看他者的姿态,当他们在社区留言互动后,拍摄者依据反馈做出回应,就是所谓的“我看人看我”,此时的评论者(人类学家)就转换成了短视频社区外来的“入侵者”。这种“入侵”不是一种侵略性质的进攻,而是一种介入与参与。双方在短视频社区中的这种互动模式下,完成了我与“他者”身份的相互转换,自我即是“他者”,“他者”亦是自我。
(二)系列拍摄形成视觉“接力”
新媒介环境下的信息具有碎片化的特点,网络移动社区中的短视频也不例外。一方面是短视频平台对视频拍摄时长的限制,最初的抖音平台规定用户只能上传15 秒的视频,而早期的微信平台的视频号也只允许上传1 分钟之内的短片;另一方面是用户拍摄的碎片化,普通用户的非专业性导致拍摄效果欠佳,由于个人拍摄的喜好不同和自身所处时空的限制,拍摄的时长、格式、稳定性、清晰度等都不尽相同。这种碎片化的创作结构使得新媒介环境下的短视频影像“微”不足道,“不足以展示人类学宏大的整体观、变迁观和深层的文化意蕴”。短视频的拍摄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其拍摄的手段和呈现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如果以短期的视角来评述某一现象对视觉人类学学科的影响的话语也是不够全面和客观的。前文已经提及,不仅要关注短期大环境对视觉人类学学科的影响和变化,同时要把这种变化对学科的影响放置于整个时代大背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中来把握。短视频的碎片化特点不可否认,但某些情况下它又具有一定的视觉“接力性”。
一种是系列式的拍摄。系列式的拍摄与记录类似于连续的影像短片,单一的短片记录往往不能够讲清楚故事的成因结果、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若将各个短视频片段连接起来,也具有宏大的叙事和整体性,其背后的拍摄环境、语言、人物面貌、使用工具等都可见一斑。由于拍摄主体和被摄对象的发展性,其拍摄的内容与题材也具有连续性和渐进性,人物的思想观念、物质条件、工具技能等处在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这些条件的变化带动着拍摄内容的更新与发展。同时,拍摄内容的渐进变化,也侧面反映出被摄对象的物质生活水平与人物精神风貌。二者是一种相互完善、协同进步的开拓式发展,视觉的渐进发展,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印证。
另外一种是“围观”式的拍摄,这种拍摄集中表现为拍摄主体的“在场”性。生产实践或故事(事件)的发生被在场的“围观者”记录,形成一种全景式的拍摄,对于被拍摄者来说,自身仿佛处于一种被观看的“全景敞视”(Panopticism)的“监狱”之中,围观者就像是监狱外围筑起的高墙,而具身的摄录设备就像是无数个摄像头,实时记录着正在发生的一切[12]。这种无意的或是猎奇式的在场记录,也许每个人拍摄的角度、时长、焦点都不相同,也正是这种拍摄的多样性,促成了视觉“接力”的可能性。人类学者可以将这些视频片段整合拼接加以重构,实现“虚拟田野”的调查,这种无数个短视频的接力就是人类社会视觉的合集与传承。
(三)群体影像重构民族叙事
在摄影术发明之前,人们依靠文字来记录本民族、本族群或本地区的历史,出现了所谓的“民族志”“县志”“乡村志”等。其中记录了民族的起源发展史、乡土的风貌与乡村的变迁等,这些文字读本对于文本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如同照片、视频之于视觉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往的视觉人类学影片主题较为特定和单一,往往只能反应其固定的人群、民族、地域的风貌,无法再现与时代相关的整体历史风貌与人文情。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被世界公认为视觉人类学纪录片的经典之作,再现了爱斯基摩人渔猎和建造冰屋的情景,但是这种再现是家族式的个案,且囿于时代、技术的限制以及资金、人才的匮乏,无法完成对北美地区整体狩猎方式和房屋建造的记录,更无法较为完整地展现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状况和同期的社会历史发展水平。不同于现代短视频时代下全景式的拍摄与展现,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能发声,人人都能记录并分享着身边发生的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器官的延伸,以及其所具有的“具身性”(embodiment)使得视觉记录的空间大大拓展。
“全民参与”式的拍摄和记录,给视觉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充盈的影像资料。拍摄者个人的记录或许是基于自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没有目的性,但是无数人的共同记录就会形成一种影像的合力,这种合力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与社会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现,也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表达。视频记录的是个人的故事,而视频的合力则诉说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人类学者研究整个时代的影像民族志。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庄学本作为纪实摄影师在中国西南地区拍摄时,也未曾想到其所拍摄的具有国家民族意识的照片竟对整个视觉人类学或民族志摄影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甚至其本人都不认为自己是人类学者。反观新媒介环境下的短视频发展,也许短时期内无法凸显其自身拥有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价值,但是在数十年乃至百年以后,这些影像不再是个人当下生活的简单朴素的实时记录,而是成为了整个时代影像合力的一部分,未来的人类学家一定可以依靠这些纷繁复杂的影像发现属于这个时代发展的印记和规律。
(四)视觉技术发展赋能学科创新
视觉人类学的发展和研究离不开影像的记录,传统影像在拍摄录制时囿于技术和器材的单一,常常表现为固定机位、角度单一,且叙事文本不够灵活,互动性不足,无法表现出民族志影像的整体风貌,在视觉人类学研究中具有局限性。视觉技术尤其是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和各类移动剪辑App 的诞生,极大地改善了拍摄手段、提高了拍摄效率。在后期的剪辑方面也呈现出专业性向普适性的过度,普通用户等非摄影师、非人类学者也能轻松驾驭。
高速移动互联网络(5G)和移动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的发展带来了全民影像的狂欢,手持云台的拍摄为移动短视频、Vlog 的拍摄增强了稳定性,也带去了视觉观看上的舒适。Dji Osmo Mobile 的短片拍摄软件生态更是为用户提供了拍摄的模版,在拍摄完成后自动生成视频短片,无需剪辑一键配乐即可上传至短视频社区。相较于传统的摄录设备的笨重,Dji Osmo Pocket 以其小巧便携但又功能强大值得视觉人类学者关注。同时还有无人机、穿越机拍摄提供的新视角,普通的摄像机一般保持在与人等高的位置,而无人机的拍摄提供了一种“上帝视角”,用俯瞰的“眼光”观察村落的地理位置、形态样貌和族群分布等。这些新的媒介拍摄方式不仅为短视频社区的分享提供了便利化和可观赏性,同时也为视觉人类学整个学科“赋能”。
此外,还能利用AI 技术为老照片、黑白影像上色。例如利用AI 上色修复的1936 年德国老城德累斯顿的纪录片,再现了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街区和人物风貌;还有利用AI 与声像合成技术将一段拍摄于20 世纪20 年代的北京市井百姓生活的影像资料还原成符合现代视觉观感的案例,原本黑白分明、模糊不清的黑白影像在经过人工智能修复合成后色彩明快,清晰度高,透过视频可以看到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遛狗、剪辫、喝茶)、交通出行(马车、轿子)、穿衣服饰(长袍马褂,青灰土衫)以及礼仪社交(作揖、跪叩)等,彼时的人们对于摄像机这样的“异物”依然是带着凝视和怯懦的目光。CG(Computer Graphics)技术的应用,也打开了还原珍贵历史影像资料的大门。如果说AI 能够对现有的影像进行色彩修复,CG 则能够对已经消逝的文化进行还原,其动画和特效能够对于还原历史事实和增添视听魅力提供强大技术支持。
人类学者在面临这些新技术、新变革时切忌充耳不闻,应紧随时代步伐,学习新媒介技术尤其是视频拍摄与剪辑的相关知识与技能。“我们需要这些新媒体、新技术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手段和力量,这也是这一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优势所在。”[13]在器材使用上,掌握传统的摄录设备使用方式,也要关注新兴的媒介记录产品;后期剪辑方面,在专业的电脑剪辑软件和适应上传短视频社区的手机移动剪辑App的使用上齐头并进;同时还要关注“虚拟田野”中的大众媒介生活方式的变化,在新兴领域挖掘出相关学科属于人类视觉影像的独特魅力。
三、问题与展望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记录载体的便捷化,也带来了信息传播的最大化。人们利用新的视频平台和社区记录、分享着身边发生的一切,使得人类社会的影像的丰盈程度前所未有。视觉的“静向”向“动向”逐渐过渡,但是这种动态的影像不会取代静态的照片和绘画,二者同时存在互为融合发展。新的影像表达和呈现方式,对于视觉人类学的考察和研究也提供了新思路、新视角和新要求。传统的田野调查变为“虚拟的田野调查”,观看与被观看都是一种相对的视角,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没有绝对的他者也没有绝对的自我;短视频的记录见证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与变迁,相信在时间的沉淀下注定会成为后来的视觉人类学者考察现有大众媒介生活的重要手段;也许当下每一个个体的记录“微”不足道,但是全民参与式的记录就会形成这个时代视觉的合力,传承着时代的物质与精神风貌。
在关注视觉影像呈现新业态的同时应该注意到,随着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崛起与应用深化,如Sora 这样的先进模型正对视频生产领域产生深刻而重要的影响,技术的变革进一步加剧了短视频社区内影像的纷繁复杂性。其自动化和大规模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视觉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严肃性、客观性。同一视频在不同平台反复上传,这无疑给视觉人类学者筛选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素材增添了大量潜在的无效冗余信息。另外,由AIGC 技术支持所催生的新型娱乐化表达方式,其内容创作往往倾向于迎合大众趣味和瞬时吸引,对于思想深度和严肃议题的关注程度则有待进一步探讨。尤其当这些技术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美颜、换脸、拼贴、合声合成以及VR、AR 等被广泛运用于视频制作以模糊现实与虚拟界限时,实际上可能正在侵蚀视觉人类学坚守的真实性原则基础。面对这一形势,学科在积极接纳和利用新兴媒介技术的颠覆式创新时,必须审慎地界定技术与学科研究边界,精准评估技术融合带来的效度变化,防止因过度依赖或不当使用而导致研究偏差与精神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