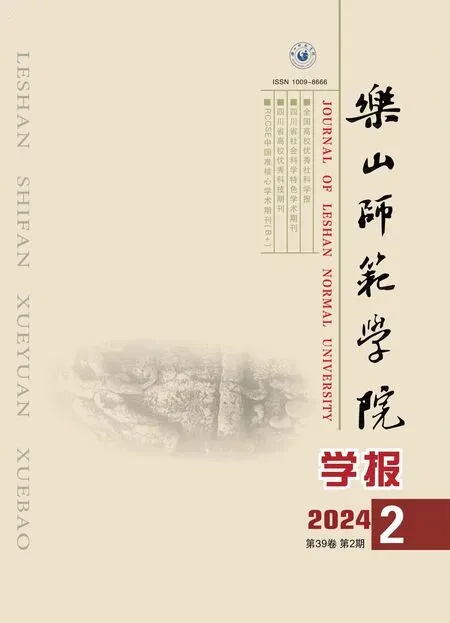探源“不穀”
——以《国语》为例
陈婧颖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关于《国语》《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记载,楚、越、吴地区的君王常自称“不穀”。这个问题近20 年来,多有前辈研究,但是近年来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楚书》的全面问世,“不穀”的本字也浮出水面。
一、《国语》文本中的“不穀”
《国语》汇集各国嘉言善语的宝贵对话资料,是考证春秋战国时期口语的佳选;它也较全面收录了各国史料,是一部可参考性较强的史集。《国语》目前公认有明道本与公序本两个版本,俞志慧先生比较研究发现:明道本中多将会造成阅读困难的字改为熟字、后起字,因此明道本成为点校、注疏首选底本;而公序本则是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样”,脱文、衍文也更少。[1]因此本文选择上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出版的《国语》,它以明道本为底本,参校《四部丛刊》的公序本,在方便阅读的前提下,也保证其准确性。
《国语》中,“不穀”一词凡11 见:
(1)(楚成)王曰:“虽然,不穀愿闻之。”(《晋语四·楚成王以周礼享重耳》)[2]352
(2)(楚平王)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韦之跗注,君子也,属见不穀而下,无乃伤乎?”(《晋语六·郤至勇而知礼》)[2]415
(3)(楚)恭王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业,覆楚国之师,不穀之罪也。”(《楚语·子襄议恭王之谥》)[2]531
(4)(楚灵)王曰:“子复语,不穀虽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楚语·白公子张讽灵王宜纳谏》)[2]553
(5)(楚昭)王使谓之曰:“成臼之役,而弃不穀,今而敢来,何也?”(《楚语·蓝尹亹避昭王而不载》)[2]575
(6)吴王(夫差)惧,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于越君,君告孤请成,男女服从。”(《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2]618
(7)(越)王(句践)曰:“不穀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越语·范蠡进谏勾践持盈定倾节事》)[2]641
(8)(越)王(句践)曰:“吴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越语·范蠡劝勾践勿早图吴》)[2]648
(9)(越)王(句践)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耶?”(《越语·范蠡谓人事与天地相参乃可以成功》)[2]650
(10)吴王(夫差)帅其贤良……曰:“昔者上天降祸于吴,得罪于会稽。今君王其图不穀,不穀请复会稽之和。”(《越语·范蠡谏勾践勿许吴成卒灭吴》)[2]655
(11)范蠡辞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越)王(句践)曰:“不穀疑子之所谓者何也?”(《越语·范蠡乘青轴以浮于五湖》)[2]658
其中有5 次为楚地君王自称,分别为成王、平王、恭王、昭王、灵王;5 次为越王勾践自称;1次则为吴王夫差自称。从时序上,可初步发现君王自称“不穀”在楚地先行。
在《国语》中最早见到君王自称“不穀”是在例(1)中楚成王的自称。再据《左传》中记载僖公二十三年楚成王对重耳说:“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3]以见其记载与例(1)所述之事相同,所以据《国语》《左传》记载“不穀”最早出自楚成王之口在公元前637 年左右。而“不穀”首次出现在楚国以外的场景是在例(6)中,越王勾践要灭吴国,吴王夫差派使者向越王求和,吴王自称为“不穀”。依韦昭注:“鲁哀二十年冬十一月,越围吴。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灭吴。”可知在《国语》中吴王自称“不穀”大概在公元前473 年。这是《吴语》唯一一次记载君王自称“不穀”,也已和楚地君王最早自称“不穀”相距164年。而在越国首次出现“不穀”见例(7),是越王勾践继位三年想攻打吴国,在与范蠡对话时自称“不穀”。依韦昭注:“勾践三年,鲁哀之元年。”而该对话则在“三年,而吴人遣之”,韦昭注“鲁哀五年也”后发生,即公元前490 年,与楚成王自称“不穀”相去一百多年。因为吴、越两地君王使用“不穀”自称的时间都晚于楚君且相差较大,可推测“不穀”发源于楚地,为楚地君王的自称,后受地域文化影响传播至吴、越两地。
本人统计,《左传》中“不穀”共出现20 次,其中楚地君王自称使用17 次,齐侯使用2 次,周襄王使用1 次,周景王庶长子王子朝使用1次,其中齐侯的言说对象为楚国使臣。
(12)齐侯曰:“岂不穀是不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穀同好,如何?”(《左传》僖公四年)[3]248
(13)冬,(周襄)王使来告难,曰:“不穀不德,得罪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以氾,敢告叔父。”(《左传》僖公二十四年)[3]365
(14)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兹不穀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左传》昭公二十六年)[3]1290
例(12)为公元前656 年,“不穀”为齐桓公与楚国使者屈完对话时的自称(由齐侯转述),齐桓公自称“不穀”比史书记楚成王以此自称还早19 年。对于此例,夏先培先生和杨伯峻先生皆认为,齐侯以“狭天子以令诸侯”的口吻与楚王对话,因此“不穀”是周天子专属的“降名”。而楚王之所以用周天子的“降名”,是因为楚王最早僭越称王。但是这种分析有如下问题:第一,在史书记载中有许多“狭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但自称“不穀”也仅《左传》僖公四年的一例。如僖公九年,齐侯也以王室之命会诸侯却自称“我”;《吴语·吴欲与晋战得为盟主》中记载吴王夫差以周王室之命“令诸侯”,但吴王也以“孤”自称。由此可以否定夏先生和杨先生齐侯以“狭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使用天子专属“降名”的结论。第二,“不穀”与“孤”“寡”连用。例(12)中齐公自称“不穀”,楚王自称“寡人”;例(6)吴王将“不穀”与“孤”连用,都可说明三者的地位相同,都是诸侯王表谦的自称,并非楚王僭越称王野心的“傲称”。第三,不若杨先生所言,君王自称“寡人”比“不穀”更谦卑。在《清华简六·子仪》中,秦王在公元前627 年崤之战后求和于楚王时,自称“不穀”。同样,《清华简六·郑文公问太伯·甲本》中,郑文公在依附楚国、晋国期间,与其公子元对话时也以“不穀”自称。由此可见,楚国君王使用“不穀”作为谦称,并非出于僭越称王的野心,与“孤”“寡”等谦词无异。而例(12)只是根据言说对象为楚国使者“入乡随俗”改变其辞,楚君应该早就以“不穀”自称了。
例(13)为公元前636 年,周襄王因得罪弟弟而流亡至郑国,为避难着凶服自贬称“不穀”,比《国语》中最早的楚王自称“不穀”还晚一年,推测周王使用楚君谦称“降名”;例(14)为公元前516 年,周景王庶长子王子朝为避王室之乱,奔至楚国,与大夫们对话亦自称“不穀”。清人崔述(1740—1816)在《考古续说·齐桓霸业附考》中提到了楚君之自称“不穀”,而清人钱绮(1798—1858)也在《左传札记》卷二中提到:“国君自称皆曰‘寡人’,有凶则称曰‘孤’,独楚常称‘不穀’,齐桓召陵效其言亦称‘不穀’。”所以,可以确定《左传》中周天子因“降名”以“不穀”自称,其他国君则是受到楚国影响以此自称。
在《老子》中老子也两次将“孤”“寡”“不穀”并提,可见在老子认知中,君王谦称有“孤”“寡”“不穀”,中原地区君王多以“孤”“寡”自称,老子之所以会补上“不穀”只因其生长于楚国,而楚国国君多以“不穀”谦称。又见例(6)中,吴王也并提“孤”“不穀”表谦,那么杨伯俊先生“侯自谓孤、寡,王自谓不穀”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15)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子谓孤寡不穀。[4]221
(16)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4]233
《老子》的记录更证实君王“不穀”之称源自楚地,其用法与“孤”“寡”相似,后受地理、文化等因素影响吴越地区君王也开始以“不穀”自称。如“陵”,本为楚国方言,多出现于楚国地名中,后因文化传播和地域原因,吴、越两地也开始使用“陵”字。该情况与“不穀”从楚地发源传播至吴越两地情况十分相似。可见,“不穀”源自楚国,为楚地君王自称,后传播至吴越两地,也为两地君王所用;别国使者出使楚国时、亦或别国君王言说对象为楚王时也会“入乡随俗”以“不穀”自称;周天子避难降名也会以“不穀”自称。
二、“不穀”源自楚地,为何吴、越两地君王也会使用“不穀”?
据《国语》载,越王勾践5 次自称“不穀”;而依照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的汉简《孙子兵法?见吴王》吴王阖闾与孙武的对话中多次自称“不穀”,如“不穀之好兵”“不穀未闻道”“不穀愿以妇人”“不穀好”等。可以看出吴、越两地君王也自称“不穀”,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呢?
(一)地理位置
《国语释地》:“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自号于越。僻在海滨,不与中国通。”[5]据《辞海》[6]中对会稽郡描述,自秦以来其盘踞于今天的东南沿海,西汉时囊括福建府,但不论何时期皆以今天浙江一带为中心,因此古时越国范围当在今浙江一带。
《史记·楚世家》中记录楚成王封郡于熊绎,楚文王迁都至郢,“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7]。在《汉书·地理志中“丹阳郡”“丹阳”条下班固注云:“楚之先熊绎所封”》[8],而熊绎时的丹阳尚在今安徽当涂县境。《说文解字注》:“郢,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9]又段玉裁在词条注解中写道:“南郡江陵、二志同。今湖北荆城。”所以可知在楚文王前楚国定都于今安徽一带,文王后定都于今湖北一带。
《国语释地》:“泰伯、仲雍让其弟季历而去之荆蛮,自号勾吴,今无锡县东南三十里泰伯城是也”,“阖庐始居于今之苏州府”,因此可知吴国定都于今天的江苏一带。
综上,大致可以确定楚国在今安徽、湖北一带,越国则在今浙江一带,吴国则在今江苏一带,三国地理位置相邻,气候、饮食习惯相似,来往频繁,文化上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也体现在语言上,如“阿拉”原为宁波、舟山方言表示“我”,后因宁波人大量移居上海,使得上海人也开始用“阿拉”,并逐渐代替上海话中的“我伲”。
(二)交往频繁、文化渗透
1.楚、越两国
楚、越两国在勾践灭吴前都是以友好的关系在历史舞台上亮相,两国不仅来往频繁还结成联盟,这对两国的文化交流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久而久之,两国文化交流中发生了融合、渗透,由以下几个方面可见:
首先,楚越两地交往频繁的特点体现在古代诗歌创作中,《越人歌》在写作文辞和表现手法上都与后世的《离骚》有异曲同工之妙。《越人歌》全诗以“兮”做语气停顿词与《离骚》中所使用“兮”相似。李调元在《粤俗笔记》中也对此进行分析:“说者谓越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辞不可解,以楚说译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则绝类〈离骚〉也。”“其原辞不可解”可见虽然两地所说的语言不同,但是两地语气词和文辞风格由于长期的交往也发生了融合。
其次,楚越之间特别的关系也在史书中可找到依据,在《史记·楚世家》中记录“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从楚庄王手抱越女可以看出当时楚越关系密切,越国才会给楚国献宫女。而大概是公元前601 年《左传》宣公八年记载:“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从楚国与吴、越两国结盟这一细节可以看出楚国与吴、越两国所处环境和利益较为一致。再看《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大约为公元前518 年记载:“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王及圉阳而还。”此时楚国发动水兵打吴国,越国大夫、公子支“后援兵”慰劳楚平王,送船并领兵跟随,可以看出楚、越两国的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记录:“五年,吴王以越不从伐楚,南伐越。”[10]在这时还可以看出越国与楚国坚定的统一战线。综上所述,楚、越两国关系在勾践灭吴之前都较和睦,来往也很频繁。
再者,楚越之间的友好关系影响深远还表现在出土文物中,出土文物中多表现出两地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特点。第一,是出土炊食用具的变化。越国典型的炊食用具为陶鼎、斧、罐、瓮、碗、盘这般组合,而到了春秋晚期楚国与越国来往频繁之际,其炊具组合新增了楚式的鬲、钵、罐。如2004 年在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塘山村发现的一座西汉越墓中就出土了楚式罐1 件、钵1 件,还有越式炊具若干。再如1983年在广州越秀山发现的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各式越式炊具及饮食用具、酒器、等器具中唯一一件铜剑为战国的楚式剑格外引人关注。还有许多越地、楚地出土陪葬品中的器物融合楚、越两地的文化元素。由此可见,楚、越两国来往频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文化交融。
2.楚、吴两国
楚、吴两国的关系较楚、越两国相比更为复杂。据《左传》宣公八年记载,大概于公元前601年,楚、吴两国关系较好,还结为盟友。自楚国壮大以来,晋国以吴国为棋子与楚国对立,两国长期处于对立、抗争的状况。从《史记》记载来看公元前584 年开始至公元前504 年间楚、吴两地征战频繁,虽说两国的来往记录多为战争,但是战争也容易引起文化的相互流动。其文化的相互渗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国文化渗透表现于出土文物中,许多吴国墓出土的文物中都带有楚国的文化色彩。在春秋中期,吴国较楚国来说还是一个国力稍弱的国家,其礼制较楚国也落后。这一点从礼器的特征可窥,吴国鼎特点“浅腹、圜底、小直耳、三细高足外撇”[11]、“器形都较小”[12],而楚国鼎的特点“深腹、圜底、附耳、蹄形细高足外撇,盖面微凸,中有桥纽套提环,周围三个竖环纽”[12]。但是吴国墓的出土陪葬品中却发现了许多有楚式风格的青铜鼎,如1980 年在江苏省吴县枫桥公社水泥厂发现的何山东周墓中有两件鼎:一件为典型的吴国鼎,其器小,腹浅,但是该墓中又发现了一件极具楚国风格的青铜鼎,造型纹路都与楚国鼎十分相似。这足以证明两国虽长期处于战争状况,但是两国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交融、渗透。再如1968 年在苏州六合县程桥镇发现的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中也出土了两件青铜鼎:其中一件铜鼎极具楚式风格“盖有环钮三个,腹、圆底,直立长方形附耳,蹄形足。器盖、器腹有雷纹饰带,附耳内外和蹄足根部均 饰蟠蟀纹”[12],而另一件铜鼎则表现出典型的吴式铜鼎的特征“敛口、折沿、浅腹、圜底、蹄形足”[12],可见吴国当时已经开始有意识仿照楚国的青铜鼎。由以上两口吴国墓出土的青铜鼎却极具楚式风格,可以看出两国不但来往频繁,文化上也相互影响,并不因长期的战争关系而相互封闭。
其次,楚、吴两国文化相互渗透还表现于丧葬习俗上。吴国在春秋时期流行土墩墓和平地掩埋,而这两种方式都无需挖墓穴。据考证,吴国是从春秋中末期开始效仿楚国建墓室、设棺椁、挖竖穴。如1982 年在江苏省丹徒县大港公社赵庄大队采石场发现的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就是以平地掩埋的方式进行墓葬,其“不见使用棺椁之类的葬具”“将尸体陈列于草木灰垫上,再封土掩埋”[13],而专家根据该墓出土物的文字、纹路判断该墓为西周早期的吴国墓,由此证实了西周早期吴国人仍使用平地掩埋的方式进行墓葬,此时还没有挖墓穴的习惯。还有1954 年在江苏省丹徒县烟墩山发现的春秋墓,“墓坑平面呈刀形,由长方形墓室和长条形墓道组成。墓坑上大下小”[14],可见春秋中期吴国人已开始效仿楚国人挖墓穴、设棺椁的习惯。楚国的墓葬方式对吴国影响极深,也折射出楚、吴两国虽长期处于战争关系,但两国之间的文化影响却并不因此而减弱。
综上所述,基于楚国和吴、越两国的地理位置相近、来往频繁的原因,文化交流也造成文化融合、渗透,因此也不难推断发源于楚国的君王自称“不穀”会因文化交流由楚国流动到吴、越两国,也成为了吴、越两国君王的谦称。
三、“不穀”本字、本义考
(一)“不穀”之“穀”本字考
探索“不穀”词义必先探索“穀”之本字,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上文已确定“不穀”一词为楚地方言,固从楚地出土简帛中探求“穀”本字。涉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集成》[15]、《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16]、六[17]、七[18]、八[19])、《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20]、三[21]、六[22]),下分别简称《马王堆汉帛书》《上博简》《清华简》。
《上博简》这批战国楚简为楚国迁郢前贵族墓中的陪葬物,简文所涉史事与楚国有关,简文也为楚国文字;《清华简》的抄写时代大致为战国中期,其文字风格也主要为楚国的,且其中有多篇简书记叙与楚国有关的事,如上例(12)简中记叙楚人与晋人激战的过程就是其中之一;《马王堆帛书》出土于楚地,但依照其中字体可识别帛书书写年代跨度很大,最早可能为战国末期如《阴阳五行·甲》,最晚则至西汉初年。而其中《马王堆帛书·老子》分为甲、乙两本,甲本不避讳刘邦,且为篆体字可能为秦末期书写,而乙本避刘邦讳且为隶体当抄写于汉初。且其内容创作者为老子,而老子又是楚国人。所以马王堆出土的《老子》应为老子所作原本的传抄本,为较早的楚国文献传抄文献,其反应了传抄过程中文字的变化也有一定参考性。而这些简帛中皆发现了“不穀”的原始文献。如:
(17)晋文公立四年,楚成王率者(诸)侯以回(围)宋伐齐,戍(穀),居。(《清华简二·系年·第七章》)
(22)(楚)庄王就夫(大夫)而与之言,曰:“郑子家丧杀其君,不(穀)日欲(以)告夫(大夫)”(《上博简七·郑子家丧·甲本》)
(26)(楚王)“是则聿(惟)不(穀)之辠(罪)也,后含(今)勿(然)。(《上博简八·志书乃言》)”
上例(22)、(23)、(24)、(25)、(26)分别为楚庄王、楚灵王、楚简王、楚昭王、楚王自称“不穀”,例(21)为郑文公与公子元对话①时自称“不穀”,郑文公即位期间摇摆依附于楚国、晋国,与其结亲、结盟,结果就是文化交融下郑文公也自称“不穀”。且依据《清华简》中有多篇关于郑国子产(郑文公曾孙)的记叙,推断该简为子产后人和弟子流落楚国所作,《清华简二·系年》也记录该事:“郑太宰欣亦起祸于郑……明岁,楚人归郑之四将军与其万民于郑。”因此,也极有可能为传抄者“入乡随俗”的写法。例(19)、(20)则是秦穆公与楚国子仪对话时,为重修秦楚关系,自称“不穀”,遵循楚国习惯,以示尊重。而在同一时期的楚国简帛中“不穀”之“穀”皆作“”,由此可见在东周时期“不穀”一词“穀”本字极有可能为“”。虽在例(27)中“不穀”以的形式出现,但《马王堆帛书》成书时间晚于《上博简》《清华简》,且为该篇为传抄文献,传抄过程中字体会发生变化。但这还不能确定“”就为“不穀”之“穀”的本字。现在有如下几种可能:第一,两者互为通假字;第二,“”为讹误字;第三,两者为异体字;第四,两者为古今字。
在《古今字》[27]一书中提出古今字定义:“古时造字较少,一个字承载较多意义,后世为了避免用字和阅读的困难再造新字承担其中一个及以上的义项。”这是狭义的古今字定义,本文也采取该标准判断古今字。若“穀”是再造“新字”就是承担“古字”义项的存在,且古今字并存。但在现存文献中“穀”逐渐取代“”,汉晚期后几乎不见“”字的使用,如《银山汉墓竹简》中“不”之“”皆作“穀”、《马王堆汉墓帛书》中则是作“”这都违背了古今字造新字的原则,文字是意义的载体,除非“”字所承担义项不常用该字才会逐渐消失。而“”有“养”之义,搜索后发现“穀”在汉以后的许多文献中仍有“养”之义,如元代《句容金石记·元·重修社稷壇碑記》云“穀我穰穰,乐我康寿”、后梁《后梁·海东金石苑·卷二》云“乳穀之则”,这两句话中“穀”的意义为“养”,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的消失不符合新字义项使用频率低的情况,两字当不为古今字。
(二)“不穀”本义考
关于“不穀”的词义,除了辞书注释所采用的“不善,古代往后自称的谦辞”这种说法,学界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胡勃、徐流[31],杨树森[32]等人则认为“穀”是“毂”的借字,“不穀”即“不毂”;刘秉忠[33]则认为“孤、寡、不穀”皆为丧期用语不存在具体意义;夏渌[37]则提出“不穀”义为“不穀食”指不吃带糠壳的粗粮,是君王独特地位的象征,并非谦称;刘秉忠还提出“穀”通“彀”义为孺子,“不”通“丕”义为大,“不穀”义为大子;蒋兆鹄[34]、高诱提出“不穀,不禄也”。综上所述,关于“不穀”的“穀”本字有“彀”和“毂”两种说法,而本义则有“不善”“不禄”“大子”“不能为群臣爱戴”。
1.“不穀”语境浅析
分析词语的运用情景有助于准确把握词语意义,因此在此将一一分析上述例句中的具体语境。例(1)是楚成王与晋国流亡重耳的对话、例(2)是楚共王召见鄢陵之战时的晋大夫与之的对话,这两例对话的情景较为轻松愉快;例(6)、(10)都是吴国使者向越王求情时的对话,都带有求助的口吻;例(5)则是楚昭王召见大夫蓝尹亹;例(7)、(8)、(9)、(11)都是越王勾践与范蠡探讨问题的对话,都带有较强的商讨意味;例(14)、(20)则是求和言辞,明显带有谦虚意味,在这里秦穆公称楚大夫为“君”,而自称“不穀”;例(22)则是宣告丧事带有悲伤意味;例(24)则为君王临终之言,诚恳深切。
总之,“不穀”所运用的场合较广,有与大臣轻松愉快的对话,有危急时刻的求助,也有与大臣的严肃商讨,还有宣告丧事的悲痛及其临终之言。这样来看,“不穀”应与“孤”“寡人”一样为运用于各个场合的谦称。
2.“不穀”本义浅析
《诗经·小雅·蓼莪》[35]:“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穀,我独何害!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穀,我独不卒!”郑玄注:“穀,养也。”义为:“大家都没有不能不抚养父母的,却唯独我不能终养父母。”《诗经·小雅·小弁》:“弁彼鸴斯,归飞提提。民莫不穀,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在此,“不穀”也译为“不能终养(父母)”从下文“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可证该篇阐述了自己对父母的愧疚和思念。
由此可见,在《诗经》中郑玄译“不穀”为“不能抚养(父母)”,该释译比较符合《国语》《清华简》《上博简》等资料中楚君自称“不穀”的本义。虽然在《诗经》中“不穀”还是一个名词性的词语,但从它出现频次可以看出该词是一个固定搭配。而在春秋晚期,该词才转变为楚国君王的谦称之词。如同“孤”《说文解字》中记本义为“无父也”,常与名词搭配构成短语,如“孤子”“孤雏”等,段玉裁注引申义“单独皆曰‘孤’”即单独义,又引申为孤独的人,而在《论语·里仁》中“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反之,不德者则为“孤”;“寡”《说文解字》中记本义为“少也”,段玉裁注引申义“单独皆曰‘寡’”,所以“孤”“寡人”分别从本义“无父者”、“少者”引申为“不德之孤者”,作为君王谦称意指“少德者”。而“不穀”本义为不能赡养父母,与“孤”、“寡人”一样作为君王谦称时也表示自己在道德方面有不足之处。所以,无论从楚地方言释义,还是使用语境去分析,“不穀”本义应为“不能终养(父母)”较妥当。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不穀”一词是源于楚国君主的谦称,在文化传播的影响下吴、越两国君主也开始以此自称,但时间晚于楚国。而其他国家君王在言语对象为楚国人的前提下,也会自称“不穀”。“不穀”之“穀”本字为“”,但随着楚国的灭亡,该字由音近的通假字“穀”取代,汉后基本使用“不穀”而不用“不”。而“不穀”的本义为“不能终养父母”表谦义。
注释:
①子居在《清华简〈郑文公文太伯(甲本)〉解析》一文依据《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推断该“太伯”应为公子元。
②高诱在《淮南子·人间训》中注“不穀亲伤”为“不穀,不禄也”。